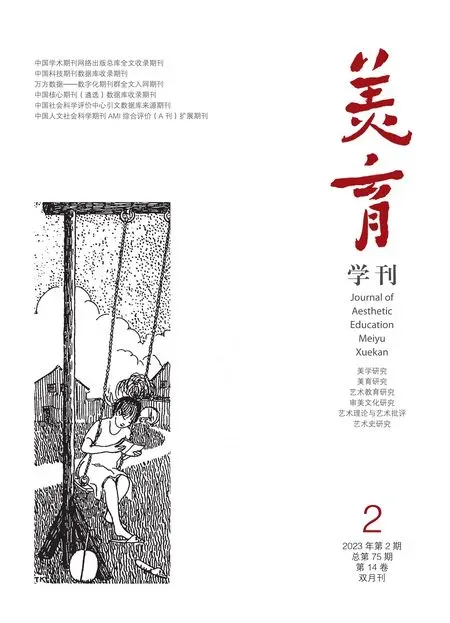在餐厅中寻思,于迷宫中前行:室内歌剧《要求很多的餐厅》艺术特色探析
张 蓉
(浙江音乐学院 声乐歌剧系,浙江 杭州 310024)
室内歌剧《要求很多的餐厅》(下文简称《餐厅》)由姜昌恩编剧、刚妍作曲,是2020年浙江音乐学院主办的室内歌剧作品征集比赛获奖作品展演活动中三部完整歌剧获奖作品之一(1)2020年浙江音乐学院主办的室内歌剧作品征集比赛获奖作品展演活动中三部完整歌剧获奖作品分别为《阅微草堂记》《要求很多的餐厅》《信使》。。在这场旨在推进歌剧学学科建设、鼓励室内歌剧探索、支持青年人才歌剧创作的征集活动中[1]67,涌现出多部展现中国当代室内歌剧创作面貌的优秀作品。
所谓室内歌剧,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歌剧类型,常以简练的人物、洗练的情节、细腻的形象著称,有着小而精、微而妙的结构形式。本次择《餐厅》为探讨对象,不仅因为该剧的戏剧性表达和现代化的音乐风格,更是因其展现出来的深刻哲思与人文关怀。在剧中,作曲家刚妍以室内歌剧这块作曲家创作歌剧的“试金石”为体裁,取材宫泽贤治的童话故事,从中表达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1]66,并通过现代化、形象化的音乐语汇与戏剧性表达,塑造了立体丰满的歌剧架构。
以下笔者便从《餐厅》出发,对其体裁与题材、音乐创作技法等要素进行分析与探讨,对该作品的戏剧性表达与演唱诠释等内容展开具体分析与论述,以该作品为个案探讨当代室内歌剧的创作特征,探寻室内歌剧的诠释与表达,进而对室内歌剧的戏剧性演绎与音乐化呈现展开思考。
一、精巧且凝练:体裁与题材探究
在歌剧创作时,剧作家常因歌剧组织结构、戏剧性表达等要求对剧本原作信息进行一定的调整与再创作。《餐厅》剧本选自日本童话大师宫泽贤治创作的同名童话故事,在受到室内歌剧体裁的限制下,为了更符合室内歌剧短小凝练的特征,剧曲作家均采用相对简约的方式进行创作表达,剧作在角色名称上有所调整,同时剧情走向也更为紧凑,角色对话更富有情节性和引导性,为歌剧情节的发展助力。
该剧本原作讲述了两名绅士在森林中打猎而迷路,饥寒交迫中被一座餐厅吸引,在这座餐厅中,他们不断被提出各式要求,实则被山猫当成了食物。在室内歌剧中,剧作家同样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分别是餐厅老板胡丽丽、瘦猎人和胖猎人,分别对应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图1)作曲家通过三个声部的角色安排,从而对角色性格进行了初步刻画。剧曲作家同时结合宫泽贤治童话中常见的对话形式设计歌剧的对话,生动真切地反映角色的内心世界,塑造富于戏剧性的形象,推进情节发展。张宝华、于学友在论述题材选择对于室内歌剧创作的重要性时,以《餐厅》为成功案例[2],可见该剧作在室内歌剧创作题材内容上方向正确。

图1 《要求很多的餐厅》剧照一
歌剧情节发生在一片森林,剧作家并未对故事时间进行明确限定,在三幕歌剧中,音乐的戏剧性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样态蕴藏其中,借由短小又富于现实意义的童话故事呈现。在剧情中,作为餐厅老板的胡丽丽从开始便是一个虚幻性的人物,她所虚构出的富丽堂皇的环境与琳琅满目的佳肴,实则是资源对于人类的价值与诱惑力的隐喻。置于此环境之中的猎人被一步步引诱,逐渐落入陷阱,生动展现出人类面对诱惑时的贪婪。故事中的猎人实则是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杀害无辜生命的人物形象,沉浸在发现“餐厅”信息之中的猎人也成为要被猎杀的对象,这里暗示了因果间循环的关系:从猎人对世间生命的无情猎杀,到胡丽丽为报仇而猎杀猎人,最终到“狐狸”心爱的孩子被杀害的结局。这之中的“狐狸”则暗指胡丽丽。
从歌剧的具体情节来看,在第一场胡丽丽独自拿着红酒杯在灯光昏暗的餐厅里介绍自己时,角色便依托语言和动作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台词中“醉生梦死”“特别的魅力”等均为其后剧情的戏剧化发展埋下伏笔,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名字像是‘狐狸’,其实我是个好人”这一句台词,则与第三场男中音以旁白角度讲述的情节——“听说在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她一直在那,等待着她的孩子,同样也等待着沾满血腥的手”形成首尾呼应,强化了全剧的结构性和整体性。
此剧还蕴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猎人无度猎杀生命的批判,对“狐狸”最终失去孩子的讽刺,实则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讽刺,也是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呼吁。剧作家、作曲家依托童话故事隐喻性的语言,借助音乐化的情感表达,揭示出社会中真实复杂的人性,刻画出具有鲜明且生动的现实脆弱感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故事中,三个人物形象实际上都是自以为是好人的坏人,他们为谋求个人利益损害着他人与他物,从而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剧曲作家巧妙地安排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循环之径。
二、打破与循环:音乐创作技法探究
再来看音乐本体,《餐厅》作为一部室内歌剧作品,其在音乐创作技法上有所继承与突破,最具特色的便是“循环”概念的运用。以下便从配器手法、节拍处理、音乐主题形象等角度切入,基于对该作品音乐语言的表达,对作品的戏剧性表达与情节性设计进行分析和把握。
首先,将目光投注在作曲家的配器手法上。该作品的乐队编制中除人声外,作曲家配有长笛兼短笛、bB调单簧管、打击乐、巴扬、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其中打击乐组使用定音鼓、吊镲、三角铁、小钟琴、颤音琴、铃鼓、木鱼、小军鼓、卡巴沙、康佳鼓、通通鼓和音树,色彩性乐器丰富。并且,作曲家在创作时特别注明所有乐曲各有一名演奏员进行演绎,这实则是出于对室内歌剧体裁的响应。在第一场猎人出现伊始(见谱例1),角色尚未有台词,此时打击乐组便采用吊镲和木鱼进行环境的烘托,尤其是木鱼点奏响的间歇性出现,可谓别具趣味。

谱例1 《要求很多的餐厅》第63~75小节打击乐声部
笔者认为,剧作中丰富的打击乐组主要有三重作用:其一是衬托人物性格,如用颤音琴的音色表达来代表胡丽丽阴柔且神秘的人物性格;其二是对环境气氛的营造与烘托,如在瘦猎人和胖猎人吃“美食”的片段中,用小军鼓演绎类似进行曲般的节奏,从而提示情景的滑稽、荒诞;其三则是对剧中人物的动作予以提示,如胖猎人“有人吗?有人吗?到底有没有人?”片段中通过富有色彩差异的乐器增添作品的戏剧性与冲突性,为人物形象增添趣味与生动气息。
歌剧的节奏设计方面同样蕴含着作曲家的巧思。吴佳在其文中对此有着较为细致的分析,她对胡丽丽形象的配乐所演绎的变形华尔兹节拍展开讨论,从三拍子的多重性(见谱例2),进而关注到节拍的展开、强弱规律的打破以及音乐的发展动力等问题,并对猎人出场时的三拍子音型进行剖析,从而探寻猎人形象与性格刻画背后的处理。[1]68

谱例2 《要求很多的餐厅》第63~75小节人声与弦乐声部
此外,该作品在创作、演绎与聆听中凸显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循环”。这一特征在音乐处理技术方面有着生动体现,如最开始的小提琴主题在剧情发展到“猎人走不动,寻觅餐厅”的时候更换乐器,一定音高再次呈示;主题“请将……”也在整部歌剧中一直以同样的音调重复,尤其是从第482小节起,弦乐声部中“始终自由循环拨弦加拉奏直至作品结束”的处理,一方面意在突出“要求”的繁多,另一方面则是音乐形象与主题的加固,从而增强歌剧作品的荒诞性意涵。并且,在剧作最后胡丽丽吃人的情节中,钢琴声部也处于循环音型的不断运动中,描绘的是四周封闭的墙壁与胡丽丽的顽固的阻挠,故事中的形象无论他们如何走都是置身于循环之中,宛如处在迷宫中一般。[3]205在特定音乐(素材、主题)的出现时使聆听者产生类似回旋[4]的印象,在“循环”的外在结构下,实则是随着戏剧情节的推进发生的变形与更新。
在音乐结构上,该作品并无严格的传统回旋曲式结构,作曲家在创作时采用“回旋”思维写作,但在两个片段中有着相对完整的曲式框架。其一是在猎人们刚进场时直到“狗怎么死了?”部分,这一部分构成再现三部曲式(A—B—A1)。其二则是在胡丽丽的咏叹调部分。这是一个非方整的多乐句构成的一部曲式结构,分句由a—a1(a句的模进)—b(对比)—c(高潮)—d(结束)构成。从该作品结构中可以看出作曲家对传统歌剧结构的继承与创新。
从以上对作曲家音乐创作技法的讨论中可感知,配器、节奏、曲式等诸多音乐基本要素均服务于歌剧本身,在戏剧性表达、音乐化处理中为歌剧情节处理、冲突描摹助力,通过多重方式表达与呈现该作品中的“循环”思维,表达作曲家的内心世界。
三、视听与审思:戏剧表达与演唱诠释
在歌剧这一舞台表演艺术形式中,戏剧性意涵的表达不仅依托于音乐语言,还受到舞台布景、灯光、动作、道具等观演要素的制约,在诸方面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歌剧演员的表达与配合,共同展示一部精良的作品。以下便从构成歌剧舞台呈现的诸多要素出发,探寻《餐厅》的戏剧性表现。
(一)视听结合——叙事与冲突
《餐厅》作为征集比赛获奖作品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演出,在极佳的剧场环境基础上,搭配富有巧思的舞台美术、布景、灯光,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听觉双重维度的精彩体验。(图2)作为物质承载体的舞台,其布景以现代化风格为主,布置较为简约,别具特色的是舞台中的灯光与幕布,圆形幕布中的灯光形象随着剧情发展逐渐变化,如开始时的复古吊灯、全剧终舞台灯光大幕投射出的狐狸形象等。此外,《餐厅》所采用的道具以写实为主,如胡丽丽手持的红酒杯、猎人手持的猎枪等。从上述诸要素中均可见得该作品舞台布置与歌剧情节间的密切关联。舞台美术借助造型艺术手段,为戏剧表演创设一个模拟的时空环境[5]。舞台运作是歌剧美感生成的重要物质载体。对于欣赏主体而言,观演环境中的舞台布置、变化对其审美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视听结合的表演诠释下,视觉系统与听觉系统相互支撑和制约,从而建构一部多维立体的歌剧作品。

图2 《要求很多的餐厅》剧照二
室内歌剧的叙事性特征在观演场域中逐渐显露,与此同时,歌剧的戏剧表现力也在歌剧音乐、演员的舞台诠释中呈现得越发鲜活。在《餐厅》中,作曲家充分利用旋律、节奏、和声等技术手段来营造氛围、刻画人物形象,除前文所论及的三拍子节奏与独特的配器手法外,作曲家设计了诸多鲜明的力度对比,如第415~417小节力度从mp到sfffp的细腻转变、全剧末位置处力度从ppp变化为fff等。并且,在乐器演奏法上,作曲家进行了非常规演奏技法的尝试,如巴扬在变化音和弦上的多次刮奏,尝试营造出内心世界的波澜与纠结;第465~473小节钢琴声部长达9小节的持续颤音,则表现猎人面对死亡时内心的畏惧与恐慌。可见,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综合性的视角与手段进行设计与布局。室内歌剧戏剧性冲突的营造离不开这些音乐要素,这些要素的设计同时也为建构富于戏剧化、叙事性的音乐表达助力。
在这场视听盛宴中,精巧的舞台布景与戏剧化的音乐表达相映衬,在音响符号的多次再现、人物对话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情节戏剧化发展,戏剧节奏紧凑地向前推进,从而用音乐组织起《餐厅》的整体架构。
(二)真实可感——人物与对话
作为当代室内歌剧作品,《餐厅》以贴近生活的对话式的歌词推动着情节发展,使听众易于理解剧情发展、了解人物形象心理。口语化的歌词在发挥叙事功能的同时,也给剧作音乐的抒情性带来了挑战,以下笔者便结合具体唱段进行分析。
首先看胡丽丽咏叹调唱段,在创作此部分内容时,作曲家采用无调性音乐技法创作,这使得歌者需完全依托以往固定音高训练记忆来进行诠释。在表达时做到叙事性、抒情性和音乐处理的精准平衡对于歌者可谓是一大挑战。其次在胖猎人与瘦猎人两个角色的唱段部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其中的节奏设计——两人节奏相互补充映衬,乃一唱一和,如若有一方节奏出现差错,便不能达到理想的舞台呈现效果。最后当全剧三个人物演绎三重唱时(见谱例3),相应的音乐伴奏几乎不具备旋律性,且胡丽丽与两个猎人所演唱的声部间看似并无关联,实则又处于一种和谐的搭配与映衬之中,这些因素对于歌者的把控音高、音准、节奏都有很高的难度。

谱例3 《要求很多的餐厅》第342—348小节(部分)
笔者认为《餐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饱满且鲜明,这与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的符号化处理、重复性手法运用息息相关。如在猎人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伴随着特定的主题动机、音型的变形贯穿,符号化的音乐素材与人物形象产生联系,且在剧中多次出现,使得结构化、形象化程度更为深入。
四、结语
正如娄文利对现代中国歌剧艺术提出的展望所言:“在歌剧创作领域更具实验性、先锋性和专业性的室内歌剧创作应当走得更远、更快、更大胆一些。”[3]207在《餐厅》中,笔者体悟到了当代歌剧创作在题材选择上的延伸、在音乐风格上的综合、在舞台呈现上的突破。作曲家将音响巧妙构思处理叠置,利用音响符号来勾勒角色形象,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同时将单个戏剧情节与整部剧作的发展密切勾连,从而增强作品的完整性、中心性和戏剧性。此外,从丰富的打击乐色彩、乐器演奏法的尝试以及音乐语汇的丰富等诸多巧思中均可窥见室内歌剧的戏剧化与叙事化特征。
居其宏曾在《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一书中论及“中国当代歌剧创作的四大症结”(2)四大症结分别是剧本缺钙贫血症、戏剧功能紊乱症、歌剧音乐痴呆症、如歌旋律失语症。参见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21-223页。,并分析其背后的“病因”有两点,一是对欧洲歌剧认识上的误解和实践中的“误访”,二是各种评奖的误导和生存环境的误伤。依托本次对《餐厅》的探寻与思考,笔者认为浙江音乐学院主办的室内歌剧作品征集比赛获奖作品展演活动为当代室内歌剧发展搭建了有力的助推平台,让室内歌剧的生存环境及文化市场较以往有一定的良性发展。同时,当代歌剧创作也逐渐朝着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与审美习惯、趣味的方向发展。
以《餐厅》为例,中国室内歌剧的创作与发展离不开题材的选择、脚本的撰写、音乐语汇的设计,这要求我们对中国歌剧创作发展予以关注,同时深度解析中国歌剧音乐文本的深刻内涵。作为歌者、歌剧演员,既要准确把握角色形象,对剧作进行专业化的诠释与演绎,做到唱演并重,又要深刻理解作品背后之意涵,领悟其中的哲思意蕴,借由唱演进行生动诠释。这启发笔者在今后的歌剧表演与体味过程中,用心、用情感受中西交融的笔汇下谱写的歌剧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