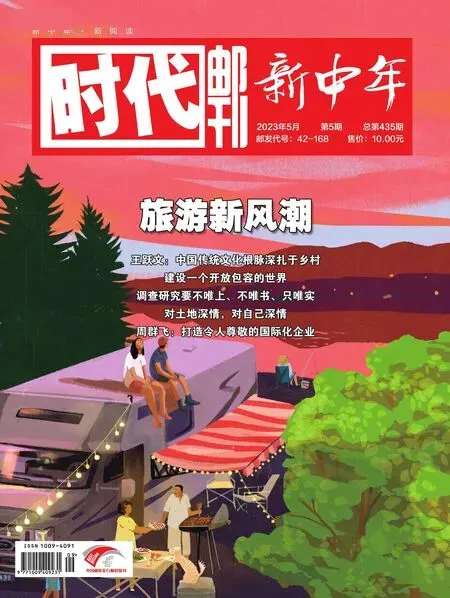“背奶妈妈”的隐秘战争
● 侯庆香
选择成为母亲,选择坚守职场,选择母乳喂养。这看似平常的三个选项,直到做母亲,王廉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艰难。没人告诉过她要怎么一边不耽搁工作,一边哺育孩子。
去上班,那怎么实现母乳喂养?带着焦虑,她逛了一圈母婴论坛,学到了一个新词,“背奶妈妈”——在公司吸奶,下班带奶回家的哺乳期妈妈。这似乎是最优解决方案,于是,一场“战争”在她结束产假、返回岗位的第一天拉开了帷幕。战场上除了她,还有不计其数的母亲。

颠沛流离的母爱
早高峰期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背奶妈妈”是很容易分辨的。她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格外多,用来冷藏母乳的冰包、电动吸奶器、洗刷用具、哺乳巾、储奶袋等。
王廉在青岛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工作,生育之前,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算太忙,朝九晚五,双休。自从做了“背奶妈妈”,尽管由于刚休完产假,工作量暂时只有之前的一半,她还是感觉自己成了突然被拧紧的发条。
晚上的睡眠被分成很多段,至少每三个小时要给孩子喂一次奶,一夜要起来三到五次。上班期间,一般每二到四个小时需要吸奶一次,每次吸奶大约用时半个小时,生活像她的身体一样被挤压。
有时领导布置紧急工作,王廉会尽量连续几小时不休息不喝水不上厕所,领导说“没问题”时才长舒一口气,马不停蹄跑去吸奶。同事看她拿着大包小包往外走,有时会调侃:“又去做饭啦?”公司没有母婴室,她找到了一间很小的废弃厕所,放置好板凳后,她拿出吸奶器设置好,看着乳汁一点点填满奶瓶,她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座“工厂”。
在一家媒体公司工作的陈蕙运气好一些,她的公司有一间母婴室,据说是由杂物间改造而成的。房间紧挨着楼梯,里面有张不小的桌子、三把椅子和一个一人多高的冰箱。第一次走进母婴室的时候,她发现冰箱不通电,门锁是坏的,每个人最想抢的是背对门的座位。
陈蕙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自己背对着门坐在桌前,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和谈话声越来越响,很快掩盖了面前吸奶器的嗡嗡声。她分辨出来,声音来自公司几位高层领导,还有陌生的声音,可能是老板在接待客人。她想:怎么声音这么近?领导会不会误入这个就在楼梯边的小屋?低头看着面前的吸奶工具和“袒胸露乳”的自己,她骤然紧张。
会议和出差是最让“背奶妈妈”头疼的。岳涵经常出差,每次她都要提前和当地酒店沟通,询问有没有冰箱,能不能存放乳汁。
出差两三天还好解决,最长的一次出差时间是12天,岳涵每天都要上课、开会。她特意跟酒店要了一个冰箱,把吸出来的奶放进去。会议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开着开着,她发现自己的胸部因为涨奶硬得像石头,乳汁逐渐溢出,打湿了防溢乳垫。她会冲到离会议室最近的卫生间,拿出吸奶器,吸几分钟缓一缓,尽管胀痛的感觉还在,但只能赶紧回去继续开会。
被吸奶这件事“绑架”了——这是很多“背奶妈妈”的感受,好像有一个四小时计时器悬在头顶,时间一到,无论手头上有什么事,都要先停下。
职场?妈妈?
202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新宇出版了《礼俗时刻:转型社会的婴儿诞养与家计之道》一书,讨论当下社会的母乳喂养环境与现状。
在研究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职场妈妈,她们中有的为了无穷无尽的会议放弃“背奶”,有的特意在公司附近租一套房子,中午回家喂一次孩子。尽管母亲们会为了最小程度影响工作使出浑身解数,但职场对“背奶妈妈”的“隐性歧视”依然存在,比如在奖金发放、职位晋升中的劣势,或是被排挤在某个小群体外等。
他采访过一位在大厂做程序员的职场妈妈,这位妈妈原本承担的是程序维护工作,产假结束后,她回到公司,被调离原岗位做销售。在刘新宇看来,“工作和生活”这一选择题背后的本质是母亲的牺牲。
在“职场妈妈”的标签下,到底“职场”和“妈妈”哪个更重要?王廉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妈妈”。
王廉加入了很多“妈妈群”,在群里,她感受到母亲的身份让所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给孩子喂奶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她在有100多人的群里询问职场妈妈在哪里吸奶,大部分人都说自己的公司没有母婴室,有的人甚至边开车边吸奶,还有的妈妈抱怨坐地铁时,安检员会询问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液体,有的甚至被要求“喝一口”,“太尴尬了”。
公司的母婴室是妈妈们的另一个“小世界”,“母亲”这一身份认同在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被放到最大。陈蕙第一次在母婴室遇到别的妈妈的时候,站在门口有些犹豫,她和对方并不熟识,没想到对方招了招手说:“来呀,一起吸呀。”很快,她也毫无心理负担地招呼后进来的妈妈“一起来呀”。但走出这几平方米的“结界”,她们在公司里再触及母乳话题,总会带着一些微妙的尴尬。
在母婴室有冰箱之前,陈蕙试过把母乳放在公司公用的储物冰箱里。她会封好储奶袋后再加一层外包装,但把母乳放在面包、蛋糕、冰淇淋旁边,总让她觉得有点不合适,她更担心这也许会让别人觉得不适。除此之外,摆在工位上的“背奶包”有时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事看到她放在窗台上的“背奶包”,好奇地问“这是饭盒吗”,她只能强装镇定掩盖自己的尴尬。
有次陈蕙离开工位去吸奶时,一位年轻女下属前来询问工作事项,被另一位男同事告知陈蕙“去吸奶了”。尴尬感同样包裹住了这位年轻女孩,她觉得自己似乎触碰到了领导的私人领域。
负重的爱
“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做了母亲之后,责任感和负罪感都会很强。”白雪成为母亲后发现,无论是对孩子还是职场,她总是很容易感到愧疚,“平衡”成为了怎么都完不成的难题。
王廉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的吸奶量,有一天,她总共吸出了420毫升母乳,在日记里掩盖不住兴奋,觉得自己“站起来了”。在奶量不足的日子里,她会绞尽脑汁分析到底影响因素是什么,食物?工作压力?和丈夫吵架了?对宝宝的愧疚感会持续到她下一次吸奶。
每次吸完奶,她也会在妈妈群里“打卡”,记录吸出了多少奶。有时身体状况好,她一次能吸200多毫升,但会特意在群里少报一点。“有的妈妈看到自己不如别人奶多,心里会不好受,觉得对不起宝宝。”
“母爱”的负担越来越重。刘新宇发现,女性在母乳喂养过程中常常感到尴尬和挫败,并且会因为难以平衡母亲身份和社会角色而自责,进而产生愧疚感。尤其近年来,随着婴儿养育标准和成本的提高以及社会压力的增加,女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愧疚感便越发频繁地出现。
在研究过程中,刘新宇加入了一个妈妈群,参加了数次线下聚会。妈妈们围坐在一起,安慰着一位因为身体不适想停止母乳喂养的母亲,但也有人劝她还是不要轻易放弃,“不然对孩子的愧疚感可能持续很久”。
一名叫凤青的母亲讲述了她的“背奶”经历,劝其他妈妈“打消这个念头”。她觉得东躲西藏的自己格外狼狈,如果被男同事碰到,就算表面上“心照不宣”,心里也很别扭。更麻烦的是,她好几次因为吸奶,在自己的工作环节掉链子,她愧疚地觉得自己没干好工作,对不起团队。“哺乳本该是在家里处理的‘私事’,而工作单位是公共场合,不应该把‘私事’带过来。”
凤青放弃“背奶”后,决定要在职场重整旗鼓,向将她换岗的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找回工作节奏并不容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她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突然的高压工作让她一下子很难承受,最难以接受的还是她之前指导过的年轻同事职务已经比她高了。“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
凤青想过辞职,但算了算养孩子的成本,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终于熬过“背奶”后,她换了新的着装和妆容风格,挑了一个假期给鼻子做了微整形手术,决定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王廉实在不想在厕所吸奶,她找到人事部门磨了又磨,最终申请到了一间暂时不用的办公室。但时不时会有同事进来打电话或处理其他工作,她只能趁着没人使用的时候赶快把办公室“占住”,有时一边吸奶一边能听到同事在外面打电话的声音,可能对方并不知道她在里面,但这同样会让她觉得尴尬。
王廉希望公司能设置一间专门的母婴室,但并不敢贸然跟人事部门提出要求。“因为我们只是小众群体。”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哪里不对,毕竟每个女职员都有做母亲的可能性。“如果能有个母婴室,会觉得自己作为女员工得到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