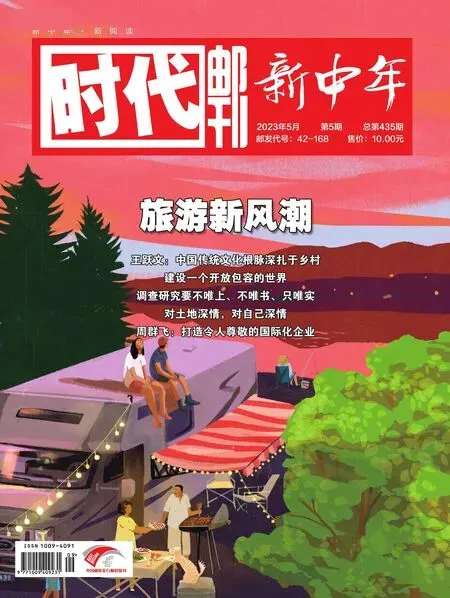他用双手描摹地球“脊梁”
● 董瑞丰 彭韵佳
中国西南,川滇藏交会处,重岩叠嶂,雄岭巍峨,是研究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过程的绝佳位置。
32年前,一名博士生用7年时间走遍南迦巴瓦峰地区,用双脚丈量着鲜有外人涉足的土地,用双手一寸一寸画出这片区域的地质图,让喜马拉雅东部大峡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32年间,翻越一座座雪山,经历一次次科考,对高原地质的热爱,沉淀为更深挚的情感。岁月化成山风,吹白少年头,58岁的他已满鬓风霜,依然奔走在科研一线,勇攀青藏高原构造地质学的“科学高峰”。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丁林。

▲ 丁林 (图片来源:“北大人”公众号)
用双脚丈量地球巨型断裂
青藏高原是研究地球板块构造最理想的“天然实验室”。1988年,刚出北京大学校门的丁林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读研究生,跟随他的导师、构造地质学家钟大赉院士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考察。23岁的他被安排在中缅边界地区的高黎贡山进行硕士论文写作。
“当时很兴奋,年轻也不害怕。”丁林回忆说,那个时候高黎贡山还没有像样的公路,白天他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寻找新的勘探剖面,绘制地质图,晚上就住在当地人翻山时借宿的山顶茶馆或猎人的窝棚,和猎人“侃大山”,了解当地风俗。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多月。
跋涉在山林荒野,风吹日晒是常事。“我们都是铁人,手里拿着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到处跑。”丁林笑着说。
即使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也要找到研究的“铁证”。铁人、铁杆、铁证——这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院士对丁林的评价。
“工作做完了,就要打上一颗‘金钉子’。”丁林说,在他看来,获取“铁证”最可信的是双手和双脚,无人机等现代科技只是辅助工具。“必须把手指放在要研究的断层面上,获得最踏实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丁林说。
群山浩荡,高原辽阔。研究完滇西高黎贡山,丁林顺着大山一路向北,挺进藏东南迦巴瓦峰——位于喜马拉雅山最东边的一座高山。那时西藏墨脱还没有通公路,丁林便在每年5月至10月的“窗口期”翻雪山进南迦巴瓦进行研究,一干便是7年。
丁林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用7年时间亲手绘制了南迦巴瓦峰区域地质图,让喜马拉雅东部大峡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现在世界面前。接着,他沿雅鲁藏布江继续向西,首次在日喀则西侧发现了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初始碰撞的关键证据。西至巴基斯坦北部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东抵印缅交界的那加-若开山脉地区;翻越缅甸野人山,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都有他手持地质锤和罗盘奔波来去的身影。
很多人都知道,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而丁林在墨脱的山顶上挖开积雪采集样品的时候,公路还没修到那里,全靠他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如今,丁林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对于东喜马拉雅构造结认识的空白,该区域至今仍是青藏高原以及世界地学研究的热点。
“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
丁林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青藏高原了。起初,路还没修通,他从北京到云南昆明再到云南大理,从大理再到西藏墨脱,仅路上就要花费20多天。弯弯绕绕、磕磕绊绊的土路,从来没有让丁林停下脚步。
完成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研究之后,丁林顺着雅鲁藏布江继续向西,首次发现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碰撞前陆盆地系统,随后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西构造结——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
对青藏高原痴心不改的求索,也回馈给丁林地球上最鲜为人知的秘密,他不断拿出刷新世界认知的野外证据,在大陆碰撞、大陆俯冲、高原隆升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他提出了印度与欧亚大陆于6500万年前首先在中部发生初始碰撞,随后两大陆之间的新特提斯洋向东西两侧逐渐封闭。两大陆于5000万年前全面碰撞的新模式,引领了国际印度-欧亚大陆碰撞研究,同时还开创了青藏高原大陆岩石圈俯冲研究的新领域。
后来,丁林把自己在青藏高原的科考路线导入地图,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走遍了整个青藏高原,有的地方还被密密麻麻的路线反复覆盖着。
从2005年到2007年,丁林六赴可可西里,组织完成了3次大规模科学考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探寻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地”的无人区。
促使丁林数次带队勇闯可可西里的是一个最基础的科学问题。在青藏高原核心区,有一条长约2500公里、宽约100公里、相对高差1000米的中央造山带。造山带以北发源的黄河、长江、澜沧江等,都流向了太平洋;而造山带以南发源的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都流向了印度洋——它在地质学上的意义,显然非同一般。那么,这条世界屋脊的“脊柱”,青藏高原的“分水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就藏在可可西里。
都说万事开头难,可是同可可西里打交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容易过:他们曾经与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擦肩而过;曾经有同伴在野外突发阑尾炎,因为没有条件做手术而命悬一线;他们还遇到过这样的危急情况:地图上指示的必经之路已被大水淹没,只能靠队员们在冰冷刺骨的湖水里站成一排人墙,指引并保护大型油罐车顺利通过……但无论多苦多难多危险,丁林从未想过放弃。

▲ 丁林在藏北野外考察寻找古土壤(图片来源:“北大人”公众号)
六进六出,丁林完成了对可可西里的全面地质调查,提出了大陆俯冲诱发高原“隆升”的新理论,重建了高原主要山脉从海底到世界屋脊的差异隆升过程。他的一系列发现,对青藏高原地质形成机理和对环境气候的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助于探索这一地区铜、锂、铅、锌、金矿床成矿潜力和分布规律。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丁林坦言,基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如果不做,永远不知道岩石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不了解我们生活的星球。
近些年,丁林承担和参加了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川藏铁路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前期安全评估工作。“这时候再做基础研究,就来不及了。”丁林有了新答案,“基础研究能够为国家重大工程应用做贡献。”
“拎包”变“引领”
曾经,有关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多由国外主导。
丁林亲历了这一阶段。国内仪器设备有限,往往借助国际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科考,采集的样品也需送到国外开展少量分析,再加上对地质学的认识和积累有限,中国在国际青藏高原领域的原创研究很少,话语权很微弱。
筚路蓝缕已成过去时。“现在,我们的研究手段不弱,研究理念也先进。”在丁林看来,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从“拎包的”变成了“引领者”,地位在不断提升。
2003年,丁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挂牌之前,同行们帮着出主意,想出许多“高大上”的名字。丁林却敲定了这个最朴实的名字——“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
“这个名字最土,却很实。”丁林笑言,碰撞和隆升正是青藏高原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后来,这个“土名字”在国际上也叫响了。
印度和欧亚大陆持续至今的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大规模隆升。近20年来,随着定量古高度计的发展,高原隆升由定性描述转向定量约束,科学家突然发现,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还很不清楚。
丁林发现,青藏高原并不是整体抬升,不同山脉各有千秋。
冈底斯山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山脉,在高原产生之前已是一座影响全球气候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却非常年轻,6500万年前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之前它还处于海底,2400万—1500万年前才快速隆升到现今的高度。
随着喜马拉雅山“隆升”,季风大规模北上,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团受阻于喜马拉雅山前,转而向东传输,给我国东部带去大量降雨,使得原来被沙漠覆盖的江南变成鱼米之乡。
“青藏高原21世纪还有地理大发现!”丁林笑着说。他们提出的高原山脉差异隆升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地理学界的广泛认可,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山涛风浪,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正如高原磐石无声地讲述着沧海桑田,丁林坚守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用双手一点点描摹地球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