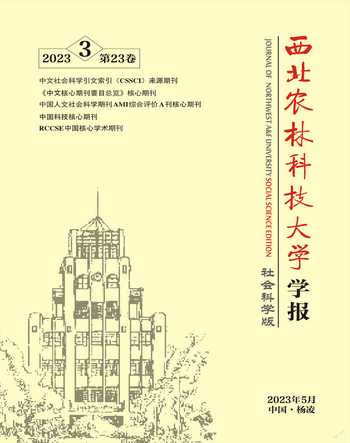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问题反思与重塑
刘鹏 崔彩贤

摘 要:我国一村一法律顾问实践在近十五年里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推进乡村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S省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运行中尚存如下问题:村民好评率低、村委会认可度差、驻村法律顾问自我成就感弱、司法行政人员满意度低。问题背后折射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自身的不足:工作职责内容规定过于宽泛导致角色冲突;过度的行政资源配置手段违反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责权利配置不合理导致工作开展不可持续。为了进一步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优势,需要重新定位驻村法律顾问的岗位角色,明确其主要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出发重新明确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重新归位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充分尊重和维护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实现责权利对等;并建议司法部尽快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条例》。
关键词:乡村法治;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反思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3-0143-09
收稿日期:2022-09-14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3.15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1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452021191)
作者简介:刘鹏,男,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法治与生态环境法治。
*通信作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首次提出“法治乡村”概念,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2020 年)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法治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法治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主要任务、组织实施等作出了详细部署,法治乡村建设进入了换挡提速的新时期。如何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已经全面推广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有效作用,是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命题。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效果直接影响着法治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关系着法治社会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学界对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已有密切关注,有学者从政策过程视角分析,认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政策活动中存在短板、缺乏有效的评估体系,多元监控机制的缺位导致“内卷化”等[1];也有学者从制度设置和运行分析,认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设置过分一体化[2],运行存在过度行政化,造成非可持续性困境[3]。针对现存问题,学者提出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4],加强舆论宣传、重视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创新工作机制和健全考评监督机制等建议[5]。现有的研究从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的现存问题出发,试图通过优化制度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但是现有研究仅关注问题的表象,缺乏对问题表象之下的角色冲突内在原因分析,因此提出的制度完善建议不能对症下药,无法为破解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困局提供正确的进路。因此,要不断强化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法治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深入反思并予以修改完善。
一、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历史沿革与变迁
(一)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初创探索阶段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2006年),要求拓展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律师要为农村提供法律顾问、法律咨询、代理诉讼和法律援助等服务;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担任村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帮助农村建章立制、实施依法治理等,服务农村社会的法治化管理。该意见尝试引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为农村提供法律服务,这为乡村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政策基础。自2007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率先制定了《宁波市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意见》,将全市執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纳入法律顾问队伍,明确了法律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为全市两千多个行政村配备了一村一法律顾问[6],因此宁波市成为我国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实践探索的发源地。在2010年,浙江省和海南省分别制定了《关于推进全省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和《农村法律顾问管理规定(试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探索正式起航。
(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全面普及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重要任务,农村法治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部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该意见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乡村法律顾问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向乡村选派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乡村法律顾问制度首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中。自此以后,广东省、江苏省、陕西省等20多个省份先后制定了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制度文件,并将其纳入重要工作。司法部明确要求,全国范围内应在2018年底基本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三)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深化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治保障。截止2019年4月,全国65万个村(居)已经配备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99.9%。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成为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石。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逐步带动了法律资源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推广,加强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普法力度,在解决农村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各地高度重视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围绕乡村法治建设的中心目标,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模式,诸如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建立了社区法治“1133”工作模式[7]、广东省建立了政府购买机制与跨区对口支援机制[8]。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短短的15年里,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国,经历了快速推进的发展过程。制度推进的背后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是自发的需要促进了制度的产生与实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统一安排部署推进。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客观上对于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对于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实际的运行效果也应当值得关注,只有充分了解实际的运行效果,才能把制度治理效能发挥到最佳水平。
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面临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研究选擇了位于S省的63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在调研期间共发出调查问卷3 370份,收回有效问卷 3 091份,访谈记录40份。通过对数据基本结果进行处理分析后发现:村民、村干部、驻村法律顾问和司法行政部门对于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反映的问题各不相同。
(一)村民对驻村法律顾问工作好评率低
村民对驻村法律顾问存在不知道、不认可、不信任的问题。经过调研发现,村民知道驻村法律顾问的占比为54.6%,不知道有驻村法律顾问的占比45.4%;21.5%的村民认为驻村法律顾问有较大作用,42%的村民认为驻村法律顾问作用不大,认为驻村法律顾问完全没有作用的占比36.5%;20%的村民认为法律顾问能公正地解决问题,46%的村民认为法律顾问解决不了村里的主要问题,认为法律顾问站在村委会一边替村干部说话的占比34%。
“驻村法律顾问使用的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在对村委会的工作有意见的情况下,驻村法律顾问基本都是向着村委会说话,我想要解决的问题,驻村法律顾问也根本解决不了。”(村民访谈记录:SYLJG20210825)
(二)村干部对驻村法律顾问工作认可度差
村干部认为驻村法律顾问存在工作时间难以保障、工作开展组织困难、部分建议实施困难等问题。村干部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驻村法律顾问的每一次蹲点服务都得首先与村干部联系。经过调研发现,55%的村干部认为驻村法律顾问能够每月到村蹲点服务一次,35%的村干部认为驻村法律顾问一年之中偶尔会到村驻点,10%的村干部反映驻村法律顾问一年都没来过村里;除开个别法律咨询服务之外,在面对驻村法律顾问提出开展法治宣传时,61%的村干部认为多数村民觉得学习法律知识对自己作用不大,导致人员组织困难;39%的村干部认为场地有限和时间冲突导致组织群众困难。“驻村法律顾问对我们村委会集体决策提出了很多合法性建议,但是有些建议与我们村一贯遵循的习惯不一致,有些建议只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导致有些法律建议难以实施。”(村干部访谈记录:SYZJF20210826)
(三)驻村法律顾问工作自我成就感弱
受司法行政机关指派下乡提供法律服务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工作报酬低、村干部不积极配合、村民缺乏积极性。经调研发现,85%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当前司法行政部门发放的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完全不对等;15%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当前的报酬无法承担下乡的交通费,每次驻村法律服务不仅耽误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机会,甚至自己还得自担成本,面对生存压力根本不想承担驻村法律顾问工作。37%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村干部能尽最大努力为开展法律服务提供保障;但是63%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村干部在组织保障上敷衍了事,无法为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提供有效保障。24%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每次蹲点都有一些村民主动咨询并解决了一些法律问题;76%的驻村法律顾问认为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村民缺乏积极性,每次蹲点前来咨询的村民寥寥无几,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是一名年轻的专职律师,生存压力挺大的,每次下乡蹲点开展法律服务得到的补贴还不够来回车费,我原本以为能在蹲点村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拓展一些案源。但是驻村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并不容易,村干部在工作组织上存在畏难情绪,留守的老年村民也并没有多少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村里的很多问题我从法律的角度解决不了,一段时间之后村干部和村民对我就十分冷淡,我觉得后期的工作开展真的挺难的。”(驻村法律顾问访谈记录:SYYWP20210929)
(四)司法行政人员对工作满意度低
一村一法律顾问是各地司法行政部门主导推进实施的具体工作任务。司法行政人员在推进驻村法律顾问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驻村法律顾问人员不足、财政经费支持不足和监督考核手段乏力的难题。
“我们县行政村共计65个,全县只有2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共计不到10人,加上基层法律工作者,能担任驻村法律顾问的人员不到13人,人均包村5个之多,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量确实很重;由于全县经济不发达,列支驻村法律顾问工作的专项经费较少,给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补贴基本是象征性的;在考核评价驻村法律顾问工作时,简单量化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定性效果评价机制却难以建立,考核结果对驻村法律顾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建立常态化的驻村法律顾问工作激励机制一直是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访谈记录:SYZZJ20211006)
通过对S省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涉及四方主体的调研访谈可以发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与预期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各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观点分歧、有时甚至是对立,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并不能让村民、村委会和司法行政部门满意,而近乎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驻村法律顾问也存在难处和怨气。
三、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问题内在原因检视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行旨在推进基层法治,通过行政权力配置法律服务资源,满足乡村各主体的法律服务需要。其初衷符合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顺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需求[9]。但是从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无论是作为制度受益者的村民与村委会,还是作为制度实施者的驻村法律顾问,抑或是作为制度实施推动者的司法行政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怨言。究其原因,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本身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截至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专门性规范和文件,现行的制度分别由各省市县自行制定,指导思想不统一,制度具体内容也存在失当和不完善之处[10]。本文选取浙江、广东、江苏和陕西四省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见表1)作为分析样本,审视制度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
(一)驻村法律顾问工作职责过于宽泛导致其角色冲突
从现行各省关于驻村法律顾问工作职责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驻村法律顾问服务对象包括村民、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等其他涉诉涉访维稳部门,服务事项既包括特定主体的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纠纷化解和法律援助等,又包括不特定主体的法治宣传、乡规民约等规范的合法性审查等。驻村法律顾问既是村民和村委会的法律服务者,也是法律纠纷的调解员,还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法治宣传员、维稳情报员。驻村法律顾问的多重社会角色会导致角色冲突。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不同的社会角色应当具有与其相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每个角色都有一定的角色期待,但这些期待彼此出现矛盾或个体对过多的角色期待难以应付时,就必然会造成不同角色间发生冲突[11]。驻村法律顾问多重社会角色在理想层面可以共存,因为制度设计者把全村看成一个利益整体,把驻村法律顾问视为能时刻坚守中立并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理性人。但是现实中,村域范围内的矛盾纠纷可能会发生在村民内部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有时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村民与基层人民政府之间。身为法律服务人员必须坚守的职业伦理根本要求是,要坚定地站在服务对象一边,尽最大努力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让服务对象满意;法律服务人员对当事人负有忠诚义务。当一名驻村法律顾问在面对具体的法律争议时,他很可能先后为争议双方提供法律服务,为两个利益冲突方提供法律服务违反了忠诚义务,便会发生角色冲突。驻村法律顾问同时为争议双方提供法律服务,从逻辑上也构成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所禁止的双方代理,尽管这种双方代理与律师执业中的双方代理不尽相同,但是驻村法律顾问为争议双方都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必然会引起争议双方的警惕、猜忌,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可能会充满不信任,这种状态下的法律服务很难取得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驻村法律顾问担任法治宣传员、维稳情报员,往往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履行管理者委托其承担的职责,当村民与管理者发生法律纠纷时,驻村法律顾问的介入很可能既是裁判员(站在管理者一边),又是运动员(站在村民一边),必然会造成角色混同与冲突[12]。把唯一的驻村法律顾问当成多元利益主体的委托人,有时甚至是两个利益冲突方的法律服务主体,必然会造成驻村法律顾问角色冲突。驻村法律顾问角色冲突直接导致了广大村民对驻村法律顾问的不认可和信任危机。
(二)过度行政配置资源违反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客观规律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弥补乡村法律资源的不足,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动作为,将法律服务优势资源通过行政配置手段补充到法律资源稀缺的乡村地区,从而实现乡村法治。从现行制度规范看,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行政配置的主导地位是明显的。《浙江意见》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统筹安排基层法律服务力量,加强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广东意见》规定地级以上市司法行政部门统筹本地区的法律服务人才资源,指导县(市、区)建立完善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有关制度;《江苏意见》规定省辖市、县(市、区)司法行政、民政部门负责统筹指导,组织实施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陕西制度》规定市司法局根据所辖各县(市、区)的村(社区)数量等基本情况和工作需要,负责本地区村(社区)法律顾问的统筹协调和配置工作,县(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村(社区)法律顾问的选派和更换工作。其他省市的一村一法律顾问都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的主导职责。由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自上而下全面覆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有与没有的问题,对于阶段性缓解偏远乡村的法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之初目的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应当着力去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着力解决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关注焦点将从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形式全覆盖的数量要求逐步转向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将使用者付费等市场化原则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13-14]。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下,法律服务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服务是供需双方根据自愿和实际需要达成的一项服务交易,需求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满意的服务商,服务商为了立足市场必然会为需求方提供最好的服务[15]。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一村一法律顾问法律服务资源配置[16],对需求方而言可能是一种生硬的送法下乡服务,原因主要在于驻村法律顾问可能只精通单一业务或能力欠佳,需求方面对这种无法选择的法律服务难免抱怨,原本作为惠民工程的法律服务变成了减损政府形象的负面事件。
(三)责权利配置不当导致工作开展不可持续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关键在于驻村法律服务人员。驻村法律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责任心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法律服务效果,关乎乡村法治建设水平。如何发挥驻村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作用,各省在制度规范中明确了一些措施,《浙江意见》规定加强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对经济欠發达地区乡镇和行政村的法律顾问工作,政府及相关部门予以一定的经费支持,重点加以扶持;《广东意见》明确规定村(社区)法律顾问“每个月至少到村(社区)服务累计8小时,每个季度至少举办1次法制讲座”,并建立评估制度;《江苏意见》规定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的评估检查和舆论宣传;《陕西制度》规定村(社区)法律顾问应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办)司法所的监督指导,“对于工作懈怠的驻村法律顾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提出更换律师的要求”。从以上省份的制度规范可以看出,对于近乎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驻村法律顾问规定了严格的工作要求和检查监督;而对那些违反工作要求或检查结果较差的驻村法律顾问,仅面临着被替换的处理结果,这种处理结果对其毫无督促之力,对个别驻村法律顾问而言可能正中下怀,使其借机脱身。
从待遇保障来看,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为驻村法律顾问提供了一定的工作补贴,但是个别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提供的工作补贴甚至无法保障必要的交通费。从各省驻村法律顾问组成人员结构来看,驻村法律顾问主要由执业律师组成,执业律师是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依靠提供法律服务获得物质生活保障,承担驻村法律服务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近乎是无偿的,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17]。对于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驻村法律顾问来讲,仅仅依靠情怀而不从理性经济人出发考虑劳动对价,他们的工作动力是不可持续的;况且多数被指派驻村的执业律师是年轻律师或收入不高的律师,他们本身还在为生计奔波,近乎无偿的驻村法律服务工作只会让他们疲于应付[18]。当前一村一法律顧问制度重点放在对驻村法律服务人员工作要求和检查监督,在责任无限大而权益无保障的情况下,无法从根本上激发驻村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过多的硬性要求甚至有可能消减部分积极参与人员的公益热情,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四、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重塑
(一)重新定位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驻村法律顾问作用应当持续强化。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乡村,乡村法治建设是未来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乡村仅依靠乡规民约已经无法化解全部矛盾纠纷,无法维护乡村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无法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客观需要。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9],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有效把国家法律植根于乡村大地。我国广大乡村法治人才严重匮乏,要推进乡村的法治化进程,短期内必须依靠外部法治力量的输入,驻村法律顾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乡村长期无法律服务的空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问题会越来越多,对法律服务的需要也会越来越强烈。乡村“法律明白人”虽然已经进入试点阶段[20],但是全面普及并发挥作用仍需时日,也无法从根本上替代驻村法律顾问的作用,因此,持续改进和强化驻村法律顾问的作用是基本方向。
要重新认识驻村法律顾问到底是谁的法律顾问?这个问题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之初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几乎各省都把驻村法律顾问看成是一个乡村法治建设的万能支柱,既为村民服务,又为村委会服务,甚至还为基层综合治理部门服务。这样理想化的设计忽视了乡村各主体之间的内在矛盾分歧,造成了驻村法律顾问角色冲突,严重影响了工作效果。要优化驻村法律顾问工作,必须首先明确定位驻村法律服务主要服务对象。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来看,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同时承担着部分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在涉及农村土地、开发建设、基层治理等其他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项中存在违法的可能性[21]。现实中乡村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挑战法治建设最大的因素就是村委会有法不依及违法行为,村委会侵害村民利益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往往是个别的、零星的,基本不会影响社会基本面上的正常秩序。因此,在乡村社会最需要法律护航的是村委会,驻村法律顾问应当为村委会服务,保证村委会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是其主要使命。村委会依法办事也就达到了维护村民合法利益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设置驻村法律顾问的初心。
驻村法律顾问是村委会的法律顾问,其工作职责就应当相应予以收缩。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重心和主要职责为列席村委会召开的重大会议,为村委会提供法律咨询,为“乡规民约”进行法律“体检”,为村委会的各项决策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为村委会开展涉及村民利益的各项工作进行事前合法性审查,确保村委会依法办事,确保村干部合法尽责履职。在履行主要职责之外,驻村法律顾问可以开展法治宣传、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帮助村民申请法律援助等事项,这些事项是鼓励性的法律服务,而不是职责性的法律服务内容。
(二)重新归位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
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总设计师,也是制度的执行者。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起草和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统筹本区域一村一法律顾问的选配、考核监督管理,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推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司法行政机关的推动。在个别法律服务资源较为紧缺的县市,司法行政机关要做好法律顾问与村之间的对接安排,确保每一个村都会有一名法律顾问。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之初,司法行政机关强制性地进行法律资源配置,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完成一村一法律顾问全覆盖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乡村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行政手段配置法律资源的方式可能会违背法律服务供需双方的意愿,造成资源浪费的不良后果。
在注重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实际运行效果提升的新阶段,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聚焦宏观制度的设计与优化,定位于宏观统筹监督检查。将一村一法律顾问法律服务人员与各村的对接等具体性事务交给市场去解决,充分尊重村委会与法律顾问之间的沟通和磋商,充分尊重村委会与法律顾问之间的互选意愿,由村委会与法律顾问之间签订正式的法律服务协议,法律顾问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需要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非律师法律顾问人员由其管理单位)审核盖章方能生效。村委会在法律顾问不履职或履职不尽责的情况下,可以单方解除协议,另行选聘;在村委会不尊重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擅自做出违法事项或其他侵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时,在不听从法律顾问建议的情况下,法律顾问可以解除协议并向律所(非律师人员向其管理单位)报告,律所(或其他管理单位)应当将报告内容转送当地司法行政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看得见的手必须适度收缩,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及时补位,借助市场的力量不仅节约了行政运行成本[22],而且大大激发了村委会和驻村法律顾问作为主要当事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村委会为了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自会全面考察法律顾问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责任心;驻村法律顾问为了被村委会这个当事人认可,定会尽最大努力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只有这样的法律服务关系才能取得最好的制度运行效果。
(三)完善激励保障措施
驻村法律顾问主要服务对象是村委会,因此,村委会就是驻村法律顾问的实际委托方;驻村法律顾问为村委会提供法律服务,村委会作为实际聘任方应当支付服务对价,同时对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决定续聘与解聘。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村委会一般具有支付法律服务的能力,如果驻村法律顾问获得了满意的服务对价,就不需要任何司法行政力量的介入,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就是一种纯市场上法律服务交易行为。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大多数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支付驻村法律顾问费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驻村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就是一个需要司法行政机关介入并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证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中村委会与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变,司法行政部门的保障激励措施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列支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村委会购买法律服务的费用。各省每年度对本省乡村进行分类评估,根据乡村经济年度发展状况,划分为驻村法律服务费用自理型、半自理型和不能自理型。对于自理型乡村不需要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对于半自理型乡村给予50%的法律服务费用财政资金支持,对于不能自理型乡村给予100%的法律服务费用财政资金支持,各级地方财政根据合适的比例分担支持专项资金。第二,增加对律师事务所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考核内容。将一村一法律顾问服务作为律师事务所必须开展的年度公益服务活动,每年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对于评估成绩良好的律师事务所公开进行表彰奖励,对于评估成绩较差的律师事务所,由其主管部门约谈律所主任,并限制其参加本年度各项评优。第三,将担任村法律顾问工作并考评结果优秀作为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一种形式。担任驻村法律顾问的律师,在本年度尽职尽责,考核结果优秀的可以免于承担其他法律援助义务。
(四)健全全国统一的一村一法律顾问专门制度规范
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基层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不可或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偶尔会被全国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文件提及,但尚未就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囿于缺乏全国统一性的一村一法律顾问行为规范指引,该项制度运行便缺乏体系性和科学性,实际运行效果无法保证。我国制定统一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文件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是进一步强化基层法治建设的需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的意见》(中法委发〔2022〕5号)都强调要“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是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为建设法治乡村提供制度保障。二是上升为全国一般性规范的实践基础已经具备,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全国已经实践十多年,各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也制定了成文的制度规范,各地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文本为制定全国统一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行为规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司法部应及时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实施条例》,为进一步推进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体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制度保证。
重塑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就是抓住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重塑后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需要由全国统一的部门规章为指引,进一步明确驻村法律顾问主要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出发重新明确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确立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原本由司法行政机关推动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借助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司法行政机关仅需从财政支持和考核监督上发挥作用。未来的乡村法治建设,在充分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优势之外,还需更多的法律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既包括本土的“法律明白人”,也包括乡村之外的法律资源引入。只有多元化的法律服务主体才能满足乡村居民对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内在需求,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才能推进乡村法治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牛广轩,姜国兵.政策过程视角下“一村( 居)一律师”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广东省M市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05):60-68.
[2] 杜承秀.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村寨非正式制度的融合[J].广西民族研究,2021(01):65-72.
[3] 邵珠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南海法学,2019(01):79-89.
[4] 王红卫,李建华,刘基智,等.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与探索[J].中国司法,2021(03):91-96.
[5] 孙伟峰,古钰钦.乡村法律顾问制度的功能、问题与完善[J].天中学刊,2021(03):39-43.
[6] 汪如坤.实施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法治宁波建设[J].宁波通讯,2008(02):58-59.
[7] 董春瑜,陳蕴.深入推进基层法治建设“莲湖经验”写进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司法局社区法治“1133”工作模式成绩卓然[J].人民法治,2018(13):82-83.
[8] 张紧跟,胡特妮.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村 ( 居 ) 法律顾问”制度——以广东为例[J].学术研究,2019(10):47-55.
[9] 姜晓萍.基本公共服务应满足公众需求[N].人民日报,2015-08-30(07).
[10] 曹吉锋.村 (社区) 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与问题反思[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7(01):85-95.
[11] 喻安伦.社会角色理论磋探[J].理论月刊,1998(02):40-41.
[12] 赵毅,宇廖永安.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91-98.
[13] 吴浩.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认识[J].光明日报,2020-03-17(13).
[14] 胡象明,杨拓.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视角——评《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管制创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07):175-176.
[15] 闫娟,李正明.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角色与责任[J].中州学刊,2013(09):5-9.
[16] 周喜梅,黄恒林.民族地区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基于G自治区H市的调研与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51-58.
[17] 程滔.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以《法律援助法》的颁布为视角[J].人民论坛,2022(09):100-103.
[18] 林茂.法社会学视角下律师群体的社会性[J].河北学刊,2020(03):183-189.
[19] 高其才.走向乡村善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13-121.
[20] 杨临宏,赵申.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86-95.
[21] 刘志鹏,王伯房.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权力博弈的矛盾及其协调——以广东省S村和Y村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1(05):140-143.
[22] 许明月.国家政治安全前提下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重心转移[J].比较法研究,2019(06):121-129.
Abstract: The 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 system in China has grown from a spark to a raging trend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 system in S province,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low praise rate by villagers, poor recogni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s,weak sense of self-achievement of legal advisors in villages,and poor satisfaction of judicial administrators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The problem reflect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 system: the content of job responsibilities stipulates that greed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lead to role conflicts,excessive all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violates the objective laws of mercerization of legal services,and inadequate safeguards lead to unsustainable work.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repositi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gal advisors,further clarify their main service objects,and redefin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rvice objects;The func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should be reset;the main body of marketable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the village legal advisors should be fully respected and maintained;Incentives and safeguards should be put back in place to achieve equality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a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form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for the Work of 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rural rule of law;one village one legal advisor;system reflection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