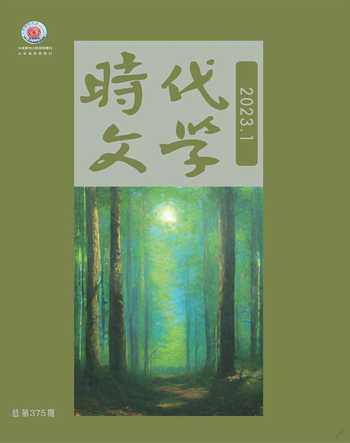印象记:不鸣则已的一鸣
张清华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声响亮,最初来自在山东博兴县最南端的一个村子里。
博兴,古时为千乘,其南苑与齐国都城临淄搭界,而齐被称为“千乘之国”,可见博兴一带战国时即为齐国屯兵的地方。这在军事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拱卫都城嘛。加之,这一带属鲁中平原,南部为低矮的丘陵,临淄及以北则均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便于用兵,且须屯以重兵,故称千乘也。
千乘出了孝子董永,《世说新语》开篇不久就说了董永的故事。而未被人加工过的版本里说,董永因为家贫,父死无钱治丧,便卖身葬父。守丧三年后,董永要履行自己的契约,去给大户人家当奴,但没想到这位乡绅为人厚道,念他孝顺,不要他干活。而董永生性诚笃,定要信守承诺,这感动了天上的仙女,以他媳妇的名义,帮他给财主织了一百匹生丝。完工后,二人各归其家,相忘于江湖,并无痛苦挣扎,也没有黑暗势力的阻挠。
说这些,是因为要说博兴的历史地理,大平原,靠近齐都,史上有淳厚的民风,而这是一鸣的生长之地。
说来,一鸣的老家那个村子,已是博兴县的最南端了。在一片海一样的绿色中,他站在故乡的地平线上,从青纱帐出发,发出了嘹亮的鸣声。
我与一鸣相识,其实已是多年以后。我与他同出生于博兴县,但我的家鄉是滨湖一带的水乡,与他相隔大概近三十里,所以童年自然是未曾谋面了。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至鲁北小城滨州,便闻知了他大名。
一鸣之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亮,那些年文学是热门,城市再小,也有一大群文学青年,滨州的文学圈子,提起一鸣没有不带着赞许的。可巧那时,一鸣又跑去省城读书了,而我与他交叉换位,分配到滨州一座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任教。便只能闻其名,而未能见其人了。
再后来又是若干年,我考取了研究生,回到了省城母校任教,那时再来滨州,才真正见到了一鸣。
彼时的一鸣,已然是真正的青年才俊了,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且以刚及三十岁的年纪,已经做到了医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三十五岁时,又一鸣惊人,担任了医学院副校长,在职业生涯中,已是占尽风头,成为小城的青年领袖。至于他和同事们到烟台海边筚路蓝缕创建大学新校区,那是后话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终于在一位作家朋友的研讨会上,真正见识了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李一鸣。
一鸣年轻的时候,确乎是一表人才的,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的个儿,一双活脱脱的大眼,身材修长且挺拔,就像鲁北平原上迎风挺立的一棵白杨——只是肤色稍显深了一点,谈不上黑,反而是如今时髦的“小麦色”。走在路上,一头诗人的发式,一甩一甩的,见人先笑,一口雪白的牙齿露出来,极富感染力。
一鸣事业上的成功,兴许与这副喜人待见的形象有关。谁不喜欢开朗、帅气的小伙儿,有才而不任性,自信而不高傲,聪明又不耍聪明,确乎是一鸣的做人之道。这当然不是修养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先天如此,骨子里带来的。
这就有了少年得志的一鸣,从那以后,一鸣的人生就是一路飞奔的节奏。
一鸣有一个绝活儿,见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就是可以当场作诗;不但作诗,还即兴朗诵出来,一边想着,一边嘴里就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地溜达出来了;不但溜达出来,而且充满不动声色的诙谐、现编现造的调皮,让所有人都笑得捧腹,笑得脸上的肌肉都疲劳酸软。
那以后,每次有一鸣的场合,最后都要让他表现这绝活儿。有时会是年纪稍长或有权威的人出题目,有时会让他现场为每一个人作一首。那效果,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仿佛一鸣那一口洁白的牙齿在吐露珍珠玛瑙,弄得大家满地找牙——不是被那调皮的词语给打掉的,是被那爽朗的笑声给累掉的。
如今,大家聚在一起,他不乏活跃而生动,但那活跃生动里,常常透出老成持重,毕竟,生活的风霜会在人的年轮上刻下印痕,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老成与活泼叠合起来,岁月带走的最美好的年华,总是让人忆念怀想。
一鸣的文字,朴素而直接,情感饱满,喜欢歌吟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礼赞那大平原上的一切,那里的庄稼草木,那里的乡人亲友,那里的土地风物,那里的人情百态,对我来说,都是再亲切不过的了。读之会疑心,难不成这是我的文字吗?
自然,那是此前的一鸣,那时他是一鸣惊其人,如今再鸣则是惊其国了,这国当然主要还是说其同行,其界别。但一鸣的影响,确乎已溢出了故乡那块土地,到达了更远的远方。一鸣依然低调,并没有做出一副专事写作的样子,端着架子写散文,还依然是一副顽皮的做派,书写着他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
但散文新作《在路上》,与早期一鸣的作品比,却有了变化。至少我是感觉到了他的认真,他确乎是开始“下功夫”地写作了。我注意到,作为自选集,他刻意选择了那些最能反映他“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的篇章,“那些人”“那些年”“那些事”“那些地”,分别收罗了他对故友故知、往昔时光、身历事件、走过地方的描绘,寄托了他对生命历程的追忆与眷怀。
他做功课是认真的,就像开篇的《远眺华不注》,就从学生时代的一堂课荡开,从孔孚先生的诗,谈到了元人赵孟頫的画,从《诗经》谈到了李白,从元好问扯到了周密,从《左传》扯到了《水经注》,几乎是集三千载于片纸之间,纳九万里于尺幅之内,从容谈笑,就把一首诗、一座山、一个涵纳古今的故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叫人读之爱不释手。
也长知识。
一鸣的散文其实是很讲章法的,不做作,喜实录,但始终有个“我”在里头,在现场。人在旅途中,情在山水间,这样节奏与境界就全出来了,这就叫“有我之境”。《过无锡》《彭山访故人记》《每逢暮雨倍思卿》诸篇皆是如此,上下古今,思接千载,把古人的命运与处境,通过环境与物的点染酝酿,活脱脱地表现出来,读之叫人意兴湍飞,浮想联翩,没法不拍案叫好。
当然我也很喜欢他那些写童年、忆往昔、怀故人的篇什,如《串杨叶》中,家庭突生变故,懵懂少年的莫名迷惘与悲戚心境,读之令人愀然;《在路上》中,他清寒且带着屈辱的童年也叫人揪心;而他一路走來的成长履历与酸甜苦辣,与多年后孩子考入北大、亲子一起漫步燕园的那份喜悦,则叫人百感交集;还有那些记录他温暖的家庭生活的篇章,读之也令人心生艳羡。因为通常人们都不太会在散文中书写此类内容,而一鸣则毫不隐讳地写了出来,确乎显出了他情感的纯良与朴实,实在是难得。
常想,文字之道,其实就在乎文字后面的那个人,修身与修心,人物的胸襟就是文字的质地,人的内心即是文章的境界。一鸣正是如此,常人会觉得一鸣有外向的一面,有诙谐的一刻,但他文章中的诚朴,确乎在印证着他的为人。一鸣是有襟怀、怀着大爱的,是一直坚守人生底线与精神之边界的人,所以才会有了这般令人欣悦的文字。
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我此刻还在想着一鸣在近二十年中的两次“蛙跳”。一次是考博士,我在调至北京工作之前,恰巧有机会做了一鸣考博的引渡人,他在四十多岁时考上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上了这班快车,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次就是十年前,他参加全国公选,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从一个地方医学院的副校长位置,来到中国作协工作。这委实是两次长距离的跨越,因为工作环境的差异,会使他在迈出这两步时面临抉择的困惑。
然而一鸣确是有决断的人。那时我曾略略担心,他跨越不同行当,来到人才荟萃、翘楚靡集的中国作家协会,会不会有某种程度的不适。可是并没有,他一来就如鱼得水,人见人爱,工作得热火朝天了。
这次系统地读一鸣的散文,除了文字上的收获,其实也解开了我积久的一个疑问:究竟一鸣为了什么,必定要迈出这南辕北辙的一步,我总算真正懂得了。因为在一鸣的心中,最核心也最原本的那个梦,其实不是别的,乃是文学。青山遮不住,他必定会走出这一步。因为他属于文学,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准备,绕了那么远的路,他最终还是要回归属于他的正途。
是的,这会儿,他正在东土城路那栋大楼里,在众多大家名宿出入的那座殿堂里,心安理得、安之若素地忙碌着,调度着,扮演着属于他的那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鸣是快乐的,他的快乐,既来源于一种有着难以言喻之神妙的“文学生活”,也来源于比那生活更为久远的文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