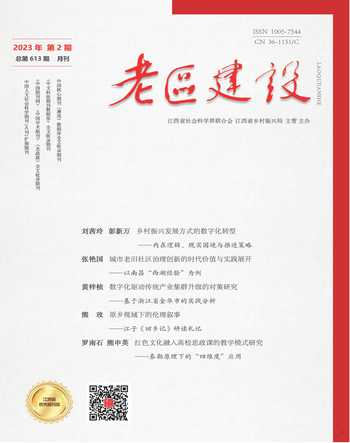原乡视域下的伦理叙事
[提 要]江子散文集《回乡记》的叙写敏锐地将社会变动与乡村的历史时间和现在时间进行了有机关联。作品对于原乡社会文化在不同层面的伦理形态进行了表现与思考。在职业伦理层面,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坚守,时代新因素的加入又在无形之中促进了它的嬗变与异化;在家庭伦理层面,儒家文化中的道统总体呈现了守恒的特性,异动亦展示了个体人无法驾驭的人性的失衡与跳转;在物性伦理层面,物象在保留文化原初性特征的过程中表现了持守的倾向,而乡村在进入与整体城市化进程的连接中又毫无疑问地出现了新的转向。江子《回乡记》对于原乡伦理形态的观察、考察和洞察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城乡变动的一次生动而全面的回应,其温柔敦厚之风可谓秉承了儒家哲学的基本范式。
[关键词]原乡;伦理叙事;江子;《回乡记》
[作者简介]熊玫,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教授,博士。
江子,本名曾清生,江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自1989年吉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散文创作。曾获老舍散文奖、孙犁散文奖、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等重要散文类奖项。
赣江以西是江子的成长之地。离别故乡的江子一次次将目光回移,用质朴谦和之笔书写了原乡大地上沧海桑田的故事。江子的笔触温情而不乏深沉,坦荡而不乏忧思。故乡于其既是精神的原生地,亦是无法再度抵达的久远记忆。故乡在时代的脉搏中跳荡,促使其笔耕不辍,书写了魂牵梦绕的原乡诗篇。
散文集《回乡记》全书共三辑,分别为“出走”“返回”以及“他乡”。凡13篇作品兼具散文与小说的双重品格,体现了跨文体写作的内在追求。
如果说钱钟书长篇作品《围城》创造性地展示了人类在面向诸多人生问题时的两难困境,江子对于原乡文化变动的思索则与历史进程本身达成了深度的和解,并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拉锯战式的对抗式框架。对于江子而言,原乡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断变化、解体甚至是再造的过程,但并非所谓的二维制情境所能指涉。江子对于原乡社会及其文化的体认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中由鲁迅所书写的对于“藏污纳垢”的乡土文化的批判传统,也不同于由沈从文先生所书写的对于“湘西风情”的乡土文化的抒情式追忆的传统,其更大的特点在于走进故乡不同时空聚焦的现场,以真诚地原乡人的身份去触摸乡村文化的纹理与内核。近距离的视点使得这位离开故乡而又始终参与故乡血脉跳动的叙事者讲述着赣江以西由古及今的故事,并在温厚地讲述过程中抒发着地道而质朴的超越于批判和诗意的更为厚重的情感。
一、职业伦理的坚守与嬗变
随着整体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乡土社会必然面临的变化在于社会行业的调整,随之必然发生的即为个体所从事的职业变更。
《回乡记》涉及到了原乡文化视域下多种职业的变迁史。其改变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演绎,更显见的是历史进程与人的道德观念之间碰撞所产生的职业伦理的调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1]人在历史的推力下总是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被动感,但真正推动人前行的力量本质上与人的深层文化积淀与道德自律密切相关。
职业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生存的工具。在生存的基础之上,职业伦理作为文化精神激活或者展示了原乡视域中不同职业与文化的融合。“在政治、伦理的层面上,更加深广的价值关怀,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总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2]《练武记》中的祖父与《行医记》中的周秋明都明显在职业伦理的作用下进行了自我的改造和蜕变。不论是“老座”的隐忍还是“医生”的持重都显示着职业对于身份及深层自我认同意识生成的对应性作用。文武之道至少在原鄉文化中保持了被敬重的至高地位,因而相应的职业人也在职业进程中获得了对于自身的提升和修炼,也即作为道统中的有机组织成分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而言的技术伦理。而传统文化被追忆和体认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自身所能提供给后来者的精神品格。所以,“武术”在赣江以西至少一代人的视野中并非简单等同于强身健体的“形”的层面的追求。鲁迅先生反省国民文化的劣根性时认为:身体即便如何康健也抵不住精神的困顿。这一认识固然令人振聋发聩,但原乡视域中的文化集成一旦生成超越性的内在精神因子,身体便可获得有效的力量,与精神协同并进。
精神力量的生长性很大意义上成就的是职业伦理的道德化内涵。这与职业对从业者人格的锻造形成互为表里的关系。在原乡文化中,其德行力量更多的是渗透在整体的无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职业伦理并非个体性意识,而是具有积极建构性作用的有作为的精神改造力。在江子笔下,民间乡野生态中具有非批判又超越于文化抒情性的认同机制。《练武记》中的“祖父”人生的高光时刻与整个村子的安全感关联在一起,“斗蛇”的英雄壮举使得武者精神进行了个体化的突围。这也是在时代不断更替中与以“练武”为噱头的纯商业行为的本质性不同。尽管祖父的高光时刻可能意味着武术传统在民间辉煌的末端。从社会发展演进的视角来看,“武术”最终被取代或者成为有名无实的幌子,与商业社会利益的驱动对其形成的遮蔽有关。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武术的位置逐渐被取代已为不争的事实,但散见于民间的习武者仍然在传承武术文化的要义。当武术转身消融于看不见的民间大地,其在场的标志已经进行了本质性的切换,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进步的表现。因而,所谓“挽歌”式的叹息实则是叙事者的情感忧虑,但又确实经不起时代步调的暗中调节与控制。无论去留,都不是个体性的力量所能改变,而精神能够传承则不必为时代的选择进行担忧。
同理,周秋明“医疗事故”结局的反转也生动地展示了民间大地上的温情。“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意外本不应负任何责任,但从生命的视角出发,周秋明选择为了避免新的意外事件而倾其所有。民众对其同样回应了善良和认同。在周秋明即将告别“医生”这一职业时,最朴实的赣江以西的老百姓却对之盛情挽留。生命的珍贵自不待言,但超越于生命的信任使得普通农民具有了对于常识、同理心的理性认知。职业伦理一旦爆发出其人性的光辉,医生可以治病,亦可以救心。在民众当中存在的善良和纯朴需要的是被点亮的“高光时刻”,江子悟见的并非国民性的劣根性,而是惺惺相惜的包容和扶持。尽管乡村医生在现代社会缺乏存在的历史性契机,但其曾经在乡村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作为伦理情怀所产生的原乡文化的感召力,正与治病救人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人文效应。
随着原乡社会及其文化的不断更移,职业伦理也随之发生嬗变,并表现出多样态的特征。职业伦理之所以发生变化与普遍性的价值转向密切相关。9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崛起对于原乡文化的改造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上,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的精神也同样被席卷进时代的大潮,并形成不同的冲击波。经济与精神形成的关系互为表里,可以看见的是行为及表象,不被看见的则在深处形成更大的旋涡,展现的是人自身在面向社会变动过程中的扭结状态及无力感。对于原乡文化面临的挑战及其产生的蜕变,江子的叙说并不简单批判或圣化。叙事者更多保留的是一份仁者之心,即投入足够多的宽容和会意,始终站在对象的角度,展示着在时代进程中职业人所面对的现实的乃至精神的隐忧。江子的叙述大多凝重而又体贴入微,对人的切肤的剖释和观照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超越于语言的情感流使得理性因素获得了极具动人的感性外观。
《怀罪的人》中的主人公三生虽为小学毕业,却因理发的天赋成为县城的名人。成为名人的三生结交了一批官员,并秉承了父亲“善人的秉性”,一度为家族办妥了诸多事务,成为具有传奇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及时雨”。“故事从来不离群索居:它们是一个家族的分支,我们必须向后追溯,向前寻觅。”[3]叙事者在此采取了双重视角对“三生”其人进行了写照:其一为职业伦理的跨界行为,即超越本分的对于既有社会准则及尺度的跨越;其二为延续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家族理念的守成使得三生获得了超越于一般职业表现的境界。双重标准的交织本身意味着文化形态错乱所产生的畸形儿必然走向无着的状态。传奇的坍塌始于三生的卷款私逃,其社会身份也随之转换为人人唾弃的“恶人”。作品对于三生逃跑后“罪感”心理的描绘使用的是先锋的笔法,对于其“回乡赎罪”情节的描绘多半出于对于所谓“罪人”的体恤情怀以及对于人性至善的期待与开掘。对于江子而言,“善”是本态,“恶”则包容着极大的转换的可能性。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理路也使得《回乡记》在书写乡土大地的过程中获得蕴藏于人性及人情土壤中的温厚与纯良。当批判无法获得坚实的对象,诗意想象不再充满感伤,江子的回乡之旅也注定获得了别样的生长机运。
相对热闹的转型也给曾经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自我展现的时空条件。《指上的航行》中的盲人按摩师们及《购房记》中活络的售房中介都来自于乡野大地,并曾经经受着不同的人生磨难。但在时代的磨洗中,其内在生命潜藏的力量获得了生长的机缘,并因之表现出极大的弹性和活力,从而也使其个体生命的史册变得生香活色。江子的笔法中不无冷静和达观,在近距离的观照和洞察中,原乡文化一边自我拆解,一边又获得了凤凰涅槃的生机。
二、家庭伦理的守恒与异动
“与西方人注重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不同,中国人则是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寄托自己的情怀,在为自己家庭成员的幸福牺牲中体验自己人生的价值。”[4]《回乡记》对于家庭伦理的表达总体上凸显了赣江以西文化本土精神中的尚和传统。作为文化及社会转型的中间代,江子叙写了其身份的尴尬及身不由己,但总体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和谐气息。《回乡记》除了表现自古以来家庭伦理的守恒特征,同时也应和着时代自身的变动,演绎了原乡文化可能遭遇的种种变体。
“回乡”主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文人表现情感的重要载体,其所隐含的动态性过程则折射了人与大地、故土之间必然存在的复杂关系。对于此,江子的观察和书写并未站在道德家的位置,而是以最为豁达的心态任由文本中的主人公在去留之间遵从于生命的本意。这是怀有诚意的作家对于生命的最高体认和敬重,是一位叙述者的最深层次的自觉和自律。
面向“原鄉”是去是留,回与不回都不是简单的“围城”法则所能囊括,正因为此,作品所蕴藉的人生形式显然充满无限的张力。这也意味着在尊重生命本意的基础上文学自身的一次飞翔。“回乡”作为传统文学中的意象在江子的笔下获得了极为丰富的表意空间。
首先,去而不回成为了几代人的选择。按照一般的逻辑,一辈子与土地产生亲缘关系的老一辈人更倾向于将落叶归根即“回乡”作为必然的价值选择。而江子却真实地通过“父亲”的形象刻画了城市化进程中父辈心态对于传统思路的反拨。老一辈农民在集体离开农村之后又迅速融入城镇,并找到新型的对话交互的渠道和方式。古典文学感伤的意象在现代新式农民的话语形态中遭遇了失落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以叙事者为代表的曾经生活成长于农村后又走出的现代职场人及其下一代已经逐渐和原乡文化产生了疏离感,原乡之根已然松动并发生了位移。叙事者“我”对于乡土的醒觉意识即对于其必然性转型和变动的认知充满自责意识,但情感上的自责显然无法与必然发生的事实产生实质上的碰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自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苛责”。“不孝子孙的自责”更多源于内心深处的伦理情怀,而出走是历史的推动,并非来自于个体性的力量。在《高考记》中,深情的父母与努力拼搏的孩子不过共同在践行一次远离故乡的行程。在不可知的潜意识中,故乡已经必然地让位于对于现代化本身的追寻。
其次,去乡后返乡亦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而返乡的原因由于主体所处的情境表现出了差异性。身心在异乡所遭遇的非对话状态成为返乡者做出选择的重要维度。《杨家岭的树》中的满崽年轻时出于生计、出于爱情、出于传承子嗣的需要远走他乡,几经周折后终又回到了故乡。返回的代价可能是和其年轻时追寻的一切进行告别,但唯有回乡,方能治愈身体的病痛,回归心灵的安顿。原乡文化以看不见的烟火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心灵结构图式。叙事者的理解更多包含着对于主人公表层性处境与深层性处境的双重互动及探索。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乡愁之所以成为乡愁最根本的原因,与其说出于情怀,不如说出于主人公所处的社会身份及其位置。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来看,满崽之所以不能适应异乡生活固然与原乡情结密切相关,而通过与去乡不归者进行比对可发现,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及身份可能更深层地决定了其与故乡之间的亲缘关系。《磨盘洲》作为返乡者的书写是具有独到特色的一篇。其独到之处在于文本根本性地拆解了矛盾的聚焦,作品整体流溢出古风尚存的融洽之意。作品尽管触及到死亡,亦书写了身体面向的困顿,但死亡是福寿已至的意外,失眠则是一次心田归途的引领和暗示。广东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城市固然具有强大的召唤力,但福米依然选择了通过回乡获取内在的休憩。返乡并不能作为一种仪式,但可以隐秘地宣告与原乡的内在贴合。
再次,原乡的留守者与回而不归的返乡者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家庭伦理的新型互动模式。《杨家岭的树》中的牛崽作为为数不多的年轻留守者之所以留守乡村,与其“阴阳人”的生理因素直接关联。牛崽固然存在着身体的缺失和障碍,但其个性中的阳光面带给家庭甚至是整个村庄的向善向美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作为补偿的确可以消解生理性的天然不足。作为象征性主体,牛崽代表的是与乡村可以产生紧密连接的弱势群体,古老的抒情诗式的叙说无声地隐喻着原乡社会必然走向逐渐自我封闭的旅程。《不系之舟》则将抒情诗式的美好想象直接撕毁,对传统儒家文化的道统进行了无情解构。主人公曾善春事业、婚姻顺风顺水,却因家庭变故感受了人性的巨大黑洞。作品之叙事具有不可比拟的冷静,其背后的空白却隐藏着巨大的玄机。曾妻拐卖夫家侄女事件表层摧毁的是一个家庭,深层警醒的却是人性的暗礁。沉默的侄女一直处于无力表征自我的状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原乡文化的蛮荒与落后。因而,作品以喜剧起始,以悲剧结束,没有结尾的结尾尽管可以延宕或隐藏矛盾的剧烈程度,但等待补白的巨大虚空内隐着必须直面的问题:伦理并非万能,外在的光环与内在的缺失正是所有“不系之舟”流离失所的动因。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时空流变包含的信息不仅仅与个体家庭关系及状态相关联,自古及今的文化血缘所形成的家族血统仍然成为中国人思考问题的重要依据。《回乡记》中涉及到主人公空间转向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拘泥于狭隘视域中的家庭本位。中国社会乡土文化中的宗族意识亦是难以颠覆的潜伏因子。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其发酵和生长的形式尽管可能隐匿,但却不会呈现消失的形态。“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5]
《怀罪的人》以先锋的笔法构建了主人公向家族自省的结局。这是叙事者的精神自觉,亦可见传统文化因子的强大附着。《回乡记》中的伯父形象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其生命历程的得志及不得志体现了自我构型与家庭、家族要求之间的复杂纠合关系。担当、责任等宏大的视角已经无法概括其强烈的内在生命冲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以收敛的形式屏蔽了自身的光芒,这是由家庭而家族的文化负累必然引向的结局。所幸的是,伯父将晚年生活安放于乡土大地,亦可见出其“潜志”之梦已经得到心甘情愿的松绑。从个体生命的视域来看,最终的结局复原了伯父的内在自由和自觉,也即在不得已的文化捆绑中最终得到了自我心灵的栖身之所。《临渊记》是鲜明地将古今融于一体,将家庭和家族叙事进行粘合的叙事范本。看似年代隔阂的故事却描摹出了一代代人在个体与家庭或者家族关系中的冲突与缓和的艰难进程。无论故事的形态发展有何差异,从强烈的冲突到寻亲的温馨场景,时间成为了一个古怪的参照物,既可钢化一切,亦可柔化一切。说到底,身心的割裂可能起于阳刚和血性,身心的统一同样回归于阳刚和血性。
三、物性伦理的持守与转向
《回乡记》以人的变动作为叙事的核心,物象作为人的行动之中不可割裂的部分使得文本叙事具有了着力点和抓手,人与物的交织形态共同形成了圆整的存在景观。物可以独立存在,但在与文化及人的交互关系中,又呈现了由外至内的生命及伦理属性。因此,人的世界因为物的参与获得了更为多元的情境及文化生长性,因而也展示了诗学意义上的美学形态。
原乡文化中的物象在时代的更迭中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其作为物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文化延续过程中所衍生的象征意义使得故乡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沉淀。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加剧,离乡者的数量远远大于留守者及返乡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乡村自然景观所保留的物性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持守与转向。持守指示的是保留文化中原初性的内外在供给,转向则指示着与整体城市化进程产生的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持守与转向的多向协同,原乡文化才因此而获得了时代进程中的独特风貌。
首先,在《回乡记》中,物具有与人性等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类在幼年时代所深信不疑的万物有灵论在乡土世界中更能展示其本体性特征。叙事者对于物性中人格化的展示不仅获得了美学的意旨,也对于人自身进行了隐性的反思。《三叔家的狗》放在第三辑“他乡”之中似有突兀,这是整本书中唯一一篇以物贯穿始终的叙事性作品。“他乡”意味着奔赴与远离,从表意系统来看确实与文本讲述的故事无法建构起关联。作品主要讲述了在深山办理养殖场的三叔所豢养的狗的故事,其中尤以祖母狗与母亲狗的壮烈为作品的聚焦点。祖母狗为死胎的孩子痛苦而死,母亲狗为被三叔活活剥皮的丈夫殉情而死。两代狗的深情在文本中无疑具有超越于现实世道人心的寓言学意义。在整体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出走的可能仅仅是人本身,人性却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经受自我及他者的磨炼和拷问,相对于人而言,物反而显示了超脱于时代进程的本性。或者说,人和物的区别在于面对乡土社会的变更,物更容易保持自身的本性。“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必须理智看待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边界和限度,以使文学发展在遵从“自然伦理的同时不违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前提。”[6]也许江子本身并无批判性的指涉意味,但故事本身所能引发的思考却毋庸置疑。
其次,物性除了具有自我的表现途径,人自身也常常将自身与物性价值及其伦理进行绑缚,并成为具有暗示甚至挟持意味的文化伦理。在此过程中,物不具有选择性,而是无条件成为人的世界价值整合、重组的代表和载体。在此,人的作用逐渐固化,并在历史的车轮中形成较为牢固的权力话语和机制。物性伦理本质上仍然是人的意识的投射對象,而其延续不衰的命运也寓示着人类生活本身较为稳固的部分。世界不断变化,唯其原乡文化较多地保留了物性伦理的文化行为及记忆。而当离乡者占据绝对优势并在时间不断推移的过程中,其最终将日渐成为后人追忆的历史沉积物。
在《回乡记》中,风水文化、拜菩萨、祠堂修建、烧塔仪式等风物或风俗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与乡土文化之间的长期久远的互渗关系。无形或有形的风俗成为乡村代代相传和沿袭的经典,但又在崭新的时代里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景象。被植入原乡心灵世界的文化模型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不同代际之间的生活。《建房记》中李茂才因为建房地址的选择和村民发生分歧,“我”则因势利导,从赣州以西人认同的风水文化入手对之进行了有效的规劝。此处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妙趣横生,也从生活的实景图中演绎了传统文化对于国人内心建构所发生的深厚影响。当然,任何影响能发生作用本质上都出于实利。从村民的反应来看,所谓信仰已经悄然转化为实用性机制,因而才能产生让渡和反转的效果。此情节的幽默诙谐多少消解了原乡文化的神秘色彩,表现了与世俗价值的高度吻合性及趋同性。拜菩萨和祠堂修建在《回乡记》中作为群体性活动得到了民间的高度认可。对于广泛的村民而言,拜菩萨仅仅是臆想中的心灵超脱,通过此举村民可获得极强的心理暗示及内在的安慰。神祇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念中的自我支持获得了外在世界具体形体的附会和确认。村民修建祠堂之慷慨也经由文化的传承在民间生活中转换为对于个人性力量的重视和认可。民间香火之所以旺盛的深层原因在于个体性力量对于自我确证的论证诉求。烧塔仪式作为民间风习的描绘在文本中表现了独到美学意蕴及其色彩,尽管其过程与叙事者回忆中的鼎盛时期不无差别,且在对比的过程中的确展示了时代本身必然走向的断裂。过去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在不断退场的过程中,也正好腾出了空间接受新形式的到来。尽管叙事者不无感慨,但从能量守恒的视角来看,惟其如此,方才显示了事物本来应该遵循的发展轨迹。
再次,原乡文化还存在着被忽略的见证者。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其存在本来就与村庄融为一体,比如花草树木,比如房子。这一系列物的存在是村庄的有机部分,见证者的角色使得物获得了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及象征意义。《杨家岭的树》中的大樟树作为“世界上最美的墓碑”,亲历了村庄的过去时代,其无声的祭奠也是对于不可阻挡的历史脚步的无奈退却。大樟树的年龄会超过所有的村民,其长存的精气又将夹裹着村野文化中看不见的气息一路向前。《建房记》讲述的是房子这一身体的庇护之所对于不同村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房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既可以连接过去和现在,又可以连接城市和农村,还可以连接走出去的村民和村中的留守者。作为中间媒介,房子毫无疑问具有高度的辐射力及渗透力,将时代变化发展的轨迹进行最为多线条的囊括和展示。“它包含着在任何时候都与人类最高价值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考虑,即: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的命运以及在这个世界中我的命运、我的同类的命运是怎样的。”[7]
因而,从《购房记》到《建房记》,作品记录的是不同年代之人求取生命庇护之物的多元形态。房子是一个极具浓缩意味的实体,其包容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落到实处的体系。从原始社会身体的庇护所到现代社会的功能价值的多元转向,房子已经转身化为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和观念及物质形态之间既对抗又不得已投降的折中产物。辗转于房屋权力有无现场的过程就是在现实世俗欲念中实现自我预设价值的过程。一部城乡文化既博弈又融合的历史在“房子”意象中找到了栖身之所。所以,见证者似无所见,却又从最真实的生活流对现代人的精神情感史进行了把脉。作为观察者的江子,深刻洞察了其中的秘密,以不动声色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实际上都掐准了时代人的命门。
《回乡记》是一次对于个体精神缘起的回忆和抚摸,叙事者触碰往昔生活的神经,将原乡社会的变与不变融汇进深层的思考,不可更移的历史图卷鲜活地描绘了赣江以西乡野大地的繁华与衰退、跌宕与起落,也从极具个体化的视角映射了几代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变迁。
《回乡记》更是一次次对于群体生活表象和内在心理的探问和描摹,叙事者摒弃了批判主义者的剑拔弩张,也无意于建造希腊小庙似的抒情殿堂,赣江以西的血肉之躯缠搅着历史的烟雾和泥尘渴望一场大雨清洗之后的畅快诉说。
江子在看,江子在听,江子在思,江子在说。江子的所思所感所悟所言是一叶感情的扁舟,载动着乡愁,回眸遐思,言有尽而意无穷……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彭刚.叙事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英]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M].黄少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4]曹书文.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J].武汉大学学报,2005,(3).
[5][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映理论[M].金元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黄轶.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叙事的伦理基点——以《豹子最后的舞蹈》《这一生太长了》为例[J].当代文坛,2017,(2).
[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熊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