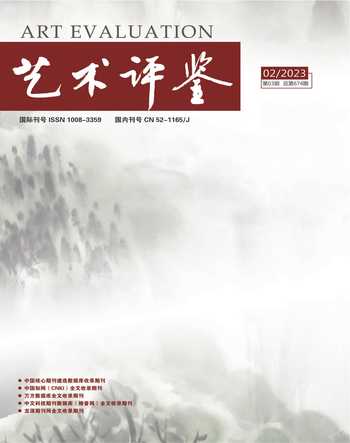现代古筝协奏曲《行者》艺术特点分析
尚瑞芳
摘要:《行者》是魏军先生于2015年创作的一首古筝曲,该曲结合龟兹音乐风格特点与西安鼓乐元素,采用现代作曲技法创编而成。本文重点从该曲的创作背景、音乐本体、新疆音乐元素等几个角度出发,以探寻《行者》的音乐美感。
关键词:《行者》 审美体验 西安鼓乐 龟兹乐
中图分类号:J63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3)03-0165-04
元代杨维桢《鸣筝曲》:“断虹落屏山,斜雁著行安。钉铃双啄木,错落千珠柈。愁龙啼玉海,夜燕语雕阑。只应桓叔夏,重起为君弹。”闻筝声為之动容,可见,筝可以传情,可包容万物,筝与人合二为一,琴附于人,人寄情于筝,古往今来,无不如是。古筝,亦称秦筝,有东方钢琴之美称,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筝这一乐器,筝乐作品更是盈千累万,本文所述《行者》,是众多佳作中的璀璨一星。笔者通过演奏该曲,被曲中的意境美所折服,曲中所展现的龟兹音乐意蕴深长,浓厚的新疆音乐色彩在不同的音程中穿梭,恍若置身龟兹古国,而源自龟兹的西安鼓乐,更是把燕乐典雅清丽的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基于此,笔者对此曲加以分析和探讨,从作曲家生平及音乐的创作背景、音乐本体分析、音乐的艺术特征几方面着手,探寻《行者》中音乐本体与创作个体经验结合的方法。
一、《行者》作曲家简介及创作背景
我国陕西筝派代表人魏军是著名的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陕西秦筝学会创建人之一。魏军先生创作古筝作品颇丰,以陕西音乐风格或元素居多,兼有创编移植外国音乐作品。从所采用的演奏形式分类来看,他的作品有古筝独奏曲《紫竹调》《绣金匾》《牧民新歌》等;古筝重奏曲《晴朗的天空》筝二重奏、《婆罗门引》筝三重奏、《秦调》筝二重奏等;古筝与钢琴协奏曲《五陵吟》《源》《行者》等;古筝与打击乐《大漠行》《碗碗儿》;古筝钢琴打击乐协奏曲《清风·舞月》。
《行者》创作的灵感源于魏军先生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西域古国——龟兹,联系魏军先生往昔改编的一首西安鼓乐《婆罗门引》而作。笔者查阅资料得知,魏军先生运用“行者”一词之义乃同于《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象,不畏艰难险阻,为着唯一的目标,一路西行,矢志不渝。笔者以为其行者之意应是与《婆罗门引》内核相同的四大皆空之行者,也可是古丝绸之路上穿梭来往之行路者,还可喻为魏军先生在筝事业上一路前行、不断创新的追求,实为行者。魏军先生将《行者》赋予生命意义,将生命活力贯穿于音符中,把握时代特点,综合多元创作手法,将遥远古国的音乐写进了现代曲目中,结合魏军先生个人实践,诸如在收集的资料中获得的经验、在学习中获得的经验、在演奏中的经验,乃至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等,将其融入曲中,通过古筝丝丝入扣的音符,传递出了他对龟兹音乐的真实感受。
二、《行者》音乐本体分析
《行者》为E商燕乐七声调式与B羽燕乐七声调式交替而成。采用人工调式定弦依次分别为 B1、E、#F、A、B、c、e、#f、b、c1、#d1、e1、#f1、g1、b1、c2、e2、#f2、a2、b2、e3。从这个定弦可以看出,八度内定弦都不相同,但都包含E、#F、B主干音。作曲家将d1升高小二度,#d1与下方c1形成不协和的增二度,打破传统五声音阶听觉效果,#d1与上方g1形成减四度,增加乐曲紧张感,而这些特殊音程正是龟兹音乐之特点,赋予神秘异域气息。第21弦为B1,此音为全曲最低音,既在琴弦调节松紧合理范围内又与第20弦构成纯五度关系与曲调和谐统一,可见作者设计之巧妙。
《行者》由缩减再现的复三部曲式结构构成,引子部分由15小节构成,b-e1上行四度跳进,#f1-e1下行二度级进,采用重复的发展手法强调了二度与四度关系,确立了主题的两个核心动机,构成了围绕核心音e的上下进行,此二者贯穿全曲,确定乐曲基调。
慢板部分是曲子的首部,共19小节,可划分为A、B两个乐段,呈示段A起于b音,以四分音符节奏为主,运用打破4/4拍节奏强弱关系的方式,突出伴奏音乐稳定的节奏感,创造出行者在丝绸之路上负重前行的音乐形象。序幕逐步拉开,力度由弱到强,音乐听觉上由远及近,第18小节起钢琴伴奏#f3-g3的级进,钢琴高音同古筝低音对比强烈,听觉刺激加大,西域神秘感加强。钢琴伴奏织体柱式和弦与分解和弦交错,音乐由引子部分极强极弱的力度对比渲染出的紧张感转向平静悠远,音乐流畅自然。
中部是《行者》的快板部分,和首部形成展开对比,速度达150,也是对演奏者要求极高的部分。中部篇幅宏大,可分为三个部分,核心音调贯穿其中,使各乐段在结构上相互联系。第一部分C为35~57小节(共23小节),可划分为两个乐段,第35 小节实为起过渡作用的连接句,第一乐段结构为8+3,由右手稳定的八分音符开始逐渐加入十六分音符,节奏紧凑,第44~46小节空拍的加入,划分出乐句中的音群,即突出停顿感,又对音乐起推动作用。第二段结构为8+3,固定节奏型从一而终,每两小节级进上行后级进下行,音乐富于流动性,前后连接紧密。第二部分D为58~111小节(共53小节),其中58~65小节为第一段,整句皆为十六分节奏型,音符密集,点奏弹法下突出小节重音,由主音e开始,在主音e结束。第二段为66~82小节,结构为9+8,此时右手高音部演奏内容充当伴奏部分,左手为实际旋律部分,其主题材料由第18小节变化而来,钢琴伴奏主要在每小节强拍或次强拍烘托,主要起支撑作用,第72小节3/4的插入因节拍强弱位置变化使旋律律动改变。第三段83~93小节,双核动机在此处贯穿,第87小节与第二段中74、80、81小节呼应。此句中钢琴声部采用三连音弱化节奏重音,取消小节间的独立性,使整体乐句更为融合,紧密联系,分解和弦快速律动也是西方音乐伴奏织体常用模式,此处中西结合,相得益彰。第四段是第94~111小节,再现第一句,变化重复其内容,在B羽音中结束。第三部分E为112~161小节(共49小节),可划分为三乐段,速度上可看成慢快慢三个部分。第一乐段112~123小节,此为抒情段落,古筝声部以右手摇指为主,歌唱性的长音,似有凄凉萧条之感。第二乐段124~139小节,此处由中部第一部分第二乐段变化展开,采用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型,音符密集,快速指序为此中技法,既要连贯又要强弱分明,重音突出。第三段140~161小节,该乐段相较于其余两段篇幅较长,结构上可划分为7+15两句,主题材料来源于慢板部分,前后呼应,左手和弦突出节奏稳定性,连接到第二句,以扫摇技法开始,用相同音符、相同节奏变换声部,做出对比,同时伴有钢琴声部八分音符节奏柱式和弦伴奏织体推动乐曲达至高潮。
再现部为慢板,缩减再现首部音乐素材,由三度关系e1-c1引入,泛音奏法使乐曲由极致热烈回归于平静神秘之中,这与《婆罗门引》呈示方式相同,两曲在此契合。高八度再现第一句,使之与前后两音区相适应,前后衔接更为合理,听感更为舒适,亦保持了声部上的连贯性。减四度与增二度音程再次体现主题核心动机,音乐在微弱的刮奏中结束,宽广幽深之感油然而生,龟兹古国神秘的面纱渐渐远去,留给听众的是对西域古国人文、民俗的无尽遐想。
三、《行者》的元素化与节奏性特征
(一)西安鼓乐《婆罗门引》的音乐元素与龟兹音乐特点的运用
魏军先生用多种音乐发展手法汲取西安鼓乐《婆罗门引》的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具有西安鼓乐音乐风格的古筝曲《行者》。《婆罗门引》其曲调来源与西域有关,据宋《高僧传》中记载:“龟兹境内有一处地方(千泪泉),其水滴溜成音可爱,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已成曲调”。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成了音乐家创作的重要源泉,山间流泉滴水成音,在微风相伴下,龟兹音乐家灵感突发,日后被敬献给唐玄宗的那首《婆罗门曲》应运而生。天宝十三载,唐明皇修订乐韵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松仁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论述《霓裳羽衣曲》的来历:“余观唐人西域记云,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之声均节成音,后番入中国,皆自龟兹至也,则知霓裳亦来自西域云。”由此可知,西安鼓乐《婆罗门曲》源于西域古国龟兹。
魏军先生所作《行者》与《婆罗门引》皆为D宫系统调中E商调式,两首作品,围绕E音形成上下小跳与大跳结合的旋律走向,且主干音皆有B、G两音,如《婆罗门引》中第一乐句1~8小节,B音常常出现在小节重拍上,且G音围绕B音三度跳进,乐句结束时Ⅰ声部落在E音上与Ⅱ声部G音形成三度和聲。《行者》中引子部分第9~10小节,六连音由E、G、#F、C、B五音组成,E作为起始音,占据主要地位,B为尾音,G音过渡,以此形成了六连音的四拍反复,E音在第10小节节拍重音上,且以E、B两音构成的五度和声作为小节收尾。《婆罗门引》中的泛音技法也在《行者》中有所运用,如《婆罗门引》中第83~96小节,此处音乐整体音量小,呈收缩趋势,与此前以摇指与刮奏技法为主的乐句小高潮形成鲜明对比,且主旋律在Ⅰ、Ⅱ声部中交替,泛音技法声部一拍一音,使乐曲呈现一种稳定且幽然之意。《行者》再现部中第162小节,由E音与C音构成的旋律,以泛音技法演奏,既承接上句结尾的E音,乐曲由快板进入慢板,又引起了以每分40拍为速度的再现部主题旋律,音乐情绪由激烈喧闹转为幽远宽广,听觉感受得到极大满足,似是浊浪滔天回归于水波不兴,似激烈的厮杀结束后的宁静,但这种平静是一种开阔,是回归自然的脱俗体验。
丝绸之路上繁复的音乐对中原音乐影响甚广,其中包括龟兹乐。经笔者查阅资料知,龟兹乐起源有“印度说”“中原说”“综合说”三类,支持“综合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即龟兹乐以本土音乐文化底蕴为基础,广泛吸收西方音乐文化,较为显著的就是天竺佛教音乐,与波斯音乐、希腊音乐融合,加之中原音乐影响,于历史中积淀而成,是融合且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筝曲《行者》中定弦与普通的D调定弦不同,#d1音的加入,使得原本的燕乐加入了西域音乐色彩,如慢板中第23小节出现的#d1与c构成的增二度,该音程的不协和性让音乐萌生出不稳定色彩,增加了音乐的神秘感。慢板伊始,B1音起,接纯五度音B-#f,用切分节奏以慢而和谐的基调带出主题旋律,伴奏声部模拟了龟兹鼓乐,这是作曲家创作技法的精妙之处,首先此处呈示了慢板的主题旋律,以长音为主,叙述性的线性旋律将音乐拓宽,而左手鼓点般的切分节奏,在长音中更容易凸显出来,而这种高低声部的搭配方式,也是新疆音乐极具特色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这正是作曲家将民族音乐元素置于现代曲目中,完美地将其呈现的具体体现。
(二)特性节奏
筝曲《行者》中,第14小节第4拍后半拍三连音应属慢板部分,弱起连接伴奏声部,此三连音起承上启下的作用。16~24小节伴奏声部切分节奏,改变了4/4拍节奏强弱关系,此节奏型为龟兹音乐常用节奏。休止符的使用也大大增添了音乐的节奏特点,快板部分44~46小节,次强拍休止符,增加了乐句的停顿感,也为音乐的层层递进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快板部分伴奏声部以带附点节奏和切分节奏感与空拍结合形成的节奏型规律性重复为主,而旋律声部以改变重音位置来体现此节奏型,此节奏型是新疆音乐最显著的节奏特征,具有跳跃的舞蹈性,富有动感,众所周知,新疆是个人人能歌善舞、人杰地灵的地方,曲中的鼓点节奏,正是当地人民跳舞时的伴奏节拍,如此,将快板欢快热烈的音乐氛围发挥到了极致。这体现的是作曲家对于新疆音乐的了解、把握和精确运用,融合地方特色民族音乐文化的特点,也是充满人文情怀的艺术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的实际表现。
四、《行者》审美经验的意义阐释
古丝绸之路联通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多元文化间的融合,音乐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地衍变,龟兹古乐在这条路上发展创新,无数的音乐人都是这条路上的践行者,筝曲《行者》所传递的精神内核,以及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吸引无数听众的动因,也切实让演奏者能够深刻感受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刻内涵,身临其境地体会西域音乐的真实所在。
语言中的表情音调往往能决定语言的总体含义,其通常通过高低、大小、粗柔等音调变化来体现。筝曲《行者》中所具有的非语义性(表情性),就通过音调变化来体现。引子部分开篇的厚重低音,将听众拉入一个神秘之境中,如在迷雾中寻找方向,充满探索的意味,随着音乐演奏力度加大,音乐情绪递进,紧张的氛围逐渐蔓延,音乐在同音反复中探寻路径,旋律经由中音区转向低音区,散板在结尾有了稳定感与停顿感。音乐由三连音带入慢板中,开启了古丝绸之路,旅人与骆驼在夕阳下行走在沙漠中,他们步履维艰,在漫长旅程中相伴相依,乐曲旋律声部于高音区级进与跳进结合渲染环境的恶劣,摇指长音似是在其中吟唱。当声音作为艺术的媒介时,音乐就成为了感性材料,在创造性的基础上,蕴含在模仿、象征、暗示和表现手段之中。快板部分整体以热烈的情绪展开,快速指序所呈现的紧凑密集的音符也为西域富有动感的音乐锦上添花。作者的巧思就体现在这种民族气息与现代意识的结合之中,其中的增二度音程是龟兹音乐的具体体现,同时在气势庞大的钢琴伴奏依托之下,其运用点奏技法,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热烈,更值得称赞的是,古筝左右手旋律的相符性和左手旋律的鼓点节奏处理上,可谓是匠心独具。快板动中有静,长音空灵飘来,似是述说,这无不证明了音乐是人类感情的语言表达。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列宁反映论为指导思想,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某种形式的反映,筝曲《行者》快板所体现的龟兹古国的音乐文化,是龟兹繁盛时期的缩影,通过作曲家心理体验的形式反映音乐,是音乐本体与主体经验的结合,通过主观能动创造,把现实生活中的美,特别是其思想感情加以集中、提炼和升华,并运用富于独创性的音乐艺术形式加以体现。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主体在感情体验的同时,还会沿着非音乐元素所指的方向做定向联想,使音乐中概括性的内容具体化,从而感受到某种特定性的社会价值,音乐中非音乐元素有两类,包括限定性的如歌词、标题等文学内容,另一类是广义的社会内容,如作品产生的时代特点、社会思潮等。魏军先生以《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象来喻《行者》,孙行者在大众思维中,是敢于直面困境,不怕艰难险阻的艺术形象,而此正是《行者》所表达的精神内核。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运动,不能像语言艺术那样为人们提供某种观念或叙述某一事件的动作过程,而是以单纯的表达方式,去表现人的主体感情。《行者》所唤起的文化认同感,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听众,也激励着创作者不断探索,其所有的音乐内涵为多元的文化增添了无穷无尽的色彩。
五、结语
古筝协奏曲《行者》是作曲家将新疆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其综合自身体验,将音乐形式及东西方元素有序组合,是音乐本体与自身经验的有机统一,也是对新疆音乐文化的傳承、创新与发展,是文化融合的集中体现。作曲家立足于民族音乐创作语境,综合听觉审美体验,为听众展开的是一幅锦绣山河的大美古筝曲,曲中包含的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将自身的内在经验融入音乐本体中,音乐不再是单纯的音乐,是生活化的,是富有生命力的,是饱含了民族特点与民族文化内涵的。作曲家为广大的作曲人提供了“西为中用”的创作范式。首先,音乐所具有的音强、音高、速度、调式,这是无数音乐人逐步学习探索而来的音乐基本要素,作曲家将其进行了巧妙地结合,音乐既可以赋予流畅歌唱般的旋律美感,又可以具有舞动鼓点的节奏动感,这是在这首古筝曲中呈现出的鲜明民族特点。其次,乐曲中西方曲式结构的音乐框架搭建,结合中国传统燕乐调式,为奠定乐曲庄严典雅的音乐基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结合,使整首乐曲逻辑结构分明,层次清晰。音乐强弱、快慢的对比,引起听众的心理期待,亦是引起听觉注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音乐心理学的理论,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个体通过听觉感受产生联觉的审美过程。综上可知,《行者》一曲,不是一首普普通通的古筝作品,而是作曲家呕心沥血所作的民族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技术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部彰显了西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又各自绽放的现代古筝曲目。它代表的是文化的多元发展,更是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张佳怡.筝曲《行者》的艺术特色及其演奏技法探析[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1年.
[2]袁静芳.西安鼓乐“大乐”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01):79-97.
[3]褚历.西安鼓乐的曲目积累与发展创新[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9(02):30-37.
[4]薛莲.鼓乐新弹——筝曲《行者》的音乐本体分析[J].音乐创作,2018(01):129-130.
[5]孙振民.丝绸之路与龟兹乐的形成和传播[J].音乐探索,2019(04):36-40.
[6]田蕾.古筝协奏曲《行者》的音乐特征与演奏技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22年.
[7]刘子懿.古筝曲《行者》的艺术风格与演奏探析[D].成都:四川音乐学院,2022年.
[8]陆媛媛,杨连莲.筝曲《行者》的音乐特色分析[J].当代音乐,2022(07):100-102.
[9]金家玉.现代筝曲《行者》的音乐特性与演奏初探[J].黄河之声,2021(04):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