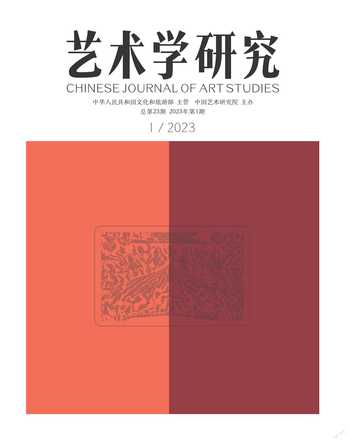近世相声唱片的学术面向与研究价值
赵奇恩



【摘 要】 民国时期,唱片与留声机传入中国,作为记录声音的重要载体,这种复制、传播曲艺的新技术很快得到国人的认可和接纳,原生于市井街头的撂地伎艺在当时盛兴的信息与科技技术的引领下,于都市传媒中抢占了一席之地。《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对此时期的相声老唱片进行了发掘整理,对相声艺术的推介和拉动功不可没,但囿于外界因素,其仅仅是将音响与文本作简要辑录,并未进一步剖析。基于此,对《大考》所辑相声史料作系统汇考彰显出重要意义:对有声资料逐一作个案研讨,考述每段曲目的学术价值,大致勾勒出晚清、民国期间相声发展的基本样貌,进而深入思考如何处理科技与原生态、雅与俗以及对“笑”的本质之理性审视等问题。
【关键词】 民国相声;相声老唱片;传统相声;《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
清末之际曲艺蔚然盛行,相声名家之声、像、表因碍于当时科技条件所限,随时间流逝而湮没失传。民国初年,唱片与留声机等舶来品传入中国,这一复制、传播曲艺的新技术很快得到国人的认可与接纳,成为记录声音的重要载体,大部分传统相声的音响资料都以唱片形式留存至今。然而我国对相声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之对唱片保护不善,散佚现象时有发生。2019年,由蒋卯卯、张博、佀童强等人共同整理的《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以下简称“《大考》”)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大考》收录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音频936面,唱片唱词文本54万字,涉及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西河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时调、荡调、单琴大鼓、莲花落等北方流行及濒临失传的曲种24项;其中,相声录音共计122段,出演艺人28位,时间跨度从1909至1949年,涵盖百代、高亭、胜利、宝塔、丽歌、国乐等多家唱片公司各时期灌制的珍贵音响,极大地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和对史料的搜索范围。
此次有声史料付梓出版,虽名为“大考”,希冀将北方曲艺唱片音响悉数囊括,并加以考察鉴证,以期唤起相关人士重视,重见于知音;实则囿于外力因素,《大考》仅仅将音响与文本做了简要辑录,并未进一步剖析,亦非出于学术研究之目的,因而略显缺憾。本文将对《大考》中所存相声史料逐一作个案研讨,系统考述每段曲目的学术面向,并由此深入到晚清、民国期间相声发展的基本样貌。
一、有声史料的摸排:相声唱片遗响汇考
兹将《大考》所存相声唱片之音响按年份做如下汇考,并对其个别目录、条目重新加以修正:
(一)发轫期:20世纪前10年
李德钖(万人迷)、张德泉(张麻子):张、李二人同为恩绪之徒[1],第4代相声艺人,列于“相声八德”[2]之内。1909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发卖对联》《灯谜隐语》《巧对春联》《唼封钱粮》,这是相声史上最早发行的音响资料,但因录制时长所限,作品均除去“垫话”[3]部分,直接“入活”[4]。《发卖对联》《灯谜隐语》《巧对春联》属文字谜语类作品,其中《灯谜隐语》的“底”[5]采用互唱方式一问一答,4句谜语半说半唱,无器乐伴奏,但具节拍,腔调也大致相仿,疑为“老调”太平歌词,属早期伎艺中的“柳儿”(指唱);《唼封钱粮》,又名《交地租》,是传统“倒口活”,又称“怯口”,指摹仿各地方言土语的作品,现同音改字,统以“怯”字开头命名。
(二)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前后
1.谢芮芝、高玉峰:二人均为李德钖“代拉师弟”,同属第4代相声艺人,早期“清门”[6]流派代表人物。1925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洋药方》《八扇屏》《新名词》《菜单子》,上述作品均为“贯口活”[7]。其中《洋药方》用“念白字”作“垫话”“入活”;《八扇屏》用“歪批《大学》”作“垫话”“入活”,“正活”[8]背诵“小孩子”“趟子”[9]一段,其后选取《洋药方》“沒症”“趟子”作结;《新名词》整体构架为“垫话”《暗八扇》,“入活”《西江月》;《菜单子》又名《报菜名》,其“趟子”背至“豆腐丸子”为止。
2.王昆山(人人笑):未见此人被列入相声谱系,1928年胜利公司为他灌制唱片《百鸟语》《百兽声》,《大考》将其收录在口技项。据《中国曲艺志·天津卷》载:“擅学鸟兽鸣叫的人人笑,就将暗相声中的口技改以明场演出,成为以学为主的单口相声。”[10]张寿臣在《早期的相声》一文中提到,“光学鸟叫并不能占用很多时间,挣不了多少钱,所以一般演员就在表演口技之前,说段笑话逗哏凑乐儿,有时也把口技和笑话掺在一起表演”[11]。口技是相声成型之初最重要的伎艺手段,“明地”相声出现之前,就有将口技与笑话结合在帐内表演的“暗相声”,内容从摹仿鸟兽百音扩展到描摹社会百态,体现在“学”字方面,据此可将上述曲目重新划归至相声项。
3.大饭桶、傻小子:未见二人列于相声谱系,1928年由胜利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王二姐思夫》《客心鬼雇活》《大饭桶开心》《绕口令》《说落梦》《说三桶》以及《英法小调》,《大考》将上述作品统归到相声项,但《大考》中的附录手册却将其定名为滑稽项。其中,《王二姐思夫》大体是学唱蹦蹦戏;《客心鬼雇活》似二人转“小帽”;《大饭桶开心》在每句唱词之间均有唢呐牌子过板,内容与竹板书《十道黑》相仿。《说落梦》《说三桶》《英法小调》则为对口语言类节目,《说落梦》《说三桶》与传统相声《梦中婚》《讲帝号》结构相仿;《英法小调》“垫话”情节与传统相声《树没叶儿》《羊上树》相似。
4.吉坪三、王兆麟:吉坪三师承冯昆志,是第4代相声艺人;王兆麟师承裕德隆,是第5代相声艺人。1929年由胜利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对对子》《绕口令》(一、二)以及太平歌词5段。太平歌词5段包括王兆麟《劝人方》《黑大姐·小上寿》《韩信算卦》(一、二)与吉坪三《百家姓》,其中只《百家姓》为清唱,其他曲目艺人均手持“玉子”伴奏数唱。唱词字字上韵,“第一组唱词的上句限定全篇辙韵,下句随即开始押韵,此后的每组唱词,上句落音较自由,下句落于固定辙韵”[1],可将其视为“新调”太平歌词。
(三)成熟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
1.焦德海、刘德智:焦德海师承徐有禄,刘德智为卢德俊代拉师弟,与焦为一师之徒,二人均为第4代相声艺人,同属“相声八德”之列。1932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切相面》《大杂烩》(一、二)。《切相面》为“倒口活”,今写作《怯相面》;《大杂烩》(一、二)为对口拆唱太平歌词,首段焦德海言明要数唱《排王赞》,实际所唱曲段属人物乱入式的“歪唱”[2],与今《排王赞》唱本迥异,第2段内容与太平歌词《世态炎凉》(又名《颠倒颠》)唱本相同[3];同年,由高亭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洋药方治病》(一、二)、《歪讲〈三字经〉》(一、二)以及《学绕口令》(一、二)。《洋药方治病》内容结构完整,“垫话”今被传统相声《学英语》借鉴,其后贯口分别为“不症”“没症”“子症”“杂症”4项;《学绕口令》首段选取《俏皮话》作为“垫话”“入活”。
2.张寿臣、陶湘如:张寿臣师从焦德海,为第5代艺人“门长”,天津“五档相声”[4]代表人物;陶湘如师从裕德隆,是第5代相声艺人。1932年由高亭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开粥厂(乐善好施)》(一、二)、《寿比南山》(一、二);同年由胜利公司为二人灌制《地理图》(一、二)、《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以及《卖春联》(一、二)。二人所录作品共包含两段“贯口活”、两段“文哏”[5]和一段“念喜歌”,内容紧凑完整,是20世纪30年代“文明相声”的杰出代表,与今舞台演出本承接紧密,更是相声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3.于俊波、郭启儒:于俊波为张寿臣“代拉师弟”,是天津“五档相声”的代表人物;郭启儒师从刘德智,二人均属第5代相声艺人。1933年百代公司为他们灌制《俏皮话》,内容用屎壳郎、“王八”插科打诨,有大量“暗臭包袱儿”[6]出现,反映出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情绪,其俚俗言语迎合了不同阶层的娱乐需求。
4.华子元:又名华德茂,为恩绪弟子,属第4代相声艺人,1935年由百代公司为其灌制唱片《戏迷传》《戏迷闹学》。《戏迷传》前半部分摹仿北京话、上海话,后侯宝林遵此路数,将其扩充改编成《戏剧与方言》;后半部分摹仿卖估衣,与今传统相声《卖估衣》相同。《戏迷闹学》则通过口腔发声摹仿胡琴的过门、散板,最后以“银纽丝”做结。上述作品虽以“戏迷”定名,却未曾在其中学唱京剧。
5.张志成(张君)、沈观澜(沈君):张志成未被列入相声谱系;沈观澜则拜师张寿臣,为第6代相声艺人。《大考》附录手册记有:“张君,本名张志成……曾拜师刘万奎、郭荣山、韩永先。沈君,本名沈观澜……拜师张寿臣……”[1]。据《中国曲艺志·天津卷》载,郭荣山、韩永先本是拆唱八角鼓、双簧艺人,曾收徒沈观澜、张志成;又载:“(刘万奎)相声并没有拜过师,因此相声界不承认他,他的相声弟子后大多另拜师。”[2]1935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口技》《学梆子》,《大考》将张、沈之作归入口技项,但因沈观澜师承相声门户,加之二人所演口技与“暗相声”关联紧密,其中《學梆子》也非口技,而属“柳活”[3],是传统相声《山东二黄》的雏形,故此,将二作重新纳入相声项。
6.陈子贞、广阔泉:二人的师承据《清门后人—相声名家陈涌泉艺术自传》记述,1921年李德钖在上海演出期间,提议代拉陈子贞、广阔泉为师弟[4],因此可把二人列为第5代相声艺人,同时二人也是“清门”代表人物。1936年胜利公司为他们灌制《粥挑子》(一、二)、《说俏皮话》(一、二)、《抬寡妇》(一、二)。《粥挑子》又名《买面茶》;《说俏皮话》继承了于俊波、郭启儒《俏皮话》中粗鄙的语言,未见改进;《抬寡妇》又名《牛头轿》,充斥着伦理哏以及乱伦等低俗内容,可见当时艺人尚不能将快感与美感区分开,打磨作品,提升内涵,实现艺术上质的飞跃仍需时日。
7.张浩然(掐脖张或捏脖张):未见此人录于相声谱系,评书门师承高桐明。1938年丽歌公司为他灌制《戏迷相声》(一、二、三、四)。《戏迷相声》是由效仿京剧名家唱段串联而成的滑稽故事,其中包括仿学马连良之《乌龙院》,余叔岩之《定军山》《打棍出箱》,王又宸之《宝莲灯》《哭灵牌》,以及知名戏目唱段《珠帘寨》《桑园寄子》等,是早期真正学唱京剧的代表作品。
8.吉坪三:1938年由丽歌公司为其灌制唱片《戏迷传》(一、二)、《打游(油)歌》、《傻子转文》、《学京话》、《一个字的笑话》以及《姐夫戏小姨》。《戏迷传》中的“包子铺”“馄饨摊”两段情节,在侯宝林创作的传统相声《卖包子》中被改编为周信芳卖包子和金少山卖馄饨;“卖油炸鬼”之情节在侯宝林的《改行》中被改编为刘宝全卖早点。《打油歌》今名《打油诗》《吃饺子》,今存马三立、郭全宝、刘宝瑞、郭荣起等人的录音。
9.常连安、常宝堃(小蘑菇)、常宝霖(二蘑菇):常连安,是焦德海之徒,属第5代相声艺人;常宝堃,是张寿臣之徒,天津“五档相声”的代表人物,属第6代相声艺人;常宝霖,是侯一尘之徒,属第6代相声艺人。1935年高亭公司灌制了常宝堃、常连安合说的《大上寿》(一、二)。1936年百代公司灌制了二人合说的《摆卦摊》(一、二)、《书迷闹洞房》(一、二)、《学四省话》(一、二)、《卖估衣》(一、二)、《女招待》(一、二)以及《闹公堂》(一、二、三、四);同年,胜利唱片灌制了常宝霖、常宝堃、常连安合说的群口相声《报菜名》(一、二)、《小孩语》(一、二)。1939年国乐公司灌制了常宝堃、常连安合说的《数来宝》。其中,《书迷闹洞房》中的“垫话”,今多用于《学评书》;《女招待》头段“垫话”又名《山东儿跑堂》;《报菜名》首次将对口改为群口,音频中常连安话语极少,似乎是为提携幼子特地上场帮腔助演;《小孩语》实为传统群口相声《抢三本》;《数来宝》今衍化出《三节拜花巷》《对坐数来宝》《五数同仁堂》《点头数》等曲目。
10.汤金澄(汤瞎子)、田瘸子:汤金澄师从焦德海,属第5代相声艺人;田瘸子真名不详,未见被收入相声谱系。据《天桥一览》载:“(田瘸子)以耍杠子享名,幼时学过武艺”[1],似非同一人。1939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绝门口技》(一、二),该作品已非单纯口技,而是笑料与口技相结合的对口相声。《江湖行当》提到,“唯有田瘸子、汤瞎子说的相声……大概是无师自通,自己研究的,或是拆改人家有活儿。尤其是汤瞎子,能够坐在场内学飞禽走兽叫唤,学磨剪子磨刀的吹喇叭、消防队的警笛、斗蛐蛐,样样仿真”[2]。
(四)多元期:20世纪40年代前后
1.吉文贞(荷花女):吉坪三之女,自幼随父学艺,英年早逝,未见录于相声谱系,是唱片中收录的唯一女相声艺人。1942年由胜利公司为其灌制太平歌词《饽饽阵》(一、二)。
2.常宝堃、赵佩如:赵佩如师从焦寿海,天津“五档相声”的代表人物,属第6代相声艺人。1942年由胜利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嘉禾钱粮》(一、二)、《父子词》(一、二),《嘉禾钱粮》实系传统相声《交地租》。同年,由百代公司为二人灌制唱片《龙凤呈祥》、《改良数来宝》(一、二),《龙凤呈祥》系传统相声《牛头轿》;《改良数来宝》首段持快板伴奏,数唱时事。同年,由胜利唱片灌制常宝堃、赵佩如、吉文贞合说的群口相声《训徒》(一、二)、《七仙过海》(一、二)。《训徒》为传统相声“文武训徒”中的《文训徒》;《七仙过海》则由传统相声《切糕架子》和《找五子》拼凑而成。1943年,百乐公司为常宝堃、吉文贞、赵佩如、常连安灌制小戏《打面缸》,《大考》将《打面缸》归入相声项,但《大考》的附录手册则将其列入小戏项。
汇总上述信息可知,20世纪30年代,灌制唱片之风盛行;40年代初有女性艺人崭露头角,艺人跨界反串小戏的苗头初现。囿于昆仑、哥伦比亚、百乐等公司的唱片音源音质不佳,部分曲目又含有浓重的政治意味与情色描写,故未悉数收录,仅将存目、文本附录于《大考》手册后,供方家参考[3]。
二、卑从的艺术:
基于相声存世录音的思辨
唱片作为一种新兴史料,具有形式新颖、高度真实等特点,无疑是解读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也是一种非文字的精神遗产。《大考》为我们理解和认识相声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当时相声录音中的诸种特征,并对此阶段相声艺术的历史样貌有所揭示。
(一)过滤与时长:对蓄音的严苛要求
20世纪初,胜利、百代等西方唱片公司纷纷来华录音,主动开拓中国市场,相声也在唱片业的推动下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些许缺陷,值得重视的是蓄音时长问题。《上海老唱片》中提到,“一张每分钟78转的配用钢针的唱片,正反两面,一面可以承载总共不到4分钟(多为3分钟左右)的录音。这种形式的唱片从20世纪初始,在中国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为密纹慢转唱片取代”[1]。因此,早期录音设备对唱片时长与灌音过程都提出严苛要求,以至于大多数音响资料只能削足适履,时长均维持在3分钟左右,艺人在蓄音前往往要经过反复斟酌甚至大幅删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变相消解乃至局部异化了相声艺术。类似《对对子》《俏皮话》等易于调控的作品重复录制率较高,虽为后世留下多种可供比对的版本,但究其根源,是蓄音容量的精短导致大量传统作品不宜录制。譬如高玉峰、谢芮芝的《八扇屏》就因“垫话”占据时间较多,后半段只能择取篇幅较短的“小孩子”“贯口”,临近尾声处又不够再背诵一段完整“趟子”,只好转录《洋药方》一段做结,这便破坏了整部作品的逻辑结构。更有甚者,或掐头或去尾,不乏有节本、选本出现,与舞台演出足本相比颇有差异,甚至不能判定该作品究竟为雏形还是选段。又如高玉峰、谢芮芝灌制的单面唱片《菜单子》,“贯口”至“丸子”处便戛然而止;而常宝霖、常宝堃、常连安合说的《报菜名》采用双面录制,说到“板鸭、筒子鸡”则结束,已与今《报菜名》通行本接近。由此观之,在辨析与审定唱片版本时,需格外注意对当时许多“权宜之计”的处理问题。从音响资料录制数量看,常宝堃参与录制的唱片共有25张,占艺人录制总量的半数以上,为保证节目完整性,常氏父子多将一段作品灌制成双面唱片,像《闹公堂》更是灌制成两张4面唱片,这些在信息记录和保存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不可估量。
可见,相声艺术与唱片技术的初步“联姻”,改变着原始创演的固有规律,当下性与随意性的抓哏砸挂、艺人与观众间的临场互动,囿于时长容量和官方的审核而被排拒在蓄音之外。面对公众的撂地相声一旦进入录音间或整合成唱片,在便利传播的同时也势必减少了说表的现场感,艺人的口音、语调、身段、表情、现场氛围等经剪辑修饰后,显得尴尬且拘谨,单调且呆板。表象上是对原本生发于民间的艺术的提升,实际上经由机械转化、过滤后的街头艺术已然缺少了真实的味道,二者仍需一个双向调适的过程。
(二)抉择与态度:俗与雅的扭结
原生于街头市井的撂地伎艺,在当时盛行的信息、科技引领下,于都市传媒中抢占了一席之地,一些进步艺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相声打造成知识性与趣味性合一的艺术产品,以迎合上层民众市场,毕竟民国初年,较为殷实的家庭才置有留声机。1925年的《申报》记述道:
近年以来,中国留声机业,颇称发达。中产之士,几于家置一具。考其原因,大半系以京剧又至复盛时代,故嗜者日多;更有一部分欧化士女,以娴于舞蹈西乐为时髦者,亦不得不购办外国唱片以资练习。是以勿论中西唱片,現均销行甚广。[2]
就当时相声的生存状况而言,能兼顾不同演出场所、不同演出形式、不同传统载体才是相对科学合理的。在当时社会城乡差别、贫富悬殊、阶级差异明显的现实环境下,能够广为传播并始终保有活力的草根艺术,必然需要依赖新奇式样、多元内容来吸引和满足民众的口味。唱片中既有文学素养较高、以文字游戏立意的《对春联》《小孩语》等作品;又有突出技巧、卖弄唇舌的《地理图》《菜单子》等节目。另外,相声艺术在顺应科技时代发展、迎合审美趣味变化的同时,也固守着传统和过去,未能完全脱离乡土生活的一些陋习,如《俏皮话》《牛头轿》等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裁度,是颇具低俗气息和市侩味道的“荤口”相声。这些作品原产于民间,未经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也未受到主流意识的疏导与规范,却代表着一个时代广大群众的审美水平,反映出近代社会的民生,构成了民间文化记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研究这类“荤口”相声时,要基于一种更符合民众人性归宿和生存需要的心态。
相声登堂入室后,所面向的人群层次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对艺者创编作品的机趣与格调提出更高要求。原属街头的撂地者在从业之前不要说读书接受正规、儒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只是记问之学,为谋求生存时常放弃艺术提炼与思想开掘而刻意媚俗讨好、流于肤浅。然而艺人们对自身谋生的手段和对艺术的态度,却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自我审视,并有意愿摆脱现有的自在状态,向着艺术的审美境界迈进。检索唱片不难发现,早期作品中常用“别挨骂了”作为节目的结束语,联想到《论捧逗》中的台词,逗哏曾对捧哏的话语做出戏谑性总结—无非“唉、呀、这、是、额、嚯、嘿、呦、别挨骂了”之类的套话,由此一来,只好将“别挨骂了”作为相声的程式化表演简而括之。事实上,语言的表达常带有暗示性和情感流露,相声语言无时无刻不存在或隐或显的自贬,在张寿臣看来,“挺大的人说难听的话,把人逗乐了自己也寒碜”[1]。艺人表演时,常常在人物与讲演者间跳进跳出,不免将一些低俗内容编织成笑料抛向观众,丑角式的演绎确实有损自身在公众中的形象,只好以自嘲的方式疏解心理压力。久而久之,相声也就自甘于穷于途的撂地“玩艺儿”,将“伺候人”的下贱属性内化为对自我卑贱的认同,并最终在约定俗成的滑稽言行中表露出来。因此,如何看待近代相声格调的升华与沉沦,以及如何处理草根与精英、大俗与大雅的扭结关系,一直是民间艺术自觉传承中值得观照与思考的文化现象。
(三)笑感和伎艺:传承下的变与不变
谈到相声的表现手法,听者首先会将“逗”字置于首位,认为如果整场演出不能引发观众接连的笑声,甚至酣畅淋漓的大笑,那便是失败的。反观老唱片中的相声,内容过于陈腐,不再契合当下致笑的触点,跟不上受众求新、求变、求异的审美观念;甚至每当听到这些老段子时,现代听众会产生审美疲劳,笑感丧失,有昏昏欲睡之感。凡此种种,并不能说明传统相声已经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传统”本身也不是导致现代听众喟然慨叹、失望不满的根本原因。
表面上看,相声是笑的艺术,这种认识并没有错,若将“笑”与“逗”一再强化乃至夸大滥用,进而成为裁定曲种优劣的标尺,势必会把艺术审美引入极大的观赏误区,最终使相声艺术沦为忸怩搞怪的娱人戏弄。归根结底,这对相声实现自身艺术价值—“笑”,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对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运作程式未能进行足够的研究与起码的掌握。殊不知,老唱片中的相声虽历经岁月蹉跎已达不到欣赏者内心的审美预期,但那些彻底失掉光泽的话语曾经也是那么新鲜和炽热。因此,要实现艺术表现与欣赏接受的审美对接,告别种种审美错位,感受真正地道、典范的相声,需要把握相声传承的特殊性。伎艺才是其百年不衰的关键所在,改变的是逗笑的内容,不变的是传续的伎艺,是历代艺人为总结艺术、课徒授艺而概括出的实践成果,是每名艺人都需要掌握的繁复的基本功课,而上述所有艺术手段都在为审美创造的“逗”服务。纵观唱片文献,即便在规定时长下,艺人还是能够有效地将说、学、逗、唱各门功课一一进行展示,通过对筋节儿、劲头儿、尺寸的拿捏制造出“笑”的效果。
一直以来,泛娱乐化影响着受众的审美态度,对相声的内核、对笑的本质缺乏理性审视,仅停留在经验主义的感性阶段,这导致受众在潜移默化间沿着这一方向去感知艺术,形成审美框范,曲解了相声艺人对每门功课的传统表述。反思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取舍,挖掘技巧的深层规律,将正确的艺术评判导向引入对伎艺的观察中,才能对唱片有声史料给予客观、中肯的评价,避免相声艺术走向“娱乐至死”的迷途,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余论:极简与有声的相声别史
唱片未引入中国之前,相声主要的演出途径仍以“明地”[1]作艺为主,而艺人想要拥有一块固定且不受滋扰的场地实非易事,“露天拉场、打走马穴,不靠长地”是为常态。随着曲艺在近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声逐渐步入剧场,拥有了专属的演艺空间,然而实时演出具有不可复制性,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仍是亟须协调解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前后,《相声一集》《笑海》等介绍相声的启蒙读物刚刚问世,绝大多数文人墨客不屑于创编和阅读相声文本,底层民众文化水平又普遍偏低,即便能够识读,也难以理解语句的臻妙,平面传播无法复刻声响,给相声的普及带来极大障碍,毕竟以语言为重心的相声艺术在聆听上的感觉至关重要。直到唱片、留声机的介入才彻底突破了时空限制,听众可以依照个人意愿随意重复,反复聆听,媒介技术改变着人们对声音的接受方式,艺人在录音传媒所能带来的名利驱动下,顺应时代潮流,与唱片公司一拍即合,适时调整传统、单一的演出模式。尽管灌制唱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禁锢了艺人发挥的弹性时间与言语上的即兴碰撞,以往“明地”上的演出习惯和表现方式被相应打破,甚至还要受到当局话语霸权的管控,但录音对相声的深远影响,功劳远远大于弊端。现如今,相声研究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曲艺理论已取得丰硕成果。《大考》有声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对相声艺术的推介和拉动功不可没。它以声音为切入角度,突破以往只对档案文献、口述轶闻进行收录整理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曲艺研究的不足;利用声音直观地审视民国期间相声伎艺的变迁,为曲艺演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史料;成为相声在这一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真实佐证,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时期传统作品的表演特征与伎艺技法,是一部极简的有声相声史。
《大考》搜集的有声资料抓住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色和现代传播媒介对传统相声文化的塑形,清晰反映出民国时期相声的发展走向,把诸多因素统统纳入考察范畴,收录了极多具有行当代表性的前輩艺人及其作品。其中收录了20世纪20至30年代活跃于北京最负盛名的“相声八德”中的4位人物—李德钖、张德泉、焦德海、刘德智,如今绝大部分传统作品均出自这代艺人的整理和创作,他们使相声从伎艺发端走向关注社会生活,是肩负起承上启下重任的桥梁式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天津地区的相声名家,被世人称为“五档相声”中的4位代表人物—张寿臣、常宝堃、赵佩如、于俊波,他们是“相声八德”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当时津门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艺人群体,也是相声由俗入雅的探索者和实践者。除此之外,《大考》还收录了相声发展初期“清门”流派4位代表人物—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清门”子弟未下海之前多受过良好教育,创编作品时专注于遣词造句、精细修结,后世将这种追求文化意蕴的作品统称为“文哏”;王兆麟、吉坪三等人演唱的太平歌词,为该曲调的流派特征和革新开化留存了较为直观的考察样本,其中荷花女更为后世研究近代女性艺人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人人笑、汤金澄、田瘸子等人的口技作品是清代“像声”与“隔壁戏”的延续,反映出早期相声艺术由暗而明的递进式演变轨迹。
即便有众多专家、民间收藏者和爱好者提供许多珍稀的曲艺唱片,并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对相声有声史料的框架构建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然而在极力挽救发掘下,仍有部分唱片因遗失不易考证,而只能根据现有音频大致勾勒出晚清至民国期间相声发展的基本样貌。庆幸的是,相声艺术的“根”与精髓—伎艺得以薪火相传,在专业人士的编目、甄别、修复中再次焕发活力。随着相声有声资料的集结出版,随着市场的再度繁荣与自我调节,对文雅诙谐、不闹不爆的传统相声的有声研究,势必会迎来充满机遇的崭新局面,继续彰显传统曲艺艺术的价值与魅力。
[1] 参见殷文硕、王决:《相声行内轶闻》,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2] “相声八德”是对20世紀二三十年代活跃于北京、天津及沈阳等地的8位相声名家的统称,包括裕德隆、马德禄、李德钖、张德泉、焦德海、刘德智、周德山、李德祥,另有说法是用卢德俊替代李德祥。
[3] “垫话”指表演正式节目前所说的开场白。
[4] “入活”指以一段相声开始进入情节,或者开始引入正题。
[5] “底”指相声的结尾。
[6] “清门”是相声发展初期两大流派之一,与浑门相声相对。
[7] “贯口活”是以大段连贯流利语言叙事状物、介绍情况为主的作品。
[8] “正活”指相声作品的主体部分。
[9] “趟子”是“贯口”段子中通过大段背诵所要展示的内容。
[10]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2009年版,第85页。
[11] 倪钟之:《中国相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1] 王双福:《太平歌词》,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2] “歪唱”指依靠曲解、谐音产生笑料,与“正唱”相对。
[3] 参见佟守本编著:《中华太平歌词珍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4] “五档相声”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活跃在天津的5对相声搭档的统称,分别是张寿臣、侯一尘;马三立、刘宝瑞;常宝堃、赵佩如;侯宝林、郭启儒;戴少甫、于俊波。
[5] “文哏”是对语句雅驯,讲究语趣,注重内涵的相声作品的统称。
[6] “暗臭包袱儿”是用隐晦的手法,描述男女情色、性行为等内容来设计笑料。
[1] 蒋卯卯、张博、佀童强:《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536页。
[2]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第934、912页。
[3] “柳活”指相声中以唱为主的作品。
[4] 参见陈涌泉、蒋慧明:《清门后人—相声名家陈涌泉艺术自传》,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 张次溪:《天桥一览》,中华印书局1936年版,第76页。
[2] 连阔如:《江湖行当》,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3] 除《大考》附录手册中的辑录外,见于民国报刊记录的唱片信息还有小蘑菇、赵佩如的《新新数来宝》《白事会》《拴娃娃》《卖布头》。“第二天灌的是相声,小蘑菇、赵佩如合唱的《新新数来宝》《白事会》《拴娃娃》和《卖布头》。”《收音师力疾灌片 小蘑菇漫游山水》,《游艺画刊》第3卷第2期,1941年8月16日。
[1] 钱乃荣:《上海老唱片190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2] 漱梅:《留声机业》,《申报》1925年12月1日第17版。
[1] 许秀林:《相声那些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 “明地”指民间各行艺人的露天演出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