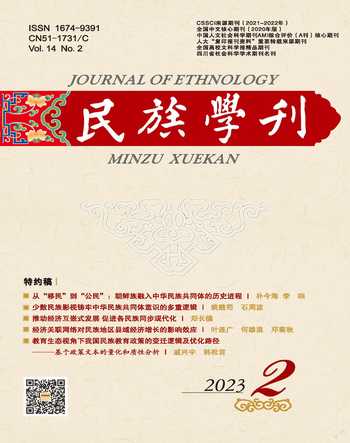神话、仪式与生态: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
[摘要]凉山彝族灾难观的形成与其神话传统、仪式实践以及生态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解释了灾难的起源与肇因,将灾难归咎于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生态格局的失序。仪式为灾难的禳解提供了神圣路径,以自然崇拜和鬼魂观念为信仰核心,体现了彝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生态伦理则在社会、心理两方面奠定了应灾的基础与策略。这使得彝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在文学、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传统,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关键词]灾难观;彝族;禳灾表述;神话传统;仪式实践;生态伦理;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2-0120-08
作者简介:罗燕,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彝族社会文化。四川 成都 610064
各民族对灾难的定义、理解以及应对方式与其文化系统息息相关,“灾难风险是历史地与结构地深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1]对于凉山彝族而言,复杂多样的地貌气候、万物有灵的信仰基础,形塑了他们对灾害的独特认知,体现在民间信仰、宗教仪式、人生礼仪、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通过探究神话与仪式中,人与自然及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发掘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可以丰富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为人类灾害研究提供本土视角。
将灾难置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框架进行剖析,是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核心所在。从理论的整体视域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奥利佛-史密斯(Oliver-Smith)关注灾难的历史沿革、生态模式,灾后重建等方面,将灾难人类学的研究概括为三种基本范式:行为反馈模式、社会变迁模式、 政治—经济/环境模式。[2]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关注灾难的社会文化属性,聚焦于文化和灾难的概念和性质,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在灾难发生中的重要作用。[3]
在灾难研究的本土实践中,中国学者从本土环境的多样性、文化的复杂性,结合实际的历史过程和政治生态,试图发展灾难研究的中国话语。庄孔韶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对灾难中的组织应对、社会互动、宗教仪式、生死哲学与文化适应等方面加以探讨,总结了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4]李永祥分析了傣族社区遭遇的泥石流灾害,认为在外界各种援助力量的支持下,建立在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能动回应,是减少灾害损失、完善灾害救助机制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5]以杨庭硕、游俊、罗康隆等为代表的吉首大学的人类学者们,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引入到灾难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发现苗族在应对石漠化灾变时,以磨合推进、最小改动、弥补缺环这三大原则获得生存安全,体现了苗族的生态智慧。[6]
除此之外,以仪式、神话等文本中的禳灾表述为切入点,来看文化中灾难的预防、发生以及应对,是本土化灾难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陈雪英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呈现的灾难观,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禳灾仪式及日常践行构成了灾难认知叙事外化、仪式内化并向生态伦理转化的过程。[7]张原、汤芸从地志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彝族神圣观念、文本表述以及社会组织三者共同在彝区灾难应对中的重要作用。[8]谢仁典则将禳灾仪式看作彝族人民消灾祈福的重要精神寄托,是彝族人民敬畏自然的具体表现。[9]唐钱华基于“拟人论医学体系”,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下探讨彝族文化对瘟疫灾难的省思。[10]
总之,从灾难人类学的宏观理论视域,具体到彝族文化中相关的禳灾表述,可以看到学者们都试图找寻“灾难”这一术语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呈现样态和意义,以“通过灾难应对的实践,为人们的生活经验开拓出一番新境界。”[11]本文汲取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经验,通过解释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灾难认知的生产、表述、实践及作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致力于探究灾难、文化及生态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一、失序与冒犯:神话叙事中的灾难肇因
彝族教育经典《玛穆特依》中的《命运论》一篇提到彝族对灾害发生的认知:“要说灾祸呢,天之赋予的”。可见,在传统彝族文化中,多将灾难的发生与形成归咎于神、鬼行为,这在流传至今的各种与灾害相关的传说和禁忌中均有体现。
依据史诗的内容记载,灾害由众神降罪于人类而产生,也就是说,灾难是一种惩罚,专门用来整治人间的秩序。神灵对人类行为的规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层面,例如道德、准则、习俗等,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以维持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二是自然层面,涉及环境、动植物以及各种山川河流,关注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相处方式,形塑彝人的自然观、生态观。
(一)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灾难的发生
彝族神话文本中的创世内容大都有洪水、旱灾等相关的记载。流传在云南红河州的彝族史诗《尼苏夺节》叙述道:[12]26
龙王的儿子造了天地万物,也用泥土造了独眼人。在独眼人时代后期,人类变得无人性又无仁心,天神大怒,降下洪水灭绝独眼人,只有娥玛姊弟心地善良而幸存,通过滚石磨、簸箕等仪式结为夫妇,开创了直眼人时代。若干代以后,直眼人又變坏了,天神又降下洪水消灭直眼人,好心的独阿姆老头(或作杜姆) 由于天神的帮助乘木棺得以避水。获救之后,天神将独阿姆变成小伙子,并做媒与三个天女婚配,生下九男十二女,开创了横眼人时代。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中对于人类起源的创世篇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梅葛》中写道:“格滋天神来造人。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13]30第一代人矮、独脚,第二代人身形高大、嗜好睡觉,他们全被晒死了。第三代是直眼睛人,“这代人心不好,他们不耕田不种地,他们不薅草不拔草……一天到晚,吃饭睡觉,睡觉吃饭。……糟蹋五谷粮食,谷子拿去打埂子,麦粑粑拿去堵水口,用苦荞面、甜荞面糊墙。”[13]23直眼睛人自私,无道德感,惹怒了天神,格滋天神遂决定换一代人“这代人的心不好,这代人要换一换。”[13]24于是,神降灾于人间,“洪水淹了七十七昼夜”,[13]30毁灭了直眼人。天神幻化成乌鸦,测试人心的善恶。留下了善良的两兄妹,让他们在灭世洪水中幸存下来,成为神灵选中的善种,他们的后代是第四代横眼睛人,形体五官与现在的人无异,是彝人的远祖。
《査姆》中的故事情节与《梅葛》大致相似,均是经历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几代人种的发展和淘汰,最终留下外表正常、内心善良的人种继续生存繁衍。独眼人的时代“不分男和女,不分长幼尊卑,不分白天黑夜,……”[14]7他们不讲伦理道德,“辜负了仙王一片心”[14]25,于是众神商议“独眼睛这代人心不好,要换掉这代人。要找好心人,重新繁衍子孙。”[14]26到了直眼人时代,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好转。“直眼睛这代人呀,他们不懂道理,他们经常吵嘴打架。各吃各的饭,各烧各的汤。一不管亲友,二不管爹妈。爹死了拴着脖子丢在山里,妈死了栓着脚杆抛进沟凹”[14]27。于是众神又决定“要重发一次芽,要重开一次花,要重结一次果,要重换一代人。”[14]51便发动大水,结束了直眼人的时代。这次,他们十分谨慎,立志要“查访好心人,要让好心人传宗接代,要一代比一代聪明能干,要一代比一代兴旺发达。”[14]51
以上的三个文本对于人类灾难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的范式:神造人——人无德——换人种——人再生。在这个范式中,人无德是导致灾难的主要因素;换人种的方式则是发动洪灾,毁灭现有的人种;人再生,则是留下善种,得以繁衍。“神”实际上是彝族共同的道德基础与社会秩序的抽象化存在,人由神造,且需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可以理解为文化形塑了彝人的行为,神化的秩序准则在精神信仰与身体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对人进行规训。将此范式进行结构化的梳理,可见,整个洪水神话实际上是将灾难看作对人类失范行为的一种矫正,通过灾难的发生,对人类于神的冒犯、于当前秩序的挑战,进行再构与整合。
(二)生态格局的失序与灾难的发生
除了犯神失德会导致灾难,破坏生态秩序亦是致灾的重要原因。“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体系,它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15]在凉山彝族人的生态文化观念中,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人在大自然之中并非处于中心位置,而是与所有动植物处于平等的地位、共享自然的资源。例如,在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中就有讲到“莫猎禽与兽,禽兽若猎尽,人类也临危;瘦熊不能杀,杀熊杉林怒;肥鹿不能猎,猎鹿杉木怒,大雁不能射,射雁天公怒。”[16]教育世人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正是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之中,平等、平衡的生态格局在彝族文化系统中得以呈现。一旦固有的格局被打破,灾难便会接踵而至。彝人的生态格局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主要是指自然观的建立与维系,指涉他们如何看待自然,建立何种关系?微观则具体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从与动、植物相关的食物禁忌中,窥见关于自然的观点与看法会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
《勒俄特依》第三章《阿俄蜀布》记载了自然界的起源,《阿俄蜀布》中写道:[17]35-37
地上不长树,去到天上取,取来三种树,栽倒地面上,树木长成林,荒山有了杉木树……引来鹿子放林中……从此林中有动物……取来三种草……荒坝成草原……
本则传说记载了阿德布尔求助熊神阿俄署布建造自然的故事。熊神阿俄署布从天上搬来了树,地上便有了葱葱树林,搬来了草便有了茫茫草原,搬来了水便成了滔滔江河,搬来了石头便成了层层峰峦,还引来了林中的鹿、云中的雀、水中的鱼和岩间的蜂,鬼斧神工锻造了大自然。自然万物来自“天界”,为“神物”,具有灵性。山有山神、湖有湖神、林有林神,壑有壑神。正所谓“高山有魂云雾升,物类有魂便昌盛,草原有魂草茂盛”。所以,世人不可随意伐木、狩猎、污染水源,否则将会“遭天谴”,受到神灵的惩罚。
除了宏观上,整个自然界具有灵性,动、植物亦是灵性的存在,因此衍生出了相关的食物禁忌。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第四章《雪子十二支》记载了自然界中的物种起源。讲述了世间有了山川河流、树林草原后,诸神开始造人。在屡次尝试失败后,天上落下泡桐树,霉烂三年后,化作三股雾升到了天空中。于是天上下起了三场红雪,红雪融化了九天九夜后,从红雪中生出了雪族子孙十二种。其中有血的为六种动物:蛙、蛇、鹰、熊、猴、人类;无血的为六种植物:黑头草、柏杨、针叶树、水筋草、灯芯草、蔓藤。并且每一种都对应一方自然地的归属,如灯芯草住在沼泽边、蔓藤住在树根岩壁边、蛙住在水池边,鹰住在白云山……,而人类则分布天下。
《雪子十二支》记载了人类与动植物是同根同源的,都是雪族的子孙,因此这些动植物是人类的“兄弟物种”,不可虐杀,更不可食用。如果猎杀了禁止杀害的动物,也要举行相应的赔罪仪式。彝谚云“打雁苍天怒,打妻亲家怒”。杀雁者须举行“赔雁赎罪仪式”,彝语叫“耿则”,意思为“赔还大雁”。“在毕摩帮助下,赔罪者身着白衣,手执一只黄色母鸡肃立高呼:‘神鸟异禽雌雁阿乌前来接受赔偿。并指名道姓认错说自己不明事理冒犯,杀鸡赔偿,请求宽恕。杀蜥蜴者也须举行‘赔蜥蜴赎罪仪式,因为彝族认为‘天上有雁不叼鸡,地上有鲁(蜥蜴)不咬人。赎罪者须用柳枝和杨枝各刻一个蜥蜴模型,带鸡蛋和荞粑到现场祭祀赔礼致歉。”[18]
彝人关于物种的分类决定他们的生态观念,例如什么东西能食用、什么东西不能食用;什么东西能追捕猎杀,什么东西要供奉崇拜……久而久之,这些观念有的成为了禁忌,有的成为了习俗,一旦被迫打破则必须诉诸神灵,需请毕摩进行相关的宗教仪式进行禳解,否则将会带来噩运、造成灾难。
彝族史诗、神话中的相关表述中,灾难与人类总是相伴相生的,人类起源之初,既受到了灾难的毁灭,又在其中再生,并且每一次都在向着更美好的方向“进化”,这也反映出彝人面对灾难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同时,道德观念的失范(冒犯神旨)与生态格局的失序(破坏秩序)是灾难的首要肇因,这隐喻了神话表述中,灾难在社会、生态两重方面的影响和功能,它对奠定共同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准则、巩固生态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整合作用。
二、崇拜与祛秽:信仰表述中的禳灾仪式
“‘表述既与言说层面的‘写作 ‘表达 ‘讲述 ‘叙事等关联,同时也跟实践层面的‘展现 ‘表演 ‘仪式及‘践行等相关。”[19],因此,对彝人禳灾表述的研讨,亦可从仪式实践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探究。从仪式的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失序和结构的错置,所以要“拨乱反正”除了依靠人力,实行切实的减灾举措,还必须诉诸神力,通過神话的示意和仪式的力量,合力预防、应对灾难的发生。
彝族文化中对于灾难的禳解仪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祈福类,针对没有实时发生的灾难,主要是未雨绸缪,对灾难起到预防的作用。另一类则是祛秽类,有较强的针对性,是对已经发生的灾难进行应对和处理。前者以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为基础,后者则围绕彝人丰富的鬼魂观念展开。
(一)自然崇拜:祈福防灾仪式
祈福防灾类的禳解仪式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相对固定性和周期性,也就是说这类仪式与现实生活中灾难发生的具体类型联系不大,而是针对整体的灾、祸、病等对人产生不利的因素进行的预防机制。
彝族人认为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难免会欠下许多债务,或是与人交往中犯下大大小小的口债,或是在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总之人总会亏欠神祇怪灵、天地父母、飞禽走兽。因此,在彝族义诺地区每年许多家庭都会举行“吉觉”仪式,以期偿还孽债,祈求安康。“‘吉觉是彝语的音译,‘吉意为敌人或敌咒,‘觉有转、返之意,‘吉觉意为‘转回敌咒。彝族谚语有称:‘春季要还债、夏季要吉觉、冬季要赎魂。”[20]“吉觉”仪式的目的在于遣返、还债、扭转局势,偿还人所亏欠的孽债,重新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
人类作为大自然的“负债人”,偿还孽债是其天然的义务。如果不履行,神灵便会进行“报复”,从而给“负债人”或其子孙后代带来噩运。
祈福类仪式中有一种类型专门用于天灾防范,“毕摩特依”中的《防雹经》专用来应对冰雹天气所带来的灾难,名为“则斯哈马希”。“则斯哈马”指冰雹灾害,“希”则是一种宗教仪式的术语,有“驱逐”或者“对……做法”的含义。“则斯哈马希”可以理解为“驱逐冰雹”,或者“对冰雹做法”。通过田野访谈,可知虽然各地的仪式过程稍有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大致如下:一般来说,仪式委托人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毕摩做法以委托人为核心开展仪式,而防雹一类的仪式委托人则以全村人为整体,毕摩的职责在于驱逐作祟的鬼怪、保佑全村人的土地和庄稼。因此,做法事需要全村人出动。仪式过程中的动物献祭既可以选择鸡也可以选择羊,这主要取决于全村人口的多少,以及对冰雹威力的估计。以鸡为献祭的仪式,需要摘取三枝杉树枝,三根竹根;以羊为献祭的仪式需要三双(六枝)杉树枝,三双(六枝)竹根。仪式地点要选择荒地而不能在耕地,并且要选择全村的制高点,旁边有水,可以是溪流也可是水塘、水池。
仪式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木古茨”,即“放神烟”。将一块点燃的火炭放入草堆(不可出火光),让袅袅升空的草烟通报神灵前来助法。“意思是现在的天地相距甚远,世人难以攀达神界,只有借助火烟向天上的神灵通报,请天神下凡助法。咒词中念:‘无法无天的作祟鬼,请上天来审判。”[20]第二阶段,由毕摩的助手抱着鸡或羊绕着这个村落顺时针走三圈。第三个阶段毕摩开始念《防雹经》,驱逐鬼怪。最后,全村人将会把鸡、羊等牲畜分而食之。在传统彝族社会,冰雹对人们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彝族群众无法用已有的知识来进行有效的预测与防控,便将它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借助宗教仪式与之抗衡。
以上两种仪式均以万物有灵为核心观点,人类的“亏欠”以及对自然的“偿还”说到底是对生态平衡的维护。人类和自然就像天平的两端,宗教仪式则是砝码。一旦人类索取太多,天平发生偏移,宗教仪式则发挥它的调和作用,阻止人类的索取,为大自然“加码”,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平衡。从生态伦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实际上是将自然界升华或拟人化,并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道德关系,以此来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畏惧,对大自然无私赐予的感激与珍惜。”[21]
(二)驱鬼辟邪:祛秽祓祟仪式
彝族人拥有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在他们看来遭受灾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鬼怪作祟,二是丢了魂。一般来说天灾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鬼怪作祟,因此必须要从“毕摩特依”中选择恰当的经书,举行相应的仪式来进行禳灾解。这类经书主要有“《百解经》《解罪经》《除魔经》《断口嘴经》《禳解经》《祛秽经》《送鬼经》《招魂经》等等。”[22]70而“丢了魂”大多数时候会导致疾病。在彝族的传统观念里,疾病和“魂魄”是相连的,人生病往往是因为“丢了魂”,摔跤、被动物咬、做噩梦、去陌生的地方等都可能导致丢魂从而引起身体不适,需要请毕摩做仪式,将丢失的魂魄唤回,以保安康。
彝人将致灾致病的鬼怪都归为不洁、污秽之物,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23]一书中认为污秽其实是人们在构建秩序中出现的不正常的、反常的事物,所以“污秽”需要通过清洁来达到“干净”,即重建正常的秩序。污秽因为打乱了秩序,跳脱了约束,人们为了维护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秩序,需要将此推出自己建立的秩序范围内,并且定下“禁忌”来进行维护和巩固。例如,在彝人的观念里,世间的生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俄迪”(vo ddit),雪族,包含了《雪子十二支》中有血的和无血的十二类生物。原诗中所提到的动物名称实际上是指一类动物,就如现代生物学中所提的“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概念一样,每一类动物名下又有多种分支,如原诗中说鹰为雪族中的第三种,鹰有三子。长子为神鹰;次子是普通的鹰,次子又生三子:黑色秃头鹰、白色鹞和饿老鹰;幺子则为褐色山鹞子。
第二类为“都迪”(ddu ddit),羽族,“ddu”有翅膀的含义。包括鸡、鸭等禽类,也包含天空中有羽翼的飞鸟。
第三类“比迪”(bbit ddit),分蹄族,如牛、羊、猪等,马、驴、骡子不分蹄因此不被包含其中。
第四类“俄布迪”(vop bbup ddit),掌族,包含猫、狗、狮子、大象等执掌类的哺乳动物。
人类的“雪族身份”决定了其生态位置,同根同源的“雪族”是不可食用的,同时“掌族”动物亦不能食用,因此彝族禁食狗肉、猫肉等。一般而言,“羽族”和“分蹄族”中的部分是可以食用的,如牛、羊、鸡……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彝族人都会遵從这种分类体系的规则,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生态平衡。
将自然界的物种分类,并制定相关的饮食禁忌,实际上是维持秩序的手段。在彝族社会中这种秩序一旦被打破,就需要宗教仪式来进行“清洁”,解除“危险的肮脏”带来的威胁,重建正常秩序。彝族民众认为如果有人不慎吃了禁止食用的动物,则会沾染“措卓措尼”,人会生病、无精打采、交噩运。因此,必须请毕摩进行“卓尼说”的仪式,驱赶晦气。根据当事人的症状轻重不同,“卓尼说”仪式又分为“阿曲说”“阿则说”“阿诺说”,法力逐层递增。
除了误食、错食会招惹鬼怪、沾染污秽,人会惹“鬼”上身,失魂落魄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前文中提到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欠下各种“债”,因而会招惹孽债鬼“正”,“负责讨还这些债务的司职鬼怪据说有独腿孽债鬼公‘正布席孜、独臂孽债鬼母‘正嫫洛孜和斜眼孽债鬼仔‘正惹略吉三个。”[24]51-52如果不及时进行相关仪式进行禳解将会为人们的带来灾难,例如,彝族传统社会看重男嗣,彝有谚语“生儿子有名气,生女儿有福气”,可见男性后代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如果某家人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往往是因为自己或者祖上狩猎过多,惹恼了神灵。若想破解这个困境,则需要请毕摩进行“还禽兽债”的仪式,调和人与山神林神之间的关系,以抚慰神灵。又如,如果一个人患有皮肤病,久病不愈,甚至患了麻风病、痨病等,往往被认为是因为滥砍滥伐或者过度狩猎而遭受到山林之神的惩罚,从而获病获灾。“如果遭遇了这种情况,必须请毕摩行彝称‘波窝诗普洛的祭祀山神岭神的仪式。”[24]78
彝族文化中关于灾难禳解的信仰表述,主要包含了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祈福防灾类仪式和以鬼魂观念为核心的祛秽祓祟类仪式。前者将季节、时节等时间因素视作仪式发生的周期标志,是彝人在与大自然相处的历史进程中,把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节律得出的经验实践。后者则看重时机,强调共时的空间中灾难发生的具体形态,是彝人在面对不可抗的消极因素时,把握宏观环境,省思自身而阐发的对当前境遇的哲思与应对,体现了他们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
三、合力与共生:生态伦理中的应灾实践
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凉山彝族的生态伦理形成与其万物同源的神话思想息息相关。
在他们看来,整体源于万物同根,所以要和谐共处;分类则代表界限,界限则有限制,限制衍生禁忌,禁忌维护秩序。这样环环相扣的生态观念才能使人的欲望得到节制、维持大自然的良性循环。于是,在神话和仪式的语境下,合力与共生的生态伦理成为了生活世界中,应灾实践的指导基础。
灾害对人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具体事物上,还会对人的精神、心理、情感等方面造成伤害。因此,灾害的应对也应该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来谈。彝族社会中,关于灾害的应对处理,一方面会成立相应的互助组织,团结一致渡过困难;另一方面,在信仰的层面,则会联结自然界中的万物,整合万物之力,共同消除心理上致灾的“恶鬼”。
(一)合人之力,应生活之灾
彝族人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积淀了深厚的毕摩文化。尽管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指导着彝人的生活实践,他们遵从教义、恪守“规矩”,但是他们也从未完全依赖自然、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天命”。《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说“彝人不能自已之事,则祈祷于人、权威,而不是祈祷于天,遇不能自医之病,不曰‘祈祷于鬼而是送鬼、咒鬼、赶鬼。如遇无可奈何之敌,则祈师于亲戚,而不是祈祷于鬼神。祈师亲戚而不胜,则塑泥为像以煮之,编草为敌以射之。”[25]531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同时他们也相信人力胜天,相信团结的力量。
“团结互助”既是一种生态道德,又是一种社会道德,同时关照了彝人的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遇到灾难和不幸时,他们既创造了一套“精神意志治疗法”,合大自然之力面对未知的超自然,疗愈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他们以家支为单位,群策群力,共同面對灾难、解决纠纷。
凉山彝族的家支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结成的血缘群体组织,它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彝有谚语“马的力量在鞍上,人的力量在家支上”,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每位家支成员都有义务献一份力,而“尔普”则是家支成员共同的经济基础。“‘尔普(hly pu)是凉山彝语,‘尔是交换的意思,‘普是价钱的意思,‘尔、‘普连在一起意即‘交换的价钱,相当于汉语的‘份子钱……‘尔普只用于丧事、命金,纠纷赔偿等方面。”[26]当家支某位成员需要帮助时,其他成员就要按规矩出“尔普”,帮助成员渡过难关,这也体现了彝人之间团结互助的道德伦理。
遭受灾难时,彝人重神的法力,也重人的群力。所谓“天人合一”不仅是说人类社会的运作规律与大自然的生态伦理是相统一的,同时也是指人的本质是归于自然的,正如《勒俄特依》中描述人的构成:“结冰来做骨,下雪来做肉,吹风来做气,下雨来做血,星星做眼睛。”[17]53骨肉来自冰雪,气血来自风雨,这便是彝人观念中人类归属于自然的生命本质。
(二)共万物情,疗灾难之伤
为了认识自然,彝人将大自然拟人化,用人的情绪来诠释万物的更迭、气候的变化。将大自然赋予人的情感,创造了人与自然共情的基础,让人类在抗争自然的过程中,理解自然、“同情”自然,以此来建立良好的生态关系。
关于雨季的来历,在彝族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传说彝族英雄支格阿龙的母亲蒲莫列衣因龙鹰滴下三滴血在其身上,而诞下支格阿龙,因此他是鹰的后代。长大后他娶了两位妻子,一位住在“木吉黑叠”、一位住在“木吉库叠”,中间隔着名为“叠坡蜀诺”的茫茫大海。支格阿龙经常骑着他的飞马,往来于两地。两位妻子为了将他留住,不让他去另一地,便在他每次回来后,都悄悄剪掉一点飞马的羽翼。九月的某一天,当支格阿龙正骑飞马越过大海时,不幸坠入了大海,被海中的鱼兽吃掉了。听闻噩讯,老鹰大怒,便决定报复。无奈当老鹰飞到海面上时,它的身影就倒映在了海面上,鱼兽看见后纷纷躲避逃跑。于是老鹰请求天神帮助,每年支格阿龙的死祭时,即九月到十月,天空不出太阳,乌云密闭,雨水绵绵。使得老鹰在海面没有倒影,让它能够猎杀鱼兽,以报仇恨。也因如此,彝人常常把九月、十月称为“格测日”,即阴雨绵绵,不见太阳的气候。
每年“格测日”的时节,天气阴冷,雨水不断。当地的民众描述:“连干柴火都捡不到,只能烧湿柴,每次一烧全是烟子。”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然,把“情感”作为人类社会道德逻辑与自然世界气候规律共情的基础。从生产生活方面来看他们是对立的,阴雨气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诸多不便,但是将神话作为“反结构”的助力剂,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又是统一的,人类理解“鹰的悲愤与仇恨”,进而也与自然达成了“和解”。
正是在与自然万物的共情基础之上,人与自然和谐、互惠、平衡、平等的各种生态伦理内涵被凸显。仪式场景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御灾邪的观念。彝人在进行禳灾仪式时候,会联合自然界之中各类动、植物的力量,将他们作为牺牲、礼物以及各类神祗的象征,共同完成对秽祟的驱逐与灾难的禳解。
彝族的宗教仪式尽管种类繁多、目的不一,但是从场景和步骤上来讲,大致有着相似的布局和程式。一场宗教仪式由这几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毕摩(有时候会带学徒)、主人家(受“毕”的人可以是一家人或者一个人)、献祭的牲畜(根据仪式类型不同所需的动物也有所不同,常见的有鸡、猪、羊、牛)、植物(依仪式类型进行选择,常见的有柳树枝、竹根、杉树枝等)。除此之外,有时候毕摩会携带法器,如神扇、神笠、神铃等。
从步骤上来说,常规的仪式过程会包含:点神烟、烫净石、报人丁、反口业、献牲畜、扔草偶……“仪式场中使用的‘神枝被加工成 ‘矛、‘钩状;驱鬼仪式中常用带刺的川续断、悬钩子属植物来拦鬼,圈鬼;漆树的乳汁会使人过敏,因此认为鬼也怕这种树,在驱鬼仪式中使用。”[27]可见,完成一场宗教仪式实际上是人和动植物合力作用的结果。毕摩负责请神相助,牺牲动物特定部位犒劳各路神灵。万物的“灵格”在宗教仪式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将大自然视作共同抵御灾难的伙伴,便是彝人和谐、平等生态观的最好体现。
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一切人事应当遵循自然的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彝人的观念里,人常伦理与自然规律同样是彼此通融、一脉相承的。无论是通过成立各种类型的“尔普”,联合人力制定应灾机制;还是在仪式中,培养与自然共情的能力,整合万物,共同完成儀式的展演。并通过仪式的神圣功能,呈现灾难中心理创伤的疗愈体系,都体现了彝族文化中关于合力与共生的生态伦理。
四、结语
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彝人用经验和智慧建立了一套以本土生态为基础,以禳解灾难为目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神话、仪式和生态分别从原因、过程及后果三个层面,对灾难的形成、禳解及应对提供了相关的历史支撑和现实依据。面对莫测的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局限,彝人试图通过文化内部的神话逻辑找到应对灾难的突破口——他们将自然拟人化,寻找人类与自然共情的基础,以理解自然,善待自然,同时约束自身,克制欲望。从而创造出一套生态秩序。为了维护这套秩序,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仪式和禁忌。并通过“尔普”相关禳灾仪式的开展,同时观照了灾难之中,社会中的群体处境和个体的心理疗愈两个层面。总之,本文论述的传统神话与仪式传统影响着彝人的世俗生活,让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面对自然灾害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从凉山彝族的灾难文化中,可以看到这种“地方性知识”在释灾、应灾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作为多民族中国的话语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参考文献:
[1]Anthony Oliver-Smith,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J],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5,1996:28-303
[2]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彭文斌.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01):1-9.
[3]苏珊娜·霍夫曼,陈梅.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和文化要素的探讨[J].民族学刊,2015,6(04):29-35+104-106.
[4]庄孔韶,张庆宁.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05):1-10.
[5]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云南新平曼糯村的研究案例[J].民族研究,2011(02):44-55+108.
[6]Luo Kanglong and Shao Kan,The Value of the Miao People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for a Solution to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Mashan[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March,2011,Vol.2 No.1:
[7]陈雪英.西南少数民族灾难认知图示、叙事及传统应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07):15-20.
[8]张原,汤芸.栖居生境的地势感知与弹韧性营造——凉山甘洛彝族地区的地志学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4):92-100.
[9]谢仁典.生境、生计与灾害文化:昭通彝族灾害认知与传统节日中的禳灾仪式[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40(06):36-42.
[10]唐钱华.防疫文化资本:凉山彝族瘟疫认知与应对的人类学省思[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14(01):99-109+155.
[11]张原,汤芸.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07):13-18.
[12]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尼苏夺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13]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梅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14]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搜集.查姆[M].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郭家骥.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J].民族研究,2003(01):48-57+107-108.
[16]中共昭觉县委宣传部编译.彝族传统道德教育读本[M].内部印刷本,2007.
[17]《彝族传世经典》编委会.勒俄特依[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
[18]陆文熙,陆铭宁.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2):8-10.
[19]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01):149-154.
[20]蔡华,张可佳.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J].民族研究,2010(03):35-43+108.
[21]杨红.凉山彝族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凉山彝区生态文明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22-25.
[22]叶宏.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3](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4]阿牛史日,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5]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6]巫达.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J].民族研究,2004(01):60-66+108.
[27]王静.四川凉山彝族传统民俗中的植物及其文化意义[J].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2014,36(04):537-544.
收稿日期:2022-08-01 责任编辑:贾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