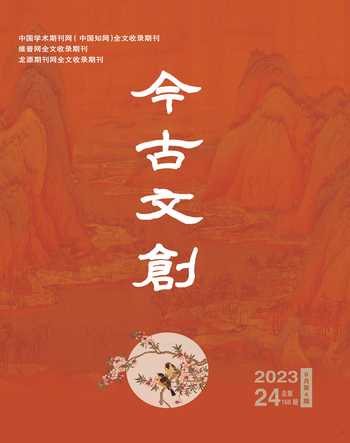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人物悲剧色彩分析
【摘要】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因“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政治品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作品《静静的顿河》描写了顿河哥萨克人在1912—1922年间的生活和斗争,以其恢宏的叙事风格和深沉的悲剧思想,成为世界文坛的不朽著作。《静静的顿河》是顿河哥萨克人的悲歌,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是这一特殊群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通过分析《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妮娅这三位主要人物形象,以此来找出顿河哥萨克人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静静的顿河》;人物分析;悲剧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4-002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4.006
一、肖洛霍夫和顿河畔的哥萨克
1928年,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声名鹊起。当时的读者都以为,年轻的肖洛霍夫之所以能够如此细腻生动地讲述顿河畔哥萨克人的故事,是因为他是纯正的哥萨克人。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肖洛霍夫并不算是世代居住在顿河的真正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家庭从祖父辈才开始迁居顿河地区,和当地的哥萨克人共同生活。虽然如此,肖洛霍夫仍深深地着迷于顿河的优美风光,醉心于哥萨克人的歌谣和传说故事,扎根于顿河哥萨克的文化和生活中。顿河哥萨克人带给肖洛霍夫的一切,都呈现在《静静的顿河》中。
《静静的顿河》让读者们认识到了一个特殊群体——顿河哥萨克。曲折蜿蜒的顿河,落差却并不大,因此当地人把顿河称为“静静的顿河”。顿河孕育着顿河平原的文明,成为一部分哥萨克人休养生息的家园和征战生涯的归处。“哥萨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生活在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游牧族群,他们的起源至今不详。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哥萨克人的祖先是受尽地主压迫而出逃,并逐渐定居于俄罗斯南部许多地区的“自由民”。俄罗斯南部地区地域辽阔,物产富足,自古以来,这里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当地哥萨克人生活无拘无束,但是也经常遭遇外族侵扰,所以哥萨克人在保护家园的世代征战中变得骁勇善战、杀伐果决。
不断壮大的哥萨克人保护家园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保护俄国的疆土,因此,沙皇开始慢慢注意到哥萨克群体,开始让哥萨克人尽情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去保卫或开辟疆土。纵观俄国历史,哥萨克人留下了赫赫功绩,从1552年到20世纪中叶,哥萨克人参与了攻占喀山汗国、征服西伯利亚、1812年卫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等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仅大规模战斗就有24次,平均15年参加一次大规模战争。好战骁勇的哥萨克人让拿破仑都感慨其战力剽悍。
生性自由率真、坚守荣誉和信仰的哥萨克人让不少俄国作家不吝笔墨去塑造,如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起义军首领、顿河哥萨克人普加乔夫,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中淳朴善良的哥萨克女孩玛丽雅娜,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格里高里,巴别尔《骑兵军》中视死如归、作战英勇的哥萨克骑兵群体……可以说,俄国作家的“哥萨克情结”让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生动真实、可歌可泣的哥萨克人形象。
二、《静静的顿河》:顿河哥萨克人的悲歌和灵魂归处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用140万字集中讲述了1912—1922这十年间顿河哥萨克人平静的乡野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巧妙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历史大事件嵌于作品中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里,让读者看到戎马征战的顿河哥萨克人的喜怒哀乐和家庭生活,看到战场上无畏生死、捍卫荣誉的顿河哥萨克也面临着生活的难处和不可言说之痛。
(一)格里高里·麦列霍夫——复杂、摇摆的哥萨克勇士
男主人公格里高里出身中农家庭,是个标准的哥萨克男人,半农半兵。他勇敢正直,善良勤劳,敢爱敢恨。在顿河乡间,他遵从长者安排,娶了从未谋面的哥萨克姑娘娜塔莉亚为妻,尽管他对妻子并没有太多感情;他时刻惦记农活,经常和父亲夜间垂钓;在战场上,他战功卓越,甚至曾经官至师长之位,还是乔治勋章获得者,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有着哥萨克血脉和传统的格里高里却并没有迎来圆满结局,而是家破人亡的场面,他在最后只能紧紧地拥抱住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此时才明白,只有儿子才是他和大地仅存的联系。
格里高里的悲伤结局,源于他性格中最致命的缺点——摇摆不定,犹豫不决。面对婚姻和爱情时,他一边没有拒绝长辈的安排,娶了娜塔莉亚为妻,却一边和有夫之妇阿克西妮娅保持亲密而禁忌的关系。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割断这段孽缘,因为他依恋情人阿克西妮娅的热情而厌恶妻子娜塔莉亚的顺从。他多次带着情人私奔,多次试图离开情人,又多次回到妻子身边。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反复,最终导致两个深爱他的女人——妻子和情人都不得善終。
面临政治站位,他同样犹豫不决,徘徊往复于白军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甚至还参加过匪帮。他曾为布尔什维克战斗,毫不手软地斩杀白军;他也曾为报仇加入白军,手上沾满红军的鲜血。他并不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只是“从心眼里不能跟这个荒谬的时代妥协,但又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光荣……”[1]换句话说,他只是在执行身为哥萨克的历史职责:上战场、为捍卫哥萨克的荣光而战。但是,在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最终也让他在两方军队中被怀疑、被驱逐。虽然赫赫战功让他一度成为整个鞑靼村的光荣,这战功最后也成为困住他人生的羁绊,漂泊归来的格里高里扔掉兵器后才如释重负。
格里高里的悲惨结局让人感慨,但是顿河所有的哥萨克命运却也和他的结局如出一辙。格里高里将枪支弹药扔到河水中之后,顿悟了自己和生活唯一的联系,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许多顿河哥萨克们已经和普通生活毫无联系,他们的家人都死于战火和等待之中。为荣耀征战一生的顿河哥萨克们,被迫裹挟到历史洪流中挣扎彷徨之际,有多少人为此丢掉性命,无家可归,又有多少人活着荣归故里,或者名垂青史。
(二)娜塔莉亚——忍耐、温顺的传统哥萨克女性
出身富贵之家的娜塔莉亚并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她和普通哥萨克女性一样勤劳能干,她双手因为干活而磨得粗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孝顺公婆,与家人之间相处和睦,任劳任怨操持着整个家庭。娜塔莉亚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她对家里给她安排的婚姻完全不排斥,对素未谋面的格里高里也并不排斥,她对婚前的格里高里在鞑靼村的种种荒谬行径充耳不闻,一心只想嫁给格里高里,她认为格里高里就是她的爱情和幸福。
面对格里高里的多次背叛,娜塔莉亚始终都恪守妇道,但是格里高里带给她的并不是安稳的幸福生活,而是长期的冷暴力和短暂的安宁日子。尽管如此,身为有夫之妇的娜塔莉亚也从未自甘堕落,从未对别的男人动心或者和别的男人厮混。格里高里带阿克西妮娅私奔,还有了私生女,娜塔莉亚觉得十分屈辱,她自杀未遂还在脖子上留下很大的疤痕。她甚至去找阿克西妮娅,求阿克西妮娅将格里高里还给她,却被阿克西妮娅咒骂。后来,格里高里突然明白了妻子的柔情和包容,和娜塔莉亚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与娜塔莉亚有了两个孩子。可是浪子终究无法回头,娜塔莉亚期待的平静生活最终还是破灭了。在得知格里高里和阿克西妮娅旧情复燃后,娜塔莉亚也曾当着婆婆的面诅咒格里高里死在战场上。伤心欲绝的娜塔莉亚不愿再为负心汉生育,最终因流产失血过多而亡。即便如此,想到害她丧命的丈夫格里高里,娜塔莉亚仍在死前叮嘱儿子米沙要亲吻格里高里。娜塔莉亚身上的人格魅力让读者动容,可即便如此,格里高里仍不是娜塔莉亚的良人。
娜塔莉亚和格里高里的婚姻是传统的哥萨克婚姻,媒人说媒,男女双方不曾谋面也无甚熟悉,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便成了夫妻。婚姻对格里高里只是一场仪式,甚至说是完成一项父亲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格里高里始终无法真正和娜塔莉亚举案齐眉。但是婚姻对于娜塔莉亚而言,是将自己的人生和幸福都交给丈夫的重要节点,“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宗法制婚姻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而是追求一种建立在夫妻双方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爱情婚姻”[2]。很明显,娜塔莉亚只是一个有婚姻之名的贤妻良母。娜塔莉亚与阿克西妮娅相比毫不逊色,娜塔莉亚出身大户家庭,温和谦顺,勤劳善良,美丽端庄。可是在格里高里眼里,妻子娜塔莉亚只是一潭死水,冷冽没有感情。拥有女性所有优点的娜塔莉亚并未得到爱情,而成了男权社会的殉葬者,逃不掉凄苦的命运。
(三)阿克西妮娅——反叛、勇敢的非传统哥萨克女性
如果说娜塔莉亚是忠贞、温顺的家养百合花,那阿克西妮娅就是叛逆、热烈的魅惑野玫瑰。阿克西妮娅同样是一个美丽勤劳的哥萨克女性,但是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她直爽火辣,热烈奔放。在格里高力眼里,阿克西妮娅这朵“野花”比只知道一味順从的妻子要更有女性魅力,因此格里高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深陷与阿克西妮娅的禁忌之恋中无法自拔,即使被家人和鞑靼村的人发现了他与阿克西妮娅之间的私情,也不愿与她完全撇清关系。
在沙漠中行走的人突然发现绿洲,会开心到疯狂,同样,生活在痛苦煎熬中的阿克西妮娅遇到格里高里后,就发疯似的爱上了他。“女人晚来的爱情并不是紫红色的花朵,而是疯狂的,像道旁的迷人的野花”[3]。她无视格里高里的家庭和婚姻,甚至无视传统道德,不顾一切地与格里高里保持令人不齿的情人关系。她为了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感情,甚至不惜恶语中伤格里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致使娜塔莉亚自杀未遂,甚至还成为害死娜塔莉亚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众多读者眼里,阿克西妮娅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因为她破坏别人的婚姻和家庭,甚至还因为出轨另一个男人被格里高里抛弃。表面上看,阿克西妮娅就是个“坏女人”,但她真的只是一个“加害者”吗?
阿克西妮娅在少女时就被生父玷污,在丈夫斯捷潘的眼里,没有“贞操”的她是一个“荡妇”,所以他可以任意欺辱阿克西妮娅,不给她一丝一毫的尊重和感情。他在娶了阿克西妮娅为妻的第二天就有计划地把她关到仓房毒打,并且出去和别的女人鬼混。阿克西妮娅在婆家的境遇非常糟糕,繁重的家务事、处处挑刺的婆婆和心狠手毒的丈夫都让她一直活在水深火热中。因此,她必须紧紧抓住像救命稻草似的突然出现的格里高里,她不想,也不能把格里高里还给娜塔莉亚。阿克西妮娅并不是男权制度的幸存者,她和娜塔莉亚一样深受其害。但是阿克西妮娅敢于反抗传统,敢于追寻自己的真爱,这一点是娜塔莉亚这样的传统女性所没有的优点。我们无法以现代的视角去评判阿克西妮娅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也许这正是肖洛霍夫塑造这个特殊人物的用意——让人生恨的人同样令人恻隐,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可是在那时候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多少女性有阿克西妮娅这样的反抗意识和自由精神,所以这也注定了阿克西妮娅的悲惨结局——孤勇者最终死于枪下。
书中有关于铃兰花的一段描写,铃兰代表着“奔向幸福”,可是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妮娅最终都没能拥有幸福。勇敢勤劳的格里高里戎马半生,原本应该是衣锦还乡,可是他归来之后仅有儿子米沙陪伴身边。娜塔莉亚执着地爱着多次给她带来伤害的格里高里,痴痴地等待格里高利回心转意,却最终死于流产。阿克西妮娅勇敢追爱,却死在和格里高里最后一次私奔的路上,死在征粮队的枪下。这种凄美的结局令人唏嘘。阿克西妮娅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在寂静的顿河平原格格不入,因此阿克西妮娅最终消失在冰冷的枪声中。
三、不朽军团——哥萨克
肖洛霍夫将《静静的顿河》写成悲剧,从文中人物的人生走向中,可以读出肖洛霍夫对哥萨克这个群体的深厚感情,他始终关注哥萨克的命运。纵观俄罗斯历史,哥萨克既是历史的畸形产物,也是时代的牺牲品,从始至终哥萨克都只被统治者视作一个军事群体,似乎军事才能是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
从哥萨克作为军事阶层崛起的那一刻,他们的摇摆不定和太过于坚定的信仰就在历史发展中为他们埋下了隐患。哥萨克自16世纪起效忠沙皇,“怀柔”政策让哥萨克将自己困于无形枷锁中,他们将捍卫哥萨克荣誉和对沙皇无条件效忠看得比生命还重。哥萨克人既热爱自由又拥护沙皇,这样的群体十分矛盾。
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沙皇垮台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而此时的哥萨克就面临着影响极为深刻的抉择,是加入白军负隅抵抗,还是加入红军为正义而战。犹豫不决的哥萨克人既急于寻找新的信仰,又十分警惕。格里高里在政治立場上的不坚定和矛盾性格,是哥萨克群体在俄国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之际挣扎彷徨的生动诠释。
1919年的“非哥萨克化”政策让哥萨克失去了一切特权和优待,曾为布尔什维克卖命的一部分哥萨克面临着大厦倾颓的现实。但是哥萨克人还是封闭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固守他们的土地和传统。守旧、落后和偏执成为哥萨克群体的独特性格。卫国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哥萨克人又受世代相传的使命感的驱使奔赴战场保卫国家,无数哥萨克人为了苏联失去生命,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哥萨克人带着各种目的投奔德国,站在苏联的对立面。但是不管做何选择,哥萨克人还是被动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中,曾一度沉寂。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领导人才重新注意到沉寂已久的哥萨克,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恢复哥萨克作为军事群体的存在感。
四、结语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史诗巨著,这部作品以悲剧性的口吻向人们讲述了在历史洪流中一个人以及一个群体的命运。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妮娅被肖洛霍夫塑造成俄罗斯文学史上十分饱满真实的顿河哥萨克形象。格里高里的犹豫彷徨和生活代表着顿河哥萨克甚至整个哥萨克群体的历史宿命,从他身上,可以读到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的悲悯和咏叹,以及顿河哥萨克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迷惘。就像小说题诗里引用的哥萨克歌谣一样,悲凉贯穿了整部作品,也成为哥萨克在历史中的缩影。
在历史洪流的波涛汹涌中,哥萨克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军事传统自古以来是为了拥有安宁平静的生活,但是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哥萨克人的战斗属性注定他们要世代为荣誉和统治者而战。哥萨克男人只能以其骁勇善战的历史传统被禁锢成永远的战士,洒下血泪,而哥萨克女人们则守在家园,等着归期未定的丈夫。历史长河永不停息,哥萨克的传统和悲歌世代传唱。
参考文献:
[1]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陈慧君.美的毁灭——谈《静静的顿河》中三个哥萨克悲剧性妇女形象[J].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1):21-26.
[3]曹海艳.论《静静的顿河》中的女性形象[D].黑龙江大学,2008.
作者简介:
尹艺璇,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天津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