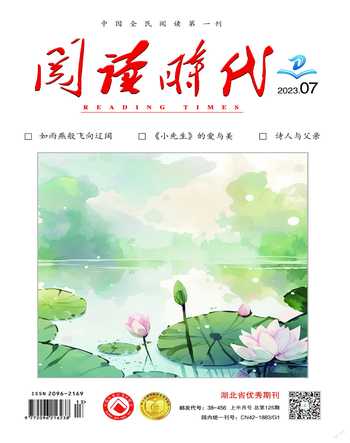诗人与父亲
余珊珊

1993年初,长子出生,父母远道赶来纽约,在白皑皑的雪景里,迎接家中的第一个外孙。数月之后,父亲写了《抱孙》一诗,让我感而动之的,不仅是他获孙之喜,还有他在诗中带出我降世的情景:
宛如从前,岛城的古屋
一巷蝉声,半窗树影
就这么抱着,摇着
摇着,抱着
另一个初胎的婴儿,你母亲。
就这样,一个男婴诞生,在我初为人母之际,不仅让我贴身抱住满怀的生之奥妙,也让我品尝了三十五年前另一对父母所历经的那一片心境。读罢此诗,热泪盈眶之际,我蓦然醒悟,一种看似清淡的关系,背后其实有着怎样的记忆。而一种关系似乎总要和其他的关系相互印证,才能看得清明透彻。
所谓清淡的关系,其实也只是自我赴美求学以后。初到堪萨斯州读书,狂热于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塞尚与毕加索的艺术史之余,只能偶在图书馆的中文报刊上与父亲神交一番——但即使这样也是奢侈的。例外是在赴美翌年,父母相偕来美,探望在美的三个女儿。去密歇根看了佩珊后,我们即和幼珊四人一车从俄勒冈“长征”至加州的一号公路。自从两地相隔后,和父母团聚的日子总共不超半年,而和父亲的就更少了。家书总由母亲执笔,报告身边大小事务;而通越洋电话时,也总是母亲接听居多。然而每教我哽咽不能自已的,总是接获父亲手书时。在他那一笔不苟的手迹之后,是平时难以察觉的感情,似乎他的大喜大怒,全浓缩到他的文字之中了。
初识父亲的人,少有不惊讶的。在他浩瀚诗文中显现的魂魄,俨然是一气吞山河、声震天地的七英尺之躯。及至眼前,儒雅的外表、含蓄的言行,叫人难以置信这五英尺刚过的身材后,翻跃着现代文学中的巨风大浪。但将近一甲子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又让人不得不惊诧于那两道粗眉及鏡片后,确实闪烁着一代文豪的智慧之光。许多朋友就曾向我表示:“你父亲实在不像他的文章!”至少他假想成真的一个女婿就这么认为——我的先生即戏称他为“小巨人”。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中,似乎隐藏了一座冰封的火山,仿佛只有在笔端纸面引爆才安全。
然而能和书中的父亲相互印证一件事,就是父亲坐在驾驶盘后面时,那时常觉得他像披着盔甲冲锋的武士,不然就是开着八缸跑车呼啸来去的选手。这倒不是说父亲开车像那些玩命之徒,而是他手中握的是方向盘而不是笔时,似乎凭借的更是一种本能,呼之即出而不再有束缚。在父亲《高远的联想》《咦啊西部》那几篇文章中,已有最好的描写。
我们四姊妹小的时候,父亲在坐镇书房与奔波课堂之余,常与我们戏耍、讲故事。爱伦·坡的恐怖故事在父亲讲来格外悚然,他总挑在晚上,将周围的电灯关掉——在日式老屋阴影暗角的烘托下,父亲对细节不厌其烦地交代,语气声调的掌握,遣词用字的讲究,气氛已够幽魅诡异的了。而讲到高潮,他往往将手电筒往脸上一照,在尖叫声四起时,听者讲者都过足了瘾。他也常在夏夜我们做功课时,屏息站在我们桌前的窗外阴森而笑,等我们不知所以抬头尖叫时,即拊掌大笑。这方面,父亲有似顽童。
1971年,父亲应美国丹佛寺钟学院之聘而前往教书。那一年是他较为悠闲的一年,远离台北,教职又轻,十分满足了我们对父亲角色的需求。那一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中,在离家十分钟的一所公立中学注了册。自此,每天早上即由父亲开车送往。在那十分钟之内,我们通常扭开收音机,从披头士、琼·贝兹一直听到鲍勃·迪伦。当时,越战尚未结束,却已接近尾声,不像我们1966年经过加州时,满街长发披肩的嬉皮,大麻随处可闻,我虽只有八岁,却在满眼惊奇中感到某种弥漫人心的气氛。回台湾后,父亲力倡摇滚乐,原因不仅在其动人心弦的节奏,更在其现代诗般的歌词。而此后,我却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有一种莫名的认同,这实在是因为曾经身历其境。
西出丹佛城的“阳关”,回到台北故居后,似乎一切又走上往日的轨道,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父亲又开始陷入身兼数职的日子:从教授、诗人、评审、译者、儿子到丈夫。而“父亲”在众人瓜分下,变得只有好几分之一。我常想,一个人要在创作上有所成就,总要在家人和自我间权衡轻重。在父亲数十本的著作后,是他必须关起门来,将自己摒于一切人声电视机车应酬之外,像闭关入定,牺牲无数的“人情”,才能进入自我,进入一切创作的半昏迷状态。父亲写作时,既不一烟在口,也不一杯在手,凭借的全是他异常丰富而活跃的脑细胞。然而追在他身后永无了断的稿债演讲评审开会,也常教父亲咬牙切齿,当桌而捶。有时在全无防范下,他在书房里的惊人一拍,常使我们姊妹心为之一跳。只听见他在房中叫道:“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找不完的人!”然而他从不当面推辞,宁可骂过之后又为人作序去也。习惯之后,我们也觉得好笑。父亲每天几乎总伏案至深夜一两点,写毕即睡,从没听说他患过失眠,也没见过他晚起。而他的睡姿有如卧倒的立正。仰面朝天、头枕中央,双臂规规矩矩地放在两侧,被角掖在下颏,有如一个四平八稳的对称字。我们姊妹常觉这实在不可思议,却从来没有问过母亲觉得如何。
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那十多年,我们全家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宿舍背山面海,每天伴我们入眠的是吐露港上的潋滟,七仙岭下的渔灯,而人间的烟火似乎都远远隐遁在山下了。我们姊妹当时渐近青少年的尾巴,虽仍青涩稚嫩,但在餐桌上有时竟能加入父母的谈话。我们当时对中外文学都极为倾心,也略涉一二,偶然也提些问题、表示看法,而和父亲不谋而合时,即心中暗喜。与此同时的是访客的精彩有趣,常吸引着我如磁石般定坐其间,聆听一席席抛球般的妙喻,或一段段深而博的高论。然而在我如一块海绵,将触角怒伸、感官张开而饱吸之际,隐隐,几乎自己也无所觉的,是有某种不安、某种焦虑,觉得这种幸福是一只漏网,网不住时间这种细沙,在其无孔不入的刹那,一切将如流星般逝去。
而在我长大成人,远到异国开辟另一片疆土后,常觉从前恍若隔世,眼前既无一景可溯以往,亦无一人能接起少时。不但先生是在新大陆相识的,一双子女更是在新大陆出生的。生命变得有如电影的蒙太奇,跳接得太快太离奇,从一片景色过渡到另一片,从一群相识衔接到另一群时,这之间是如何一环环相连扣的呢?有何必然的脉络、有何永恒的道理可循吗?而在追溯到起点,在极度思念那远方的一事一物而无以聊慰时,我拿起了父亲的诗集。在以前忽略的那一字一行间,我步入了时光的隧道,在扑面而来的潮思海绪里,我不但走过从前的自己,还走入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从旧大陆南迁而来的最后一批候鸟,带着史前的记忆,在季候风转向而回不去的岛屿,一住就是一辈子。好在,今风势已缓,候鸟不但纷纷探首,亦个别上路,只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惘然。其实,于殷勤回归之际,这片岛屿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无论有形的、无形的都已根植在这块土地上,成为照眼的地标。
我在父亲的诗文中,找到这种失魂的呓语,一种移居他乡的无奈。然而在铅字中反映出来的,却渐由无奈而接受而投入,追昔抚今,成为另一种乡愁。而我,如今不也在新大陆上思念那海岛的人与物、我的童年吗?只不过物换星移,中间差了一代罢了。我仿佛随时可以回去,却又不能真正地回到过去。于是,我有些了然,有些伤痛,又有些释然,像我父亲一样。毕竟,宇宙的定律是不轻易改变的,而血,总是从上游流到下游。
(源自《余光中都是你》,离萧天荐稿,有删节)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