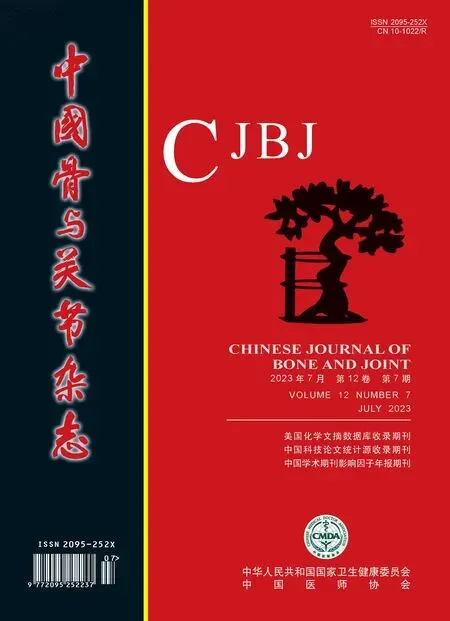微创通道下后路一期经椎间孔病灶清除、椎间植骨融合治疗单节段腰椎感染性疾病
陈龙伟 魏见伟 刘海飞 刘兰涛 薛慧 解思毓 王德春
腰椎感染性疾病发病年龄集中在 50~70 岁人群[1],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增高[2-3]。腰椎感染性疾病以化脓性、肉芽肿性 (结核性、布氏杆菌性、真菌性) 最常见。文献报道 55%~80% 的化脓性感染的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7%~33% 的为大肠埃希菌,然后为变形杆菌属和克雷伯菌属,近年来脊柱结核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4]。布氏杆菌病文献报道骨关节受累发生率在 10%~85%,其中高达 54%有脊柱受累[5]。部分患者通过尽早、规范、足量应用敏感抗生素可以获得治愈[6],但仍有很大部分患者需要手术治疗。
买尔旦·买买提等[7]采用经椎间孔腰椎椎间融合术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 治疗 34例胸腰段脊柱结核患者,术后优良率为 94%,效果良好。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间融合术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MIS-TLIF) 借助微创通道,可以减少肌肉剥离带来的手术创伤,在治疗腰椎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等退变性疾病时显现出明显优势。但应用 MIS-TLIF 治疗腰椎感染性疾病的具体临床效果鲜见报道。回顾性分析我科于 2017 年1月至 2019 年 12 月,应用一期后路MIS-TLIF 行病灶清除、取髂骨椎间植骨融合治疗的25例单一间隙腰椎感染患者,将结果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1) 明确诊断为腰椎感染性疾病者;(2) 严重的持续性腰痛伴或不伴神经功能障碍者;(3) 病变仅累及一个运动节段者;(4) 无严重局部畸形者。
2.排除标准:(1) 无法耐受手术,如严重心、肺的功能障碍或合并其它基础疾病者;(2) 病变破坏范围较大,后路无法进行病灶清除植骨融合者;(3) 合并全身其它系统活动性结核患者。
明确诊断腰椎感染性疾病需符合以下标准中的一条或多条:(1) 细菌培养得到明确的病原学证据;(2) 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或病原高能量基因测序证实为某种病原感染;(3) 组织病理学证实为感染性改变;(4) 抗感染治疗有效[8]。
二、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25例,其中男 15例,女 10 例;年龄 24~77 岁,平均 (61.1±11.2) 岁;病程 0.5~12 个月,平均 (2.5±2.4) 个月。化脓性腰椎感染性病变 9例,结核性腰椎感染性疾病 5例,布氏杆菌病腰椎感染性疾病 3例,原因不明的感染 8例。发病部位:L1~23例 (12%),L2~33例 (12%),L3~45例 (20%),L4~59例 (36%),L5~S15例 (20%)。7例合并糖尿病,13例合并高血压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表1)。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腰背部疼痛,休息及口服消炎镇痛药物无明显缓解。所有患者均无明显诱因。13例有发热病史,其中仅 1例有明显午后低热伴乏力、盗汗并最终确诊为腰椎结核。3例发热时出现寒战。11例以腰痛为主,14例腰痛合并下肢放射性疼痛,10 例合并下肢肌力减弱,5例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表1 本组 25例患者的一般资料Tab.1 Basic data of the 25 cases included in the study
三、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5例 (20%) 出现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为10.1×109~13.0×109/ L;21例 (84%) 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 > 20 mm / h,范围在 25~95 mm / 1 h;23例 (92%)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增高 > 6 mg / L,范围在6.5~259.5 mg / L。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X 线、CT 及 MRI 检查。腰椎 X 线片无明显骨质破坏共 14例,其余 11例可见明显骨质破坏,节段塌陷。所有 25例 CT 扫描及三维重建可见病灶节段上下终板虫蚀样改变,不同程度骨质破坏,部分病例可见死骨形成。腰椎 MRI 显示 T1加权像为低信号,T2加权像呈高信号或混杂信号,范围累及病变椎间盘及邻近椎体,椎旁或椎管内脓肿形成。
四、治疗方法
1.术前准备:高度怀疑特异性感染患者需进行血清布氏杆菌凝集试验和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cell spot test of tuberculosis infection,T-SPOT.TB)。术前诊断为结核的患者常规给予 2 周四联 (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 抗结核药物治疗。术前一般不经验性应用抗生素。
2.手术方法: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取俯卧位。选取症状严重或影像学病灶压迫程度较重一侧,中线旁开约 2~3 cm 做纵向切口,钝性分离肌间隙,依次扩张置入 Quadrant 通道,显露病变节段关节突及椎板。切除下关节突及部分上关节突,显露硬膜及神经根并保护,进行清创操作:主要处理无血供的椎间盘组织、坏死骨组织及与之连通的脓肿灶,通过左弯右弯刮匙可以较容易处理对侧椎间组织,保证植骨床清创彻底、准备充分即可,对椎旁及椎前的少量炎性病变可不处理,以免损伤腹腔血管,彻底清创后生理盐水冲洗。在同侧髂后上棘取自体髂骨块及松质颗粒骨,椎间植入松质骨后打入自体髂骨块支撑植骨。置入椎弓根钉棒固定,放置负压引流管。对侧仅行通道下钉棒固定,不进行椎管减压。
3.术后处理:所有病例术中清除的病变组织均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组织病理学检查,如病理学检查怀疑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则行结核 PCR 检测以明确诊断,其中 6例留取标本进行未知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应用敏感抗生素,如无法确定细菌种类,则经验性应用抗生素,待术后病理结果及细菌学培养结果调整抗生素种类。
化脓性腰椎感染患者术后应用抗生素至少6 周[1];结核性腰椎感染患者继续应用四联抗结核药物 1 年;布氏杆菌性腰椎感染患者应用多西环素、利福平至少 6 周。术后 3 天、出院前分别行外周血血常规、ESR、CRP 化验,用于监测治疗效果。
五、随访及疗效评估
所有患者术后定期门诊复查,项目包括血常规、ESR、CRP;结核性腰椎感染患者服药期间每个月定期复查肝功、肾功;术后 3 个月、半年、1 年分别复查 X 线片、CT。
1.临床疗效评估:分别于术前、术后 1 周及末次随访时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对腰背部及下肢疼痛进行评估。末次随访时采用 Kirkaldy-Willis 功能评分对患者术后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优:患者恢复日常生活及正常工作;良:可恢复生活及工作但某些活动受限制;可:可以恢复轻度工作,但需要经常休息;差:无法恢复日常生活及正常工作[7]。
2.影像学评估:患者随访时复查 CT 并进行矢状位重建,按照 Bridwell 标准评价融合效果:Ⅰ 级为骨块融合重塑完全,骨小梁存在;Ⅱ 级为骨块完整,骨块重塑不完全,无透亮区;Ⅲ 级为骨块完整,上方或下方透亮区;Ⅳ 级为骨块塌陷、吸收[7]。
六、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时 VAS 评分、外周血白细胞计数、ESR 及 CRP 指标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结果
所有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均可见不同程度的椎间盘、终板破坏。8例 (32%) 椎间隙发现脓液,10 例 (40%) 术中发现炎性肉芽肿组织突入椎管,2例 (8%) 被侵犯椎体内可见死骨形成,4例 (16%)术中发现干酪样坏死组织。手术时间 (166.0±45.5) min;术中出血量 (120.0±76.8) ml。负压引流管平均放置 (3.2±1.3) 天,引流量共计 (204.3±153.7) ml。所有患者术后随访时间 12~49 个月,平均 (23.9±14.1) 个月。
二、实验室指标
25例均进行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细菌培养阳性 11例 (44%),结果如下:金黄色葡萄球菌 3例 (12%),大肠埃希菌 2例 (8%),肺炎克雷伯杆菌 2例 (8%),布氏杆菌病腰椎感染性疾病 3例(12%)。细菌培养阴性 14例 (56%)。6例进行未知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结果均为阳性,其中 4例与细菌培养结果相符,2例细菌培养结果阴性 (1例为非结核分枝杆菌,1例为微小单胞菌)。
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均证实腰椎感染。除 5例结核性感染组织病理有特征性的肉芽肿性炎、朗格汉斯巨细胞外,9例化脓性感染、3例布氏杆菌病感染以及 8例不明原因感染患者的病理学无特异性表现,包括炎性肉芽、化脓性炎、中性粒细胞浸润、淋巴细胞浸润等,1例布氏杆菌感染和 1例微小单胞菌感染的组织病理中出现了多核巨细胞。
术后第 3 天及出院前复查血常规、CRP、ESR。所有病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术后 3 天较术前均有增高,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出院前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RP 在术后第 3 天及出院前与术前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SR 术后第 3 天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出院前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2)。

表2 手术前后外周血白细胞计数、ESR、CRP 变化Tab.2 Changes of White blood cells, ESR and CRP pre- and postoperatively
三、临床疗效评价
腰部 VAS 评分从术前 (4.7±1.7) 分下降到术后 1 周 (2.1±0.8) 分,末次随访为 (0.3±0.5) 分;存在下肢疼痛的患者,下肢 VAS 评分从术前 (4.2±1.4) 分下降到术后 1 周 (1.2±0.8) 分,末次随访为0 分。术后患者疼痛明显缓解。术后诸次腰部及下肢 VAS 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0),表明该手术可以显著缓解腰痛及下肢疼痛(表3)。

表3 手术前后腰痛及下肢痛 VAS 评分变化Tab.3 VAS score changes of lower back and lower extremity pre- and postoperatively
按照 Kirkaldy-Willis 功能评分,末次随访时15例 (64%) 优,7例 (28%) 良,3例 (8%) 可,优良率 88%。证实该治疗方式有较高的有效率。
四、影像学结果
根据术后 CT 矢状位重建结果进行融合等级评估,术后 3 个月随访,19例 Ⅲ 级融合、6例 Ⅱ 级融合。术后半年随访,22例 Ⅱ 级融合、3例 Ⅲ 级融合,术后 1 年及末次随访均 Ⅰ 级融合。无内固定失败病例。典型病例见图1。

图1 病例 7,患者,女,53 岁,因腰痛伴发热 3 个月入院 a:术前腰椎侧位 X 线片示 L4~5 椎间隙轻度变窄,相对缘终板骨质破坏、硬化;b:术前 CT 示 L4~5 上下终板虫蚀样骨质破坏,部分骨质硬化;c~e:术前 MRI 示 L4~5 上下终板骨质信号变化,T1 加权像呈低信号,T2 加权像及脂肪抑制序列呈高信号,符合椎间盘感染的信号特点;f:术中用于处理对侧间隙的左弯右弯刮匙;g:刮匙处理对侧间隙示意图;h:术中取出的椎间病变组织;i:术中取出的髂骨用于椎间植骨;j、k:术后腰椎正侧位 X 线片示 L4~5 椎间植骨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后;l:术后 3 个月 CT 矢状位重建示植骨块完整,上下方有透亮区,符合 Ⅲ 级融合;m:术后半年,骨块完整,骨块重塑不完全,无透亮区,符合 Ⅱ 级融合;n:术后 1 年,骨块融合重塑完全,骨小梁存在,符合 Ⅰ 级融合Fig.1 Case 7: A 53-year-old female complained low back pain with fever for 3 months a: Preoperative plain X-rays showed mild narrowing of L4-5 intervetebral space, endplate bone destruction at the opposite margins, and sclerosis; b: Preoperative CT scan showed erosion like bone destruction of L4-5 endplate, and some osteosclerosis; c - e: Preoperative MRI showed bone signal changes at the L4-5 endplate, hypointense on T1 weighted images, hyperintense on T2 weighted and fat suppressed sequences, consistent with disc infection; f: Left and right curved curette used to remove the contralateral intervertebral lesion; g: Diagram showing the contralateral intervertebral lesion removed by curved curette; h: Intervertebral lesions removed intraoperatively; i: Crest bone harvested for intervertebral fusion; j - k: Postoperative plain X-rays showed intervetebral bone graft and posterior pedicle screw instrumentation; l: CT scan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showed bone graft intact with lucent areas, consistent with fusion levelⅢ; m: CT scan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showed no lucent areas with uncompleted remodelling of bone graft, consistent with fusion level Ⅱ; n: CT scan 1 year postoperatively showed complete remodelling of bone graft, with trabecular bone crossed, coincided with fusion level Ⅰ
五、并发症
取髂骨切口渗液 1例,清创换药后逐渐愈合。切口深部感染 1例,术后 1 个月出现发热,清创及细菌培养为金黄色葡萄球菌,与第 1 次手术细菌相同,根据细菌培养药敏结果应用万古霉素抗感染治疗后逐渐好转。
讨 论
一、腰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腰椎感染性疾病常见于存在一定基础疾病如糖尿病、恶性肿瘤以及高龄、营养不良、应用激素等患者中,细菌来源多为血源性[6],但本组病例中共有 10 例不合并基础疾病,其发生腰椎感染的原因无法明确。
MRI、ESR、CRP 是发现腰椎感染较为敏感的检查手段,本组 25例中,21例 ESR 升高,23例CRP 升高,所有患者 MRI 均发现病变局部炎性水肿信号,因此,对于慢性腰痛的患者,如果怀疑存在腰椎感染的可能,尽早行 MRI 检查及 ESR、CRP 化验是必要的。
病原学证据是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阳性率有限,本研究仅有 11例 (44%) 得到病原学证据。造成该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术前经验性应用抗生素、病原培养条件受限、特殊类型的病原感染等。
未知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通过对手术标本进行高通量基因测序,并与已知病原基因序列库比对,为腰椎感染的病原诊断提供有力证据,尤其对于普通条件难以培养的细菌,如厌氧菌、结核分枝杆菌、非结核分枝杆菌、布氏杆菌等,具有良好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9]。笔者收集的病例中,有6例进行了未知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均查到了较为准确地感染病原,其中 4例与细菌培养结果一致,另外 2例细菌培养结果为阴性,1例为微小单胞菌,1例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依据此细菌学检查结果,通过严格抗感染治疗,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证实了该技术在腰椎感染性疾病病原学诊断方面的价值。
二、微创通道下一期经椎间孔入路病灶清除、取髂骨植骨治疗腰椎感染性疾病的可行性
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核心措施为彻底病灶清创及应用敏感抗生素。对于已经取得细菌学证据和抗生素敏感试验的患者,及早行抗感染治疗,部分患者可免于手术。如无法取得有效的细菌学证据,经验性用药存在治疗周期长、治疗效果不确切等问题,不及时手术会导致病灶扩散、骨质破坏加重,丧失微创手术时机,该情况下及早手术干预可以缩短病程,减轻患者负担。内固定的应用可以稳定病变节段,对感染的治疗有积极作用,同时,手术清创能够获得较为可靠的组织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查,可以在病原学层面确诊疾病,配合积极有效的抗感染治疗,可以极大地降低感染迁延的风险。尽管MIS-TLIF 手术在微创通道辅助下显露及处理的范围有限,一般 < 2 个运动节段,但由于腰椎感染性疾病通常累及椎间盘及相邻椎体终板,以单节段受累多见,对符合微创适应证的患者,微创条件下对椎间隙的清创操作范围与后路开放手术基本一致,可以做到彻底清创,因此通道辅助的腰椎后路微创手术同样可以应用于大多数腰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10-12]。局部结构稳定是腰椎感染性疾病恢复的重要条件,椎间融合往往是腰椎感染性疾病治疗的结局,也是感染治愈的标志之一。因此,腰椎感染性疾病完成病灶清创后,往往同时进行植骨融合与内固定。因自体骨同时具备骨诱导、骨传导、成骨作用,仍然是植骨材料的金标准[13-14]。
本组 25例均为单节段腰椎感染,并且全部顺利完成了微创通道辅助下的经椎间孔感染病灶清除、取自体髂骨椎间植骨融合、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操作简便,手术过程顺利,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微创经椎间孔入路治疗腰椎感染性疾病的优缺点及适应证、禁忌证
传统腰椎后路手术对椎旁肌肉及后方韧带复合体的损伤重,不利于术后腰椎功能恢复[15]。通道辅助下 MIS-TLIF 视野清晰、操作方便,显露硬膜囊、神经根充分,对于感染病灶侵及椎管内的病例可以做到直接的病灶清除,对于仅需处理椎间盘病灶的病例,可以在直视椎管内结构的条件下,经椎间孔进行病灶清创操作,减少对神经根及硬膜囊的侵扰,避免损伤。由于不需要去除棘突、棘间韧带、棘上韧带等结构,肌肉间隙在通道取出后自动闭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产生的无效腔,利于感染的治疗,较传统后路手术具有显著优势。
相较于前路或侧路手术,MIS-TLIF 需要经椎间孔进行椎间植骨操作,需要去除一侧关节突关节,破坏了部分后柱稳定结构,同时操作空间有限,只能填充颗粒骨或小块髂骨,前柱重建和结构性支撑相对不足,以上两点也使内固定应力较大,增加了内固定松动的风险。
该手术的适应证包括:(1) 确诊或高度疑诊为腰椎感染,包括普通细菌感染及特异性感染;(2)感染以椎间盘为主,一般累及一个运动节段;(3)感染造成的骨质破坏范围不影响椎弓根螺钉置入,且不需要前柱重建。
该手术的禁忌证有:(1) 感染范围超过 2 个运动节段;(2) 骨质破坏严重,短节段内固定无法保持局部稳定;(3) 合并无法耐受手术的基础疾病。
四、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为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受病例数量限制,统计的偏倚较大,没有设置对照组,仅进行了临床疗效的观察,证据等级不高。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丰富临床病例数量以及开展多中心研究,优化实验组及对照组设置,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为临床诊疗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综上所述,微创通道下一期后路经椎间孔病灶清除、椎间融合相对于传统开放手术创伤更小,临床效果优良,是治疗腰椎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