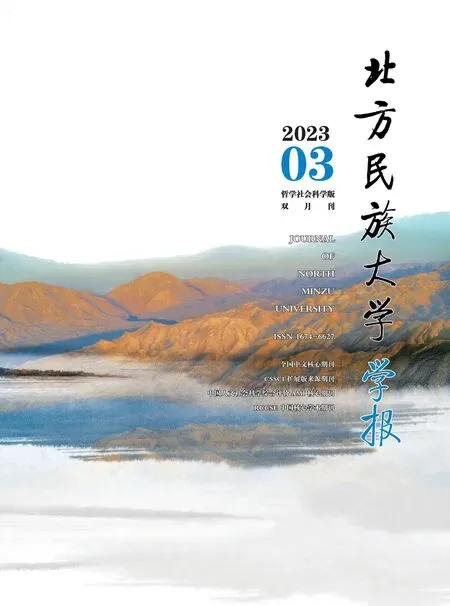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夏文学内涵及价值探论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西夏文学以深厚的儒家主流文化为根基,以传统主流文学为渊源,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儒外蕃”的文化形态赋予西夏文学崇尚儒学的精神内质,西夏文学在文学体裁上涵盖诗、表、奏书、铭、奏章、表文、书简、碑铭、谚语、歌辞等,在内容上包括政教伦理、社会民生、颂赞歌辞、风俗民情,与儒家主流的文学精神一脉相承。此外,西夏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如奏章的雅正华美、书表的犀利论辩、诗歌谚语的通俗,总体上具备完整的创作体系。到目前为止,支撑西夏文学研究的史料文献较为丰富,综合史料层面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书事》《俄藏黑水城文献》等;文学史料层面有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王仁俊的《西夏文缀》《西夏艺文志》、罗福颐辑《西夏文存》等;文本层面有《新集锦合辞》《新集碎金置掌文》《圣立义海》《西夏诗集》《宫廷诗集》《拜寺沟方塔佚名诗集》等。一些学者从文献梳理与文学个案研究层面对西夏文学的相关问题予以研究,使西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拓展。事实上,北宋、西夏、辽、金文学共同构成了10—12 世纪中华文学的创作格局,共同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学的艺术宝库。今天我们研究西夏文学,既需要进一步整合、汇集、梳理相关文学史料,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也需要拓展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尤其将西夏文学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之下,以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视角,深入发掘西夏文学蕴含的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为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与互融模式提供参考路径,从而使西夏文学的研究更立体、更具时代意义。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发掘西夏文学的精神内涵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学界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内涵提供了有效的学理依据,也为研究主流文学与多民族文学互动交融提供了理论支撑。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出了“中华文学”的概念,并编写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对中华文学的形成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梳理与呈现。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首次以历时性视角对历朝历代多民族文学关系进行了梳理。此后,刘跃进、朝戈金、关纪新、李晓峰等学者也提出构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倡议。面对“中华文学一体”与“多民族文学交流交融”的新理论框架,如何揭示多民族、多地域文学之间的互动交融方式,成为学界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课题,也带动学界对古代多民族文学予以全面关注与研究。西夏文学作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意识在10—12 世纪得以进一步加固与彰显的必然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追溯到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的主流思想催化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在各个时代的生成与延续,这也是历代朝代更迭但社会基础始终稳固的根本所在。从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伴随着历史发展和思想自觉而变迁”[1]。由此,文化认同、家国认同与情感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进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认知与情感体验,自然潜入文化与文学内质的构建之中,文学形态也在历时与共时的时空网络中渐次变化与交融,并最终形成中华文化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体为历史基础,是深入发掘西夏文学内在文化根基与精神内涵的核心价值引领。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历史进程来看,以战国时代《公羊传》提出“大一统”思想为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已由自在状态开始走向自觉状态,并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共同追求的政治理念,也影响着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构建。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大一统的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观、大一统的思想观以及大一统的民族观”[2],“大一统”思想的实质是崇尚政治统一、文化和合,并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建构和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国历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源与精神纽带。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高度强化的时代,理学更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将传统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伦理思想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通过政统与文统的统一使“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得到进一步加强。西夏对中原王朝与边疆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元昊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中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3](151)。元昊“认祖归宗”有其实质性目的,但至少说明他有着“华夷一体”的根本性认识。此外,西夏文人对北宋社会的政治形态亦有清晰的认识。西夏都统嵬名济在宋夏永乐之战后,给宋将刘昌祚的书信中云:“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3](299)。守“礼乐”而归为“正”,是儒家思想主导下北宋社会政治形态的根本体现,这也是实现政治与文化一统的必然路径。西夏对中原王朝采取的礼乐制度与崇仁尚德相表里的政治治理体系深表认同,元代文人虞集对西夏社会治理的方式有所概括,其在《西夏斡公画像赞》中说:“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3](447)。可见,西夏社会治理方式以事礼、尊亲为外在维度,以经典化育人心为内在维度,而这恰恰是儒家文化倡导的治世理念。可以说,西夏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传统主流文化,显现出对传统主流文化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西夏从文字、官职、礼制、文化、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接受并融汇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覆盖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层面。西夏学专家史金波说:“宋辽夏金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断加大,共同的历史基因增强。各王朝出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自觉或自发地涵化、认同,其中包括物质方面、制度方面和深层次的精神方面。各王朝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又各自有新的发展和弘扬,对中华民族文化作出新的贡献。”[4]这段话精准地概括了西夏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认同及贡献。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对汉文化精神的学习与汲取,李继迁曾云:“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5](122)。事实上,李继迁“成霸王之业”的需求背后是自觉的“慕汉心理”,将游牧文化崇尚的刚毅尚武精神与中原儒家文化倡导的诗书礼乐精神融合,“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这是西夏对儒家礼乐文化接受与认同的最好说明。李元昊秉承这一思路,他一方面认识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3](146)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树立道德纲常,主动在文字、礼仪、典章、制度、科举等方面进行文化吸纳,进一步加快了“内儒外蕃”文化模式的建构进程,从而催生了合于主流的文化认知、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身份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意识由此得到巩固与加强。传统儒学经过元昊、谅祚、秉常、乾顺的提倡,至仁孝时期达到全盛,从而成为西夏党项羌族的主体价值与文化信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北宋时期的建构与壮大。
中华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流淌着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血脉,是对儒家仁爱、和合、大同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梁庭望先生认为“中华文学的背景是中华文化”,并以地域版图分布将中华文化圈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这四个地域文化圈共同组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辐射其他区域文化的中华一体文化[6](113~129)。按照以上划分,西夏文化显然属于“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也就是说,北宋与西夏在同一历史时空下的精神交集既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中华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呈现,并构成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形态,而民族的交往必然催生文学的互动。事实上,“从文学现象上看,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学互动,在不同的时代,或隐或显,从来没有停止过”[7]。西夏文学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底色,并与主流文学在内质上交汇融通,在外延上各呈其貌,在历时与共时的空间中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格局。中华文学是历代多民族文学在互动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文学气象,也是多民族对中华文化精神集体认同的必然结果。
作为历史与文化凝结而成的精神形态,文学总是承载着政治制度、历史镜像、文化思潮、人文地理、风俗人情等社会图景,尤其是文化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使文学具有跨越时空与语言的独特沟通功能,从而使文化自觉意识通过文学书写转化为情感与心灵体验,最终呈现出多民族文学共同呈现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盛景,也构建出中华文学丰富而广阔的精神版图,西夏文学正是西夏文人对儒家主流文化进行精神与情感体认的产物。西夏文人骨勒茂才在其《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云:“仁义忠信,五常六艺,尽皆全备,孝顺父母,六亲和合”[8](42);“搜寻文字,纸笔墨砚,学习圣典,立身行道,世间扬名,行行禀德,国人敬爱,万人取则,堪为叹誉,因此加官”[8](55~56)。从这段材料的表述可见,西夏文人将修身立德、传承经典与追求功名紧密结合在一起,与传统儒家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价值取向如出一辙。这一价值观念投射到文学创作上,则表现为对儒家礼乐制度与修身立德的尊崇与践行。在《宫廷诗集》《新集锦合辞》《新集碎金置掌文》《德行集》等文学文本中,君臣同德、敬天祭祖、乐道善仪、劝世赞德、臣子修治、天下同乐等内容集中呈现,与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达到高度契合,这也是西夏对中华文化予以认同并接受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不断强化的文化基础,并将多民族的精神与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多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与价值归属,而文学则成为承载思想、精神与情感的重要介质与载体,体现着价值观念、精神世界、心理状态与审美追求。西夏文学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同时与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主流文脉一脉相承。不论是公文文体的庄重雅正、诗歌中的人情事理,还是谚语格言中的民俗民风,无不体现着正得失、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学功能,因而与主流文学形成互融互补、表里呼应的创作格局,也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学在10—12世纪的精神与审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9]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进程中,北宋与西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重要的一环,西夏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记录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比如《夏圣根赞歌》通过追溯党项先祖繁衍与征战的史迹,深表对宗族历史的礼赞,其在叙述方式上与《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相似,有明显的承继性。《月月乐诗》是西夏诗歌中比较经典的一首作品,其仿照《诗经》的《七月》,按照月份时序依次叙述西北边地的百姓“半牧半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此外,《劝世歌》《夫子善仪歌》《天下同乐歌》等诗歌作品,继承了儒家思想中孝悌、仁善与和谐的思想,充分彰显了文学的教化与现实功能,与儒家主流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正如有学者所说:“西夏文学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渗透着汉民族文学的根基和渊源,这是夏、汉民族在各个领域长期密切交往、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10]西夏文学研究应以中华文化与文学一体观为基本立场,以多民族文学互动交融为研究视角,将西夏文学的历史原貌与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深度发掘其创作主题、思想内涵与艺术风貌生成的历史动因与文化根底。
二、以中华文学一体格局为基础,重新审视西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文学以汉文学为主体,以其他多民族文学为辅翼,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这一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交相呼应,互为表里,共同彰显了历代多民族在政治、文化、精神、情感与审美层面的互渗互融。可以说,古代多民族文学以其特有的情感与审美表征,不仅清晰呈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变迁与心灵历程,也记录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精神皈依,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并呈现出“时间的久远性、空间的广阔性、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以及语言形式的多样性”[11]的特点。因此,各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相互联系、彼此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学丰富多彩的形态。对于西夏文学而言,其“由早期单一的口传文学逐渐发展成具有多种类、多题材、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性文学态势”[12],这种由“单”到“多”的增量式、扩充式的发展,正是西夏与北宋不断交往的文学表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10—12世纪进一步凝聚的必然结果。从此意义上讲,尽管西夏文学未能如同时期辽、金文学那般繁荣,但其对中华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彰显,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承载与光大,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在中华文学一体格局的视域下,西夏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有着充分体现。
中华文学是历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构建起来的本土文学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标识与精神家园。左东岭教授在《中华文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中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学是否能够纳入中华文学史的叙述格局,其标准应该是是否与主流文学史发生了接触与关联,是否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和作出了贡献。”[13]立足于“是否与主流文学史发生了接触与关联”这一维度,西夏文学显然与主流文学有着密切关联,并成为中华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的主流文化使得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延续,逐步加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凝聚力,这无疑成为北宋与西夏文学互动交融的强大历史背景与共同基础。在北宋学者沈括《鄜延凯歌》一诗中,“天威略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14](8012)一句生动呈现了北宋与西夏文学交往的程度。早在先秦时期,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集中体现,并成为沟通天人、表达事理、承载思想与流露情感的桥梁,同时也是中国多民族跨越地域与语言阻滞,实现思想与情感交流交融的最好载体。西夏文学的深层内涵是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承载,“西夏文学中汉语文学、西夏语文学中的汉语文学元素,恰好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15]。语言仅仅是思想与情感的外在呈现形式,中华文化精神才是西夏文学的深层内涵与思想表征。
北宋文学与西夏文学在内质上交汇融通,在外延上各呈其貌,从而在历时与共时的空间中构成多元一体的文学格局,这既是儒家文化“和”的体现,也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中华文学的思想根底与精神内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辐射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方式大略有二:在文化层面,少数民族通过整理、翻译儒家元典,主动接受儒家崇礼尚德的主流思想,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态;在文学层面,少数民族文人主动接受以《诗经》为典范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传承“诗”学精神的过程中向礼乐文明回归。显然,西夏文学的精神内蕴恰恰是这两个方面聚合而成的。西夏学专家聂鸿音在其《西夏译〈诗〉考》一文中,列举了西夏在翻译《孟子》《论语全解》《孝经传》《类林》《经史杂抄》等汉文文献时,大量征引《诗经》中的诗句,如翻译《类林》时引用《鄘风·相鼠》中的“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翻译《孝经传·圣治》篇时引用《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翻译《孟子·滕文公上》时引用《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16]。《诗经》不仅是中华文学精神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符号。引诗、赋诗、颂诗活动在先秦时期便已盛行,“引诗”的最终目的在于对儒家倡导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风俗礼仪等予以传承,从而不断稳固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事实上,《诗经》作为文学文本在各种典籍中被征引,恰恰说明后世推崇《诗经》的核心要义在于其所承载的礼乐文明精神,其不断被运用和阐释,成为联结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对中华民族的交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夏文人在翻译儒家经典时采用“引诗”的方式,充分说明以下三点。其一,西夏文人对儒家文化精神实质有着明确认知。《诗经》是代表儒家礼乐制度与道德伦理文化的符号,“引诗”的目的在于承续儒家文化精神,寻求价值归属,使西夏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其二,西夏文人对儒家文化的精神意蕴有着深刻了解。西夏文人对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君子”等核心思想要义有着集中的关注,并使之成为精神与道德自觉,建构融于主流并共同尊崇践行的社会价值体系。其三,西夏文人主动接受儒家文化。在继承与发扬《诗经》的典范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西夏文人认识到《诗经》是礼乐制度的诗性体现,而“引诗”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礼乐文化的崇尚,西夏文人对传统“引诗”活动的主动接受,其深层动机是对儒家礼乐文化、孝悌观念、仁爱思想的皈依,“诗”学精神也就成为传承和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纽带。
西夏文人主动而自觉接受以《诗经》为圭臬的主流文学传统,儒家文化精神血脉不仅通过文化元典整理的方式进入西夏文人的观念,同时也贯穿于其创作中,西夏文人对儒家文化形成精神与情感的同步认同。在此过程中,维护正统、修身立德、孝悌为本、守礼归仁逐渐成为西夏文人的精神支柱与价值标准,并渗透在诗、铭、奏章、表文、碑铭、谚语等各类文体中。西夏文人不仅将《贞观政要》《论语全解》《孙子传》《孝经》《孟子传》翻译为西夏文,同时也用汉文作诗,今存《拜寺沟方塔佚名诗集》代表着西夏文人的创作水准,流露出崇尚修德、淡泊心性的人格胸襟[17](265~286)。例如,《僧》诗中的“直饶名利喧俗耳,是事俱无染我身”,与道家思想淡泊名利、超越世俗的精神高度契合;《忠臣》诗中的“披肝露胆尽勤诚,辅翼吾君道德明”,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同根同源;《儒将》诗中的“清裘缓带清邦国,史典斑斑勋业彰”,《武将》诗中的“将军武库播尘寰,勋业由来自玉关”,深刻显现出西夏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这与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几无二致。即使是《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样的辞典,也同样以“教则以仁利物,以救今时”[8](5)为编撰准则,处处尽显崇尚“忠”“孝”“慈”“爱”的伦理观念,由此可见,“以救今时”不仅仅是发挥文学作品有补现实的作用,还有着用儒家文化泽被天下的精神内涵,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所云:“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8](5)。可见,西夏文人已经意识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是文化合流的必然,而这种合流正是向儒家文化的自觉回归。
西夏文学根植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形态,深度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从而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西夏文人的文集、作品为拓展中华文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史料;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夏文学所呈现的地域风貌是中华文化多样化的生动体现;从思想的角度而言,西夏文学中的格言、谚语等俗文学中流露的人生道理,折射出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从文体的角度而言,西夏文学涵盖诗歌、碑铭、奏疏、表文、序文、公文、谚语、格言、民谣等,无一不秉承着主流文学的精神脉络与创作源流。此外,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与精神内涵上,西夏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秉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积极发挥文学“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的现实功能。例如,《上夏崇宗皇帝乾顺书》云:“自用兵延庆以来,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3](371)这段奏疏看似是以白描手法述说战争带来的影响,实则以有力的论辩发出对战争的谴责,尤其是最后的诘问表达了体恤民情、渴望和平的情感。此外,西夏文学在艺术审美层面具有雅俗并存的特征,既有“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18](107)的骈偶华丽之章,也有“白石粒不错乱,黑谷河不改变”[19](25)的通俗朴素之语,这种文学书写方式与10—13 世纪中国文学由雅文学向俗文学过渡的整体创作格局一致。这也恰恰说明,西夏文学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不论是思想情感的表达,还是艺术方式的呈现,都与中华文化及文学的发展进程共生共存,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与历史镜像,不断唤起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自信。
三、结 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文化的统摄之下,多民族和谐共生并始终聚合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连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20]我们一定要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本位与时代高度,正确认识历史上多民族文学及其发展进程,认真总结多民族文学交流融汇的经验与规律,为构建中华文学的历史与精神版图提供新材料、新视野和新问题。学界在关注和研究历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同时,应注重不同时期多民族文学交融,其目的则是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传统与审美追求,从而以文学为重要的精神维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与情感之源。各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文学格局中的子系统,在外延上展现出自我的艺术风貌,在内质上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水乳交融。当我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研究原则与视角,各民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特色恰恰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广阔性与多元性的外在表征,而其内质则是中华文化“守礼重仁”“修身崇德”与“追求和合大同”的精神本源。西夏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学与中华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