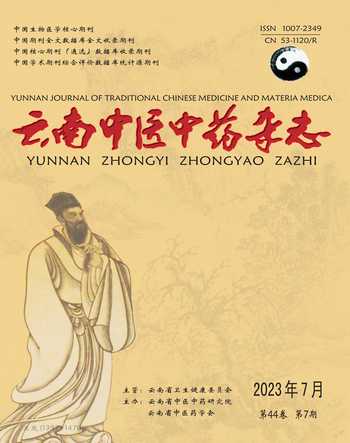中药联合穴位埋线治疗肾虚血瘀型慢性盆腔疼痛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季晓黎 宋晓庆



摘要:目的 观察中药内服联合穴位埋线治疗肾虚血瘀型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所致慢性盆腔疼痛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80例肾虚血瘀型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所致慢性盆腔疼痛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2组各40例,治疗组予中药内服联合穴位埋线治疗,对照组予单纯中药内服,共治疗三个月,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疗效、SF-MPQ量表评分、中医证候评分、盆腔体征量表评分及WHOQOL-BREF量表评分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且2组患者治疗后各时间节点SF-MPQ量表评分、中医证候评分、盆腔体征量表评分较前明显降低、WHOQO-LBREF量表评分较前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中药内服联合穴位埋线在缓解肾虚血瘀型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所致慢性盆腔疼痛患者盆腔疼痛症状,减轻盆腔体征,改善中医证候以及提高生存质量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值得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中药内服;穴位埋线;肾虚血瘀;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慢性盆腔疼痛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23)07-0001-03
慢性盆腔疼痛(chronic pelvic pain,CPP)是指由各种功能性或(和)器质性原因引起的以盆腔及其周围组织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综合征[1]。该病病程较长,一般超过6个月[2]。其发病率约为2.1%~24%,育龄期女性为高发人群[3]。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sequelae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SPID)、盆腔淤血综合征、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原发性痛经、盆腔术后粘连及心理因素等都可以导致CPP[4],其中SPID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约23%~30%CPP由SPID所致[5-6]。本病病情顽固,缠绵难愈,严重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目前临床针对CPP治疗方法较多,但疗效均不尽如人意,本课题使用中药内服联合穴位埋线对80例SPID所致CPP患者进行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本研究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21KL-004)),旨在探索“针药结合”内外合治方案治疗本病的特色与优势,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20年1月-2021年12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部确诊为SPID所致的CPP,且辨证为肾虚血瘀证的患者经筛选合格后最终共入组85例,其中完成试验80例(治疗组40例、对照组40例),脱落5例(治疗组3例、对照组2例),脱落率为5.88%(治疗组3.53%、对照组2.35%)。
1.2 分组 将80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2组各40例。治疗组年龄20~50岁,平均34.8±1.2岁,病程13.5~46.5月,平均25.5±2月;对照组年龄20~50岁,平均34.65±1.5岁,病程13.5~47月,平均病程27±2.2月。2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3 诊断标准
1.3.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修订版)相关内容制定[7]。(1)症状:下腹部疼痛,疼痛为持续性,持续时间在6个月以上,疼痛症状在劳累、性生活后和月经期间加重,其他的常见症状为发热、食欲不振、阴道分泌物增多、月经不调。(2)体征:子宫颈举痛,宫骶韧带增粗或触痛;子宫欠活动,位置固定,有压痛;一侧或两侧附件区可扪及条状、片状增厚,甚至能扪及囊性肿物,压痛,多伴有压痛。(3)辅助检查:阴道B超检查可提示输卵管管壁增厚、管腔积液,可伴有盆腔游离液体或输卵管卵巢包块。
1.3.2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盆腔炎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制定[8]。主症:(1)下腹绵绵作痛或刺痛。(2)腰腿酸痛。(3)带下量多,色白质清稀。次症:(1)遇劳累下腹或腰骶部酸痛加重。(2)头晕耳鸣。(3)经量多或少。(4)经血色暗夹块。(5)夜尿频多。舌脉:舌质淡暗或有瘀点瘀斑,苔白或腻,脉沉涩。以上主症具备2项或以上,次症2项或以上,结合舌脉,即可辨证为肾虚血瘀证。
1.4 纳入标准 (1)确诊为西医SPID所致CPP。(2)中医辨证为肾虚血瘀证。(3)年龄分布在20~50岁。④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凡符合上述要求者,即可纳入研究病例。
1.5 排除标准 (1)病因不属于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者。(2)妊娠期或近半年准备妊娠的妇女,哺乳期妇女。(3)合并有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糖尿病等严重疾病患者。(4)有精神异常或不愿合作者,无法合作者。(5)过敏体质,对多种药物过敏、瘢痕体质或埋线区皮肤有破损者。(6)近一个月内曾采用同类药物治疗,导致药物疗效难以判断者。
1.6 治疗方法 (1)对照组:予中药杜断桑寄失笑散加减口服,药物组成:川续断15 g,川牛膝15 g,杜仲15 g,桑寄生15 g,川芎15 g,生蒲黄20 g,五灵脂15 g,大血藤15 g,延胡索20 g,丹参15 g,三棱15 g,姜黄15 g;加减变化:下腹疼痛较甚,加水蛭5 g,土鳖虫5 g;腹胀者,加木香15 g;带下量多者加白土苓15 g,荆芥15 g;湿气较重者加薏苡仁30 g,茯苓15 g;有盆腔炎性包块者,加莪术15 g,山慈菇15 g。使用煎药机煎药,1日3次,每次100mL,经期不停药。连服3个月。(2)治疗组:中药口服同对照组,并联合穴位埋线治疗。具体操作:嘱患者取仰卧位,暴露埋线部位,常规洗手后使用碘伏对埋线皮肤局部进行消毒,操作者左手持一次性埋线针(北京首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苏械注准20162271059),右手持无菌镊子夹取可吸收性外科缝线1根(长度为2cm,山东博达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国械注准20173650800)完全穿入一次性埋线针内。押手捏起或撑开穴位两旁的皮肤,刺手持埋线针直刺入穴位对应的深度,询问患者得气后,用针芯抵住可吸收性外科缝线缓缓退出针管,将可吸收性外科缝线留在穴位内。若患者出现少量出血,可用无菌棉签或棉球按压针孔数分钟后取掉,最后贴上一次性穴位貼敷。选穴:第一组气海、关元、中极、子宫、足三里;第二组天枢、水道、归来、三阴交,2组分次交替进行(可吸收性外科缝线在体内15天左右可自行吸收,考虑到不同患者吸收程度不尽相同,予以2组穴位交替进行)。疗程:10天埋线1次,连续3次为1疗程,连续3个疗程,经期不埋线。
1.7 观察指标
1.7.1 临床疗效判定 疾病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8]制定:(1)痊愈:治疗后下腹疼痛/各症状/盆腔体征基本消失,评分下降>95%。(2)显效:评分下降≥70%,<95%。(3)有效:评分下降≥30%,<70%。(4)无效:评分下降<30%。
1.7.2 SF-MPQ量表评分(包括疼痛分级指数、视觉模拟评分法、疼痛强度3个部分) 于治疗前,治疗第4、8周、12周进行评定记分。
1.7.3 中医证候评分 记录2组治疗前,治疗第4、8周、12周的中医证候评分。
1.7.4 盆腔体征量表评分 记录2组治疗前,治疗第4、8周、12周的盆腔体征量表评分。
1.7.5 生存质量评定 记录2组治疗前、治疗后WHOQOL-BREF量表评分。
1.8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前后对照采用配对设计的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H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检验。所有统计分析基于双侧假设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95%)显著高于对照组(8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2组患者治疗各时间节点SF-MPQ量表评分 治疗前2组SF-MPQ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57>0.05);治疗后第4周、第8周、第12周的2组SF-MPQ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治疗后SF-MPQ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
2.3 2组患者治疗各时间节点中医证候评分 治疗前2组中医证候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36>0.05);治疗后第4周、第8周、第12周的2组中医证候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详见表3。
2.4 2组患者治疗各时间节点盆腔体征量表评分 治疗前2组盆腔体征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4周、第8周、第12周的2组中医证候评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详见表4。
2.5 2组患者WHOQO-LBREF量表评分 治疗后2组WHOQO-LBREF量表评分各维度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5。
2.6 不良事件 试验过程中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共发生3例不良事件,包括2例腹泻、1例皮肤过敏。均为轻度不良反应。腹泻考虑与口服中药有关,调整患者的中药处方后患者腹泻症状消失。皮肤过敏者出现在第2次穴位埋线时,患者右侧三阴交埋线后出现轻度皮肤红肿,伴瘙痒,查患者过敏原因,发现患者对胶布过敏,更换为布胶布后过敏反应消失。以上表明“针药合治”中医综合疗法无明显不良反应。
3 讨论
CPP是临床常见病与多发病,也是临床的难治性疾病之一,SPID是其主要致病因素。西医治疗本病主要包括抗生素治疗,止痛药物对症治疗,手术治疗,抗抑郁类药物治疗以及生物反馈电刺激法治疗等,但临床疗效尚不满意。
中医学对CPP尚无明确病名记载,根据其症状特点可与“腹痛”、“妇人腹痛”、“经行腹痛”、“癥瘕”等病互参。本病病因复杂,病机虚实夹杂,病程较长,反复发作。久病留瘀,瘀血阻滞为本病的基本病机[9]。结合中医学“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及肾”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其核心病机为“肾虚血瘀”。肾乃先天之本,主生殖,与胞宫、胞络及冲任二脉的关系密切,正如《诸病源候论》有云:“胞络者,系于肾”。肾气充盛,则冲任气血调和,外邪难以入侵;肾气虚衰,则冲任气血失和,百病自生。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房劳多产,频繁宫腔操作等,致使胞宫胞脉反复受损,局部气血失和,损伤于肾。肾气亏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可致瘀血阻滞,不通则痛。而精血同源,瘀血阻滞,旧血不去,新血不生,气血无以生化,化精乏源又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虚可以导致血瘀,血瘀反过来又可导致肾虚,肾虚与血瘀相互影响,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反复难消,胞宫胞脉之阻滞不断加重,最终导致盆腔疼痛持续加重,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针刺治疗CPP有较为独特的療效,穴位埋线[10-12]作为其延伸和发展更具优势。穴位埋线是指通过特制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将可吸收性外科缝线对穴位进行植入,埋线后,线在体内软化、分解、液化和吸收时,对穴位产生持续、缓慢、柔和、良性的刺激作用,相比普通针刺,更具普适性、持续性,与中药、西药等药物合用,还可增强疗效。有报道称,穴位埋线可改善盆腔炎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局部血管新生,清除发炎介质,快速修复发炎组织,提高机体的应激能力[13]。因此,本研究以“补肾活血、化瘀止痛”为治疗方法,制定了 “杜断寄生失笑散加减联合穴位埋线”的“针药结合”内外合治治疗方案。方案中选穴以任脉、足阳明、足太阴经为主[14],根据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选穴标准,选用气海、关元、足三里、三阴交补肾健脾益气,中极调理冲任,天枢、水道、归来调经止痛,同时根据对症选穴原则,选取治疗妇科疾病的经外奇穴子宫。而方案中口服中药选用全国名老中医杨家林教授经验方杜断桑寄失笑散加减,方中杜仲、川续断、桑寄生补肝肾、强筋骨。生蒲黄、五灵脂、川牛膝、川芎、大血藤、延胡索活血化瘀止痛,丹参活血化瘀,凉血消痈,兼有安神效果,姜黄、三棱活血行气、通经止痛。纵观该“针药结合”治疗方案,内外结合,标本同治,直击“肾虚血瘀”之核心病机,共奏补肾益精,益气扶正,活血化瘀止痛之效。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组SF-MPQ量表评分、中医证候评分、盆腔体征量表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WHOQO-LBREF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穴位埋线治疗SPID所致CPP具有明显临床疗效,“针药结合”方案能有效缓解盆腔疼痛症状,减轻盆腔体征,改善中医证候,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利于促进本病恢复并预防复发。
综上所述,“中药口服联合穴位埋线”的中医综合治疗方案治疗肾虚血瘀证SPID所致CPP患者临床疗效确切,优势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參考文献:
[1]JarrellJF,VilosGA,AllaireC,et al.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pelvic pain[J].JObstet GynaecolCan,2005,27(9):869-910.
[2]Malik Astha et al.Allied health and complementary therapy usage in Australian women with chronic pelvic pain:a cross-sectional study[J].BMC Womens Health,2022,22(1):37-37.
[3]LattheP,LattheM,SayL,et al.WHO system aticre view of prevalence of chronic pelvic pain:angel ected reproductive health morbidity[J].BMC Public Health,2006,6:177.
[4]张晓薇,欧璐.慢性盆腔疼痛的诊断与鉴别诊断[J].实用妇产科杂志,2007,23(4):195-196.
[5]李伟娟,王亚男,马艳宏,等.CPP病因及发病率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2,9(35):142.
[6]陈玮.盆腔炎性疾病所致慢性盆腔疼痛的治疗研究进展[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0.
[7]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感染性疾病协作组.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修订版)[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9,(7):433-437.
[8]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9]尹小兰.从TLRs/MyD88免疫通路调控suPAR、hs-CRP探讨益气清湿化瘀法治疗PID反复发作的疗效及机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7.
[10]姜伟佳,方俊霖,毕婕妤,等.近10年穴位埋线临床应用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中医药导报,2021,27(8):165-169.
[11]Benetti-Pinto CL,Rosa-E-Silva ACJS,Yela DA,et al.Abnormaluterine bleeding[J].Rev Bras Ginecol Obset,2017,39(7):358-368.
[12]Huo J,Zhao J,Yuan Y,et al.Research status of the effect mechanismon catgut-point embedding therapy[J].Chines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2017,37(11):1251-1254.
[13]Shamseer L.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protocols(PRISMA-P)2015[J]:elaboration and explanation.BMJ 2015;350:g7647.
[14]袁静雪,刘志顺.针灸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CPP诊疗特点的文献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3):1236-1240.
(收稿日期:2022-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