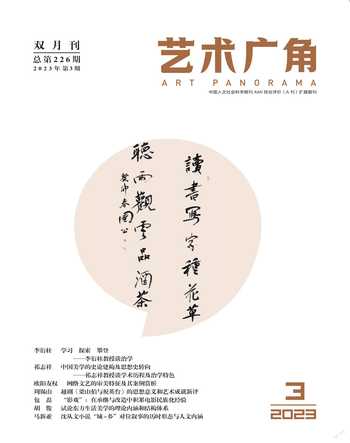沈从文小说“城-乡”对位叙事的历史形态与人文内涵
摘 要 随着“城-乡”对位叙事模式的确立,沈从文小说的人学体系完成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伦理观到生存论、从文本策略到价值立场的转换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之下,由于文明与落后、西方与东方的权力结构的套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度成为旧中国的形象的指称,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具体所指; “城-乡”对位叙事结构一方面提供给沈从文区别于主流乡土小说的视点与内在框架,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的乡土小说朝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城-乡”对位;叙事结构;人学思想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鲁迅文学创作的典范影响之下,中国新文学出现一股乡土文学创作的热潮。鲁迅根据新文学在乡土题材领域的创作实绩以及世界文学的相关标准首次对“乡土文学”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厘定[1]。从这个定义中,可以提炼和引申出两个与本文的阐述相关的结论:一是根据“作者对题材用‘主观或客观把握的不同,‘乡土文学,一开始就裂变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两大基本类型,同时也预告了‘乡土文学后来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2]。二是鲁迅并不赞赏表现“异域情调”“炫耀他眼界”的趣味主义倾向,他主张在乡土文学要反映民生疾苦,不避黑暗、丑陋、病态,借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其实也就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的主流价值取向——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批判。按照以上两个结论,沈从文应该属于乡土抒情一脉的典型代表。他对乡土世界的美化,对现代时空观念的淡化,以及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融梦幻和现实与一体的牧歌情调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总体表现形态、价值取向都大相径庭。与乡土写实派的启蒙意图有所不同,沈从文要表现的永远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一种“人生的形式”[3],“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乡土只是沈从文寄托他的人学理想的一个载体,他创作的核心意旨是延续新文学的“自然人性论”,为现代文学建构出一个形而上意义上的“人”。关于这一点,丁帆先生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指出,现代人学思想,特別是周作人所倡导的“超人意志”“个性精神”,在现代乡土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很多响应,“只有沈从文的小说用‘生命的流注来尝试这一命题”[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洞见。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这种抽象的人学思想呢?这就需要在抽象与具象、历史与文学、创作观念与本文实存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环节和阐释维度,从而避免一一对应式的庸俗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介入。从沈从文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他是从乡村与城市这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出发,来逐步明晰自己的情感认同、价值判断和身份归属,并以此来建构自己的道德二元叙事的,因此乡村与城市的对位互参,不仅是沈从文个体文学经验的外在呈现,更是其乡土叙事的情感基点和文学思维的内在结构。本文就以这一结构性范畴为问题意识的框架,力图在文学文本、社会意识、历史力量的相互关系之中,动态地呈现沈从文的人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往这个方面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多数研究偏重从乡土现实或启蒙主义的立场之上对其进行简单的判断,而缺乏对其文化心理、符号结构的深入挖掘;二是集中于对这一结构的成熟阶段的状态的呈现,而对其内部动因以及其起始、发展、演变缺乏一个全面而动态的探析。本文就是从这些未尽之意出发,力图在文本、观念、历史三位一体的动态结构中展开对沈从文乡土叙事中“城-乡”对位结构的文化内涵的重新挖掘,并对这一结构及其背后的人学思想的发展阶段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
一
沈从文的“生命形式”创作指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城乡”两极互参的叙事模式的逐渐明晰而确立起来的,这中间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伦理观到生存论、从文本策略到价值立场的转换过程。
1924—1927年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试笔阶段。按照书写内容的不同,沈从文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回忆童年、怀念故土之作。这部分作品充盈着作者对浓厚亲情、醇厚乡情的无限眷恋,也饱含着一个不为定见所缚的写作主体对自然的丰富性的感受能力。《夜渔》《市集》《屠桌边》《瑞龙》《炉边》《在私塾》《往事》《玫瑰与九妹》以细腻而饱满的笔触,在徐徐展开的风土风情画中完成了对故乡的追忆;《代狗》《更夫阿韩》《草绳》三部作品以乡土小人物为表现中心,叙事结构相对完整,现实感也较强。《代狗》写了一个被生活所迫又爱喝两口包谷酒的农民老欧要自己的儿子去南华山庙偷东西的故事;《更夫阿韩》刻画了一个和气、仁慈、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且满怀童心幻念的老更夫形象;《草绳》写了本分善良、乐观向上、以打草鞋为生的沙湾人希望在河水涨高之际谋取一点利益而最终因河水退却而希望落空的故事。这三部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社会现实,但在主题深度与情感意蕴等方面都与同时代的乡土批判小说大异其趣。二是书写生的苦闷、性的幻想等内容的郁达夫式自叙小说及散文,如《公寓中》《老实人》《焕乎先生》《怯汉》《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重君》《松子君》《篁君日记》《遥夜》《狂人书简》等。从创作意图上看,沈从文在这个时期已有与文坛风尚保持距离的意向,他湘西题材作品中流露出的朴素清新又不失健康硬朗的文风,他都市题材作品中对新文学创作程式的戏仿[1],以及他借人物之口对文坛风云人物的臧否[2],无一不在体现一位作家的主体意识的苏醒;从文本实存上看,沈从文这个时期的创作更多地体现为对文坛风尚的俯就,他湘西题材作品中的独异的地方色彩,都市题材作品中大胆直露的性幻想,无不是对新文坛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窥私心理、世纪末情绪的迎合。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任何一个卷入新文坛这个巨大产出和消费机器的青年作家,都必然被其无处不在的市场法则所挟持,最终将自我符号化为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对个体来说,“虽然明明白白是供着那市侩赚钱与吃文化运动的饭的领袖们利用”,但终究是还是“叨这时代的光”,因此也必然会“努着生命的力给这那种人当着物质的奴隶”[3]。这种与文坛风尚欲迎还拒的拉锯战,消耗着沈从文的主体意识,使他无力对自己的实感经验做进一步的理性思索,也无从建构一个包括价值倾向、审美理想、文体意识在内的文学世界。他这个时期对湘西下层人民的情感认同,仅仅是感性层面的共情,而不是建立在城乡两种经验之上的对下层人民的道德优势的理性认知,在更大的程度上,那些被时空所纯化了的湘西世界的美好人性,是沈从文借以逃遁都市困窘人生的避难所和借以克服自卑心理的精神依据。
二
1928—1931年是沈从文乡土叙事“城-乡”对位结构的酝酿时期。他这个时期的湘西题材小说一改前一时期朴素单纯的风格,将炽热的爱欲融入边地的风情,释放出新文学身体解放的热力。《柏子》里的水手虽然卖身给船老板,一年四季吃酸菜臭牛肉,兩个月的工钱仅够上一次妓船,但他在性爱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却在无形中挣脱出贫穷、奴役给他生命所带来的束缚;《采蕨》《阿黑小史·婚前》书写了湘西小儿女无拘无束的、与自然谐振的性爱;《道师与道场》写了巫师与女人的缠绵情事;《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则在荒诞不经的传闻怪谈中渲染着奇异的色情氛围……尽管这些作品不乏边地生活的质朴清新,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狭邪”“鸳蝴派”“新感觉”小说带给文坛的那种放荡颓废、淫糜感伤之风,但在精神质地上,很难说这些作品对新文学的“身体解放”有多大的超越。同样,他这个时期的都市题材作品也出现了一个爱欲书写的高峰。与前一个时期的那种幽闭寓中的白日梦、幻想中的情感满足、对“性欲帝国主义”的道德义愤有所不同,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让男主人公有了爱欲的实现,甚至有了爱欲的放纵。《长夏》里的“我”虽然穷得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但依然拥有六姐和大姐的爱慕,并且能够毫无顾忌地穿梭在她们中间;《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中的男子体验到了情欲的迷醉;《绅士的太太》虽旨在揭露上层阶级的纸醉金迷、腐朽堕落,但由奢侈、滥情等元素构成的叙事氛围却将读者引向一个暧昧不清、真假难辨的真空地带……总体来说,沈从文这个时期的以爱欲为载体的都市题材小说依然带有郁达夫式自叙小说的印记,并更多迎合了上海都市风尚对情色欲望、感官刺激的追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代大都会的上海,一方面向人们散布着金钱铁律、声色犬马,另一方面也散布着异域情调、多元文化,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危机。沈从文这个时期对苗族身份的认同,就是文化的“冲击-应对”模式的一种显现。其实,在北上求学之前,沈从文已从父亲口中得知他的苗族血统,但这种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民族认同在北京时期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上海的租界语境将之唤醒。沈从文动情地说:“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1]都市生活的堕落与民族品德的消失殆尽,半殖民地的屈辱感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沈从文感到焦虑、痛心和惶恐,也使他对汉族这个造成眼下局面的责任主体尽失耐心,他希望能够从苗族那元气淋漓、血气方刚的远古传说中寻找到生命的依托,因此他对苗族族裔的标张是通过“苗-汉”的文化冲突实现的,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与汉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以金钱为基础的两性关系不同,湘西世界中的青年男女依靠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来换得对方的爱,这是一种以“爱”换“爱”的方式[2],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爱情的重心一旦转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这民族就堕落了。实际上,“汉-苗”“城-乡”“中-西”之间的对位关系,是一种文化结构的嵌套,沈从文虽然在这里有借苗族文化抨击大汉族主义的意味,但更大程度上是借苗族文化来抵御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总体而言,沈从文这个阶段的“城-乡”视景已经逐渐明晰,并在更大的观念值域间滑动。如果单看他此时的都市题材作品或者湘西题材作品,大致可说是对“五四”新文学“身体解放”叙事的延续;但若将两者统一起来,则有着生命存在论的朝向——反顾湘西,就是反顾人类文明的童年阶段,沈从文要在这里寻找到元气淋漓的生命元素,借此摆脱金钱名利以及西方文化对生命的压抑和宰制。被贫困所挤压的城市边缘人、健康结实的水手、有血有肉的巫师、远古传说、高贵的野蛮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生命形态却有个一个固定的本质——打破事物的常规。重心不在于用一种形式代替前一种形式,而在于“打破”这个动作本身,它代表着一种朝向不可穷尽、不可实现方向迈进的生命意向,一种去本质化的力量,一种永恒的生命诉求。
三
1932—1938年是沈从文“城-乡”对位叙事的成熟时期,这个阶段以《边城》为波峰,前后两个波段呈现出较为平缓的上升和下降。这个阶段的沈从文迈入了一个颇为顺遂的坦途:婚姻上,他终于在1933年9月9日如愿以偿地与张兆和女士结婚,从此获得了一个忠实的人生伴侣和一个完整的家庭;事业上,他于同年9月23日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坛地位再次提升。安定的生活环境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热情,使他有了更加从容的心境、更加高远的眼界来对人的生命形式以及民族的未来进行整体性的思索:首先是对“城-乡”对位的伦理意义的理性认识。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指出:“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3];其次是高扬“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这是对“城-乡”互参的整体叙事结构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提炼,也是将“湘西世系”的伦理意义纳入文化意义的一次有效尝试。如果说上海时期他的“城-乡”对位叙事的核心在于显现人的本能和生命的原初形态的话,他在这个阶段则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之上对前一阶段所极力标张的原初人性做出了规约。例如,《边城》除延续《龙朱》《阿黑小史》式的原始自然的爱情形式之外,还加上了“利”“义”之辩(走车路-走马路、碾坊-渡船等象征符号的对立),父慈子孝,与人为善等儒家伦理道德;《凤子》《边城》里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有朴素自然的人性,更有与自然相契合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秩序。沈从文将“湘西世系”无处不在的人性之善归结到自然所昭示出的秩序中。在《凤子》中,他写道:“兵皆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村庄里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2]“日光温暖到一切,雨雪覆被到一切,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相互微笑。”[3]显而易见,这里的自然已经不仅仅是人物的生活环境,更是生命的原发地和道德的蓄水池。人与自然的这种同源同构、相互感应、休戚与共的关系,可以在南方巫楚文化的“人神一体”、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儒家文化的“天道”与“人道”的整一性中找到相应的文化心理依据,也可以与西方浪漫主义自然的“自然神意论”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视——启蒙主义的工具理性分解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联结,浪漫主义的“自然神意论”重新将人带回同自然的紧密联系之中,完成对往昔共同体的追认。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这个阶段的人性构建已经呈现出由个体心理向民族品德重建的趋势——标志性的变化是苗族族裔的淡化和国族认同的凸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眼界的提升。有意思的是,也正是这个时期(1933年3月),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4]而在此之前,鲁迅因沈从文早期乡土小说中大量方言的使用,将其戏称为“孥孥阿文”[5]。虽然不能以此作为鲁迅态度变化的主要依据,但沈从文确实在这个时期超越了一个区域性作家的身份定位,他乡土小说中借由地方性表现出来的人性也体现着国民性的内涵。
四
1938年到解放前,是沈从文“城-乡”对位叙事结构的消解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湘西题材的乡土小说,以《长河》《雪晴》《巧秀与冬生》等为代表;二是风格驳杂的“文体实验”类作品,以《看虹摘星录》《烛虚》《七色魇》等为代表;三是感时忧国的杂文,以《一般与特殊》《读英雄崇拜》《狂论知识阶级》等为代表。总体而论,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未能在思想深度和文体创新上对前一时期有所超越,而杂文、文论、文体实验作品则鲜明地体现着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自然、天命、道德的规约让位于“人”的身体解放和灵魂自由,理想人性建构朝着“生命”—“意志”—“神性”的激越状态迈进。
1934年的回乡之旅,将湘西牧歌的衰颓之音传到了沈从文的耳畔,使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理想人性建构所依托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他在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中融入了对湘西儿女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表现出了一定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例如,在《边城》时期,他赞美妓女性情的醇厚以及她们“见寒作热”、为爱疯狂的生命热力;而到了《雪晴》中,他不能不为她们的最终命运而担心,他说:“一面是如此燃烧,一面又终不免为生活缚住,挣扎不脱,终于转成一个悲剧的结束。”[1]同样,对于“翠翠”们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生命活力的肯定,在这个阶段变为对“巧秀”们私奔的忧心——不仅被“偶然”带走的东西一去不返了,就连她本身,“那双清明无邪眼睛所蕴蓄的热情,沉默中所具有的活跃生命力,都远了,被一种新的接续而来的生活所腐蚀,遗忘在时间后,从此消失了,不见了。”[2]对湘西下层人民生存境遇的恶化感知,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增添了一些沉郁厚重的色彩,但并没有赋予他的作品类似于乡土写实派和乡土社会分析派作品那样的社会批判力度,他对造成下层人民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都缺乏一个理性的认识,他依然是从孤立的、静止的、个体的“人”的“生命形式”的角度去思考湘西世界以及东方世界命运。
对都市文明病,例如懦弱、虚浮、表里不一、无光无热、千人一面的极端厌恶,是沈从文从城乡两种不同经验中获取的直接情感体验,也是他从伦理意义、文化意义对乡村与城市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做出理性判断并建立自己的道德二元叙事的情感基点和思维基点。在这一阶段,对湘西世界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恶化感知以及与西南联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特别是留学欧美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貌合神离,再加上乱象横生的战时人文环境与个人情感生活的波动,使他很难再有上一时期的澄明心境,因此呈现在文字上的,是他对都市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充满火药味的批判:
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土窑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3]
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4]
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感情,对理想,异常吓怕。[5]
如果说第一阶段沈从文对都市的道德义愤主要集中在“打到性欲帝国主义”、争取生存权利的实体性目标,第二、第三阶段的“为上等人立一面镜子”集中在伦理、文化价值等观念性目标上的话,这一阶段的对都市“阉寺性”人格的批判则呈现出更加抽象化、符号化的趋势,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到了这个阶段,沈从文仍然没有看到都市文明病是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只是一味地从“名分”“道德”“习惯的心与眼”中去寻找原因,将文明病归结为文明自身,从而只能从反文明的角度去寻求解决方案,而当这种反文明的现实根基崩塌之后,他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假定的、形而上的區间之内完成他的个体生命的重塑与民族文化的重建: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1]
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2]
概括来讲,沈从文在这个阶段所说的“神性”,已经不是上一阶段的那种存留于人类特定时空中,由自然、天命、道德所规约的人生形式,而是一种以线条、声音、身体等实物为依托,又摆脱了实物束缚的至真、至幻、至美的生命状态。在人类的这种“爱与美”的抽象之域,沈从文完成了对“爱欲”由具象到象征的转化,也展开了他由个体哲学的生理、心理本体到民族生命机体的思索。从对人类“爱与美”的抽象之域的皈依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试图以审美观念统摄伦理观念、文化观念的努力,这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对其价值理想、审美倾向、创作动力的自我直陈,只是这个阶段,他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通过故事的讲述或主客问答、双声对话式的诘难与思辨[3]来间接表现,而是以一种呓语狂言的形式表现其内心体验到的真实。除了对这种理想之境的状态进行描述之外,沈从文还对其实现方式和过程进行了探究——“文字”“形象”“线条”“符号”既是建构“神性”的媒介和载体,也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中间层,沿着“‘生命—中间层(文字、形象、线条、符号)—‘人事”的轨道,沈从文完成了他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美学转换。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本雅明的从体验的意象到事实逻辑之间的隐喻性质的转换。[4]
五、结语
乡村与城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伦理道德,两者在现代性的纵轴上,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蒙昧”、“罪恶”与“纯真”等各执一端的历时性差异。在世界文学史上,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杰克·伦敦、乔伊斯、艾略特、爱伦·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韦斯特等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都有着生动而逼真的文学呈现。与西方作家有所不同,中国现代作家对城乡关系的文化内涵并不敏感,他们大多将视线放在“都会畸形繁荣和乡土破产这类极为具体的事实”[5]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作家侧重于书写宗法制乡村的黑暗现实,以茅盾、吴祖缃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分析派作家着力批判城市资本对乡村的掠夺,尽管这两个流派的书写内容有一定区别,但其批判意向大致相似,就是将乡村看作社会发展的对立面,极力表现其破败衰亡的历史命运,而沈从文对乡村的看法却另有起点,他是从现代文明的结果——即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角度来反顾湘西世界,这就使他的“城-乡”对位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世界文学对“本真性”人学理想的诉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之下,由于文明与落后、西方与东方的权力结构的套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鲁迅笔下的“鲁镇”一度成为旧中国的两种形象的指称,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具体所指。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城-乡”对位叙事构一方面提供给沈从文区别于主流乡土小说的视点与内在框架,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的乡土小说朝更宽广的领域发展。也就是说,当沈从文将城市与乡村进行对立思考的同时,他是把历史的维度排除在外的,他没有看到乡村与城市之间在社会发展总体进程中的关联性,而仅仅把城市与乡村进行一个静态的、空间的、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比对,从而用城市与乡村的表面对立掩盖了乡村自前现代社会以来的黑暗与城市在滚滚浊浪中的进步[1]。因此,当城乡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特别是乡村世界失去其原有的自足性、逐步向城市靠拢、并与城市呈现一体性趋势的时候,“城-乡”对位的叙事结构已经无力对现实进行回应,这也正是沈从文后期乡土小说甚至整个文学世界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介于此,他只能在人类的“爱与美”的抽象之域,在一个封闭的、狭小的、孤峭的领地实现他的理想人性建构。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西方文学却呈现出了较强的文学表现力和反思力:例如,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就突破了早期作品中的“城-乡”对位、回归田园的叙事模式, 富有预见性地将现实主义笔触延伸至乡村,深刻表现了乡村固有的黑暗,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城乡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共同处境以及现代人共同的孤立、迷惘与共同体想象,从而展现了一个伟大作家应有的社会洞察力、文化反思力、文学想象力以及应对现实、突破自我、不断成长的主体性,而相对而言,沈从文在其作品中的“城-乡”对位叙事结构日趋成熟之后,并没有将艺术的触角搭到社会发展进程的动脉之上,从立足现实的角度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模式、认知图式、文学观念,而是让其平行滑回第一阶段,避重就轻地将其定格在一个更加幽闭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许这就是“乡下人”的经验带给沈从文的局限性吧。
〔本文系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边地风景研究”(22A072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马新亚: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宏鹏)
——论传统对位教学两种体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