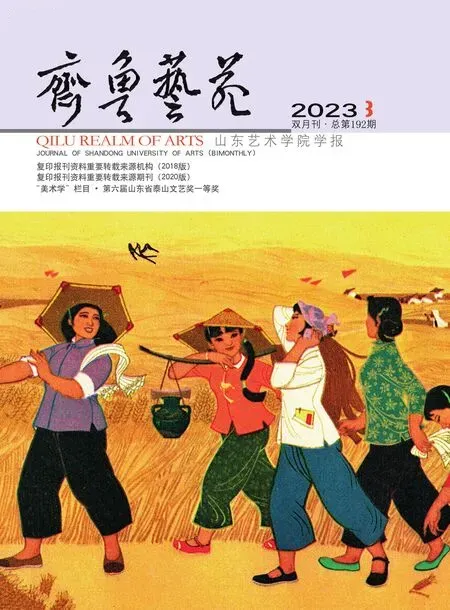撤侨题材影视剧的国家形塑、故事推进与价值扭结
乔 慧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当我们把《万里归途》《战狼2》《红海行动》《维和步兵营》《壮志高飞》等的撤侨段落放在一起考量,会发现这一类以撤侨事件为叙事中心的影视作品,已经让撤侨行动演变为中国新主流影视剧中可供深挖展现的资源库。撤侨事件作为由国家主导的国民保护行动,能够显示一个国家在对外紧急状态下的掌控力与凝聚力;而以撤侨事件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恰好能够作为承担以上国家形象与国家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功能激活、参与对话、显现效果等诸过程的“中国故事”讲述媒介。因此,及时对以上数部撤侨题材影视作品进行经验总结与问题审思,是研究影视作品如何实现中国形象形塑、中国故事讲述,如何实现中国精神与人类共同价值扭结共通的现实需要;而针对其中以“回家”为方法的影视共同体美学艺术格局、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与对外话语生产范式的研究,无疑是进入这一主题论述的重要通道。
一、“回家”:国家形象的符号呈现与及物转换
根据《万里归途》片尾字幕所展示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共发起19次撤侨行动,成功保护并撤回4万余海外侨民。在部分侨居国家政坛风云动荡与自然灾害侵袭之下,中国成功组织了吉尔吉斯斯坦撤侨、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乌克兰撤侨等侨胞救援行动,其跨国性空间与政府性职能,使“撤侨”成为中国国际外交行动中的重要话语发声事件。撤侨作为一种由国家为主体施行的领事保护行动,体现了从观念层对国家内聚力、社会控制力与整体性的认知、强化与证实。[1]以撤侨故事为中心题材的影视作品作为“有关书写(论述)国家行动”的“增补书写运动(A Supplementary Movement of Writing)”[2](P154),正在突破它作为一种电影电视剧故事文本的边界,延伸至政治话语传播、国家形象塑造、外交姿态展现的“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阿利斯特·米什基蒙)力度和“政治叙事”(Political Narrative,兰斯·班尼特、默里·埃德尔曼、沙乌勒·舍恩霍)意义。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某一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3]当“跨国”成为叙事前提,国家形象就必然成为一个被放置在国际中比较的坐标,这是撤侨作为中心事件给此一类影视场域先行自设的话语逻辑规定性。自国外艰难“回家”,就不仅仅是一个事件经过,而首先是一个国家策略与国民行动的发生场域,《维和步兵营》中台词也指出“撤侨是一次国家行动”。
(一)国家符号的“政治现象学”视听再生产
撤侨行动的“国家性”在影视作品中的具象表现主要可以分为对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应用,这些符号“既有国旗国徽等将抽象的国家具象化的物品,也有服饰、仪式等国家权威、社会身份的象征物,还有标语、建筑等以行动世界制造集体记忆的政治事务。”[4]《万里归途》里,大使馆辨别中国侨民身份组织优先救援时,要求他们“带好护照”“举起手中的国旗”;《战狼2》中,身负战力后备保证和侨民接收转移双重任务的舰艇上,镜头对熠熠闪光的国徽与迎风飘扬的国旗进行特写;《红海行动》片尾,南海碧浪上的红色国旗在强烈的色调对比和飘扬动态展现中造成视觉冲击余韵悠长的“后像”……国旗、国歌、国徽以及中国军服等作为凝结了国家主体政治经验的“政治现象学”符号标识,首先贯穿在这一题材系列影视剧的始终。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影视作品中的国家符号展现,不仅仅是一种既有理性政治意义的调用,更是一种情感政治意义的再生产,一方面是面向中国国民进行身份甄别和回归国土的国家归属询唤,以此实现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符码认知整合的运作能力;另一方面是面向国际声张国民认领与保护权利的“合法性赋予能力(Legitimacy-Conferring Capacity)”。
其次,“自塑”与“他塑”的双向建构,完成了国家在撤侨事件中“态度”与“能力”两个层级的及物转化与意义建构。《战狼2》在穿过交战区时以中国国旗为安全保障、作用胜过手中武器,《战狼2》《维和步兵营》《万里归途》在枪林弹雨中高喊“中国人”“Chinese”身份可以免于目标性的枪火攻击、并凭借发色与肤色使叛乱分子有所避讳,甚至通过恐怖分子之口说出“我们不能杀中国人,夺取政权后还要得到中国的承认”,“他说”“他塑”是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效度明证方式,也是影像叙事语言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直观呈现方法。并且在面对危险而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国家层面派出的海陆军队、孤胆英雄,或者是大使馆工作人员,承担着国家形象“自陈”“自塑”的任务,他们的态度与行动都是国家意志的政治实践和形象构建——“不把中国人留在异国战场上”。通过撤侨行动中的国家决策、紧急分派、国际交涉、即时反馈、热情迎接等政治性话语秩序的编排,体现出有理有度的国家担当和国家能力。
(二)“回家”在家国同构叙事中的意义填充与及物转换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撤侨事件成为新主流影视剧的新兴题材资源,与国家力量的崛起现状、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等宏大叙事密切相关。撤侨事件首先基于对中华民族独立并崛起以来国家主权和国家影响力的反映;撤侨题材影视也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表达和值得表达的国家形象塑造观、国家国民治理观、国家文明价值观等文化使命自觉的反映,也即,中国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涵育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在当下的审美思维性,成为这一系列影视文化镜像的膏腴之壤。但如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类宏大话语转化成具体可见可感的及物性(Transitivity)形象,仍要求影视必须采用一定的物质过程和主动语态进行叙事的归因重构。在以上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中,这一物质过程对应为“回家”,主动语态则对应为由国家主导的“带你们回家”。
《万里归途》中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战火中惴惴难安的侨民坚定发声“我带你们回家”;《壮志高飞》中的机组人员对仓惶归来的侨胞呼唤“欢迎回家”;《战狼2》中的中国工厂老板为员工争取回国机会,“都是我们家的员工,所有人我都要带走”;《红海行动》逆向而行的战士,需要的鼓舞是“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维和步兵营》陷入干渴无粮和恐怖组织追杀双重困境中的中国商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一句“我奉上级的指示,前来接你们回家”。以上影视作品中,一系列有关“家”的表达,作为一个铿锵有力的前景蓝图和一种充满温情的心理抚慰,将“家”作为从异国到祖国、从死到生之间巨大缝隙的意义填充体和性质转换体而存在,“家”实现了“国”多维指认的统一与归一,用“一种建立于对该政治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们已称之为‘系统感情’的信仰”[5](P535),使后者从政治的、传说的、想象的、抽象的概念,转递为真实可感的空间实体与关系实体。
概括而言,以“回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进程,撤侨题材影视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如今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力、掌控力与影响力;以“回到家”(《万里归途》)为结局,展开了国泰民安、祥和安宁的国内盛世画卷;以侨民所逃离的战乱国家“人救了,可是家没了”(《红海行动》)为“吾家彼家”进行对照,更具象直观地对中国的富强形象进行本国的情境化表达以及本国与他国的差异化对比,唤起国民认同感的情感浸润与国际认知度的转化塑造。这些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以“回家”“吾家彼家”为跨国时空叙事中并列与对比映衬铺排的结构关系,并建构起一个“国—家”“回国—回家”的下行向的情感性、亲缘性归属关系。对海外侨胞来说,中国有庇佑其免于战乱接其“回家”的能力;对归来的与一直在内的公民来说,中国有给其“家园”的能力,这正是影视作品以“家”勾联国家、以“回家”作为国家形象塑造力量,并以媒介形象塑造“家庭”参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方法路径所在。
二、“回家”:非战叙事的情动驱力与类型张力
撤侨行动通常被政治学家归为一种“非战争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的范畴,认为它具有与以往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对外战争所不同的价值表征。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的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中,因为先行存在的战争作为不得不进行“国家撤侨”的行动前提,使得撤侨叙事具备了战争形势下的紧迫力与危机感。也正是在战争中,“回家”成为一个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意义载体。一方面,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回家”意味着争分夺秒的危机避险和生机抢夺,构成时间维度的信仰;另一方面,“回家”意味着空间上的流动和迁徙,并包含明确的归宿与方向,构成空间维度的信仰。就此来说,在“非战争”这个国际共识的政治性话语掩体之下,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依然具备影视艺术视域中战争片的强类型性元素与时空结构张力。
(一)“最后一分钟营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整合
如何才能在把握国际交流活动中的和平话语,在“非战”或者“不为战”原则前提下呈现出国民生命利益“捍卫战”,以及如何才能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往史诗性题材主旋律作品的国家故事叙述框架,是撤侨题材影视创作实践在视听艺术中面临的挑战。“回家”作为征途,恰恰为压迫性的时间叙事和延宕性的空间叙事提供了张力和推进力。《战狼2》在时间上有18小时的限制,超出则无法及时登上军舰返航,在空间上遇到道路被恐怖分子破坏、撤侨飞机被炸毁尾翼后坠落、必经路上正是交战区等三重阻隔;《红海行动》的时间与空间变动则更为同步:救援特定任务人质(邓梅)时离限定时间3个小时,剩余一半时间时决心救下所有人质、推进离目标80公里的位置,人质解救后剩余40分钟即将成功却要为解决“黄饼危机”再次面临时空考验;《万里归途》以宗大伟的经历看待时间与空间的布局则更为明显,本来拥有立刻回家的机会,首次是因让座而延宕,再次拥有回家的机会后,又因为战友遗孀失踪而延宕,第三次拥有回家的机会,再因为需要转经邻国而延宕,第四次拥有回家的机会,结果因为需要找回少部分脱离队伍的同胞而延宕。在四次延宕中,他数次直面恐怖分子甚至是“轮盘赌”的生命危机,还有妻子即将临盆的陪伴机会倒计时……一方面是争分夺秒事关侨民生命的“我们决策快一秒,他们回国的几率就大一分”的国家层面战略动员;一方面是海外侨民煎熬面对“回家”时间的一再紧缩和“回家”空间的一再延长,双向目的与相悖进程使撤侨故事充满悬念,路途中的每一个小意外都成为影响结果的危急时刻。当故事走向侨民终于回到祖国大地的那一刻,经由压缩与延宕的张力也被拉到最大值,于是撤侨路上的最后一站,祖国派出队伍搜救或者“欢迎回家”的场景出现,作为“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仪式和类型叙事方法也得到圆满。于是,这数部影视作品皆以“回到家”为故事结局,“回到家”作为国家胜利和公民安全的双方共赢性的庆祝,使“家”有了作为一种公共仪式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想象的共同体”情感整合认知功能。
(二)“在路上”:国家意志驱动向情感驱动的话语转变
“家”作为叙事时空结构之外的存在,更有作为叙事情动力和人物塑造力的作用。《战狼2》冷锋对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妻子龙小云的深情,构成了他孤身奋战的全部动力,因罪被逐出军旅则构成了他出国的“不光明”动机;《万里归途》宗大伟对妻子的牵挂和对战友遗孀的责任使他在推辞任务和逆向营救之间纠葛摇摆;《红海行动》夏楠为纪念伦敦恐袭中死去的丈夫孤身闯荡敌营,有“干到底,死都不怕”的执拗……“为家”的情动体验在几部电影中不约而同形成叙事起承转合的驱动力。美国的情动理论研究专家勃兰特认为,“欲望是联系个人生活和大历史叙事发展的核心”[6](P21),不确定的欲望迈向稳定性的意识形态之“爱”的执着是生成情动驱力的能量。具体来说,在精神分析的层面,游移不定的“国”/“家”之欲望取舍形成了电影人物的圆形特征。《红海行动》中,李懂紧张不能抗压导致行动偏差,夏楠冲动不听指挥次次深陷危机;《战狼2》中,冷锋为战友家人悍然出手莽撞不计后果;《万里归途》中,宗大伟世故圆滑、以钱开路且急于回家私心过重;《壮志高飞》中,肖默自负过高、缺乏耐心,以上种种区别于传统典型英雄的人物形象,给情动模式下的成长叙事推进留出了空间。在情节递进的层面,对“家”的执着深爱推进了叙事的多重进展,为自己亲人而悍不畏死,为战友亲人而重返险地,在性格缺陷时造成的叙事回旋,也一步步在情动推动下得到纠偏与弥补,从而以螺旋上升的方式,构成了故事讲述的波澜。即,“回家”作为精神分析人格塑造方法与情节推进叙事动力方法的综合,实现了撤侨主导人物从“非英雄”向“英雄”的主动/被动化“在路上”成长模式套用,也使撤侨行动实现了从国家意志驱动向“回家”情感驱动的话语隐喻转变。
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认为,故事中的事件可以通过对“事件的安排(Arrangement of Incidents)”,将话语转化为情节,而这种转化归根结底还是由话语操控的。[7](P13)以“回家”途中所遭遇的时间压缩与空间延宕为叙事结构与情绪推进力,以“为家”作为撤侨行动主导人的非英雄性圆形人物塑造驱动,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以“回家”作为方法,实现了故事对“撤侨”作为国家事件的僭越,从而有效在影视类型限定中完成了关关难过关关过、攻坚克难得胜利的故事搭建和艺术呈现。与此同时,“家”的情动方法之下,撤侨题材影视其实耦合了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一个策略——“可爱中国”:“要努力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8]圆形人物的不完美,诸如章宁玩世不恭、戏谑夸张的轻忽态度,宗大伟自认为熟知人情、左右逢源,却处处碰壁、失败窘态的前期塑造,与后来勇担重任、舍己救人的奉献精神的后期逆转,两种不同意蕴的“可爱”都可以让人消除戒心,在轻松提升接收信息的积极情绪中,感知立体、丰富、多元的中国形象,这也正是媒介参与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从理性思维向感性思维转变的有效渠道。
三、“回家”:中国故事的价值扭结与国际表达
文化价值的深层结构由“三种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构成:家庭、国家(社区)、世界观(宗教)”[9](P30),讲好中国故事要兼顾故事讲述人与故事接受者两个维度,才能实现故事与价值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在这一层面上,“家”正是传播链条和价值构建的组织性起点,也应该被影视作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的方法论起点。
(一)从“中国标识”到“普世价值”的艺术性再翻译
撤侨行动的前提是侨民与其所居住的海外国遭受自然灾害、战争战火、疾病贫穷等总体性困境与危机,撤侨是被动的应对、防范与补救。因此,撤侨题材影视作品强调的是危机应对而非战斗精神。《红海行动》中的重头戏“不是8人对150人的赢面,而是解救人质”;《维和步兵营》中,则有一个明确的主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尊重生命,期盼和平”。在非主动出击的情况下,被动方本身就会拥有被同情共感的位置优势,以此为主题先置和主人公站位设定的影视叙事,也就能够天然具备伦理正义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动员优势。“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P59),求生与避害,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生存价值,也正是撤侨题材影视能够对外讲述故事与对外传播价值的先机。
应该有这么一个基础的观影感受层级的判断:“回家”是为了求生,而“家”在“国”之内,“国”能接其国民“回家”。“回家”是在跨国遭遇危机中获得最基本的人的生存机会的方法,因此在这一主题的故事讲述中,“回家”等于“生机”容易被当作第一位的感性感知,优先于“回国”的政治认知之前。全人类共同价值毫无疑问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武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对全人类“回家”渴求的深度呈现,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在对外话语传播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文艺政治”之道;但同时也是一种讲好世界故事的影视生产消费需要。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回家”提供了一个将“撤侨”的国家故事讲给世界观众的契机,一个合理化更合情化的策略,使撤侨叙事实现了从“中国标识”到“普世价值”的艺术性再翻译:以国民生命威胁为前提的侨胞回撤事件,通过从“回国”到“回家”的形式更替,形成了从“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到“原始依恋”(格尔茨)的“国家—人”的价值转换与情感生成;避险与求生的时空之旅,从“我国的”变成“我们的”生命祈望,形成了一种“社会总体性本身的动感”[11](P1-39)和全人类面临生死抉择时能够共通共有的“主体性想象”。《Amazing Grace》中那一句“Grace will lead me home”的“回家”歌咏(《战狼2》)和《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回家”传奇(《万里归途》),皆是这一主体意识的表述。
(二)从“吾国吾家”到“彼国彼家”的全人类情感共同体构建
从人物设定出发回看“共同体”或者“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会发现这几部撤侨题材影视作品首先将人物定位在了“共同”的层面。商人(《维和步兵营》)、工人(《战狼2》《万里归途》)、儿童(《战狼2》《万里归途》《壮志高飞》)又或者是外交官宗大伟(《万里归途》)这类有亲人羁绊、有死亡恐惧的普通人,更能有联通战乱或灾害国家原住难民感受的贴近性,唯“贴近”,可“共同”,撤侨叙事的第一步骤“避险”,在深层次上成为共同体叙事。另外,《战狼2》和《万里归途》都设置有一个以战乱国儿童为子女的亲缘设定。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侨民或者工作人员对异国儿童Tundu、法堤玛拼死相护视若己出,这种行动逻辑“已不只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开始承担拯救人类命运的正义使命”[12],正是在践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维护。并且,Tundu从战火中死里逃生后,意识到船即将驶向中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身下船奔向难民聚居地“我要我妈妈”“我不要去中国”,前半句转换视角切入了“他人”的“回家”需求,使“回家”不再是中国行为,而是共通行为,后半句紧接着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他人”对“祖国”的归属,“国”在分清“你”“我”之后终于超越“家”的层面,成为各有所属但共有所求的概念。同理,努米亚边境官员哈桑的临别含泪与悬尸门梁的强烈对比,也是“彼国彼家”深沉且忠诚的感情。在国民之间关系塑造上,撤侨题材影视剧也正在改变以中国英雄救苦救难为中心的叙事原型,拓新性增加了国外难民在共患难中的伟大作用:《战狼2》中小男孩Tundu的母亲与中国人一起反击暴乱,表现奋勇坚定且泼辣带有一定喜感;《万里归途》里向导瓦迪尔为拯救中国侨民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倒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其英勇与悲情成为宗大伟成长线中的关键推动因素,也令观众为之心折。在这些撤侨场景中,无论中国侨民与战乱国的国民,无论幸福与动荡,尽皆处在一种家国之念与互助共生的共同情感体验之中。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归家”神话或史诗性原型叙事,增厚了文化含量,唤起观众的“集体无意识”而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共情。[13]在本国价值伸张的基础上,尊重且同样重视他国人民的家国情感与命运需求,在共同命运、共同情感的生发历程基础上,使跨国语境中的人类故事真正触及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叙事的核心。
结语
影视依凭“图文互见、视听结合以及多媒体互动的符号编码方式,已经逐步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方式。”[14]在坚守和平原则的前提下,展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力,表述中国关于全人类共同意识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是影视艺术工作者重要的国民使命和职责担当。撤侨题材影视剧因其和平原则、跨国叙事与国家意识形态呈现的特殊性质,正是在当下国际关系中可以深度参与纪录与塑造国家形象、展现国家力量、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佳媒介。
不必否认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存在着接受与认同的困境。这不是一个“传播—接受”“塑造—认同”的直接过程,而是“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国家的自我形象(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国民心中的本国形象)和国家的外部形象(在世界舆论中被接受的或实际的国际形象)之间的协商(Negotiation)。”[15]如何“协商”,正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命题与中心方法。在近年来中国撤侨题材影视作品中,已经隐隐找到了这一关键——以“回家”为方法,将其作为国家形塑力、故事推进力与价值扭结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民族与世界、中国与他国、主动与被动等相对关系和谐并存的样态需求。在对外传播中,国是政治概念,“回家”则是具身感受与表达。千般磨难,入境为安;万里蹀躞,以此为归。以“回家”为中国故事生产路径,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文明形态价值表征与追求,是以《万里归途》《战狼2》《红海行动》《壮志高飞》《维和步兵营》等近年已成议题景观的一类撤侨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探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世界主义艺术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