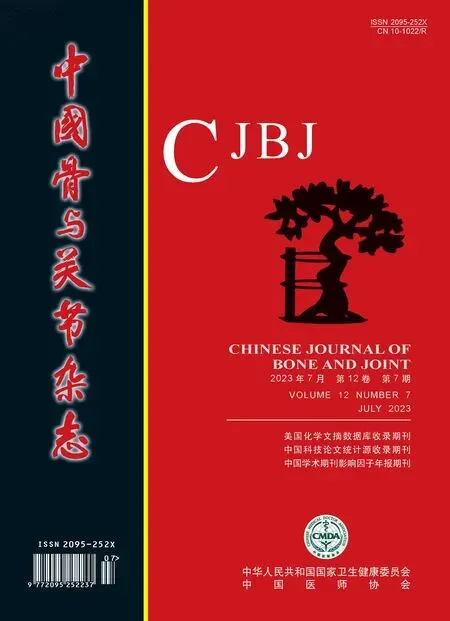强直性脊柱炎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研究进展
张雅东 张海平 王文涛 郝定均
强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AS) 是主要累及骶髂关节、脊柱及外周关节的附着点慢性自身免疫炎症性疾病。其早期最主要的特征性表现是腰背部或臀部疼痛伴晨僵,久坐或晨起加重,活动后稍减轻。多数患者起初表现为骶髂关节炎,后由腰椎向胸、颈部脊椎发展,以椎体骨质疏松、方形椎体、脊柱小关节炎症、椎旁韧带钙化及骨桥形成为特点,晚期严重广泛的骨化性骨桥而表现为典型的“竹节样”改变,出现脊柱活动受限甚至脊柱畸形。AS 的特殊病理变化导致整个脊椎骨质疏松、脆性增加以及广泛的骨桥出现可产生杠杆支撑作用,硬化的脊柱承受正常负荷的能力降低,可在无外力作用或轻微应力下发生骨折。AS 患者中有 4.1%~5.7% 合并脊柱骨折,且骨折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 4 倍,在有 45 年 AS 病史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骨折的风险每年增加 1.3%[1-3]。AS 引起的脊柱骨折较常发生在胸腰椎,其中由于整个脊柱胸椎和腰椎过渡区应力相对比较集中,又以胸腰段 (T10~L2) 好发。临床对于强直性脊柱炎胸腰椎骨折 (ankylosing spondylitis thoracolumbar fracture,ASTF) 患者,不论采取何种术式,其主要的治疗目的是:(1) 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轻临床症状;(2) 在骨折基本复位的情况下,最终达到骨性愈合,重建恢复脊柱力学稳定性;(3) 早期进行功能锻炼,防止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近年来,随着脊柱外科的发展,ASTF 的治疗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完善对 ASTF 特点和治疗方法的认识十分重要。
一、ASTF 的特点
1.临床特点:ASTF 常发生在病程的中晚期,此时椎体骨质疏松、椎体形态改变、脊柱小关节模糊、椎旁韧带钙化及广泛骨化性骨桥形等特点,导致脊椎骨的脆性增加,脊柱对外力保护性缓冲作用减弱,从而致使 AS 患者较一般人更易发生胸腰椎骨折,同时,患者常伴有脊柱畸形致脊柱生物力学稳定性发生改变,这使得其 ASTF 较一般胸腰椎骨折有其特殊性。鉴于大多数 AS 患者都有慢性疼痛,许多患者因疼痛耐受可能不寻求医疗护理,患者及医务人员对 AS 患者可在无外伤史或经低能量损伤后致使胸腰椎骨折的此特点认识不足,导致 ASTF 漏诊率较高。Westerveld 等[2]的研究中,17.1% 的患者在受伤后 24 h 内没有发现脊柱骨折。对于 AS 患者出现腰背部突然疼痛加剧、疼痛性质改变、疼痛程度与红细胞沉降率或 C 反应蛋白等炎症指标不对称、非甾体抗炎药或激素治疗效果不佳等情况,有必要高度怀疑骨折存在[4]。有学者证明了用骨密度和骨小梁评分去预估 AS 患者骨折风险的有效性[5-6],但此法只仅限于特定 AS 患者群体并不能适用于每一例患者,且缺乏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故临床实际应用价值有限。笔者认为临床上针对 ASTF 高隐匿性特点,详细询问病史时除关注患者有无高或低能量外伤史,对于无任何可回忆受伤史的慢性累积性损伤也不容忽视。对疑似存在骨折患者,应及时完善影像学检查,由于 AS 患者脊椎结构改变,只凭 X 线检查难以发现骨折存在,相较于X 线,CT 对于明确脊柱骨折具有高度特异性和敏感性,还可观察骨折碎片移位情况,其中 CT 平扫联合三维重建诊断准确率则更高,对评估软组织和脊髓损伤时应采用脊柱 MRI 检查可弥补 CT 的不足,同时还可诊断 CT 未发现的隐匿性骨折,以明确诊断及鉴别诊断,临床上借助更清晰的影像学联合检查以降低误诊和漏诊率是 ASTF 诊治的首位因素。
AS 通常胸腰椎小关节融合,椎旁韧带钙化,椎间运功单元活动度丧失,类似偏心负荷的管状骨,在站立位或仰卧位负重活动过程中,胸腰椎体承受过度屈曲或过度伸展的应力,长期积累性损伤导致骨折断端微动,机械应力阻止骨折愈合,后期可导致贯穿三柱的骨折不愈合状态即假关节形成。当下移的胸腰椎后凸顶点处于不同压力作用下,会导致不同损伤机制的骨折。其中最常见是屈曲应力,前方为压力侧,后方为张力侧,支撑应力主要集中在前柱和中柱,骨折线常经椎体水平,骨折断端接触面较大且相对稳定,骨赘形成较少,常表现轻度疼痛和神经症状,亦可有后凸畸形。而另一种则是后伸应力,前方为张力侧,后方为压力侧,支撑应力主要集中在中柱和后柱,骨折线常经椎间隙水平,患者出现腰背部持续性疼痛,而脊柱后凸较轻,若未及时发现治疗,后期可能并发假关节形成[7]。
ASTF 通常为不稳定性骨折,因其常累及脊柱前、中、后三柱呈现 Chance 骨折,脱位率更高,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粉笔骨折”[8];AS 患者脊柱后凸畸形使得胸腰椎过渡区应力分布更集中,加之患者慢性累积性损伤常在胸腰段发生应力骨折,同时椎体骨质疏松脆性增加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骨折片进入椎管导致神经损伤发生率增加,其神经功能障碍常倾向于发生在 T9~L2的骨折[1];而且应防范伤后搬运过程中易出现骨折片的移位及神经损伤的进一步加重。ASTF 骨折线复杂多样,可经过椎间盘水平、椎体中央水平和终板上下水平等,骨折后常在不同节段的关节突可见新鲜骨折线,也可表现为骨性融合的前纵韧带或棘间韧带的连续性中断,可伴骨折脱位,在矢状位上显示椎管狭窄从而引起相应的神经症状。在骨折平面的邻近椎间盘的椎体和终板侵蚀性改变病损称之为 Andersson 病损(andersson lesion,AL),部分骨质吸收而出现断端分离,类似于长管状骨骨不连的 X 线征象,其临床易误诊为脊柱结核[9]。由于 AS 患者的脊柱后凸顶点的远移至胸腰段形成杠杆作用,且应力远大于颈椎,骨折部位多低于 T7,且发生在 T10~L2居多,此类患者骨折不愈合率及假关节形成率均增高,同时手术时对融合及稳定性的要求也更高[10-11]。部分患者有明确的影像学证据,证明以前有过未诊断的隐匿性骨折。有研究发现,AS 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概率为 64.1%,其原因可能是慢性自身免疫性炎症导致破骨细胞活性增强[12]。由于 AS 常伴有脊柱增生骨赘形成伴骨密度假性升高或正常,因此不能以患者的骨密度正常与否来判断是否存在骨质疏松,最可靠的是结合 CT 平扫椎体内部骨小梁结构来判断实际骨质情况,此特性也是自发性椎体骨折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此项重要特征亦可影响手术方式及预后。
2.分型:目前对于 ASTF 的骨折分型国内外报道较少,Graham 等[13]将 ASTF 分为剪力骨折、应力骨折和椎体压缩骨折 3 类。其中剪力骨折多发在颈椎,应力骨折好发于胸腰椎,又以胸腰段 (T10~L2) 多见。Trent 等[14]提出慢性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胸腰椎骨折有 3 种类型,即剪切或片状骨折、楔形压缩损伤和骨折相关假关节。Westerveld等[15]研究发现,ASTF 中 74.4% 的损伤是伸展损伤,其次是屈曲损伤 (20.0%)、旋转损伤 (5.4%) 和压缩损伤(4.7%)。Zhang 等[7]依据损伤机制和应力特性将 ASTF 分为椎体型 (vertebral body,VB) 和椎间隙型 (intervertebral space,IS)。以上分型均未全面纳入影像学表现、损伤机制、应力特点、是否伴神经损伤和骨折脱位等因素,对于分型也未行可信度检验及临床应用效果,因此对 ASTF 患者指导治疗价值有限。因 ASTF 自身特点而不同于一般的胸腰椎骨折,其以往的胸腰椎损伤分类和严重程度评分系统 (thoracolumbar injury classification and severity score,TLICS)、AO Spine 损伤评分和急性症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acute symptomatic osteoporotic thoracolumbar fracture,ASOTLF) 分型系统均不适用于 ASTF,其标准分型和治疗指南仍有待探索。
二、ASTF 的治疗方法
1.保守治疗:通常情况下,ASTF 非手术治疗很少被推荐,且对于 ASTF 患者行非手术治疗成功案例的报道较少,Park 等[16]和 Biro 等[17]都应用特立帕肽成功治愈 1例ASTF 患者,无论保守还是手术治疗,术后支具对于患者是必要的,由于患者自身脊柱畸形,因此支具通常需要个性化定制佩戴以匹配其脊柱形态。对于保守治疗的患者要定期观察随访有无症状加重或新发骨折的出现。有时选择保守治疗是因为 AS 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患者通常年龄较大和病程较长,常患有多种重大内科合并症,长期服用药物可能会导致麻醉不耐受以及增加术中机体负荷[10]。Tecle 等[18]认为非手术治疗 AS 骨折存在潜在风险,肋椎关节强直导致胸壁缺乏顺应性导致的肺部并发症且其卧床并发症的风险更高,骨折失去复位机会及神经功能障碍加重。对于明显移位的上中胸段骨折,胸壁不能起到理论上“第四支柱”作用辅助稳定骨折部位,损伤中的继发性骨折移位比预期的更不稳定,以及患者支具不耐受是 ASTF骨折患者非手术治疗失败率高的主要原因[19]。对于脊髓损伤的患者,保守治疗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20]。Caron等[21]在 75例 ASTF 患者治疗中报道非手术治疗患者 1 年的病死率为 51%,而手术组为 32%。Lu 等[22]报道了在他们的回顾病例分析研究中,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显著改善。Westerveld 等[2]进一步证实,在神经功能障碍和不稳定性骨折的情况下,59% 的患者行手术干预没有导致神经功能进一步加重,27% 的患者神经功能得到改善。此外,因其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可以延迟骨折愈合,对于保守治疗 ASTF 患者建议避免使用,特别是当存在其它延迟骨折愈合危险因素时[23]。
综上所述,既往虽然有保守治疗的成功案例,但多为个案报道,其临床价值有限,笔者认为 ASTF 患者非手术治疗仅适用于高龄、基础情况较差无法耐受手术、伤椎部位较稳定、无神经损伤的患者。对于不稳定性或伴神经损伤 ASTF 患者,为避免保守治疗可能导致后期骨折延迟愈合、骨不连或假关节形成从而使得手术难度进一步增大,应推荐早期手术治疗,除非患者不能耐受全身麻醉或有严重的合并症。
2.手术治疗:随着治疗技术的提升,手术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以前对 AS 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治疗风险大,治疗效果欠佳,病死率高的这种观点也有所改变,如今对于 ASTF 患者,若无明显手术禁忌多主张手术治疗,其能通过内固定提供脊柱早期的稳定,恢复脊柱的力学稳定性,直接或间接解除神经压迫,防止因骨折不稳定导致神经损伤进一步加重,尽早挽救神经功能,解决骨折后上下两端产生的杠杆力妨碍伤椎愈合而形成的假关节,同时更有效地避免因长期卧床及支具引起的各种并发症。Lu 等[22]研究报道 25例 ASTF 患者,6例接受手术治疗,术后骨折愈合和神经功能改善,8例因延误诊断均出现假关节,4例神经症状加重,11例非手术治疗后愈合 3例,假关节形成 8例。ASTF 患者应重视早发现、早诊断、早手术以防止损伤加重,但选择具体何种手术方式仍存在争议,而且可能伴随一些严重的并发症[24]。
AS 的致病机制使得患者常伴多种内科疾病,也可使头颈部关节常受累限制颈部活动出现困难气道,脊柱后凸尤以胸腰段的脊柱后凸加大气道管理难度,这使得术前麻醉面临诸多挑战[25]。有研究认为麻醉术前访视评估是首要工作,主要评估要点有颈部活动度、张口度、马氏分级(Mallampatti classification)、有无眼部疾病以及心功能等内科合并症[26-27]。一项相关性研究指出颈部活动度对可视设备的使用与否影响较大,颈部活动受限时,麻醉科医师更倾向于使用 McCoy 喉镜、可视硬质及纤维支气管镜等可视设备[26]。在 1例 AS 极重度脊柱后凸畸形患者麻醉插管中,选择右美托咪定和羟考酮程序镇静镇痛下配合表面麻醉纤支镜引导下进行顺利完成气管插管[28]。对于 AS 患者的麻醉管理,术前麻醉师应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准确评估气道状况,以及因其它疾病的用药对术中麻醉药物的影响,评估患者麻醉耐受程度,选择最佳麻醉方式、气管插管设备和麻醉药物,充分准备以最大化降低麻醉风险和并发症发生率。
由于患者整个脊柱僵直,骨折后极不稳定,在搬运或术前体位摆放时应避免二次损伤。对伴脊柱后凸畸形者,俯卧位手术时,选用合适头托避免发生颜面部和眼球压迫损伤,另外可运用弓形脊柱手术托架体位和 Jackson 手术床辅助,其具有特殊结构设计,专适于患者的畸形体态,术前可因人而异调节成弓形再联用凝胶衬垫充分贴合躯干以提供稳定支撑,提高患者舒适性,减少对血管神经的压迫,在术中复位后可将托架调节成头尾侧高,中间较低的形态,以促使截骨面闭合。若需要二次复位的患者,在肩部和下肢用衬垫垫高,再应用持棒钳和持钉钳的加压作用达到满意复位,复位结束时观察头面部和上肢,若变动较大需重新调整高度,同时整个术程需要密切关注体感诱发电位监测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EP)[29-30]。虽有学者设计可调式手术体位架用于重度后凸畸形,利用调整各平板模块高度以完成身体的贴合匹配[31],但此工具的缺点在于手动调节耗时长以及术中 C 型臂 X 线机透视较困难。也有报道在侧卧位对 AS 患者进行手术,虽然此法可避免或减少二次损伤发生率以及缩短体位摆放时间[28,32],但此体位不符合常规操作习惯,螺钉置入有一定难度和置入椎管内风险,术者长时间抬双臂进行细微操作体力耗费极大,增加术中失误率,且反复在无菌区周围操作会增加污染风险。每个患者因病情不同致体态亦不同,手术部位及方式也不同,因人而异合理选择手术体位,以及对于体位摆放辅助工具的应用恰当与否,以及术者与巡回护士的紧密配合直接关系到手术效果。此外,在术前进行体位摆放过程中,麻醉护士应密切关注气道,注意保护患者气管导管避免脱出;患者体位改变前后监测气囊压力,维持在25~30 cm H2O;全程密切观测 SEP 及动脉血压变化,警惕在进行复位时神经损伤和假性低血压发生[27]。对于 AS患者围术期管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麻醉师、护士、医师密切配合谨慎操作安全完成。
目前为止,与 ASTF 相关的报道不如 AS 合并颈椎骨折多,目前多数学者建议采用后路植骨融合长节段内固定术[33-36]。后路是大多数脊柱外科医师比较熟悉的方法,手术入路相对容易,可以修复骨折韧带的损伤,也提供了多个固定点,以减少杠杆臂对骨折节段的作用,可以修复骨折韧带的损伤同时对于脱位的骨折进行复位,并根据需要进行减压,在存在伴发畸形的情况下,若有需要且认为安全的情况下允许进行畸形矫正[21,35,37-39]。如果通过较长的后路固定结构获得了足够的多节段稳定,则在骨折复位期间开放的前柱间隙可能不需要用二次前路手术来植骨[40]。后路也存在缺点,对于伸直型前柱损伤,其植骨融合和韧带修复较困难,此情况下联合前路手术不失是一种好的选择[41]。然而,ASTF 行前路手术可行性研究高质量的文章较少,事实上,Westerveld 等[15]的研究中只有15% 的 ASTF 病例接受单纯前路手术,且支持前路手术治疗 ASTF 的证据仅限于少数病例报告。Kouyoumdjian 等[42]认为如果前路接骨板和螺钉的长度足够长,使相邻脊柱节段的长活动臂产生的杠杆作用降至最低,则仅前路固定可能有效。Escosa 等[43]认为,AS 患者合并胸腰椎假关节形成、进行性神经功能损害、AL 累及前中柱时为前路手术的适应证。在治疗骨折同时进行畸形矫正的情况下,出于对内固定失败的担心,采用前后路联合手术在一些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疗效[2,4,44-46]。对于 ASTF 累及三柱和假关节形成的患者,由于其前方椎间存在明显骨缺损,传统后路手术行后外侧植骨融合失败率高,多数学者主张 360° 植骨融合,将前路与后路入式相结合,可以达到前后方充分植骨融合[41,47]。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 AS 患者有良好的骨折愈合能力,前路植骨融合不是必要的[48]。李波等[49]对7例 ASTF 脱位患者行先后路再前路的分期治疗,取得良好临床疗效。Zhang 等[7]对慢性 ASTF 发生 AL 时,前柱及椎间骨质吸收破坏严重者,行前路减压支撑植骨类似张力带,可以为植骨提供良好生物力学环境,防止植骨移位或吸收,再联合后路椎弓根螺钉固定,使得植骨和椎体断面有效接触,改善胸腰椎矢状位平衡和脊柱立线,临床疗效满意,但此法缺乏对照组仍需大量临床实践证实其有效性。笔者认为对于急性 ASTF 和并发 AL 者,前后路联合手术这种最具侵入性方法提供了最大化的脊柱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手术创伤较大且费用高、患者耐受性差、术后并发症多、椎体前方大血管神经较多风险较大。临床上后入路式最为常用,患者接受度及满意度高,对于伴有神经损伤者,后路时可行椎板减压,当伴骨折脱位时,可借助后路椎弓根长臂拉力螺钉进行提拉复位,同时椎弓根螺钉贯穿椎体三柱稳定较高且矫形效果好。ASTF 患者成骨能力较强,行后路时也能够完全清楚病灶,并根据骨缺损范围行 360° 植骨融合,术后疗效较前路及前后联合入路类似[15,50]。虽单纯前路术式可直接病灶清除便于植骨,但此术式螺钉松动和脱出发生率较高,且不能纠正后凸畸形[48,51]。建议倾向于单纯后路联合长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可获得脊柱生物力学稳定以创造骨折愈合环境。具体手术入路应根据骨折类型和损伤机制决定,这样可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具体融合节段的选择有待探索。
后路螺钉置钉的技术挑战经常源于 AS 缺乏后路骨性标志或小关节严重融合和脊柱畸形。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透视也可能在术者置钉方面受到限制,Li 等[52]对 ASTF患者应用 O 型臂 X 线机导航辅助下术中安全有效精准置钉,取得较满意的临床疗效。此外,ASTF 患者大多存在骨质疏松,其影响植骨的融合率和内固定的稳定性导致断钉退钉等问题,对此应重视术中植骨方式选择和植骨床的制作,为了获得足够的固定强度,也有学者采用骨水泥强化螺钉和皮质骨轨迹螺钉技术以加强螺钉把持力从而治疗骨质较差的患者[53-58],但此治疗方式尚缺乏大量临床证据支持,具体疗效须进一步研究证实。
此外,由于 ASTF 报道较少且均为低水平证据的缺乏队列的病例对照研究,在 ASTF 的固定方式,包括固定节段数、跨节段固定和脊柱后凸畸形是否矫正仍存在争议。Zhang 等[59]建立 ASTF 有限元模型研究发现,与正常胸腰椎骨折相比,ASTF 患者脊柱僵直化和三柱骨折使得内固定所承受应力更大,因此推荐至少 4 个节段内固定可明显减少应力集中[60]。跳跃式固定不仅增加了内固定的工作距离还延长切口增加创伤。在固定节段相同的情况下,跳跃式固定均无明显优势,ASTF 不宜采用跳跃式内固定。鉴于多节段融合脊柱的长杠杆臂和 AS 患者较差的骨质量,Werner 等[4]建议在骨折水平以上下至少各 3 个节段进行固定,因短节段固定植骨融合,后期可能会出现骨折不愈合、假关节形成、内固定松动和脊柱后凸畸形加重。笔者认为,在实际临床应用中,应综合考量患者自身骨质情况,在保证固定强度的情况下,找到螺钉松动风险和手术创伤之间的平衡,尽可能减少固定节段以免螺钉过多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内固定的成本和移位风险,在不增加固定节段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它策略来增强内固定稳定性,例如骨水泥强化技术。
目前对于处理完 ASTF 后行畸形矫正术的报道较少[36]。Werner 等[4]在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现畸形矫正可能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然而,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对脊柱后凸畸形矫正进行研究尚不多见。在 Zhang 等[59]的生物力学模型中进行了 30° 后凸矫正发现,一方面,Cobb’s 角的减小改变了内固定的应力传导,降低了内固定的应力分布。另一方面,脊柱后凸矫正导致前柱支撑缺失,使压力更大。这两种影响相互抵消致使内固定的应力和螺钉松动的风险没有明显改变。此结果有待于临床实践进一步验证。对于 ASTF 形成的 AL,可能导致反复性腰背部疼痛、甚至进行性后凸畸形等并发症。有研究报道应用单纯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术治疗,在病灶完全清除后,在骨缺损处放入钛网或植入自体骨和同种异体骨,对抗矫形后前柱支撑缺失的应力增大,随访期间患者腰背痛症状好转,以及后凸畸形外观明显改善,并未出现螺钉松动、断裂等内固定失败并发症情况[61-63]。笔者认为术前脊柱外科医师在是否选择一期矫形术时应权衡考虑患者住院诉求、术后期望度、术者技术水平、神经功能状态及恢复矢状面平衡优势和并发症风险等因素。
鉴于开放手术更广泛的多节段内固定和融合,其手术相关的如出血和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也有所增加。随着外科技术不断发展,后路微创脊柱手术在胸腰椎骨折治疗中应用越来越普遍。刘建恒等[64]、Yeoh 等[37]和 Li 等[65]对ASTF 患者采用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术后效果较满意。近年有学者将经皮椎体成形术用于治疗 ASTF,研究表明经皮内固定可限制手术入路的侵袭性,从而降低肌肉剥离引起的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同时有手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和疼痛较轻等优势[66-69]。笔者认为此术式只适用于前柱轻微压缩骨折、后柱稳定、无脊髓损伤、不需要神经减压的患者,椎体成形术对早期轻微 ASTF 可显著改善患者疼痛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一些例如 3D 打印辅助技术以及机器人辅助内固定等新兴技术用于 ASTF 的治疗,均取得满意疗效[56-57]。笔者认为微创经机器人引导下经皮长节段内固定术在减轻患者疼痛、矫正脊柱后凸畸形方面与传统手术有相似的效果,且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创伤小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外加机器人等辅助提高置钉准确率,可认为是治疗ASTF 较为理想的方法,但以上研究多是低证据水平的病例报告和病例回顾研究,其确切的临床疗效有待探索。随着精准医疗、微创理念和快速康复理念的不断发展,或许以上新兴微创技术和应用骨水泥等技术会成为 ASTF 手术治疗的主流。
三、总结与展望
目前,临床上对于 AS 疑似骨折的患者,应借助更清晰、高质量的影像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鉴别诊断,同时在其它医疗机构中加强对 ASTF 临床诊断与认识普及,降低其漏诊和误诊率。对于疑似 ASTF 的处理需小心谨慎,早期诊断的同时给予适当体位固定并妥善转运,防止发生二次损伤。临床对于不稳定性骨折保守治疗效果常不理想,现多推荐行手术治疗,而手术方式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全身器官功能状况、骨折类型、是否伴神经损伤或骨折脱位、骨质情况、畸形严重程度、患者心理预期、风险承受能力、术者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个体最优化设计手术方案,从而获得满意的手术疗效。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是对骨折减少延误诊断,评估微创和新兴脊柱手术实际临床疗效,保证手术疗效的同时减少并发症,以及制订相应评分标准,以帮助骨折患者做出治疗决策。现关于 ASTF 的报道较少且文献主要是单中心研究、病例报道和系统综述的形式,以后仍需多中心及高级循证医学证据探讨 ASTF 骨折的标准分型以及制定治疗指南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