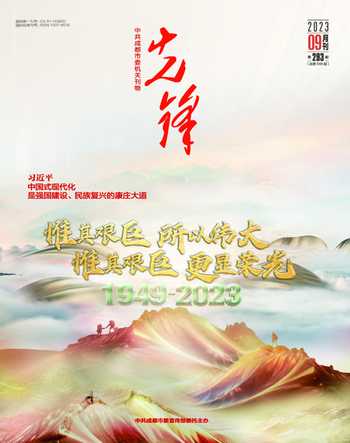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
陈婷婷 全威帆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史蒂芬·巴克斯特这样说过:“我们需要科幻作品,我们需要了解科幻的重要性。”当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天际时,总会产生很多幻想,而科幻作品正是我们脑海中幻想的一种延伸,是人类对未来的想象。
随着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日渐临近,随着科幻热度的持续上升,我们再度回归“原点”:何为科幻?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如何发展科幻产业?近日,本刊记者就以上问题与中外专家学者以及作家共话“科幻”。
认识科幻
无穷的想象 无止的探索
“科研成果本身往往带有科幻色彩”
“年轻的时候,我经常阅读科幻小说,对科幻非常感兴趣。我十分认同,科幻作品是进行科普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年9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来成都参与首届科学与科幻创新论坛时谈到。
作为在人类发展的前沿领域进行耕耘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观察者”,迈克尔·莱维特讲述了自己对于科学与科幻的理解。
什么是科幻?科幻的定义众说纷纭,认可度较高的一种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远景或者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科幻”一词在20世纪正式提出,但早在公元2世纪,古希腊语小说《真实的故事》中,就已出现关于星际旅行、外星生命、星际殖民和战争、人造生命等内容。1818年,学界公认的第一部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英国诞生,涉及遗传学、基因突变、机器人学、精神分析学、机械论等一系列科幻母题。而1902年诞生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则用充满幻想色彩的服装和布景,讲述了从发明机器到登陆月球再到凯旋的故事……科幻作品用故事讲述的方式,不斷激发读者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探索。
在科学探索中,迈克尔·莱维特感受到科学与科幻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12岁的时候,计算机刚被发明不久,不仅体型庞大而且数量稀少,“那个时候,听说计算机甚至可以用来玩游戏,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现在的计算机比那时更加新颖,是因为有更加突破性的技术正在发展,比如有大语言模型,有像ChatGPT这样的智能工具。”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在过去的60年里,他一直都在做计算机的编程工作,去年获得了ChatGPT这个“新朋友”的帮助后,他如今编程工作的效率提升了10倍,“我觉得新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有点像科幻小说中的世界,所以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我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社会将发生比过去100年更多的变化,在未来,许多科幻小说情节将成为现实。”
作为交叉学科“计算生物学”的先驱,迈克尔·莱维特首创蛋白质和DNA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致力于蛋白质结构预测技术的关键评估。他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而共同获得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科学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带有一定的科幻色彩,“以基础生物科学的研究为例,本身就非常具有科幻的感觉。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100年以前,谈到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人类最基础的DNA研究,其结构就是几条简单的线,每一个DNA的基础构成单位,是非常小的,但是每一片都承载着整个生命的信息,组合起来又运行着非常复杂的机体。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艺术的科学研究成果,所以在我看来,整个高科技的成果自然就是一个科幻的作品。”
那么,科幻作品对于科学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迈克尔·莱维特解释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一些新知识和一些新想法,而它们往往由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瞬间所促成。“有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做饭或是洗澡时突然的灵感迸发,然后就有了方向。科幻作品和中国古诗词都可以激发想象力,从某种角度来看,科幻作品也是一种创造科学的方式。”
“科技是科幻小说展开想象的基点”
“科技的发展给想象力提供了新的支点,催生的东西就是科幻。”凭借《命悬一线》入围2023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的科幻作家江波告诉本刊记者。
2003年,江波毕业于清华大学微电子学专业,同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最后的游戏》。在20年科幻创作生涯中,江波的作品屡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星云奖。此次入围2023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的《命悬一线》中,主人公是中国蓬莱空间站上的一名宇航员,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在极高的速度下,用聚合纳米管制成的“救生索”紧急救援另外两位遇险的外国宇航员。
“如果只说我的专业,和科幻创作不会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生活里,包括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我的思考方式是一种科学思维或者说工程思维,需要缜密的逻辑性判断,这对我的写作有非常强烈的影响。”谈到对科幻写作的理解,江波认为,科学是科幻写作非常重要的基础。
“人的想象力,我认为是天生就有,但产生出什么样的想象,取决于获得什么样的知识。”江波解释,在科学时代里,人们拥有科学知识之后,就会产生基于科学的想象,这就是科幻。而对科学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广泛、越有深度,所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就越有说服力。“科技是科幻小说展开想象的基点,一个科技飞速进步的时代,必然也是科幻蓬勃发展的时代,所以整体上的影响肯定是正面的。但这对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作者需要对科技的快速发展有所认知,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快速跟上时代发展。”江波说。
在江波看来,科学或者科技是科幻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出发点,在这个出发点上,人们可以向着无穷的想象空间去探索,这是他认为科幻最有魅力的一点。
“科幻产生之后,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会影响到社会很多层面,尤其是青少年。”江波表示,在科幻文学的启发下,很多青少年会开始对科学感兴趣,对于未来产生憧憬,科幻文学的精神激励作用非常重要。
“浩瀚的星空等待我们去探秘,无数科学的难题、科学的奥秘召唤我们去探索。当步入科幻殿堂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有趣。当破解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的时候,你会感到人生非常有色彩,非常有意义。”正如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所言,科学研究离不开想象力,而科幻是人类想象力的载体和呈现方式。
时间拉回到120年前。1903年,鲁迅在译完“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后写道:“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20世纪初,鲁迅、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把西方科幻小说翻译成中文,认为科幻能够激发国人新的梦想和想象,其中包含着国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现代化力量。也是从那时起,科幻文化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开枝散叶。
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这些年,涌现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蜚声国内外的科幻作家,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的科幻记忆。
今年9月,刘慈欣发文表示,近年来,中国科幻快速发展,受到更多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和关注,这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航天事业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等,有着很深刻的联系。我们处在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数字化进程之中,充满机遇和希望,也有压力和挑战。人们赞叹科学的神奇,期望科技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一切都为科幻的繁荣提供了沃土。
“科幻最美好的地方就是给人希望”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受一部科幻作品影响很大——《小灵通漫游未来》。”江波说,书中预言了大量新技术及新发明,包括“飘行车”、人造器官、家用机器人、环幕立体电影、生产蔬果的“农厂”等事物,虽然今天听来已不再新鲜,但让当年的孩子们十分神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同年8月,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面世,初版行销160万册,在当时中国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我心目中最好的科幻小说,主要的特质是能够和现实相结合,对技术进行合理想象,从而对未来提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江波认为,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是基于现有的、真实的科學和科技,能够对未来做出一种推演。这种推演或许是一种引导作用,比如青少年在文学作品里看到一种美好的未来,并产生了向往之心;这种推演也或许具有一种警示作用,比如书写出现实,引发大家深入思考,起到思想实验的作用。
“如果一部科幻小说有这样的社会意义,我觉得它的价值会远远超过休闲娱乐。”江波认为,科幻最美好的地方就是给人希望,“包括《小灵通漫游未来》同时期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展现的都是一种光辉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比如想象树上可以长出多种多样的水果,肉吃都吃不完,诸如此类。”
因此,在其个人作品里,江波总会保留下希望的种子,“我觉得我写过的,可能对人类来说最灰暗的一个未来,就是人类全部灭亡了。但最后还是有一个机器人,把自己拼装成一艘飞船,飞向宇宙去进行探索。”
这个希望的种子是由什么带来的?江波认为,就是科技的发展,“如果把历史拉远,可以看到从远古时代起,就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像彗星撞地球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一定不会再发生。比如需要发展太空技术,有一系列有力的科技,能够让我们在这种未知的恐惧、未知的灾难到来时自我拯救。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只能不断地向前发展,让人类达到一个很高的技术水平,以此来保证我们拥有未来的希望。”
去年,迈克尔·莱维特读完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我对《三体》的理解也是在发生变化和演进的。一开始非常关注里面那些关于物理学的理论,但是后来,我更多的是关注这本书对人文方面的思考,比如关于社会的治理、信息的合法使用等,这些是我目前更加关注的维度。”迈克尔·莱维特同样认为,除了科普,科幻作品带来的还有人文价值。
在江波看来,中国当前的科幻创作处在黄金时期,原因在于国民科学素质不断提高,科技不断取得进步,为科幻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谈及中国科幻的特质,江波认为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二是体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江波期待,“中国科幻的未来能够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品,表现中国社会的伟大变迁,展示更前沿更开放的想象空间。”
需要科幻
梦想照进现实 照亮未来
从科幻中“看”到科学
在186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构想了一只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艇。据说凡尔纳给后来的潜艇设计带来了启发,于是,1886年英国建造的第一艘使用蓄电池动力的潜水艇,以及1954年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儒勒·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亚瑟·查尔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并且改变了世界。
“科幻”从来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立足现实科技展开的想象。科幻不仅能反映一个时期科学发展的状况,更能启迪科学家的思考,激发科学创新的灵感。正如英国科幻作家盖伊·哈雷在《科幻编年史》一书中所说,科幻对世界的这种大胆绚丽的描述,给真正的科学家以灵感。
在吴显奎看来,幻想和科学融为一体,就等于给科学插上了翅膀,它能在人类求知的领域里,任意翱翔。吴显奎非常赞同南方科技大学吴岩教授提出的观点,想象力就是生产力,呵护和促进发展想象力,就是呵护促进发展生产力!“科学研究离不开想象力。打个比方,原子核的能量能释放出来,是因为有快速中子的轰击。科学研究好比是‘铀-235’,想象力就是‘快速中子’,用中子轰击氦核,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实现新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
“我相信我找到了自己着迷之物”
作为科幻作家,科幻对于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本届雨果奖入围青年科幻作家江波和海漄各自给出了三个关键词。江波是“惊奇、恐惧、希望”,海漄则是“好奇、探索、自我”。
“一般来说,科学或者技术都是中性的。它能够提高某种效果、引发技术爆炸的能力,包括一些辅助工作的能力,但也会让我们产生担忧:一方面,如果一种非常强大的科技落到某些丧心病狂的人手里,对于世界将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外部世界非常广阔,有可能人类的不断探索,会触发某些不可知的东西,从而对人类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未知,所以恐惧。”江波对“恐惧”如此解释。
“为什么说科幻对于我的意义在于‘自我’?”海漄谈到,“我有一份很繁忙的工作,解决物质生活问题。而科幻对于我来说,是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去实现‘自我’、认同‘自我’的一种渠道。”
自称从小就是资格“科幻迷”的海漄,对小时候泡新华书店读到的《海底两万里》《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等如数家珍,这些成为其在科幻上最早的启蒙。“上了初中后,有一次看到同学有一本《科幻世界》杂志,借来一看,立即被潘海天的《饿塔》所震撼,从此开始一期不落地购买。正如刘慈欣曾在《球状闪电》中写的‘幸福的人生,在于迷上了某样东西’,那时,我相信我找到了着迷之物。”谈到从中得到的收获,“科幻最吸引我的,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科幻启发了我在写作中的很多灵感,是創造力的源泉。因为有科幻,我在工作生活之余拥有了一段全新的体验。它所反映的想象力让我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是不会因为年龄而消退的。对我个人而言,科幻只是让自己更充实,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我们的文明将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
接受科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时间旅行者通过时间机器不断地向未来旅行,不停地观察人类物种、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科幻文学学者、国内首位科幻文学博士姜振宇向记者介绍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部给他带来科幻启蒙的作品时,止不住赞叹,“通常讲人类的演变过程,都是从进化论角度从过去到现在来说,而这部作品展现给我们的,是看未来人类社会会怎么演化。特别是时光旅行者到达802701年后,小说描述的经典场景,经常被冠以‘人类的落日’,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这种远超日常的观察视角,以及时间以数量级为尺度的扩大,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使得像姜振宇这样的科幻迷获得了超越性的审美体验,“从现实出发,通过科学、幻想,获得非常神奇的超越性的瞬间和情感——更可怕的是,科学对这种超越给出了保障,最后抵达了一个对现实的更加深层次的认知。”
在姜振宇看来,科幻吸引人之处在于将人、自然界及科学放置于同一视野下,一方面人类非常渺小,另一方面人类虽然很渺小,但是借助“去人类化”的科学,可以完成很厉害的事情,这种状态很微妙。“我们越大越会发现,现实里面有很多疑问和思考,在科幻作品里,会发现很聪明的人也跟你一样的迷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而在科幻里,科学与人文的根本一体性也是其魅力所在,“像凡尔纳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里非常明确地说,要把下一代孩子们培养出一个科技时代的理想的人格。怎么来培养理想人格,除了人文艺术教育,科学教育也必须是理想人格的组成部分。”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科技影响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生活背后的科技状态。科幻则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把科学放到你的日常经验当中。背后更深层次的是,科学发展会带来变化,科幻告诉你变化是一个正常发生的事情,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不要焦虑变化。对于未来的变化,要让孩子们做好准备,过于困难了,这个时候科幻可以说,‘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会帮你一起想一想,未来会不会变成我这个样子。重点在于它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可怕。’当接受科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就会伴随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你始终会比别人多一点点东西。”
发展科幻
“热”下去 还需形成更好生态
中国科幻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
近年来,随着国产科幻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三体》剧集为代表的高质量影视作品,让主打中国题材、展现国人想象和传统文化的科幻影视作品陆续“出圈”,加速中国科幻产业发展。
据《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877.5亿元,总体来看,中国科幻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各板块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在《报告》发布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总结了中国科幻产业发展呈现的五大亮点:数字技术赋能科幻阅读产业效能凸显,数字阅读营收首次超过纸质阅读;微短剧、中短视频等新业态表现活跃,科幻影视产业各业态融合发展态势凸显;科幻手游市场占比提高,本土科幻游戏海外市场表现良好;国创二次元科幻IP走向成熟;主题乐园科幻游乐项目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科幻景区凸显“科幻+地理”特色。
吴显奎分析指出,从《报告》显示的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构成来看,其中科幻阅读为30.4亿元,科幻电影为83.5亿元,科幻游戏为565亿元,科幻衍生品为48.3亿元,科幻文旅总营收是150.3亿元。“从中能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是科幻阅读的体量小,第二是有影响的科幻大片太少,第三是科幻衍生品明显不足。”
姜振宇表示,当前所提的科幻产业,更多是指科幻IP以及相关改编衍生的影视等为基础的“以科幻创意为内核”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报告》数据折射出的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代表,导演郭帆等主创人员通过对科幻电影工业体系的摸索,探索出一整套现代化的管理程序,推动了电影工业化,更新了中国电影生产的基本逻辑。它代表的是一系列生产制作门类的高水平发展,这是最大的意义所在。重点不在于科幻本身有多么厉害,而是我们开始有足够的基础设施,能够把好的科幻作品做出来。”
科幻源头创造力,达到世界级水平
2006年5月,刘慈欣的作品《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虽收获不少支持,但与主流文学创作相比,“科幻写作”颇显“小众”。十余年后,《三体》已经卖出2000多万册并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
“科幻热”持续升温,科幻业态不断丰富,那么中国科幻产业发展处于哪个阶段?
姜振宇介绍,业界尝试对科幻产业发展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划分,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研判体系。粗略来说,主要为早期的科幻出版产业、延伸到数字视听新媒体产业方向,进而往以场景营造、强调互动性为核心的“科幻+”多元产业发展。当前,中国科幻产业在第二阶段向前发展,“第二阶段有没有标志性的完整形态?其实是有的。以美国为例,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行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原创或者创新能力;第二,一个IP可以非常方便地改编成其他平台形态,即同一个IP在产业链上能够自由、顺畅地流动。比如,《星际迷航》是先有电视剧,然后才改编为电影等其他产品。我国目前仍然主要通过科幻小说做IP,再进行产业链的延伸,IP的流动还不是很顺畅,科幻文化产业各环节之间需要逐步形成一种更好的生态。”
科幻产业首先是内容产业。姜振宇表示,从科幻创作来说,来到了最好的一个时期,“科幻小说的创意是源头,论科幻源头创造力,中国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姜振宇特别提到,这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当且仅当科学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之后,对它的体验和审美才是可能的。同样,只有在与科技密切相关的颠覆式创新、社会伦理和哲学观念的底层逻辑演进被广泛接受之后,科幻才能在大众文化中获得生长的土壤。正如导演郭帆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成功,与中国航天等前沿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
姜振宇介绍,中国科幻版图中,还有一部分呈现出相当亮眼的活力——网络科幻文学,涌现出了大量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创作生态,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
如何形成进一步推动科幻产业发展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吴显奎认为,首先需要凝聚共识——发展想象力就是发展生产力;从孩子开始,呵护想象力、保护想象力;重视科幻原创。姜振宇表示,社会需要对创新、对失败有容忍度,同时,让科幻更多地进入日常生活,比如,在路边的公园就可以搭建科幻展览,这是一个比较期待的状态。
“科幻的半壁江山在成都”
今年10月,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行,在吴显奎看来,“科幻之都”这张名片,让成都走向世界。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名片具备三个重要基础:产业基础、文化基础和政策基础。世界科幻大会给成都带来影响力和动能,以影响力经济为牵引,以影响力聚集人才,成为创作的高地。
姜振宇认为,这是成都历史传承发展、人才聚集效应和地域文化特征综合效应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科幻最火的主要是在上海和北京,之后發展到成都、哈尔滨等地。成都有一个很妙的点——既有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状况特别适合搞科幻。到了上世纪90年代,《科幻世界》杂志培养了大量科幻迷,如今在成都各种职业、各个岗位上都会发现曾经的科幻迷,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状态。”姜振宇表示,目前成都有大量的企业和人才聚集从事科幻产业,同时结合地域文化特征,不同于深圳注重科技未来应用场景的科幻产业规划,成都没有那么的接近生产一线,反而有一些空间可以来做想象,更多地聚焦创意。
借助世界科幻大会的契机,姜振宇认为成都可以树立典型企业、典型科幻项目,加强科幻的赋能效应,实现“科幻+文旅”“科幻+教育”等领域的弯道超车;提升对科幻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扶持及政策鼓励;在技术方面,比如科幻相关的视觉呈现技术、电影特效的算法、游戏建模等方面,进行科幻文化的引导。姜振宇希望成都的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等能够加大对社会开放的力度,这能够极大地促进科学、科幻文化的传播。
中国已出现四次科幻热
中国科幻有过多次热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初,第二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次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前的科幻热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延续,同时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一次热潮
清末民初,西方科幻被鲁迅、梁启超引进中国,被当作改造中国人的梦、实现国富民强的工具
第二次、第三次热潮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目标,促进了科幻发展,造就了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等名家
第四次热潮
1992年后,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支持了当时唯一的科幻平台《科幻世界》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幻的新繁荣,培养出王晋康、刘慈欣、何夕、江波等骨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