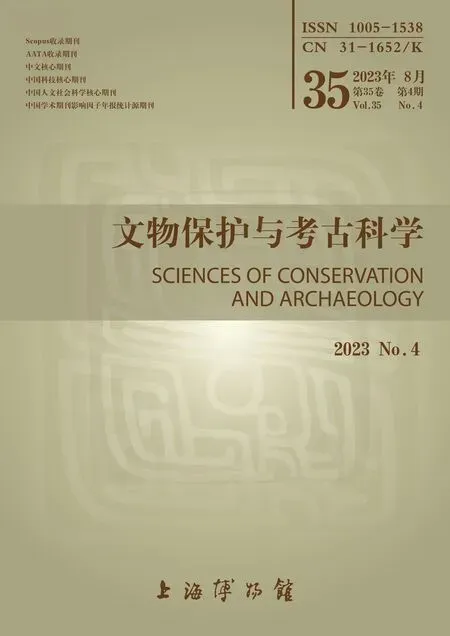麦积山石窟131窟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研究
文 娟,徐博凯,胡军舰,李 鑫,张宏英
(1. 天水师范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甘肃天水 741000; 2. 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天水 741020;3.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4. 天水市博物馆,甘肃天水 741000)
0 引 言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一处遗产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开凿和修缮,现存洞窟221个,石窟数量多、规模大,保存有10 632身泥塑石雕,约1 000多平方米壁画,造像壁画时代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保存有最早最完整的西方净土变、维摩变、涅槃变、法华变等大型经变画[1-3],是中国北朝佛教艺术嬗变的杰出代表,能全面反映5~18世纪天水地区传承不断的佛教思想和信仰。现存北魏时期窟龛数量90余个,是石窟营造的高潮时期,极大地促进了麦积山石窟造像的繁荣,北魏时期造像壁画题材多样,以多种组合形式的三世佛为主,还包括有二佛并坐、说法佛立像、弟子授记像、千佛造像等法华造像、经变壁画等[4-5],对于研究古代陇右石窟文化、佛教文化发展及石窟壁画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古代石窟寺文化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麦积山石窟131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洞窟正壁保存有佛造像一身(图1a)、左右壁各保存佛造像一身,佛像手部、腿部有残缺,四壁贴有影塑佛、供养菩萨及弟子,应为三世佛造像。该洞窟可能长期用作生活窟,洞窟内泥塑、壁画表面均覆盖有很厚的烟熏污染物,无法观察到壁画画面内容(图1b)。病害调查表明近70%的壁画已经完全脱落,保留下来的壁画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空鼓、脱落,保存状态堪忧。从洞窟内保存壁画脱落边缘部位(图1c)观察可知,131窟壁画是直接在凿刻好的崖体上涂覆粗泥层找平,厚度1~2 cm,然后涂细泥层,厚度0.5~1.0 cm,最后绘制颜料层。壁画没有重修、重绘现象,完整保留了北魏晚期壁画制作材料、制作工艺等原始信息。

(a)主佛造像; (b)正壁保存的泥塑壁画; (c)边缘空鼓壁画图1 麦积山石窟131窟主佛造像及泥塑壁画保存现状Fig.1 Preservation status of the main Buddha statue and clay sculptures and murals in Cave 131 of Maijishan Grottoes
以麦积山131窟采集的壁画残块为分析对象,使用多种分析测试方法对壁画样品剖面结构、地仗层土砂质量比及壁画原料成分等进行科学分析,探讨麦积山131窟壁画原料成分和制作工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麦积山石窟北魏晚期壁画制作工艺,并为后期壁画病害机理研究、筛选保护修复材料及保护修复工艺提供依据。
1 样品和方法
1.1 实验样品
1.1.1壁画残块样品 此次实验采集131窟内正壁及左右壁已经脱落壁画样品残块3块,分别编号为1#、2#、3#(图2),样品粗泥层、细泥层层次结构完整,表面覆盖有黑色烟熏污染物,无法观察烟熏层底部是否存在颜料层,烟熏层局部脱落部位能观察到白色底色层和地仗层,粗泥层厚1~2 cm,细泥层厚0.5~0.7 cm,粗、细泥层添加纤维明显不同。

图2 131窟壁画残块样品图片Fig.2 Samples of mural fragments in Cave 131
1.1.2自然沉积土样 麦积山石窟周边分布的主要是紫红色砂砾土,黏土中包含有较多大小不一的岩石碎屑,20世纪70年代壁画地仗修复用泥筛选实验中发现,石窟周边红土相比细质黄土,制作的地仗层试块收缩性更强,与崖体粘性低,干燥时极易开裂[6],不适合用作壁画、泥塑地仗层修复材料。为了进一步了解131窟壁画制作使用的黏土原料及其来源,为后期地仗层修复用土选择提供参考依据,结合石窟周边常用取土地点,依据由近及远原则筛选麦积区麦积镇麦积村黄土坎黄白细粒土(距石窟约0.7 km),麦积区马跑泉镇甸子村砖厂黄白细粒土(距石窟约24.7 km),麦积区社棠镇社棠村砖厂黄白细粒土(距石窟约23.4 km),剥离表层土样后,直接采集细质坚硬的黄土块,分别编号为4#、5#、6#。
1.2 仪器及实验条件
基恩士VHX-7000超景深显微镜用于壁画颜料层保存现状、剖面分析及纤维形态观察,放大倍数20~1 000倍,高亮度LED光源,大范围高精度表面观察。
Mastersizer 3000激光粒度仪(英国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分析粗、细泥层中土砂颗粒粒径,测试条件为:分散剂为水,分散剂折射率1.330,Hydro全自动湿法进样,测试量程0.01~3 500 μm,遮光度范围5%~30%。
日本岛津XRD-7100衍射仪用来分析地仗层中黏土的主要物质成分,Cu靶,狭缝,电压40 kV,电流30 mA,扫描范围10~80°,连续扫描,扫描速度5°·min-1。
Niton—XL3T 950型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高性能微型X射线管,Au靶,Si-Drift SDD探测器,电压50 kV,电流40 μA,General Metals模式,分析时间30 s,直接在壁画样品表面测试。
法国JYBIN YVON公司生产的XploRA拉曼光谱仪获取烟熏污染物,颜料层与底色层颜料物质信息。采用氩离子激光器,激发光波长532 nm,物镜放大倍数50倍,信息采集时间20 s,累加次数5次,功率5%。在体视显微镜下挑取粉末样品放在载玻片上直接分析。
1.2.1土砂比例分析 参考王丹阳[7]对须弥山48窟泥塑样品土砂比例的分析检测方法,采用悬浮沉淀法对131窟壁画粗泥层、细泥层及采集自然土样做土砂比例分析。
从壁画残片边缘部位精确分离粗、细泥层样品各2 g置于烧杯中,105 ℃烘干至恒重,使用陶瓷研杆轻轻捣碎较大块土样,将样品中的纤维拣选出来,一定注意不要研磨样品。拣选纤维时发现有较多老化断裂严重的细小纤维无法拣选,为避免细小纤维对土砂粒度测试产生影响,在粗、细泥层样品中加适量蒸馏水浸泡,轻微搅拌使纤维分散开,25 Hz震荡5 min后静置,将悬浮在水中的纤维拣选出来,重复震荡直至将纤维拣选干净后将粗、细泥层中沉淀的土、砂样品转移至具塞比色试管中备用。
分别称量自然土样10 g装入具塞比色试管中加适量蒸馏水,固定后25 Hz震荡15 min静置,记录上下层土、砂体积。然后加入适量蒸馏水震荡,将上层悬浮液倒出,多次震荡直至上层溶液澄清,将所有样品中土砂完全分离后恒温105 ℃烘干至恒重,称量记录。
1.2.2地仗层添加纤维鉴定 参考纤维横截面切片技术[8],将粗、细泥层中拣选出来的纤维清洗干净烘干至恒重,用无水乙醇清洗,室温晾干,将细小纤维完全分散后置于滴有甘油的载玻片上,用盖玻片覆盖后进行纤维纵向形貌观察。将较大较完整的纤维排列整齐,用硝基清漆包裹,固化8 min后将样品放入哈氏切片器卡槽中,用刀片迅速切片,切下的薄片立即置于滴有甘油的载玻片上,使用盖玻片覆盖切片样品用于纤维横截面形貌观察。
2 结果与讨论
2.1 制作工艺分析
将壁画残块表面黏附的灰尘吹除后观察可知:壁画样品表面覆盖了一层致密的黑色烟熏污染物,且烟熏层存在较严重的龟裂问题(图3a),部分烟熏层出现脱落,脱落部位可以观察到白色底色层和地仗层。使用手术刀刮除烟熏层污染物后暴露的颜料层呈现红褐色(图3b)。

图3 131窟壁画样品显微照片Fig.3 Micrographs of mural samples from Cave 131
壁画残片样品剖面显微形貌结构观察可知,样品表面烟熏层厚约28.07 μm,结构致密,底色层连续分布,厚度不均匀,较厚部位约35.26 μm,颜料层分布不连续,厚度不均匀,较厚部位约21.08 μm(图4a)。结合现场调查与样品剖面分析可以确定,131窟壁画依次为粗泥层、细泥层、白色底色层、红色颜料层,层次结构完整,131窟壁画先在岩体表面涂敷一层较厚粗泥层找平后涂较薄的细泥层,细泥层表面整体涂刷白色底色层,然后用颜料绘制图案,与丝绸之路莫高窟、甘肃泾川罗汉洞、克孜尔、炳灵寺等石窟壁画制作工艺基本相同[9-11]。
壁画表面由于人为因素覆盖了一层较厚的烟熏污染物,紧密黏附在颜料层与底色层上,烟熏层与颜料层、颜料层与底色层中间都存在明显的内部空鼓现象(图4a、图4b)。这种空鼓是造成壁画表面颜料层、底色层脱落的严重隐患。
2.2 地仗层及其添加物分析
2.2.1土砂比例分析 古代石窟壁画地仗层使用的黏土原料一般“就地取材”,会进行淘洗、添加砂砾等加工处理措施。131窟粗、细泥层与自然土样分析所得土和砂的体积比、质量比见表1。分析结果显示,131窟粗泥层的土砂质量比小于细泥层和自然土样,说明粗泥层中含沙量高于细泥层。细泥层中土砂质量比低于黄土坎和甸子村土样但高于社棠村土样,无法体现黏土中沙砾人为添加情况及淘洗处理等后期加工信息。莫高窟第8窟地仗层仅使用自然沉积澄板土,无人为添加砂砾[12],相比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壁画地仗层含沙量最高,一般在70%左右[13]80。麦积山石窟周边采集的自然土壤线缩率0.12%~1.15%,体缩率为1.36%,缩限为3.80%,收缩系数为0.055,具有较明显的干燥收缩性,地仗层中较高的含沙量可以很好地降低黏土的收缩性,但同时会降低黏土与崖体的黏附性,是导致壁画脱落的原因之一。
2.2.2地仗层土砂粒度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麦积山131窟壁画粗、细泥层制作工艺及黏土原料来源,分别测试壁画地仗层样品粗、细泥层及自然土样中土、砂粒度,分析数据如图5所示。从土样的粒径数据(图5a)分析可知,壁画地仗层中土样的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20.9~110 μm范围内,不同粒径范围内含量稍有不同,与甸子村采集土样一致,表明131窟不同部位地仗层均使用了相同的自然沉积土。黄土坎、社棠村两地采集土样在20.9~110 μm粒径分布范围内含量降低,在132~479 μm粒径范围内含量明显增加,与甸子村采集的土样粒径分布比例明显不同,分析可知人们会有意识筛选天然细质沉积黏土作为壁画地仗制作原料,推测131窟使用的黏土可能采集于距离石窟稍远的甸子村。

图5 样品粒径分布曲线图Fig.5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soil and sand samples and natural soil samples
从砂砾粒径数据(图5b)分析可知,不同地点自然土样中沙粒粒径分布范围为15.4~158 μm,粒径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粗、细泥层样品砂砾粒径分布范围为0.759~832 μm,分布范围远大于自然土样,粒径变异性极大。从粒径分布曲线来看,在132~398 μm粒度范围内,自然土砂砾含量极低,粗泥层砂砾含量最高7.28%,细泥层含量最高9.99%,该粒径范围砂砾应属于人为添加的均匀细沙。壁画细泥层中479~832 μm粒度范围内砂砾添加量明显减少,2#、3#样品粗泥层添加量则明显增加,且粒度变异性较大,表明131窟左、右壁地仗粗泥层添加了更多粒径大且大小不均匀砂粒。
综上所述,131窟壁画粗、细泥层中使用的黏土原料是石窟周边采集的天然细质黏土,细泥层添加的砂砾细小均匀,正壁粗泥层添加的砂砾较均匀,与细泥层一致,应是人为淘洗筛选过的均匀细质沙粒。但左右壁粗泥层中添加砂砾大小不一,且大颗粒砂砾较多,推测未进行淘洗筛选。
2.2.3地仗层成分分析 131窟地仗层样品与采集的自然黏土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表明:地仗层黏土的物相成分主要包括石英、少量方解石、长石等(图6a),与距离麦积山石窟稍远的甸子村采集的天然黏土成分相似(图6b)。粒径分析数据也表明131窟壁画样品与甸子村自然土样一致,推断麦积山石窟会从距离石窟较远的地方采集更适宜壁画制作的黏土原料。

图6 样品XRD图谱Fig.6 XRD patterns of the plaster layer sample from Cave 131 and natural soil sample
2.2.4地仗层添加纤维鉴定 古代壁画制作时会在地仗层中添加较多的麦草、麻、棉等植物纤维降低黏土的收缩性,防止地仗层在干燥过程中出现开裂[14]。131窟壁画粗泥层中添加短宽的片状纤维与杆状纤维,且混合有极少量细长纤维。样品纤维纵向形貌一致,呈均匀分布柱状,边缘部分有很多紧密排列的小锯齿,纤维有很明显的结节,与麦草纤维形态相似(图7a、图7b、图7c)。图7d粗泥层纤维横截面细胞排列紧密,为枕状椭圆形,细胞较大,细胞壁明显,细胞呈网状结构,纹孔稀小,与小麦纤维横截面特征相似[15]。可知131窟粗泥层添加纤维为小麦麦秆及麦衣,混合的细长纤维含量很少,未能切出横截面,无法判断其纤维种类。

图7 131窟壁画样品粗泥层添加纤维显微图片Fig.7 Micrographs of fiber added in the coarse mud layer of Cave 131
壁画细泥层中添加纤维均为团絮状细短纤维。纤维纵向形态细长,有不太明显的横节纹(图8a、图8b、图8c),横截面形态(图8d)具有明显的麻纤维横截面特征[16],推断131窟细泥层添加的纤维为麻纤维。


图8 131窟壁画样品细泥层添加纤维显微图片Fig.8 Micrographs of fiber added in the fine mud layer of Cave 131
131窟使用掺有较多麦草麦秆、粗砂的黏土作为粗泥层,掺有麻纤维、细砂的黏土作为细泥层,涂刷白色底色层后绘制图案。麦积山石窟崖体属于砂砾岩,质地粗糙,所处林区环境潮湿,不同时期地仗层添加纤维种类不同,后秦至宋粗泥层主要添加麦草,明代粗泥层中则添加麻,127、9窟细泥层中添加棉花[13]82。地仗层中添加沙砾、纤维可以很好地减少黏土收缩开裂,提高地仗层与崖体的黏附力,是壁画在较为潮湿环境中能长久保存的重要条件之一。
2.3 颜料层分析
2.3.1X荧光成分分析 样品原位无损X荧光分析结果表明,正壁红褐色壁画样品主要显色元素为Pb及少量Ca。左壁红褐色样品主要显色元素为Hg、Ca、Fe以及少量Pb。右壁白色样品主要显色元素为Ca,推测131窟红褐色颜料有土红、铅丹和朱砂,白色颜料为碳酸钙或石膏。
2.3.2拉曼光谱分析结果 烟熏污染物、红褐色颜料层、白色底色层样品进行拉曼光谱分析。
烟熏污染物吸收峰出现在360 cm-1、1 368 cm-1(图9a),与炭黑的标准图谱基本吻合,可知烟熏污染物的主要显色成分为炭黑,与早期石窟中使用木材、油脂等燃料的燃烧产物炭黑一致。正壁样品红色颜料吸收峰(图9b)出现在181 cm-1,205 cm-1,405 cm-1,505 cm-1,与红色颜料铅丹的标准特征吸收峰(122 cm-1,226 cm-1,393 cm-1,548 cm-1)相比有所变化,主要是因为红色铅丹变色后会生成二氧化铅[17],降低了样品中散射物质铅丹的浓度[18],可知正壁红色颜料为铅丹。左壁样品红褐色颜料样品吸收峰位于265 cm-1、411 cm-1、466 cm-1、607 cm-1、747 cm-1(图9c),比照标准朱砂、铅丹及铁红的拉曼光谱图,可以判断该颜料为土红、朱砂和铅丹的混合颜料。白色底色层样品吸收峰出现在284 cm-1,716 cm-1(图9d),与方解石的特征拉曼频位移[19]相对应,可判定白色底色层主要成分为方解石。

图9 131窟壁画样品拉曼光谱图Fig.9 Raman specta of samples from Cave 131
131窟壁画正壁壁画红色颜料单独使用了铅丹,右壁壁画红色颜料使用了铅丹、朱砂、土红混合颜料进行调色,均使用白色方解石作为底色层。周国信[20]对麦积山石窟不同时期颜料分析结果表明,麦积山石窟不同时期使用的红色颜料有朱砂、铁红,红色颜料中未检测出铅丹,但是不同时期洞窟部分黑色颜料中均检测出PbO2,李最雄等通过大量实验表明敦煌石窟PbO2为铅丹腐蚀变色形成[21],北魏时期黑色PbO2应该是红色铅丹变色形成。131窟壁画表面覆盖着比较厚的烟熏层,清除烟熏层后底部颜料层呈现红褐色,结合131窟红色颜料分析结果,相比暴露在大气环境中铅丹的腐蚀变黑,变色较轻微,烟熏层如何延缓铅丹的变色腐蚀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麦积山石窟使用的红色颜料主要是朱砂、铅丹、铁红,不同时期比例不同,早期朱砂使用较多,北周后铁红颜料大量使用。不同地区北魏时期石窟壁画使用的红色颜料也存在差异,内蒙阿尔寨石窟北魏时期单独使用朱砂或铅丹[22],马蹄寺和天梯山大量使用朱砂和铅丹[23],莫高窟、炳灵寺、云岗石窟[11]75-76北魏时期使用朱砂、铅丹、土红,与麦积山红色颜料种类一致,但麦积山石窟早期红色颜料朱砂使用较多,而敦煌则是土红较多。自古以来各种文化因素在秦州碰撞、交融,麦积山石窟后秦、北魏早期泥塑融合了古代印度、中亚、西域以及中原造像艺术特点,麦积山早期颜料使用及来源可能同时受到西域、莫高窟和中原地区影响。
3 结 论
本工作通过对麦积山131窟壁画样品的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1) 从131窟壁画剖面结构来看,壁画的制作是先在岩体表面敷一层较厚的粗泥层找平,再敷一层较薄的细泥层,然后整体涂抹一层白色底色层,最后绘制颜料层。颜料层与底色层、底色层与地仗层之间均出现了内部空鼓,这种内部空鼓是壁画颜料层、底色层脱落的严重隐患。
2) 地仗层成分、土砂比例及粒度分析发现,131窟粗、细泥层使用的黏土应是麦积山周边稍远地区采集的更适合制作地仗层的自然细质黄土,土质颗粒度细腻,含沙量较低,干燥收缩大,易开裂,添加较多未经过筛选处理的颗粒度不均匀沙砾制成粗泥层,添加较少的筛选处理的均匀沙砾制成细泥层。
3) 依据纤维横、纵截面形貌,确定131粗泥层添加纤维为麦衣与麦秆纤维,细泥层添加的则是麻纤维。
4) 综合分析可知:131窟壁画单独使用铅丹,混合使用铅丹、朱砂、土红红色颜料,白色底色层为方解石,质地较致密。该研究为麦积山石窟131窟壁画材质工艺研究以及壁画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