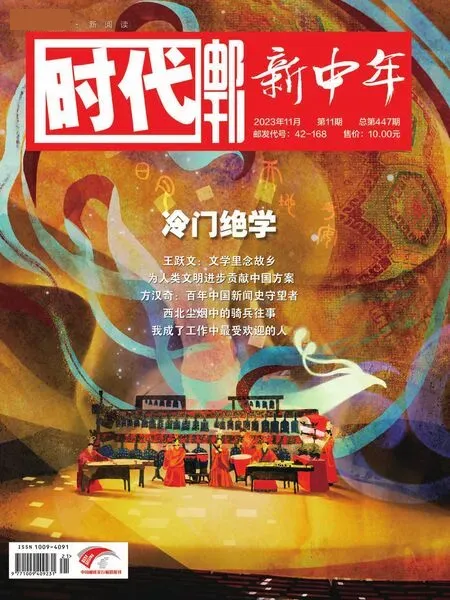田野上的社会学家:在“最普通”的村庄关注“大多数人”
● 郭玉洁
这是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两群人。一群人是研究生、教授,去过荷兰、美国、英国,会用英文写文章,善用概念、理论描述社会现象。一群人是农民,他们种玉米、红薯、山核桃,擅长养鸡、养猪、放羊,会用石磨做豆腐,在城市的缝隙里,他们拉砖、盖房、摆摊、开大车。

▲ 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团队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交流 (图片来源:央广网)
两群人的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桑岗村交织。1996年,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学者叶敬忠刚从荷兰回来,想寻找一块“长期理解中国的田野”,最终把包括桑岗村在内的4个村子选为研究点。此后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陆续把很多同事、学生带到这里,开展乡村发展和减贫实验,50余篇硕博论文在这片田野产生。
桑岗村距县城很远,有近200户人家,山不高,河不大,田地少而分散,矿产不算丰富。县里有干部曾对叶敬忠的团队直言:“你们为什么要选这儿?”叶敬忠说,他就是要选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村庄,关注那些“大多数人”。
两个名字
直到现在,桑岗村和中国别的北方山村也没什么不同。夏天,村庄在凌晨3点的鸡叫声中苏醒,村民四五点起床,去地里看玉米秧子,喂猪喂鸡喂羊。下午2点以后,村里的男人赶着羊群上山。山坡上的树枝、荆棘把放羊人的胳膊和腿划伤。养羊的人正在变多,这是村中超过60岁的人被城市劳务市场淘汰后,拾起的本行。
桑岗村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普通,但就像叶敬忠团队里一位博士生说的那样,“桑岗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国家某个层面变化的缩影”。
世纪之交,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大家脑子里都是城市”的时候,叶敬忠和他的同事、学生开始了和村庄的最初接触。
叶敬忠初次来到桑岗村是1996年,那一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30%,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当时,村里大量中青年男性去往保定、天津、北京,他们大多在工地干活。后来当过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文录那一年21岁,在北京的砖厂拉车,也摆过地摊。
叶敬忠师从发展社会学大家诺曼·龙,关注外部政策和行动究竟会在乡村引发什么反应。为了给研究创造抓手,也为了帮助农民,2000年,叶敬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筹款进行“乡村建设”项目。项目分3期,为期10年,主要做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资金数百万元。
叶敬忠的团队在坡仓乡的4个村子进行道路硬化,铺设自来水管,利用截潜流技术巧取地下水,修建了文化广场、村庄图书室,带领村民进行垃圾清理,组织妇女协会,还带村民外出参观学习。
起初,不少村民觉得“学生都是来玩的”,后来逐渐改变了看法。
学生追着村民问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干什么活都跟着,和村民一起坐在路边闲聊。晚上大家休息了,学生们还在写东西。虽然村民不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但也渐渐理解了“论文”是怎么一回事,“写论文对大家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叶敬忠那些年同时带领团队在全国乡村进行留守问题的调研,不是所有村庄都给了研究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任,“归巢桑岗”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形容桑岗村对待研究者的态度:敞开怀抱。
越来越大的“巢”
2010年,叶敬忠在桑岗村的3期乡村建设项目结束。这一年,中国GDP总额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叶敬忠的乡村建设项目经费来自国际发展组织,而国际上资助中国乡村基础设施的意愿在减弱。
2008年奥运会后,坡仓乡的铁矿与加工厂被关停。村民面临着“没有矿就什么也没有了”的茫然,有人在等待,有人重新投入城市的零工市场。
叶敬忠开始把眼光转向农民的生计。
过去,桑岗村的干部、村民知道他们在这做的都是好事,但也表达过“希望农业大学多给我们项目,多给我们钱”“在村里开个厂子,我们就都不玩牌了”。
叶敬忠的团队对此保持着警惕,因为他们做不到,这也与他们研究者和发展行动者的定位不符。他们只是想倡导、影响村庄自己成长起来,“外来的发展行动者最终会离开”。
桑岗村村民想象着能有一个大产业把他们带富。针对扶贫工作,叶敬忠在学术上提出,村庄产业发展要脱离过去那种规模化、大产业的思维。对于像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引入大产业有极大失败的可能。叶敬忠说,小农产业也是产业。他想引导农民把小农产业跟现代社会相连接。
2010年,国际上出现“巢状市场”概念,叶敬忠是提出者之一。“巢状市场”就像是个无形的小鸟巢,农民通过社交关系把农产品卖到城里,躲开了大市场的裹挟,跨越中间商。作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每个人在市场上相连,除了买和卖,还会见面、沟通,筑成一个城与乡连接的巢。其中的关键点是关系,在互动中,让“城市赋能乡村”。
完成小农户组织后,学者们通过熟人关系在城市里卖农产品。叶敬忠团队的老师们每次来桑岗,都把村里的核桃、鸡蛋、鸡鸭塞满后备厢,拉到北京,到处去送货。他们在村里选出了3个小组长作为负责人,引导他们用邮件、QQ群等来对接消费者。
慢慢地,农户每隔一两周自己去送货,凌晨3点从村里出发去北京。早上七八点,海淀区的家长去送孩子上学时,就能在小区门口取货了。这个消费者群从叶敬忠团队周边的熟人圈扩散。因为农民送货能力有限,一个点有5个消费者,跑一趟才划算。消费者便自发邀请熟人加入,这个“巢”越来越大,有了8个送货点,几千名消费者。
叶敬忠团队引导买家和卖家建立消费之外的连接,买家会请送货的农民在家里吃饭,暑假会带孩子去村里玩。北京太阳园小区的消费者们给桑岗村的孩子捐了很多儿童绘本,后来,桑岗村的图书室取名为“太阳花”。
叶敬忠团队的学者们经常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年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巢”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卖了一些东西,而且卖得又不多”。
但每次巢状市场在村里收货时,提着篮子来送鸡蛋、鹅蛋、土豆的,多是拄着拐杖、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这些老人的生计都依赖这个。”
叶敬忠团队感叹,如果村里的年轻人、思维活跃的人再多一点,巢状市场可以有更多创新。他们终究不能“代替”村民创新。
27岁的村支书许富强说,现在村里问题的核心是缺“钱”,但一位和他同岁的博士生说是缺“人”,许富强想了想,表示赞同。
叶敬忠希望村民能为自己说话,“我们是带着资源,来跟他们探讨这地方未来怎么办的。”但20多年过去,村民依然更多地用“扶持”来形容农大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此刻,盗走尸体的这只山精,体型粗壮,比成人还要高着一头,一身漆黑油亮的毛,蓬松而茂密,一看便是一只正处壮年的雄性山精。
两年前,“95后”许富强意外当选村支书,他选择担下这个责任。以前他在北京、保定做汽车销售,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为了回村,他和谈了3年的女朋友分手,每月只有2000多元工资。
村民们佩服他的初心,觉得“挺崇高的”,但认为年轻人还是太稚嫩了。在他们的描述中,理想的村干部应该是四五十岁左右,家底殷实,在村庄有威信。不少人认为村支书首先要有钱,这样可以把村里一些产业带动起来。但他们又知道,这种想象中的人并不存在,“有钱的人都走了”。
时间
某种程度上,一直在冲刷桑岗村的只有时间。铁矿厂对河流的污染停止十几年了,河流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小鱼重新出现。村民仿照“巢状市场”,也通过熟人卖起了自己的货,还邀请城市消费者来村里钓鱼。
“巢状市场”运转了十几年,村民开始每年按照季节变化进行猪的养殖、鸡的育种。发现消费者喜欢土鸡蛋,张常春买回很多土鸡蛋,尝试用孵化器孵化小鸡。为了把鸡养得更好,他还上山挖草药喂鸡。知道健康食物更受欢迎,村里近八成的农户自觉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
张常春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在桑岗村的乐队里吹拉弹唱。现在村里的文艺分子有的老去,有的离世,组织文艺活动越来越难了。但他和赵文录都提到,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叶敬忠这群人的到来,让桑岗村的文艺氛围衰退得比其他村庄慢。因为不断有外人来,有人就会有文艺表演。
如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一位副教授站在村庄的小道上,可以不假思索地讲出每个大门紧锁的空房屋背后的故事。20多年里,脚下的土路变成水泥路,而水泥路又被采矿和建高速时不断驶过的载重车压出了裂缝。
叶敬忠不会预测桑岗村的未来,“社会科学最应该避免的就是预测”。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任何趋势感到悲观,遇挫的时候,他总对学生说:“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桑岗村和他们建立了无法替代的友谊。许富强被当时团队里的学生教会了26个英文字母,一位博士生把村中一位老人当作亲人。这位老人没上过几年学,但爱读书看报,知道博士生要出国留学,老人要塞给她2000元,还买了一个10元的小手电筒送她,说:“它能照亮你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一位在桑岗扎根多年的副教授说,这是一群可恨可气可亲可敬可爱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时刻:消费者一下子订了40多只鸡,学者和村民深夜一起在院子里烧水、杀鸡、拔鸡毛。张常春形容叶敬忠是“浪漫主义者”,有时聚会后,叶敬忠带着学生们在月光下散步。一个无法被证实因果关系的事实是,这20多年里,桑岗村几乎没有孩子在中学阶段辍学。
叶敬忠觉得,现代化确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就算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也仍然有四五亿人生活在乡村,他想探索这些人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许富强希望今年的几个项目能平稳落地,能给村里安上自来水表,解决用水分配的难题。他说,哪怕就做这一件事,他当这个村支书也值了。村庄依然有吸引着叶敬忠的“能听得到的安静”,但许富强却在安静中感到孤独,村里几乎没有他能说说话的同龄人了。
今年7月的一天,中国农业大学组织的“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夏令营的学生与村民在河边办了一场热闹的联欢会。
这是一个故事被定格的时刻。联欢会“导演”张常春穿着红色的长衫,在话筒前着急地喊话,召集人们来到舞台四周。
台上,张常春和几位老人用力地吹响唢呐,赵文录在前排用力地鼓掌。“舞台”背后,那条被写进论文的高速公路上,大车正快速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