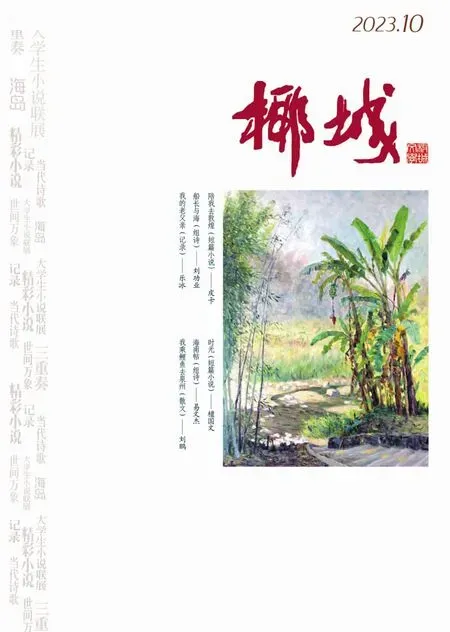风中的香樟树(短篇小说)
◎周加军
早饭桌上,朱大贵一会说菜淡了,一会说菜咸了,最后,吞吞吐吐地说:“你大姑妈病了,我想去瞧瞧。”
儿子愣了愣,抬了一下眼皮,递给朱大贵一个疑惑的眼神:“大姑妈?哪个大姑妈?”
“你还有几个大姑妈?”朱大贵鼻子歪了歪,哼了一声,“我们姐弟七个,现在就剩下我和她一头一尾两个了。”
“我以为您老在外面又新认了一个姐姐,”儿子半真半假地说,“难怪你这么上心,我就纳闷了,她怎么突然想起了你,就因为她生病了?她想起你,是不放心你,还是别有用心?这么多年她在哪里?如果她远在天边,隔着千山万水,交通不便,不跟我们来往情有可原,但情况不是这样。再说你身体不是也不好吗?就拿你这次晕倒来说,假如不是及时被发现后果真不敢设想,我就问你,你怎么不通知她来看你,你不是说她最牵挂的人是你吗?现在她生病了倒想起你来了,就通知你去,你就着急了?”
朱大贵说:“你说了这么多都没说到点子上,你也甭提我晕倒,岁数大了,难免这样,小毛小病,没必要告诉她,她当然就不知道。”
“就是知道了,她会来看你吗?做梦吧!”
“她是我亲姐姐,医院都不看了,她在昏睡中呼唤七伢子,她让儿子通知我去,我不去看她总归说不过去吧。”
“那你更不能去,他们难道不知道你是舅舅,不应该上门请吗?礼尚往来,有来才有往,但她和我们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考上大学她来了吗?我结婚她来了吗?我妈过世她来了吗?你过七十岁生日亲朋好友来了五桌,唯独她没来,她可是你的亲姐姐啊,她不来,说得过去吗?假如她生病了,走不动路,那就当别论,她活蹦乱跳不来什么意思?该来的事她都没来,太让人寒心了,你说,你还要这个亲姐姐,我还要这个亲姑妈做什么?姐姐,或姑妈,不过是顶着一个虚名而已。”
朱大贵的老脸挂不住了,在椅子上欠了欠身,突然肩膀一抖,跟着喉咙一紧,一口脓痰冲口而出,砸一下嘴有股血腥味,又砸一下嘴还有血腥味,朱大贵不停地咂嘴,心里想,血腥味快点走吧。
“你怎么了?”儿子注意到了什么,愣了一下,停住脚步,脑袋偏了偏,好像想起了什么,嘴里呼哧呼哧喘气。朱大贵没有说话,扇了一下眉毛,倔强地把头转向一边。
儿子讪讪一笑,“戳到您的痛处了?我向您道歉。”
朱大贵没理他,从椅子上撑起来,勾着腰,跑进厨房,操出一个菜篮子,在儿子一只脚放在门外的时候,把他挤回去,说:“去迟了,张二家的卤豆腐就买不到了。”
朱大贵走上了大马路,再走八百米,就会见到一个路牌,左手城郊批发市场,右手宋庄。城郊农场直供的蔬菜,又新鲜又便宜,每天一早朱大贵绕过大超市的音乐喷泉广场,经过两个街区、五个十字路口,走上画着蓝黄分界线的大马路,沿路牙再走一公里,就到了批发市场,买了菜,再散步回来。姥姥住宋庄,姐姐也住宋庄——姥姥晚年寂寞,就把姐姐说给本庄的外表孙,说来是缘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合上眼了,三个月后结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隔一年生了一对男双胞胎。
朱大贵走得急,出门时忘戴皮耳捂子了,阴冷的风吹打着耳朵,把它们变成小冰块,他不敢用手去摸,害怕它们掉下来。他根本不在意,不仅如此,脑子里装的不再是新鲜的蔬菜,也不再是张二家掺了芝麻的卤豆腐,而是病危的姐姐。早上他被电话吵醒,自称外甥的人说话如抖包袱,他掺不进一句话,干着急。外甥把话全部抖出来,才知道姐姐病危了,朱大贵的身子立即往下沉,沉到没有天日的混沌地方,感觉自己不再存在了。
柏油马路的前身是一条七拐八弯的土山路,朱大贵想起六十多年前颠簸的独轮车,一边挂着粮食和农产品,一边吊着拖鼻涕的朱大贵,推车人是姐姐。去姥姥家必须赶早,途中要翻过两个小山头,两个下坡路,第三个上坡路走到一半,就到了姥姥家。转进宋庄的岔道口,朱大贵停下来,用脚后跟在路牙的趴石上垫了垫,那个架势好像两只脚同时踏中一块元宝。不到五分之一路程,就浑身出汗了。路还长着呢,朱大贵想,散步可以到姐姐家,问题是这路程远远超出了他散步的范围。此时朱大贵多么希望能来一辆车子把他接走。他现在后悔为什么不坚持让儿子开车送他来。他也知道儿子说的是气话,如果他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儿子会开车送他。
朱大贵跑到路中央拦车,开车的人绕过他,加速通过。朱大贵想,这些人一定认为我是一个老头子,怕我讹诈他们,这年头好人做不得。朱大贵终于拦住了一辆车子。车子是一辆白色的奥迪,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朱大贵趴在车头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说拦车的理由。姑娘开车门让朱大贵上车,朱大贵一上车就让姑娘开视频拍照,姑娘说我被您的话感动了,您是一个好人。朱大贵说你开视频吧,我对着手机说一句话,我是自愿搭车的,出了问题跟你无关。
见到姐姐身体团在棉絮里,朱大贵心头一凛,一行老泪就奔了出来。姐姐睁开眼睛,见是朱大贵,惨然一笑,问是怎么来的,朱大贵说是跟车来的。姐姐挣着从床上坐起来,朱大贵按住她的手臂,让她不要动。姐姐一定要坐起来,朱大贵就拿一个枕头垫在她的后背,让她舒适地靠在床背上。
朱大贵的肩膀耸动起来,像一个小孩伏在姐姐的怀里痛哭,说到动情之处,用手拍打着被子呼喊,“我苦命的姐姐,怎么就这样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没有早点告诉你,是不想让你替我担心。”姐姐笑起来,“想不到七伢子你也老了,牙齿没了,头发一根黑的都没了。”
“可不是,一晃眼啊,人就晃没了。”朱大贵说。
朱大贵和姐姐在卧室里说话。好几次姐夫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毛玻璃上,朱大贵知道姐夫在偷听,故意提高嗓门。
朱大贵和姐姐共同想起小时候一桩事,突然一起笑起来。
“小鸟真可怜,鸟妈妈真蠢。”姐姐说。
“可不是吗?鸟妈妈以为我们要杀死它的孩子,在香樟树上叫唤了一夜。”朱大贵说。
“那个小鸟不会死吧?”姐姐问。
“肯定不会,不是你给它断腿上了药,用医药纱布包扎好,放在棉絮做成的窝里,让我守着一个晚上,害怕被猫拖了,一早就把它送到香樟树上的窝里去的吗?”朱大贵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姐姐说,“香樟树还好吗?”
“当然还好,又高又壮,就是老了。”朱大贵说,“姐姐怎么问起香樟树了?”
姐姐唉声叹气起来。
“怎么啦?姐,有什么话不能说?”
“我想要香樟树做棺材。”
朱大贵突然不说话了。
“那棵香樟树——”姐姐说,“父亲死后葬在山上,母亲死后也葬在山上,他们都是棺木敛尸,我死后也装在棺材里葬在他们身边,生前没能尽孝,死后陪伴着他们也算是尽孝了。”
“哦!”朱大贵说。
“——那棵香樟树,父亲答应过给我的,你当时也在场,父亲也问过你,你当时不住地点头,现在你舍不得了吧?”
“哦!”朱大贵说。
“把香樟树给我吧!”姐姐说。
“把香樟树给我吧!”姐姐又说。
相同的话姐姐说了不下十遍,但朱大贵始终不松嘴。两个外甥又急又气,想冲进来,逼着他答应,但他们的父亲用平静的表情安抚他们,嘴里警告不要造次。
朱大贵说话了:“做棺材的木头有许多,姐你为什么非要香樟树?再说香樟也不是什么好材料。”
姐姐说:“你就答应姐姐吧,姐姐这一辈子就向你提这一个请求,看在姐姐要死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
“香樟树是祖传遗产,父亲也有过遗嘱,我说了不算,我还有两个儿子,我得问问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二话不说就把香樟树给你。如果他们有一人反对,这个事就难办了。”
“你是我亲弟弟,他们是我亲侄子,你只要说一声,他们敢不同意?这树是我栽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可是当着全家人面说过,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姐的想法,但我确实不能做主。”
姐姐又说了许多请求的话,意思都一样,要香樟树做棺材。但不管姐姐怎么说,朱大贵都闭着眼睛不作一声。姐姐又哭了,但没眼泪。
“真是没良心的白眼狼啊!你是天底下最无情无义的人……”姐夫大骂起来。
朱大贵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在翻滚,姐姐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结婚没有新房,姐姐背着姐夫把全部积蓄给他建房,连把准备建房子的砖头都用拖拉机拉给他,这些他怎么能忘记?
“你姐姐在你身上的付出,难道抵不上一棵树?”姐夫继续骂他。
朱大贵恍然大悟,姐姐每次帮助他,都提出要香樟树,但他一直没松口。他为什么不松口?难道就是为了遵守父亲的遗嘱,让他一定留住香樟树?父亲为什么要立这个遗嘱,难道就是因为嫁出去的闺女就像泼出的水,永远不能染指娘家的一砖一瓦,甚至是一粒土?这可是古时候遗下的陋习。朱大贵想明白了,这大概是他和姐姐隔阂的原因。
“你说咋办,我们就咋办。”两个外甥一起打断姐夫的控诉,“要不我们现在去把树砍了?”
“别啊!”朱大贵差点喊出来,“你们这样做会让我很没面子的。”
“你们母亲不在早晚,”姐夫又说,“要做现在就去做。”两个外甥受到怂恿,立即从桌边站起来,摩拳擦掌,做出要去砍树的架势。
“我完全同意!”朱大贵一拍大腿站起来,冲着堂屋里的姐夫大喊,“刚才我只不过打了一个盹,回忆起许多有关香樟树的往事,说舍不得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看着它长大长粗长壮,跟我们一同经历风雨,一起度过艰难岁月,不是人却有人的感情。”
朱大贵又说:“既然姐这样说了,我怎么能不同意?姐为原来那个家做了多少事,操碎了多少心,我怎么能记不得?一句话,没有姐,就没有我。”
姐姐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过了一会儿,她下定决心似地说:“趁大家都在,帮我把家产分一下,了却我一块心病。”姐姐满怀期待地看着朱大贵,到底是姐弟情深,朱大贵立即读懂姐姐眼神里的信息。
“好!”朱大贵说,“那我就当仁不让行使一回做舅舅的权利了。”
姐姐的宝贝藏在床肚底下一个蒙着灰尘的木箱子里。朱大贵接过姐姐的钥匙打开生锈的铜锁。房产证、存折,二十块袁大头,两只银饭碗,两双银筷子,小孩子们戴的银项圈银脚铃银手铃银耳坠,出嫁时母亲送的祖母绿玉手镯。朱大贵一面赞叹姐姐的收藏,一面一一过目,认真登记在册,以防遗漏。家产当然要分给儿子。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姐夫不主张给一个出嫁的女儿分家产。朱大贵说:“即使是嫁出去的姑娘也是你的女儿,你身上的衣服是谁给你买的?你的营养品是谁给你买的?你生病了又是谁对你不离不弃,全身心地照顾你?”姐夫被朱大贵说得哑口无言。朱大贵一碗水端平,两个外甥没有异议,外甥女不在场,相信她也不会有异议。
傍晚,朱大贵回到家,又累又高兴,累是岁数大了,身体吃不消;高兴是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外甥们爱戴和尊重他,他行使了做舅舅的权利,帮助姐姐解决后顾之忧,最主要是姐姐情绪稳定,思维清晰,跟他说了许多话,回忆了许多往事,根本不像一个将死的人。
儿子回来,见到朱大贵就着花生米喝酒,又见他满脸笑容,很是纳闷,在他记忆里,朱大贵已经好多年不喝酒了,就问有什么高兴事。朱大贵把一盅红高粱倒在嘴里,咂摸了一下,把头扬起来,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你问我怎么这么高兴,我偏不告诉你。”
“你捡着钱了?要不,你买彩票中大奖了?”
“统统没有!”朱大贵往假牙缝里塞了一颗花生,朝嘴里丢了一盅酒,斜着眼睛看着儿子。
“好吧,我也有一件高兴的事告诉你,我们这里要拆迁了。”
“你听谁说的?”朱大贵一愣。
“小区里都贴告示了。”儿子抢过朱大贵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么说,这事板上钉钉了?”朱大贵心里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
“我已经算过了,我们这个老屋上下楼面积120平方,加上屋前屋后院子,少说200平方,如果按照户头,我们应该分到三套房子,我一套,你一套,还有朱同一套,我不要房子,我已经有两套房子了,我要把房子换成钱。”
“我同意!这下朱同有房子了。”朱大贵欢喜地说。
“朱同有房子就可以娶媳妇了,你是为这个高兴的吧?”
吃过晚饭,朱大贵破天荒去了小区广场。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他喜欢安静,喜欢宅。每天晚上都有人跳广场舞,听到音乐轰鸣声,他把所有窗户关紧,热闹是别人的,他心里只要安静和孤独,老伴过世后,他再没有去过广场。今晚广场灯火通明,没有人跳舞,人们东一扎,西一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烈的笑容,好像被兴奋包围了,共同的话题是拆迁。布告栏前面围着一溜人,朱大贵插了进去,看到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满了名字。他眼睛顺着第一个名字往下遛,第一个布告栏里没有他的名字,第二个布告栏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他有点着急了,把手点在名字上一个个找,像初识字的小孩看书一样,生怕漏掉一个字。第三个布告栏里也找完了,还是没有他的名字,他急得脸上流下了汗,心想是不是遗漏了,或者不拆迁了。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第四个布告栏里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个,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名字,看到名字的刹那,喉咙里哧溜一声响,好像滚落下一个东西。他把手指紧紧地按在自己名字上,生怕它溜了。
朱大贵被人群挤了出来,重新回到广场上,听到别人谈论拆迁补偿项目,心里很是抵触,感觉自己被忽视了。
“都拆迁了,住高楼了,还拉长着脸,你难道不高兴?”有人冲着他的脑袋说话。
朱大贵一抬头,见是老于。老于比他高一头,俯视着跟他说话。他们是郊区菜市场的常客,结伴买菜,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谁有高兴的事情谁请客,在菜市场高朋小酒馆里喝高粱烧,喝得满嘴说胡话,再手拉着手回家。
“住了几十年了,有感情了,换个地方住会不习惯的。”朱大贵说。
“那是你的想法,我住哪里都习惯。”老于说,“我不要新房子,新房子规划在城北,那里去郊区菜市场,要多走三里路,我走不动了,我要去敬老院。”
“你去敬老院?”朱大贵一惊。
“我反正一个人,要房子干吗?我要钱,房子和树都折成钱,放在一张卡里,随身携带,多安心。住进敬老院里,有人伺候,有人做饭,有一帮老头老奶奶整天围着你说话,难道不热闹?”
“我情况跟你不同,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成家了,小儿子情况有点特殊,到现在还没有成家,我必须给他弄套像样的房子,他结了婚,我的心事也了了。”
“对了,你那面积弄个像样的房子不成问题,而且你还有一棵香樟树,恐怕要卖很多钱。”
“香樟树也能卖钱?”
“对啊,我那棵白果树早不结果了还补贴一万元,你那棵香樟树你不是让我看过?有几十年了吧?有人把它看成宝贝,听说出价几十万,真是钱多人傻。”
“你听谁说的?”
“大家不都这样传的?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香港老板,人家要移走,你儿子都跟人家签订合同了,人人都这样说,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树不能卖!”朱大贵脱口而出。
“不能卖?你要带进棺材里去?那可是几十万啊!”
路过小区彩票屋,朱大贵买了一张两块钱的大乐透,朱大贵坚持买彩票,有人中了几百万,有人中了几千万。朱大贵也想中奖。小儿子要买房子,要成家,条件不够,拿钱来凑。安置小区的房子很多人都有成见,说质量不好,他要给儿子买一个好房子,再给一笔装潢费。钱从哪里来?干脆把自己那套房子也卖了,跟老于去敬老院,但他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朱同的确需要一个女人,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就这么荡着,早晚要出大事——曾经为了一个女人他动手把人家打进医院。不能让他再出事了,这是一个好机会。
姐姐进入了弥留期,大外甥直接开车把他接过去。
几天不见,姐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更衰弱了,脱了形骸,跟一个死人无异。
朱大贵唤了一声姐姐,姐姐没有回应。朱大贵着急,连唤三声姐姐。姐姐努力地动了动嘴,外甥趁机喂了一汤匙糖水。姐姐又动了一下嘴,外甥又喂了一汤匙糖水。姐姐眼里露出一线光,朱大贵赶忙说:“香樟树。”姐姐又闭上了眼。
姐夫把朱大贵拉到一边,“你姐姐现在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清醒起来不停地说起香樟树,说树是她栽的,外公在世的时候答应给她做嫁妆,但外公并没有兑现。她一直等着这一天,你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我就问你这事靠不靠谱,不要人死了,棺材还没有着落。”
朱大贵心里挣扎一下,本来想实话实说,但话到嘴边,犹豫了一下。说出来的是另外一句话:“等朱同回来,让他们兄弟俩把树刨了,我亲自送过来。”
黑色的轿车拦在路中央,一个瘦子从驾驶室里下来,从车头跑到另外一侧,打开车门,扶出一个胖子。胖子脖子上的金链子能拴住一条藏獒,一个手腕戴金表,另一个手腕套串珠。瘦子把胖子扶出来,让他自由呼吸空气,然后走向朱大贵,问朱全家是不是住这里。
朱大贵一惊,心想他们怎么问起我大儿子来了。但朱大贵没有说朱全是他的大儿子。瘦子说:“我们来看一棵香樟树。这是我们老板,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老板中标了,将来要开发成高档小区。”瘦子说的是普通话。胖子说的是港台话,说了半天,朱大贵一句都听不懂。
朱大贵把瘦子和胖子带到香樟树下面,让他们自己看。胖子一见到香樟树就激动不已。朱大贵对瘦子说,“一棵香樟树就这么激动吗。”瘦子说,“你不懂,这不是一棵普通的香樟树,你难道看不出来它长得像一个汉字吗?”朱大贵当然看不出来。“你从远处看!”瘦子说。朱大贵跑到篱笆那里,看了一会儿,很沮丧。
“难道不像财字的繁体字?”瘦子说,“我们老板很迷信,上次从你家经过的时候,老板在车里看到,要不是当时赶去签合同,他一定会从车里下来,他让我打听,我就打听到你儿子了。”
“我儿子真跟你们签合同了?”朱大贵问。
“三十万。”瘦子说。朱大贵心里一惊。
“这都是小钱。”瘦子又说。
瘦子和胖子走后,朱大贵围着树看了又看,怎么都看不出它像一个汉字,但是他听见瘦子跟胖子说,明天就带人刨树。朱大贵更相信,儿子跟人家签了合同。
朱同回来了。朱同十八岁就去南方打工了,人家打工一年到头,都带钱回来,而他每年回来都是空手。朱大贵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这么多年他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朱同回来不是跟他要钱,就是跟他要媳妇。零用钱,朱大贵能尽量满足;要媳妇,朱大贵就头疼。朱同一见到朱大贵就说拆迁,他这次回来也是为了拆迁,他告诉朱大贵一个好消息,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女朋友催他回来的。
“原来是这个,你想怎么办?”朱大贵要跟朱同摊牌,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老是让他缠着不放手。
“三套房子,大哥的房子归大哥,我的房子归我,你的房子我打算卖了,一部分钱装修,一部分钱结婚,丽丽说了,没有房子不行,没有礼金也不行。”
“你把我房子拿去了,那我去哪里?”朱大贵说,“让我跟你们住一起,我一天都受不了。”
“你去敬老院。”朱同冷冷地说。
朱大贵气得脸上发白,大骂:“你这个白眼狼,我养你疼你这么多年有什么用?”
当晚,朱全带来了酒和菜。他跟朱全说话,朱大贵才知道他们早就约好了。熟菜微波炉热一下,摆出三只盘子,两只碟子。酒倒在高脚玻璃杯子里。朱全让朱大贵喝酒,朱大贵不喝,朱同让朱大贵喝酒,朱大贵也不喝。朱大贵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太了解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他真喝酒,他们一定拦着他说,你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能喝酒。朱大贵瞄了一眼酒瓶,心想还不够我塞牙缝。朱大贵年轻时候很能喝酒,白酒八两很轻松,一斤刚好,一斤以上晚上走山路不偏不斜。朱大贵不是不想喝酒,而是在跟他们怄气,一个不省心,另一个也不省心,有时候两个人合起来让他不省心。他摆脸色给他们看,警告他们,不要在他眼皮底下耍小聪明。
朱大贵吃了一口饭,然后抱着一只大茶缸喝茶。两个儿子划拳,“哥俩好,三星照,四喜财……”朱大贵从侧面打量他们,发现他们长得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也不像朱大贵,外貌不像,脾气不像,做事风格也不像,朱大贵大酒量,他们充其量一人半斤。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话,他们说的是发财的话,一个不着边际,另一个也不着边际。他们又说怎样处理朱大贵。
“让他去敬老院。”一个说。
另一个一拍即合:“让他去敬老院。”
“让他去敬老院。”两个一起说。
“我哪儿也不去!”朱大贵生气了,丢下茶缸走了出去。
夜色昏暗,月亮时隐时现,蘑菇似的块云层层叠叠,在天幕上流动。今天是什么日子?朱大贵习惯于用阴历记日子,记住这些日子,就等于记住了菜场打折的日子。朱大贵使劲想今天是什么日子,走到香樟树底下也没有想起来,索性坐在磨盘上。磨盘大概有上百年了吧?朱大贵想,那时他八岁,姐姐十五岁,妈妈身体不好,其他姐姐们下田干活了,父亲挑着货郎走村串户讨生活,家里再没有其他人了,姐姐拿糖果哄他一起推磨盘的情景历历在目。自然而然,另一个场面,60年前的一个场面出现在他面前:
弟弟:“姐姐,这树叫什么名字?”
姐姐:“叫香樟树。”
弟弟:“为什么叫香樟树?”
姐姐:“它会发出香味啊!”
弟弟:“香樟树的叶子为什么是红的?”
姐姐:“弟弟,你不知道啊,我把它从山里挖出来,用双手拽着回来,手磨破了,血淌了一山路。”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棵树成了姐姐的心病。那时朱大贵刚上小学,夏天在香樟树的阴凉下读书,村里的四个二流子,他们抢了朱大贵的书,还把朱大贵打了一顿,要不是姐姐及时赶来,朱大贵一定要被他们打死。他们打了姐姐,还把姐姐按在树底下侮辱了……
两个醉鬼儿子,互相扶持着出来,一路说着醉话,好像他们早已是有钱人了。是这棵树带给他们发财机会,一个要跟发财树合影,另一个也要跟发财树合影,他们骨子里没有留念的感情,他们眼里只有钱。他们跟树合完影,才发现朱大贵坐在磨盘上,他一直冷眼看着他们丑陋的表演。
“我以为他去敬老院了。”一个说。
另一个也说:“我也以为去敬老院了。”然后,看着对方大笑起来,另一个也大笑起来。朱大贵突然悲从中来。
“我跟朱同刚商量过。”朱全说,“你去敬老院最好。”
“对,你住敬老院我们省事多了。”朱同醉醺醺地附和,“房子我们分了,钱也分了,树也卖了,你不去那里去哪里?”
“你们谁也别想,树是你姑妈栽的,她现在要死了,应该把树砍了给她做棺材。”
“你的心真大,香港富商都出到三十万了,三十万香樟树做棺材,你真豪横。”
“哥哥不要跟他多费口舌,他就是个疯老头子,三十万元的棺材,埋在地下烂了,一文不值。反正,明天富商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三十万元就是我的了,我们今天晚上待在这里不走,保护着这三十万元,防止有人搞破坏。”
夜色更加昏暗,风吹落了最后几片叶子,朱大贵抬头向上看,树木像是光秃秃的化石,感觉自己即将要砍的不是一棵树。但朱大贵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做事从来不图一时脑热,骨子里有一股快意恩仇的豪侠气概,决定做的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他当即找出早年上山砍柴的斧子。斧子包裹在油布里,拿出来锃光闪亮。砍树声惊动了鸟窝里的鸟儿,它们惊叫起来,在树梢上盘旋,不愿意飞走。朱大贵深感不安,对着树梢说话:“对不起了,鸟儿们,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姐姐比你们更需要这棵树,你们找其他树做窝去吧,我也要去敬老院了。我要把它砍了,让姐姐的耻辱永远埋在地下。”
朱大贵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拿起斧子,朝树根砍去,“吭吭”的声音在风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