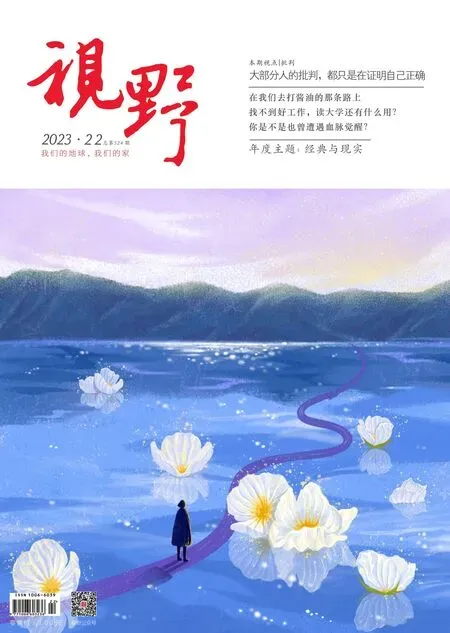我们需要“地铁判官”吗?
/维舟
前一阵,在青岛地铁上发生了这样的风波:有人指责旁边的一位大妈一人占了俩座,争执中,那位大妈的老伴说:“我占十个你也管不着!”话音刚落,旁边有个小伙子突然出手扇了那大爷一巴掌,随后转身扬长而去。
这位“地铁判官”自此成了都市新传奇,虽然事后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网上却一边倒地挺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判官,认真办案。”“第一,绝对意气用事;第二,绝不漏判一件坏事;第三,绝对裁判得公正漂亮。”甚至在他与被打的大爷和解之后,仍有人说“能不能全国巡扇,把那些在地铁上不讲素质、胡搞瞎搞的全扇一遍”。
这当然是戏谑,但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地铁判官”叫好?
在这些叫好声的背后,是许多人的积压已久的不满:他们受够了那些在公共场合“不讲理”的人,却又无法加以制止,警力既无法及时赶到,调解起来也可能耗费时日,此时,他们就格外希望有个神灵能从天而降,当即大快人心地“立即实现正义”。在这种心理期待下,“地铁判官”当然就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了。
歌德曾说过,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这体现出德国人高度的法治精神:哪怕正义难以伸张,但法律必须遵从。然而在我们国内,很多人的选择只怕正相反,因为中国人历来相信,实现正义才是道德秩序的根本,法律倒是常常不当回事。
实际上,传统社会对那些“替天行道”的侠客所寄予的期望就是如此,这些神出鬼没的英雄随时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主持正义、重申道德、保卫社会,但自己却不会加入其中。然而,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要“地铁判官”,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中国人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与陌生人大规模互动的经验,他们目睹了许许多多自己看不惯、看不懂的现象,却深感无能为力。
以往在乡土社会,没有那么多人胆敢偏离社区规范,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那会遭到所有人的议论乃至道德谴责,足以让当事人很久都抬不起头来。薛亚利在《村庄里的闲话》一书中就曾指出,“说闲话”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道德制裁,“负面性的闲话评价,很容易对个体造成一种强迫性的暗示”,因为“闲话其实主要是借助言论评说来实施的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无视这样的社区评价,将对其生活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这就足以让人们不敢做得太过分。
然而到了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在地铁上占俩座位、在景区插队/逃票、在公共场合让孩子随地小便,这些经常引起纠纷的事件,却往往拿当事人没办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共管理人员难以及时介入,此时,如果此人没有道德自我约束,又完全不理睬他人的感受,那就真有可能没什么能阻止他占到小便宜。所谓“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意味着无所顾忌的人,也就不再受什么约束。
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此有多深恶痛绝。面对这种情形,人们以往有这样几种话语:一是谴责“没有公德心”,二是责骂“素质低”,三是诉诸“文明”,四是强调“规则”。然而,这些往往要么很难立竿见影地约束对方行为,要么改变起来需要长期的社会变迁,甚至一两代人都未必能完成。可想而知,很多人已经对此失去耐心。
如果说这种心态还好理解,那么人们的正义期待则完全错付了对象:谁给了“地铁判官”权利去扇别人耳光?如果每个人都独断专行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在公共场所这样私人执法,那岂不天下大乱?
法律学者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早就说过,中国法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百姓要求“立即实现正义”,这都是基于对实质正义的理解,然而这么一来,就时有不注重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形出现,有时制造出冤假错案。“地铁判官”所理解的正义,是凭借自身的道德直觉而非法律,但自命正义就可以侵犯他人权利了吗?
对自身的道德直觉有着迷之自信,不惜对他人施暴,这种人既谈不上正义,造成的后果也可怕得多。甲午战争时,赫德曾说过:“就正义而言,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正义——也许只有这种正义,即由他们认定别的干了错事的国家必须改正。”不难看出,“地铁判官”也有同样的倾向,那就是自视为正义的化身,似乎有权去改正别人的错误行为。
就在不久前,同样是在青岛地铁上,一位大妈肆意辱骂一位怀孕少妇是“猪”,而起因只是嫌对方挤到了自己;在重庆地铁上,一位大妈用扇子狂扇女孩耳光,都打出血来了,理由是怀疑对方偷拍自己儿子;在山东东营的公交车上,一位大爷与公交车司机发生矛盾,多次辱骂并动手殴打司机。这些施暴者都丝毫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还理直气壮,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错在对方,自己的做法因而完全正当——实际上,他们就是另一些“地铁判官”。
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里,仅凭己意去裁决别人行为,那问题就更大了。在郑州地铁上,有位大妈怒怼小情侣在地铁上旖旎“恶心”;而在另一个城市地铁上,一个女孩子因为穿超短裤而被训斥“你穿这个像什么样子”。这种“看不惯”其实是一种对年轻人文化现象的保守反应,但在一些老人眼里,这些都是偏离社区规范的行为,为什么不能管管?然而,想想看,你和恋人在公共场所拥吻一下,却被人当面唾骂,你会是什么感觉?
时代已经变了,指望“地铁判官”能像侠客一样当场实现正义,往好里说也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
即便是侠客,一如龚鹏程曾论述的,从宋代起,其“原始盲动力量,必须要在清官所代表的清明道德理性精神控制、导引之下,敛才就范,才可以表现为理性”。他正确地指出,那种自认怎么合适就怎么干的侠客人格,在近代固然批判了社会不义,但却也排斥温和改革、说理的方式或合法抗争,“而把批判对象视为恶,以自己代表善与正义,更是近代知识分子权威人格的根源”。
可以说,像“地铁判官”这样的人物,制造的问题可能比他们解决的问题更多。固然其行为或许让人觉得“快意恩仇”,却让人更进一步无视解决问题的合法程序,迷信“只要是正义化身,暴力也是正当的”。这只能让类似的纠纷出现时,变得更难解决。
一个好的社会,不需要“地铁判官”。这不是他们品德高尚与否的问题,而是因为现代法治社会本来就不应有人自行执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全社会对规则的尊重、合理的纠纷解决方案,以及一套健全的执法机制——这些听起来肯定没有“正义立即实现”的快感,但这才是现代文明的可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