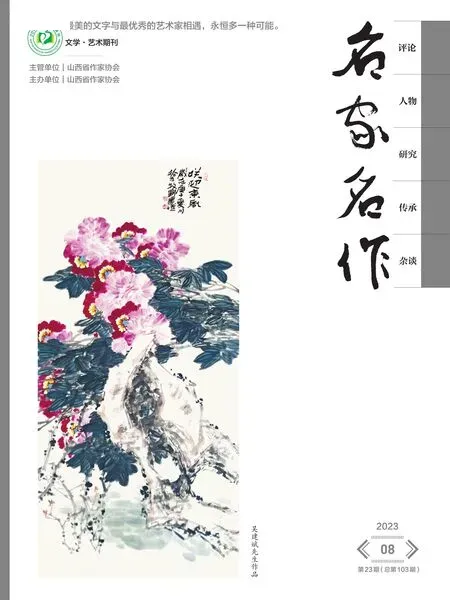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探析
——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
陈乐宣 谷 月 戴雯婧
网络小说影视化是一个文字走向影像、两种叙事艺术交融碰撞、以调动声画的形式突破文本所建构的形象桎梏的过程,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审美空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经典范式,比纸面的语言文字更具有渲染力。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喷涌是当下中国大众文化最鲜明的文化景观,《长安十二时辰》作为一部架空历史题材的IP 改编佳作,其成功出圈对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有着深刻的示范指引作用。
一、原著小说的扎实开垦
“在网络时代产生的网络小说,毫无例外地被烙上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深深的印记。颠覆了历史理性的网络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将深度模式削平,倡导平面化。网络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深度、人人围观、充满差异的凹凸世界。”[1]马伯庸深谙久久固守单一注定流于平庸之道,在《长安十二时辰》这部架空历史小说中力避单一化,力争多元化书写,以包容并蓄的态度将多种类型小说的典型特色巧为己用,在借鉴历史现实的基础上,依托现代叙事构建起一个合理的叙事空间和结构,实现作者价值观在古代社会的现代演绎,深挖历史小说的价值意蕴。
(一)古代题材的现代叙事策略
从原著小说的文体类型归属上来看,《长安十二时辰》是一部含混而又多重的作品,很难被单一化定性,它既是大唐风物的忠实演绎者,又在字里行间透出明显的现代游戏思维,譬如马伯庸写作此书缘于一个沙盘类电子游戏《刺客信条》,其游戏属性对沉浸式场景、情节的闯关式推进等方面的要求,催生出小说中章末借长安舆图标注人物行踪、同一情节不同角色的全过程同步推进等要素的构设。游戏元素的加持注定《长安十二时辰》有别于一般温暾的古装传奇武侠小说,而更倾向于古代反恐题材的快节奏孤胆英雄戏。为了让这一特质更加明显,马伯庸对小说剧情做了切割:借鉴美剧《24 小时》的分集方式和美剧思维,将“反恐”主题叙写到极致,同时建构起一种“时空高度凝练和压缩式的文体结构”[2],将故事人物的活动时空严格限制在天宝三载的长安城,半个时辰为一章。马伯庸广收博取的创作新意,使《长安十二时辰》成为网文界的扛鼎之作,其在文学想象层面高度兼容并蓄的特质,恰是书中大唐开放包容的盛世风度的完美体现。
“非线性叙事”指的是“将不同时间段的故事碎片化并重新排列组合,并非严格按照现实的时间向度来组织安排的不完整叙事”[3]。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以上元灯节张小敬与李泌破案拯救长安为主线,以右相与太子之间的朝堂争斗、狼卫步步紧逼、安西第八团守卫大唐的战斗回忆等多条副线为辅,将情节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中进行差异性编排,设计多线索并行或错位的复线叙事,将故事情节“碎片化”,肢解、分离却又始终归属统一的整体,读者只有阅读完两条并行发生且时而交错的主要故事线,才能掌握故事的全貌。
(二)庙堂权斗与江湖侠义的创新融合
《长安十二时辰》既有历史权谋小说的尔虞我诈,在心机与战术、策划与战略的你来我回之间招招致命,一子慢则满盘皆输的紧张刺激;又有侦探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中追凶破案、用丝丝入扣的推理拨开“谜”之内核外层层包裹的迷雾。然而,墨守成规、杀死一切文学新生的可能性并不是马伯庸的笔调。在拯救背景铺垫上,小说摒弃了权倾天下的在位者的正面形象的一贯书写,转而将笔锋转向摇摇欲坠的社会结构,暗潮涌动的腐朽与黑暗正一点点吸干天朝上国的能量,煌煌长安和浮沉人性都在最广义和最狭义上被掀开一角。在拯救目标上,小说否定了以“为君王服务”为核心理念的具体现实秩序,君王将此次危机视为对太子能力的考察,权臣将长安百姓的生死视为林相与太子党争的赌注,而只有作为“死囚”的张小敬为了黎民舍命奔波,那句“不讲规矩”的办案方式是他对整个现实秩序的不信任,甚至是绝望的心迹展露。再次,作为各类型小说的紧密衔接点,“张小敬”形象的刻画为“正义表达”提供了某种新的诠释类型与可能,以及重构“正义”的想象空间。张小敬的形象亦正亦邪、亦侠亦盗,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忠肝义胆、江湖气十足。其“阶下囚”身份看似处庙堂之高却又与百姓紧密相连,各方势力都盯死了张小敬,随时面临生与死的颠覆。生如浮萍,命如草芥,由不得一点自我掌控,封建王朝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命运轻而易举地拿捏,张小敬无论是身份定位还是行为归属上都充斥着对传统官府、庙堂的隐喻性批判与结构性反讽。
二、影视化过程的破壁创新
网络小说影视化的过程中并不能以还原小说剧情为第一宗旨,经济效益的趋势下更应考虑到“隐含的读者”,通过对剧情改编、影像表达等再创作环节的破壁创新,赋予网络文学新的生命力。《长安十二时辰》一方面通过还原网络小说的文本精彩满足了书迷的定向期待,另一方面针对不合理的剧情进行了理性改编,以匠心精神打造“长安”印象满足了观众的创新期待。
(一)影视化中对核心快感机制惯例的反叛
在“女性向”审美的大环境里,原著小说男频文的文本特色难免存在抵牾。作为网络男频文影视化改编的成功范例,《长安十二时辰》除却本身异于其他网络小说的文体结构和文本张力外,在原著改编剧本方面也颇见功力。人物设置上,《长安十二时辰》并未遵奉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或“大男主”路线,而是弱化了原著中张小敬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继而强化了李必这个角色的生动性,一改“大男主”为“双男主”结构。编剧没有选择强行为张小敬捏造“为爱对抗全世界”或“为爱放下屠刀”等热销感情线来保证收视率,而是在延续原著英雄刑侦主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李必及其身后的历史政治支线,两位男主一动一静,一个奔走坊间,一个案前推演,素昧平生的二人为保全长安建立起宿命般的信任。《长安十二时辰》的“双男主”影视改编,既免于落入“儿女情长”感情线的俗套,又充分扩展了受限于原著叙述时间的历史政治线,将长安平凡一日背后的英雄孤胆、明争暗斗叙写到极致。
其次,《长安十二时辰》集“架空、历史、刑侦、武侠、政治”等多类型于一体的文本特质,恰好契合“借助于想象认同来炮制正义与邪恶并存、唯美与快感与共的喧哗景象”[4]的世俗化类型小说特征,除却网络小说惯用的核心快感机制衍生出的消费性趣味外,《长安十二时辰》中对大唐长安“一街一坊、一茶一碗、一揖一喏”妙入毫颠的唯美描摹,极具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正是弱化快感机制、维持张力的反类型化书写。此外,作者始终以理性为中心,站在上层决策的角度构建故事逻辑,而非一贯地迎合大众快意恩仇的感性诉求,呈现出了良好的价值观构建,拔高了作品的格调。电视剧中改编了“唐玄宗在生死关头做出的选择”:美色诱惑>死亡威胁>帝王尊严,改为圣人切身体会百姓之苦后,励精图治、恩泽黎民,避免了虚构情节导致人们对历史的过度消费、娱乐化解读,而是维护了历史的严肃性,为剧作注入了思想性。
(二)社会历史画卷的延展与深化
导演曹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长安十二时辰》的真正主角是“长安”,他们希望通过以细节化的符号实现对社会历史画卷的延展与深化,进而建构起长安印象。对社会历史画卷的展现做了特殊的细节处理与增减式表达,是《长安十二时辰》影视化改编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在小说和电视剧里,对上元日长安印象的构建主要倚靠火元素的贯穿。火元素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一个突出外现符号,小说中有很多对九幽地狱“阙勒霍多”、太上玄元大灯等灯器的描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语言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也十分抽象;而影视剧中的火元素更加直观,视觉冲击力更强烈。如以一只掉落燃烧的灯笼特写开篇预示整个故事,每一剧集开头封面的色彩会随着案件紧急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每一集在交代完主线故事后都附有伏火雷制作进程的闪影,滚烫流动的岩浆、迸发的火星等都是火元素的化身,预示着灾难的发生。
此外,“半设计”的场景打造和视听符号的精良构造也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画卷展现的延展与深化,剧作中,从场景、礼仪风俗、服饰、妆容等非语言符号到台词、音乐、诗词等语言符号,都是马伯庸和曹盾导演的团队带着考据精神深挖中华历史文脉,查阅多方资料,借力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融入作品的细节中,通过声画的调动建构“长安”符号。
在非语言符号搭建上,剧中“半设计”的场景打造十分瞩目,比如太上玄元大灯的搭造以莲花为底座,仙山为主景,祥云漂浮;灯会盛景除了大仙灯外,还有鱼灯、走马灯、龙舟灯等多种灯笼样式;长安城参照古代营造都城的习惯,建筑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来设置。能与此等胜景相得益彰的,唯有对往来其间的人物进行细节化呈现和多样性展示。服饰是身份的象征,剧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靖安司司丞李必的发簪,有别于观众对于簪子佩戴方式的普遍认知,名为子午簪,从后向前与肩膀垂直插入,是道教人士独特的发簪。此外,穿衣人的身份、地位与做官品级则通过圆领袍的颜色体现。由于唐朝万邦来朝,受西域风格影响,唐代的妆容和服饰皆呈现出与传统美学相异的景象,常见的妆容包括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等,“浓墨重彩”是这些妆容的共同点,服饰式样新颖、充满奢华气息,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异域风情。
在语言符号的呈现上,《长安十二时辰》打破了诗词的传统价值意蕴而将其融入剧情中,并以此来渲染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咏柳》《侠客行》《清平乐·禁庭春昼》等诗词或以台词的方式出现,或以音乐的方式出现,马伯庸和导演曹盾根据诗文这一语言符号独特的内涵,将其安插在不同的场景中,诗文的出现往往伴随着非凡的作用,或改变其功用,作为机关暗语推动故事发展;或辅助彰显人物情感变化,丰富和完善叙事内容。
三、网络小说影视化改编热潮下的冷思考
好的影视化剧本的慢产出与网络便利环境带来的高需求不同步。在影视产业这条大河里,互联网这台“加速器”仅能为中游影视生产和下游观众消费赋能。“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5]好的剧本是优秀影视作品诞生的源头,需要岁月的沉淀及时间的打磨,观众绝不可能会为单一、套路化、粗制滥造的影视剧买单。面对此等“上游优秀剧本的慢产出与中下游网络便利环境带来的高需求”之间的矛盾,网络文学大IP 的改编就如同暗室逢灯、绝渡逢舟,以题材多样的故事、曲折丰富的情节、新奇有趣的人物设定特征,轻松化解了困局。而近几年,我国影视行业“精品剧”之风日起,在拍摄和制作上均讲究精益求精。《长安十二时辰》作为其中的典型,承担着经济和文艺的双重责任,其电影高质感的视听呈现、细致考究的风俗物语、家国身份认同中的价值构建等均代表了网剧生产水准的新高度,远离同类型产品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胡编乱造、生搬硬套的乱象。
剧本漏洞百出,剧情逻辑台词脱离实际,是这个消费时代环境下不断产出“速食产品”的后果,也是网络小说影视化前进之路上的遗憾与待解问题。网络小说影视化改编为了符合社会尺度与道德标尺,势必会在故事情节上做出改动。作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影视化改编需交给专业的人去判断,因而改编后的剧情逻辑、人设构建等难免与原著有所出入。《长安十二时辰》影视化后,编剧有意隐去史实人物痕迹、改动其姓名,将小说中的李泌改成李必、岑参改为程参等,但是这一改动却也造成了许多逻辑漏洞。在剧情结尾,虽然马伯庸在原小说中只做到了不可思议,却不在情理之中,但是在影视化改动之后,将最后的幕后主谋设定为徐宾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勉强能自圆其说。《长安十二时辰》在前半部分救黎民于水火的悲壮写得酣畅淋漓,后半部分却因剧情失控在始终紧绷的节奏带动下越走越偏。
四、结语
小说文本的质量是船,影视化呈现是势。船乘势,势推船,才能破浪乘风。无船之势,便只是阵空的风罢了;无势之船,也只能泊于一方港湾,无从实现使命与价值。面对网文界之时弊,马伯庸与导演曹盾偏要做那“逆行者”,以国际大都市长安作为完美切入点,并坚持以深厚的文化功底、精良的专业制作,顺应时代潮流,创新传统模式,在架空设定下不断深挖历史真实,成功创作出《长安十二时辰》这样一部既叫座又叫好的艺术作品,开拓了一条新的古装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