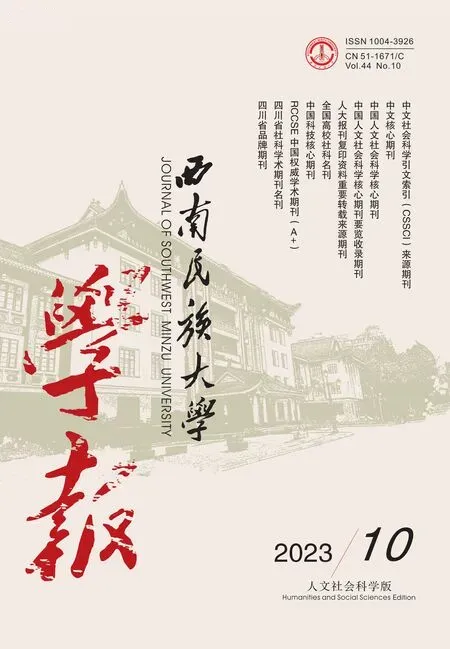感官体验对生态旅游景区游客焦虑感的作用机制研究
窦 璐
[提要]焦虑感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旅游体验在维持个体心理健康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积极效应。本研究以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多维感官体验为视角,基于地方依恋和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构建了焦虑感的抑制机制模型,采集了5A级生态旅游景区的游客数据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和触觉体验)对焦虑感的两个维度(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但通过地方依恋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焦虑感。从对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抑制总效应来看,视觉体验最强,听觉次之,触觉和嗅觉最弱。虽然安全感在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影响中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安全感显著地负向影响焦虑感。本研究结论从游客最原始和朴素的身体感觉视角拓展了旅游对个体心理健康与福祉的积极影响,为新时期生态景区精准实施感官营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体验在维持个体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1]。人类对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感,沉浸在自然环境之中,可以舒缓身体、降低压力、减轻精神疲倦、愉悦心情和获得幸福感[2][3]。三年多的新冠疫情唤醒了人们亲近自然的强烈欲望,使生态旅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但也面临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4]。因此,如何拥有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是当前生态旅游面临的最大挑战。感官刺激是体验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以体验为本质的旅游活动而言更是至关重要[5]。与其他消费相比,旅游活动带有鲜明的感官属性特征[6],感官体验在满足旅游活动的健康福祉、识别旅游区域特征和打造其独特身份等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7],可为纾解生态旅游的实践难题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但遗憾的是,虽然感官体验在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8],但以多维度感官体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对负面情绪的作用机制研究仍非常有限。有鉴于此,本文以5A级生态旅游景区为例,以安全感和地方依恋为中介,构建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作用机制模型,并辅以实证检验,最终所得的结论能够为当前景区纾困现实难题、提升旅游活动的心理健康福祉提供新的思路。
一、文献回顾
具体化认知理论(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认为,感官是外部信号的触发器和感受器,为形成认知过程提供物质通道[9]。当外部环境刺激作用于人体不同的感官细胞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10],对这些感觉信息的选择、加工和解释就形成了感官体验[11],进而为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提供重要基础。大量研究证实,感官体验、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12]。体验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强调游客的主观感受[13]。旅游体验首先表现为视、听、嗅、味、触等感官将外部刺激转化为内部认知的复杂过程[14],感官体验直接反映旅游活动的质量,并形成游客对旅游地的评价[15]。强化感官体验可诱发游客的情感反应[16],通过建立“人-地”联系,赋予旅游地形象和意义[1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游客的感官体验并呈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从感官体验的研究维度来看,视觉体验是最早被提及且成果最丰富的研究主题[18]。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视觉主义中心”的统治地位被不断挑战。原因在于,视觉仅仅是获得旅游体验的众多方式之一,而旅游却是解放日常生活中禁锢的其他感官的主要行为[19]。因此,传统的视觉感官维度研究逐渐转向听觉体验[20][21]及嗅觉体验[22]等以往被忽略的关键感官维度。但这种分散化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旅游是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综合性体验活动,本身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多感官属性[23];另一方面,五种感官体验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互动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体验都无法从整体中被剥离[24],也没有任何一种感官体验能够主导游客的认知结果[25](P.26)。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感官体验的联觉效应(Synesthesia Effect),如视-听觉[26]、视-嗅觉[27]、视-听-触-嗅觉[28]。也有少数研究涉猎五种感官的综合效应,以野生动物园[16]、乡村[29]、红酒产地[30]、森林小镇[24]等地的游客为例,但大多带有非常明显的主题特征,最终呈现的体验结果集中于对特定旅游偏好的描述,对其他旅游地不具有普适性。从感官体验的作用结果来看,遵循环境-心理-行为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探讨了感官体验对游客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呈现了如下成果。一方面,从增加游客福祉来看,感官体验能够直接引发恢复性环境体验[20]、留下长期回忆[31]、增加安全感[14]、放松心情和获得快乐感[22],进而提升游客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从促进目的地发展来看,感官体验通过提升游客对目的地的喜爱[32]、满意度[33]、形象感知[34]、依恋感[17]等,强化游客的忠诚度和环境责任行为。
焦虑感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最常见症状[35],任何人都无法避免[36]。Gudykunst和Hammer(1988)率先提出了焦虑感,认为它是对负面结果的一种恐惧感[37]。后续学者对此定义进行了拓展和完善。从起因上看,焦虑感是由于不确定的、有风险的结果带来的一种心理[38]。从造成的个体反应来看,焦虑感表现为紧张、担忧、有压力、脆弱、不安、害怕、惊慌等不舒适的感觉[39],形成挫败感和尴尬感[40]。因此,综合来看,焦虑感被认为是对压力、潜在和实际风险的一种负向情绪反应[41]。前往任何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都存在不确定和风险,出现负面结果,使游客无法避免地出现焦虑感。早在19世纪中期出现有组织的旅游活动时,就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反应,被称为“紧张状态”[42]。当时的医学专家将这种症状称为不安定或过度刺激引起的反应[43],即在旅游前和随后的过程中,对未知旅游地的期待或渴望,以及暂时离开常住安全地的恐惧,使大多数健康的个体都会在特定的压力环境下产生一种不愉快情绪。通常情况下,这种情绪为时短暂且强度多变,被称为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44](P.1-20)。它在特定的旅游类型和情景刺激下被唤醒[45],如游客在黑色旅游地会紧张财产和人身安全[46]、在亚洲的美食游客担心食用肉的来源(文化差异导致他们难以接受来自狗或爬行动物的肉制品)[47]、来自美国的康养游客由于不适应异国价值观和思维习惯而忧虑[48]、新冠疫情下害怕旅行中感染病毒等[49]。与之相反的是特质焦虑(trait anxiety),它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具有个体差异、可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的焦虑倾向或习惯[50](P.3-20),如广场恐惧症、大巴或飞机上的幽闭恐惧症、人群拥挤或大规模集聚引起的群众恐惧症及飞行恐惧症等[51]。特质焦虑可能在个体经历风险环境之前就被激发并持续存在,如有飞行恐惧症的个体仅仅是想到飞行就会出现生理症状(如失眠、出汗、心跳加快、头晕)和认知症状(如恐惧、担心、怀疑、烦恼)[52]。虽然游客的焦虑感问题早已被发现[38],但从结构维度来看,游客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是否同时存在仍存在激烈的争论。“状态中心论”认为[53],游客的焦虑感无法摆脱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情景,应该归属于状态焦虑形式。与之相左,“特质中心论”指出[38],状态焦虑感稍纵即逝,对游客的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真正对行为起作用的是持续时间长、存在个体差异、游客固有的特质焦虑感。从游客焦虑感的成因来看,风险是唤醒游客焦虑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健康风险(新冠疫情)[37][38][54][55]和社会风险(被团队排斥)[56]。同时,负面情感(孤独、伤痛、过往经历)[57]、信任感[58]等也存在显著的激发效应。此外,包括身体残疾[59]、个性[60]、年龄[61]、风险偏好[62]等个体因素也会导致焦虑水平的差异。
二、文献评价
已有文献对游客感官体验和焦虑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丰富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如下可拓展空间。一方面,虽然感官体验已成为近年来的旅游研究新趋势,但大多基于单一感官视角,基于五种感官体验的联觉效应研究还相对较少,且测量题项大多带有主题特征,不具有普适性。虽有研究指出感官体验能够触发积极情感,但是否对消极情感(如焦虑感)存在抑制作用却鲜少被验证。另一方面,从焦虑感的成果来看,虽然焦虑感在旅游研究中不是一个完全新颖的主题,但研究进展缓慢,成果较少,国内更是鲜有学者涉猎。有限的研究中,“状态焦虑”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而特质焦虑的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被挖掘。焦虑感的成因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负面情感、信任感和个体因素等方面,缺少感官体验视角下的形成路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5A级生态旅游景区背景,以地方依恋和安全感为中介变量,从感官体验视角全面解锁游客两种焦虑感的形成机制。所得的实证结论,不仅能够从人-地互动的理论视角解释生态旅游的心理福祉,还可为目的地以游客为主、精准匹配游客的景观需求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设
1.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影响
在个体认识外部环境时,感觉和情绪就息息相关[63](P.1-10)。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情绪是连接外部环境感知和内部心理,从而评估环境是否对个体有利的一种反应过程[14]。因此,感觉是个体情感的重要触发器[64]。当个体感觉到外部环境对自身存在意义时,就会增加积极情绪和抑制消极情绪[65];反之,如果个体认为外部环境具有破坏性或损坏自身利益时,就会增加消极情绪和减少积极情绪[66]。感官体验对游客积极情感的促进作用已得到了相关研究的验证。如游客从高山凝视远处的景观或身处安宁的乡村环境可以心情愉悦[67]、聆听教堂的钟声可以获得惊喜[68]以及在芬兰品尝当地美食可以心满意足[69],这些成果从反面论证了感官体验对消极情绪的抑制作用。此外,虽然没有直接的实证结果表明感官体验对游客消极情绪的作用,但可从注意力恢复性理论和一些研究中获得支持。根据注意力恢复理论,恢复性环境可以恢复个体惯常环境中被消耗的认知资源,特别是减少定向注意力,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包括缓解疲劳、放松心情和释放压力等[70]。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很容易唤醒人们的感官体验,充分舒缓游客的身心,特别是降低压力感和紧张感[71](P.26-27)。此外,有研究指出,通过观赏森林景观,可以显著降低个体的学习和工作焦虑感[72],缓解心理压力[73]自然环境中的光照、声音和温度可有效激发个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快速促进个体从压力环境中恢复心理健康[74][75][7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感官体验显著地负向影响游客的焦虑感。
2.地方依恋和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地方依恋是以空间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被定义为个体与特定地点的一种积极情感联系[77]。在旅游研究中,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和广泛应用[78]。其中,前者强调旅游地对满足游客特定需求和目标的重要性,而后者强调游客对旅游地的精神性依赖(如游客对目的地的信念、记忆、想法、偏好等)[79]。地方依恋在游客对旅游地的感知、联想和记忆等认知基础上形成[80]。游客的认知越深刻,地方依恋就越强烈[81]。在感官体验过程中,游客对旅游地环境的认知会融入个人的解释、思考和联想[82],对旅游空间的象征意义和地方感有更深刻的理解[83],更容易引发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释放[84]。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直接、持续、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地”互动形式,感官体验可使游客与旅游地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纽带,由此进一步增强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85]。因此,感官体验是塑造地方依恋的重要先决条件[17]。根据Lazarus的压力-应对模型(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个体会通过一系列的认知和行为努力,掌握、控制和容忍外部风险性事件对个体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86](P.1-10)。当个体拥有的资源无力应对外部风险引起的负面事件时,就会形成强烈的焦虑感[87](P.10-15)。为维持内部的心理健康,个体会通过一系列的外部策略,即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和情感利益来减少焦虑感[88,89]。地方依恋完美地契合了外部策略的需求,通过建立积极的人-地情感联结,获得功能性和情感性支持,进而有效削弱焦虑情绪。此外,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地方依恋对焦虑感的负向影响,但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当游客心理上依恋旅游地时,个人意义上的需求将被极大地满足,因而表现出主观幸福感[90][91]、满足感[92]、敬畏感[93]、与当地居民的情感凝聚[94]等积极情绪,由此从反面视角为地方依恋抑制负面情绪(焦虑感)提供了有力佐证。
安全感是人类基本心理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个体对自身生存和安全受到威胁的一种主观认知[95]。从旅游研究视角来看,安全感是游客依据旅游地的具体情形,对免于遭受外部伤害、物理和精神损失的一种主观判断所形成的心理舒适感[96]。安全感是与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心理认知因素,来源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97](P.1-10)。感官体验为此提供了良性基础,通过感官与旅游地环境的持续、稳定和有序互动,游客与旅游地之间更倾向于形成信任感[98],进而认为自己处于安全状态[99]。同时,安全感是预测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80]。研究表明,安全是人们开展旅游活动并建立人-地关系的基础性先决条件,如果游客感到不安全就不会形成地方依恋,反之,感到安全的游客才会逐步与目的地建立情感联系和认同感[100]。此外,安全感可显著预测个体的焦虑水平[101]。当个体安全感较低时,表明个体面临较大的风险且无力应对,此时个体必然表现出对负面结果的担忧、紧张和不安等情绪,由此引起焦虑水平升高,安全感对焦虑感的负向影响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支持[10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地方依恋在感官体验与焦虑感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3:安全感在感官体验与焦虑感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安全感显著地正向影响地方依恋。
(二)模型构建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量表选取

(二)数据收集
基于本研究的目标,必须选择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景观资源丰富、具有典型性且对游客感官体验有较强吸引力的案例地。具体标准为:首先,具有较高的国内知名度,为5A级景区,到访游客数量充足;其次,景区具有各种丰富的感官资源,并可被游客感知;最后,属于自然生态型旅游景区,通过旅游感官体验,可满足游客放松身心、恢复心理健康的需要。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和景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了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两个5A级景区作为被调查地。鉴于本研究以游客的焦虑感为核心,故在调查前询问是否为非当地居民,如非当地居民则邀请填写问卷,以此剔除非游客样本。数据收集分为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基于两个景区的实地调查,采用现场问卷发放的方式,随机邀请游客现场填写问卷,调查时间为2022年3月1日-2022年5月2日;二是通过与旅行社合作,向有两个景区旅游经历的团队游客定向发放在线问卷,调查时间为2022年4月1日-6月5日。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66份,回收率为93.2%。剔除不符合调研要求的问卷(包括填写不完整、存在漏选或空白题项、所有题项都填写同一选项等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11份,有效率为88.2%。表1显示了被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1中数据显示:被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差别不大,男性比重略高;主要为80后和70后的中年群体,其次是90后的青年群体;学历以本科居多,其次是大专、高中及中专以下;个人年均收入在6-8万元的游客最多,其次是8-10万;大部分游客第一次到访,以散客为主要旅游形式。此外,本次被调查游客全部为非本地居民,调查员在填写问卷前问询了散客的客源地(受篇幅原因没有在表格中列出),综合旅行社提供的旅游团信息,可知被调查游客的来源以江苏、安徽、上海、江西和浙江等地为主(占39.9%),其次是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等地(29.6%),以及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20.6%),少量来自黑龙江、辽宁和新疆等地(9.9%)。
五、数据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Alpha值大于0.7作为标准,效度检验采用方差最大旋转后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因子载荷值大于0.5作为标准。应用SPSS 2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触觉体验、安全感、地方依恋、状态焦虑及特质焦虑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966、0.954、0.882、0.953、0.935、0.943、0.758、0.96,全部大于0.7,说明问卷采用的量表具有较高信度;所有题项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说明问卷采用的量表有非常好的效度,可用于后续检验。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应用Amos22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如表2所示。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全部大于临界值0.7,说明测量模型有非常好的信度。模型的效度检验分为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检验: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全部大于0.5,且显著性P值均小于0.001,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全部大于临界值0.5,说明测量模型有非常好的聚合效度;经比较,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提取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上述结果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内部一致性,可用于进一步的假设检验。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

表3 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三)同源误差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对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同源误差进行检验。一是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确定单因子模型商务拟合结果是否最佳。检验结果表明:八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χ2/df =2.847,RMSEA=0.076,CFI=0.933,NFI=0.901,IFI=0.933,TLI=0.924,PGFI=0.657,PNFI=0.795,PCFI=0.823)最好,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χ2/df =10.864,RMSEA=0.176,CFI=0.615,NFI=0.593,IFI=0.616,TLI=0.594,PGFI=0.266,PNFI=0.562,PCFI=0.583)最差;此外,通过比较两模型在χ2与df的差异值也可以看出,八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故说明同源误差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严重影响。二是采用控制非可测潜在因子影响检验法,具体程序如下:首先,将同源误差作为潜变量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允许其他标识变量在该潜变量上负载;其次,比较含有同源误差潜变量的模型与不含有同源误差潜变量的模型的拟合程度,以此检验同源误差的影响效果;最后,经检验,含有同源误差潜变量的模型(χ2/df =2.837,RMSEA=0.072,CFI=0.934,NFI=0.903,IFI=0.935,TLI=0.925,PGFI=0.658,PNFI=0.798,PCFI=0.833)与不含有同源误差潜变量的模型(即前文中的八因子模型)相比,其拟合指标的改变量在0.001~0.01,并无明显变化,并且两模型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显著的;因而,加入同源误差潜变量后的模型的拟合程度并无明显改善。综合以上两种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同源误差处于可控范围内,并且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假设检验结果
1.模型拟合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SEM)的输出结果,拟合指标中:绝对适配指数RMSEA=0.078,在适配标准(<0.08)范围内,GFI=0.878,接近适配标准(>0.9);增值适配指数NFI=0.9,RFI=0.88,IFI=0.93,TLI=0.921,CFI=0.929,全部达到或接近适配标准(>0.9);简约适配指数PGFI=0.657,PNFI=0.798,PCFI=0.827,全部在适配标准(>0.5)范围内,χ2/df =2.926,在适配标准(1~3)范围内。综上所述,总体上,各个拟合指数达到或接近适配标准,说明结构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
2.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检验表明(如表4所示)。首先,从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直接影响来看,四个维度的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H1未得到支持。其次,从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来看,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对安全感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安全感对焦虑感的两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安全感对状态焦虑的影响系数为-0.867,对特质焦虑的影响系数为-0.536,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安全感在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影响中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H2未得到支持。再次,安全感虽然对地方依恋存在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H3未得到支持。最后,从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来看,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对地方依恋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982、0.83、0.493和0.521,且全部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地方依恋对状态焦虑和特征焦虑的两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57和-0.54,分别通过了1%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4 结构方程检验结果
由于感官体验对安全感不存在显著影响,故不考虑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删除安全感后建立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一方面,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检验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是否显著影响焦虑感,以及地方依恋是否显著影响焦虑感。第三步,控制地方依恋,检验感官体验的四个维度对焦虑感的影响是否显著。结果表明:第一步和第二步中,四个感官维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也显著正向影响焦虑感;第三步中,四个感官维度对焦虑感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同时采用 Boo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设定5000,置信水平设定95% 。结果表明,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及触觉体验对状态焦虑感的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756,-0.682)、(-0.154,-0.187)、(-0.821,-0.091)、(-0.776,-0.326),不包括0,表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及触觉体验对状态焦虑的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333,0.225)、(-0.863,0.248)、(-0.858,0.5)、(-0.341,0.161),包括0,进一步表明地方依恋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及触觉体验对特质焦虑感的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253,-0.093)、(-0.514,-0.257)、(-0.352,-0.176)、(-0.142,-0.044),不包括0,表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及触觉体验对特质焦虑的直接效应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574,0.358)、(-0.964,0.446)、(-0.31,0.423)、(-0.906,0.28),包括0,进一步表明地方依恋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H3得到支持。根据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系数,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及触觉体验对状态焦虑的总效应分别为-0.839、-0.719、-0.481和-0.58,对特质焦虑的总效应分别为-0.368、-0.344、-0.175和-0.188。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安全感和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多维度的感官体验对游客焦虑感的作用机制模型,并以两个5A级景区的游客为样本进行了数据采集和实证检验,进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感官体验对游客焦虑感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地方依恋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且各维度的感官体验对焦虑感的总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感官体验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涌现的成果主要聚焦于感官体验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作用[71-73],鲜有学者验证感官体验对消极情绪的抑制作用。焦虑感已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心理问题,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多的新冠疫情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旅游作为逃离惯常生活、放松身心的一种休闲方式,是否能够真正地达到释放压力、缓解紧张进而降低焦虑,最终改善心理健康的目标?本文从感官体验的视角给出了实证解答,具体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当前感官体验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仍以“视听主义中心”或其他单一感官维度为主导[21][22][27],忽视了多维感官体验的综合作用。本文综合则考察了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等四个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感官维度,以及它们对两个焦虑感维度的差异化作用效应,从而突破了单一感官研究的局限性,进一步解析了感官体验的内部复杂结构和不同的影响效果,为全方位识别和理解多感官体验激发情绪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对状态焦虑感的影响总效应来看,视觉效应最强(-0.839),听觉效应次之(-0.719),触觉(-0.58)和嗅觉(-0.481)相对较弱。从对特质焦虑的影响总效应来看,仍是视觉效应(-0.368)最强,听觉稍弱(-0.344),触觉(-0.188)和嗅觉(-0.175)最弱。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视听觉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最重要感官形式,分别占感官系统的78%和13%,而嗅觉和触觉仅占3%。同时,受客观条件和改造难度的限制,景区在实践中以提供视觉景观为主,听觉次之,而其他景观却非常少见。另一方面,状态焦虑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且持续时间较短,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而特质焦虑是个体的一种心理习惯且持续时间较长,环境敏感性较弱,故感官体验对状态焦虑的影响较大。其二,通过地方依恋的桥梁纽带作用,本文构建了从游客本“身”到本“心”的作用机制。与一般体验形式不同,感官体验过程融合了游客的思考、记忆及联想,赋予了景观功能作用和情感意义,能够形成人-地之间的“自然连接”,达到游客与旅游地的心理契合和自我认同。在这种紧密的情感联系下,游客的内心更加平和舒适,免于体会紧张、压力等不适感觉。该结论不仅回应了已有研究指出的感官体验对地方依恋的积极影响[24],还进一步拓展了“感官-心理”联系[16],提出了由生理感官到人地情感连接,再到心理健康的游客与景观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最原始、朴素的感觉为起点提出了修复游客心理损耗的重要理论路径。
第二,虽然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没有通过数据检验,但发现了安全感对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显著负向作用,且对状态焦虑的抑制作用(-0.867)明显高于对特质焦虑的抑制作用(-0.536)。一方面,安全感是游客对旅游地设施、服务、秩序及人员互动关系的一种综合性判断,受多种因素影响且需要足够的旅游时间、次数和经验进行评价,仅依靠以景观为基础的短暂性感官体验可能还不足以引起安全感的显著变化,其中还可能存在诸如信任感、熟悉感及心理距离等其他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有待挖掘。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了安全感对焦虑感的显著负向作用。风险感知是导致个体焦虑感的关键因素[44],在安全的环境下,游客对旅游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感知更低,能够更加坦然自如地释放精神压力,缓解焦虑情绪。已有文献验证了安全感对社交焦虑的负向影响[21],本研究则进一步解答了安全感是否对游客自身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具有抑制作用,从而扩大了安全感对游客心理健康的积极意义。
(二)管理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生态景区的实践管理提出如下三方面建议:
其一,充分重视和平衡多感官体验的积极作用。旅游体验是在多感官刺激下形成的,受以往单一感官体验研究,特别是“视觉主义中心”主导思想的影响和现实景观条件的制约,当前大多数景区仅关注和设计视觉景观,忽视了对其他感官景观的改造,对游客的感官刺激不足,难以为游客带来积极的心理福祉。如在调研过程中,部分游客反映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触及更多的植物,与一些可爱的小动物能够互动。还有游客反馈景区的餐厅和小吃摊过多,“商业味道”太浓,难以体验到大自然本身的味道,如花卉的芳香、草木的清香、雨过泥土的沁香等。因此,景区应该以多感官营销为主旨,充分调动被日常生活禁锢的非视觉身体部位,如游客的耳、鼻、手、皮肤等,避免由单一感官景观重叠而引起的审美疲劳,降低景观的商业化痕迹,充分提供游客接近自然的设施,创造更多人与自然的“邂逅”。同时,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考虑不同感官的协调性和联动性,实现跨感官组合,如景区推出的“视听盛宴”“如果春天有风声”“听风闲饮”“森呼吸”等。
其二,积极调动地方依恋的纽带作用。根据研究结论,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通过游客与旅游地之间建立情感联系,感官体验才能够有效抑制焦虑情绪,提升游客的心理健康。因此,在各种以感官主题为背景的旅游景观设计中,要积极构建人与旅游地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方面,提供超出游客预期的高质量、智能化和个性化的设施和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满足游客对环境的功能性需求,如西溪湿地打造的“一站式驿站”“气味体验馆”“虚拟导游”“智慧APP”,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获取游客信息、游览轨迹及流量等。另一方面,在自然景观中融入各种人文元素,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加强游客与亲友或其他间的知识交流和人际互动,打造“难以忘怀的旅游体验”,满足游客的情感需求。如西溪湿地推出的“亲子草地音乐节”“植树研学”“花海宋韵”,紫金山推出的“森林音乐节”等。
其三,建立以安全为主导的服务体系。本研究发现,虽然感官体验不通过安全感降低焦虑情绪,但安全感对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景区必须充分重视旅游安全,将设施和服务安全标准真正地融合进旅游六要素中,使游客获得安全的体验保障。首先,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要注重对游客健康安全的保障措施,加强秩序管理以避免冲突事件和情景,其次,通过社交、商业网站等持久地宣传旅游地安全形象,淡化负面事件和口碑的影响,消除游客对旅游地的负面安全认知。最后旅游地的热情、好客服务氛围,使游客真正形成“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理感受。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仅对自然生态型旅游景区进行了数据收集,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到娱乐、体育休闲等多种旅游类型,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本研究仅检验了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其他调节效应,特别是在感官体验对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是否存在其他变量(如信任感等)的中介作用,仍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