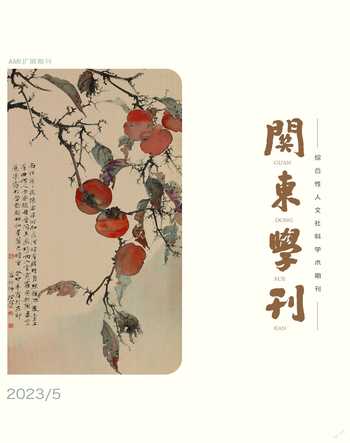《先秦名学史》及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再探讨
[摘 要]长期以来,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一直被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初稿,或一部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著作,学界围绕胡适博士学位问题更是聚讼不休。本文认为:《先秦名学史》并非一本纯粹的逻辑史研究专著,而是一本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发展史的著作,它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两本性质不同的书;胡适之所以要写《先秦名学史》,既有现实因素对他的触动,更有学术自身的因素,哲学受它的方法制约,哲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方法论的发展,唯有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发现、发掘和发展出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才能避免“引起旧文化的消亡”,才能打破“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中古遗产,从而引导中国哲学和科学走向现代化;《先秦名学史》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很好地解决了它所提出的问题。胡适用西方“原因论”和“效果论”哲学方法来阐释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方法论,通过对先秦各家各派哲学方法的还原,充分揭示了哲学方法的发展是科学和哲学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它是一篇具有极高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博士论文。本文回顾了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来龙去脉,通过各种新发现的证据,证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案是一场冤假错案,并主张取“无罪推定”的原则,来为这一“学案”画上句号。
[关键词]胡适;《先秦名学史》;哲学方法论;博士论文;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席云舒(1973-),原名席加兵,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文理学院教授(新疆 834000),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3)。
一、《先秦名学史》的版本、翻译和研究状况
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完成于1917年5月,英文版于1922年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封面上有中英文书名。初版除公开发行的版本外,还印制了100册封面印有“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作为满足哲学博士学位的规定项目之一而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且书后附有“Vita”(个人简历)的版本,这是为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而专门印制的。除封面和“Vita”外,内容与公开发行的版本并无不同,版权页写的都是“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初版”。可能是由于初版印了两个版本的缘故,1928年亚东图书馆重印该书时,版权页写的则是“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三版”,但未见1922—1928年之间印行过第二版。
1925年,《先秦名学史》就有了井出季和太(1880—1959)的日译本,书名为《胡适の支那哲学论》,该译本先由东京岩松堂书店发行,1927年改由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1998年又被大空社列入“亚洲学丛书”重印,日译本有京都大学教授高濑武次郎(1869—1950)写的序。1962年胡适去世后,纽约帕拉贡图书再版公司(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于1963年和1968年重印了两版英文版,重印版前面有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历史学教授海曼·库布林(Hyman Kublin,1919—1982)的序。直到1981年,该书才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一个有11位译者参与的《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成中文,由李匡武校订,1983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温公颐的导读《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该译本1999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并被收入北大版《胡适文集》、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等大型文集,此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译本。根据《伯尔尼公约》,2012年胡适著作进入公版,海外重印《先秦名学史》英文版也多了起来,常见的有Hard Press 2012年版、Scholar's Choice 2015年版、Wentworth Press 2016年版、Facsimile Publisher 2016年版、Forgotten Books 2018年版、Alpha Edition 2020年版、Legare Street Press 2022年版等。
《先秦名学史》出版后,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先后写了书评文章,罗素的文章刊登在1923年9月22日出版的The Nation and the Athenum上,伯希和的文章刊登在同年10月出版的《通报》第4期上。众所周知,在《先秦名学史》出版之前,1919年2月,胡适就出版了中文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29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重印时,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为方便起见,本文正文统一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然是在《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但由于两本书论述的重点不同,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对《先秦名学史》的内容也有所取舍。罗素不懂中文,他显然没读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伯希和虽然懂中文,但他在文章中说,他写《先秦名学史》书评时,手里也没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文版,然而他们都将《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进行了比较。
罗素说:
这本书标志着欧洲读者在接触中国思想方面的一个全新开始。欧洲人几乎不可能既是一流的汉学家,又是合格的哲学家,这并不奇怪。在欧洲人对中国哲学的翻译中,注释和评论往往表明,译者不可能理解书中的思想,因此很可能誤译了这些思想。对于一个想了解中国哲学而又不懂中文的人来说,这种状况会让人感到绝望。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胡适博士,他就像欧洲人一样精通西方哲学,他的英文写作能力不亚于大多数美国教授,而且(我们怀疑)他在翻译中国古代文献时拥有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能够企及的自信。正如这种独特的禀赋会令人期待那样,尽管这本书只是他后来出版的一部大型中文著作的初稿,但结果很有意思,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它写得更好。(Bertrand Russell,“Early Chinese Philosophy”,in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um,Sep.22,1923,Vol.ⅩⅩⅩⅢ.,No.25,pp.778-779.)
伯希和则说:
胡适这本书写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前,但因为他太忙,所以出版时并没有纳入他的新观点,而是直接用了五年前的手稿,所以这本书并不完全反映他当下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也不值得辩驳,因为他在后来的书中已经对部分说法加以摈弃。但此书在方法论上,以及在总体看法上,仍然反映了他的思想。(Paul Pelliot,Livres Nouveaux(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by Hu Shih),in T’oung Pao(《通报》),Oct.,1923,Vol.ⅩⅫ,No.4,pp.302-326.)
伯希和也谈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误译问题,他认为胡适的批评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同时指出,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虽然存在一些错误,可是“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因为“汉学家在世界范围内所唤起的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兴趣,对于保持这一古代文化在中国年轻一代眼中的声誉是有贡献的”,况且“并不是只有欧洲人对中国典籍有误译,中国人对欧洲典籍同样也有误译”。
罗素虽然认为“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它写得更好”,但他同时指出,《先秦名学史》只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初稿;伯希和则认为“这本书并不完全反映他当下的观点……因为他在后来的书中已经对部分说法加以摈弃”。他们的言下之意可理解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基本可以取代《先秦名学史》,因为前者代表了胡适最新的观点,而后者只是一份旧稿,其中有些观点已经过时并得到了更新。可以说,此类观点也是国内学者的共识,如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中就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许多方面继承并深化了《先秦名学史》的思想。”(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8页。另见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9页。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9页。)因此《先秦名学史》出版后,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即使中译本已刊行40年,学界也鲜有对它的专门研究,仅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和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等少数几种著作中,将其作为第一部中国逻辑史专著进行评述。
也许正因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典籍误译较多,而胡适“在翻译中国古代文献时拥有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能够企及的自信”,所以西方学者对《先秦名学史》多有引用。我的朋友陈通造发现,早在《先秦名学史》出版之前,就被印度学者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1887—1949)的文章引用过。(Benoy Kumar Sarka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in India”,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Ⅻ,no.4(Nov.1918),p.582.)法国东方学家保罗·马松-乌塞尔(Paul Masson-Oursel,1882—1956)192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La Philosophie Comparée(《比较哲学》)中也将其列为参考文献,出处写的是“Suh Hu.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inédit).1920.”(Paul Masson-Oursel,La Philosophie Comparée,Paris,Imprimerie D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3,p.138.)法文“inédit”意思是“未刊本”。我们不能确定乌塞尔参考的1920年未刊本是否为胡适1917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打字本,但显然,在《比较哲学》出版前,他并没有读到亚东版《先秦名学史》。旅美学者陈受颐1961年出版的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中国文学史略》)一书也大量引用了《先秦名学史》的古文献英译文。(Ch’en Shou-Yi,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Ronald Press,1961.)
在海曼·库布林为帕拉贡重印版写的序里,他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胡适的生平,他也指出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研究跟古代注疏的区别:“凭借他广泛涉猎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知识,以及现代方法和学术观念,他能够以一种迄今为止最严谨客观的中国学者都无法企及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近乎神圣的著作”;“胡博士与传统的中国哲学著作注疏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他的研究态度……他对科学方法的尊重,无论是在物理学、生物学、考据学还是文献学方面,都是无止境的。”胡适当然不懂物理学和生物学,但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和吴健雄都是胡适的学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曾深刻地影响了胡适的一生。库布林这里强调的主要是胡适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态度,及其对各学科的影响。他说:“只要阅读《先秦名学史》就会发现,作者的目的不是诋毁(前人的研究),而是為了阐明和正确解释本国过去的历史文献。”(Hyman Kublin,“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Hu Shih(1891-1962)”,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New York,1963.p.3.)
帕拉贡重印版《先秦名学史》出版后,又有一些书评文章对它做了介绍和评价,其中以墨西哥汉学家弗洛拉·博顿·贝亚(Flora Botton Beja,1933—)的短评较有代表性。她说:
这是一本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思想态度的书的再版。1917年,当胡适的博士论文问世时,许多怀疑论者终于接受了中国曾经有过举足轻重的哲学思想的看法。作者的优势在于对中国经典有透彻的了解,同时对西方哲学也有很好的认识。通过运用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思想,他能够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阐释,然后将其组织成一个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以一种新的解释来介绍老子、孔子、庄子和其他经典。此外,他还整合了以前无法理解的诸子百家的作品,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尽管该书首次面世已过去多年,但作为对中国思想的解释和体系化的著作,它的有效性依然存在。(F.B.B.,Review(Hu Shih,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Nueva York,1968.),in Estudios Orientales,1969,Vol.4,No.2,p.244.)
在1983年学林版中译本的导读《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温公颐对本书做了四个方面的评价。第一,《先秦名学史》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是有一定地位的。第二,本书作为中国逻辑史的学术探究,具有许多优点,具体包括:1.胡适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治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史,使人在比较参证的过程中,掌握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胡適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哲学史……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2.胡适十分重视逻辑和逻辑史的研究价值。他用东西方哲学发展的典型事例,说明哲学体系的建立,是受它所用方法制约的,而哲学史的发展,又为逻辑史发展所制约;3.他很注意逻辑史料的考证;4.胡适认为写逻辑史应以各派逻辑学家的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为主。至于各人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凡有关系到他的逻辑理论时才附带提及。这样,就可以把逻辑史与哲学史明确地区别开来。第三,胡适对先秦逻辑史的分析有不少创见,包括:1.他认为我国古代系统逻辑思想的诞生有一个孕育时期,这和西方古希腊的情况相似;2.他虽论述了孔子、荀子等儒家方面的逻辑,但把重点放在儒家以外的墨翟、惠施、公孙龙和墨辩,这与传统的意见分道扬镳。胡适之所以重视儒家以外的诸子逻辑,就是因为他们比较重视科学验证的方法,这和西方科学精神有相互契合之处;3.胡适指出,墨翟虽然注重经验,但他是以特殊经验为出发点,归纳出普遍法则的。这和孔子从普遍原则出发,是根本不同的。孔、墨双方逻辑方法的对立,加深了我们对孔学与墨学分歧的认识。第四,胡适对先秦逻辑学家的原著的解释也有诸多创见。
当然,在评价《先秦名学史》的种种优点之后,温公颐也批评了“胡适不但受他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因而违反他自己所提的正确原则,而且还用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先秦时代的社会巨变,因此,他也就不能分析到点子上,并发生不少错误”。至于发生了哪些错误,温公颐则没有举例,而是接着说:“胡适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是一向为我们所反对的。但对他作为一个哲学家、逻辑学家的学术成就,我们应予以一定的评价。”(温公颐:《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5页。)总体而言,温公颐对《先秦名学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他对胡适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评,或许多少也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当代逻辑史研究者都把《先秦名学史》看作是第一部中国逻辑史断代研究著作。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中,“近代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一章的执笔者李先焜也对《先秦名学史》做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作为第一部中国逻辑史的专著,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对后代中国逻辑史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胡适反对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逻辑的观点,而用大量材料证明了中国古代(比亚里士多德更早)就产生了系统的逻辑理论。”但他同时认为,“胡适在论述中也存在一些根本缺点,就是在谈逻辑理论时往往掺杂了很多非逻辑的(主要是哲学的)理论”。(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97页。另见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版,第345页。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45页。)宋文坚在其专著《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中指出,胡适“为发掘先秦的逻辑思想作了一些工作,尤其在墨辩方面,胡适作出了相当成绩。胡适在考察先秦名辩时,把逻辑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思想、哲学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以阐明先秦逻辑思想产生之必然。”(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在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逻辑研究工作”一章中,执笔者周文英则认为,胡适“一是强调哲学的方法论意义而降低甚至否定其世界观的意义;二是把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有意混同”,他说胡适心目中的逻辑方法就是“还带有某种哲学一般化的方法”。尽管周文英批评了胡适的逻辑方法不够纯粹,但他也承认,《先秦名学史》“乃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逻辑断代史的专著,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9、236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逻辑史学者从中国逻辑史角度理解《先秦名学史》,本无可厚非,专业研究者理应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看待一个研究对象。但问题在于,仅仅从逻辑史意义上去理解《先秦名学史》,是否窄化了本书的内容和意义?或者说,《先秦名学史》是否为一部纯粹的逻辑史研究著作?这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以上就是《先秦名学史》的版本、翻译和研究的大致情况。
二、《先秦名学史》是一本写什么的书?
这个问题也等同于,《先秦名学史》仅仅是一部纯粹的逻辑史研究著作,还是性质有所不同?它只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一个初稿,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区别?
胡适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原题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出版时删掉了“A Study of”三个字,并在“Logical Method”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早在1916年7月17日给许怡荪的信里,胡适就称之为“先秦名学”,(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页。)而在1917年5月4日的日记里,他则自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09页。)。就其准确性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个译名比“先秦名学史”更可取,但都不如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发展(研究)”来得恰当。把Logic译为“名学”,始作俑者是严复。1902年,严复就把穆勒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译为《穆勒名学》。当时还有一个从日本传回国内的译名,叫做“论理学”。从字面上看,“先秦名学史”这个译名很容易使人觉得它研究的是先秦的逻辑史,这也正是温公颐、李先焜、周文英、宋文坚等学者都把它看作是先秦逻辑史研究著作的主要原因。“The Logical Method”直译为“逻辑方法”,胡适之所以把它译为“哲学方法”,一是因为哲学方法必须以逻辑方法为基础,或者说逻辑方法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哲学方法,要想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方法,不能不研究其逻辑方法,况且书中关于“别墨”的几章讨论的确实是较为纯粹的逻辑方法;二是因为“The Logical Method”的中心词是“方法”而非“逻辑”,哲学方法包含逻辑方法,但又不限于逻辑方法,“哲学方法”是一个比“逻辑方法”更大的概念。
逻辑是思维的形式,而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思维的质料,哲学要运用思维的形式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形式逻辑当然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哲学的方法包含逻辑,也必须建立在逻辑之上,但方法的概念是大于逻辑的。比如,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属于形式逻辑,而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里,则既有归纳法,也有演绎推论,但柏拉图最根本的论证方法,却是一种被称为“产婆法”的“为真理接生的方法”,即把各种站不住脚的观点驳倒,最后剩下的一种驳不倒的观点即是“真知”或“真理”,这种“产婆法”则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方法。再如,康德哲学的基本逻辑是形而上学的演绎推论,然而他把前人所认为的“直觀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反转过来,让“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页,第11页。)这个“书斋里的哥白尼革命”就属于方法,但不属于逻辑。又如,胡适在本书中用符号学的方法讨论《易经》的卦象,这也超出了逻辑学的范畴,卦象与卦辞、爻辞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是修辞学或符号学的问题,却不完全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现代的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叙事学方法等,虽然都必须以逻辑为基础,却又不是逻辑学概念所能涵盖的。从纯粹的形式逻辑,到形式化公式(如康德的实践法则、杜威的“思想过程五步说”、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再到复杂的理论模型,哲学方法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脱离逻辑来谈方法,脱离逻辑的方法决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哲学方法去研究知识和道德的经验对象和基本原理,方法是否科学,将决定哲学的思想和观点是否科学。
李先焜说“胡适在论述中也存在一些根本缺点,就是在谈逻辑理论时往往掺杂了很多非逻辑的(主要是哲学的)理论”;(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97页。另见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版,第345页。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45页。)周文英说胡适“把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有意混同。看来胡适举的那几个例子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双重性质但又都不是纯粹的逻辑方法……胡适心目中的逻辑方法可以说就是这种还带有某种哲学一般化的方法”。(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239页。)显然,他们都是从较为纯粹的逻辑史研究角度来看的。从这个角度看,《先秦名学史》讨论的内容就明显溢出了逻辑史的范围;如果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那么,他们的批评则明显窄化了《先秦名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周文英说:“它们都具有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双重性质但又都不是纯粹的逻辑方法”,恰恰反过来揭示了本书并非专门研究逻辑史的著作,而是一本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的书。至于他说本书“强调哲学的方法论意义而降低甚至否定其世界观的意义”,则又是用哲学史的标准来衡量本书,因为世界观属于哲学问题,而不属于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从逻辑史的狭义角度还是从哲学史的广义角度来批评《先秦名学史》,都未能抓住本书的实质,观点也难免偏颇。
其实从本书的英文原题和胡适自译也可以看出,《先秦名学史》研究的并非只是先秦的逻辑史,而是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虽然原题中并未出现“哲学”一词,但胡适做的就是哲学博士论文,书中讨论的也是先秦诸子的逻辑和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方法,而逻辑学又是哲学的一门子学科,所以将其译为“哲学方法”没有问题。然而仅从书名及其翻译来判断本书的性质,还远远不够,后文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先秦名学史”这个译名,比“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更为简洁、易记,这可能是他在1922年出版该书时最终择此译名作为中文书名的主要考量。
因此,本书英文版各章节标题,如“Logic and Philosophy”,“The Confucian Logic”,“The Logic of Moh Tih and His School”等,我们应视为“Logical Method and Philosophy”,“The Confucian Logical Method”,“The Logical Method of Moh Tih and His School”的简写。例如“Logic and Philosophy”,胡适日记里就自译为“哲学方法与哲学”。当然,“The Confucian Logic”和“The Logic of Moh Tih and His School”这两个标题,日记则译为“孔子之名学”“墨家之名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509页。)从翻译的一致性上看,不如译为“孔子的哲学方法”“墨家的哲学方法”更合适。日译本译为“儒教の哲学及论理”,“墨家の哲学及论理”,(胡适:《胡适の支那哲学论》,[日]井出季和太译,东京:大空社,1998年,第36、72页。)涵盖的范围则更广;但中译本直接译为“孔子的逻辑”“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反而容易遮蔽本书所探讨的实质问题。正如在“孔子的逻辑”这个标题下讨论《易经》的卦象问题,会让我们感到困惑,译为“孔子的哲学方法”则不会产生歧义。但书中有关别墨学派的“故”“法”“效”“推”的讨论,则是较为纯粹的逻辑问题。
我们来比较一下《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章节,看看这两本书有何异同。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先秦名学史》英文本和北大讲义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两者之间自然有剪不断的关系。《先秦名学史》除“导论”外,共分四编,第一编谈历史背景,第二编是“孔子的哲学方法”,第三编“墨家的哲学方法”,其中包括“墨翟的哲学方法”“别墨的哲学方法”“惠施和公孙龙”,第四编“进化论和哲学方法”,其中包括“庄子的哲学方法”“荀子”和“法家的哲学方法”。“惠施和公孙龙”及“荀子”各占两章,显然,这两章的标题也是简写。谈哲学方法不能不谈其方法的运用,以及由此得出的哲学思想和观点,因此《先秦名学史》也讨论了各家各派的思想观点,但先秦诸子思想不是本书讨论重点,用温公颐的话说,就是“凡有关系到他的逻辑理论时才附带提及”。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除第一篇“导言”外,共分为十一篇,分别是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第三篇“老子”,第四篇“孔子”,第五篇“孔门弟子”,第六篇“墨子”,第七篇“杨朱”,第八篇“别墨”,第九篇“庄子”,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第十一篇“荀子”,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法家”是第十二篇中的一章。在《先秦名学史》中,“老子”是放在第一编“历史背景”中作为专节来讲的,而“孔门弟子”和“杨朱”则未作专门讨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每一章节均以介绍和评述先秦诸子的思想为主,虽然也谈到了他们的哲学方法,但有关哲学思想的内容占各篇的比例,较之《先秦名学史》则多得多。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篇幅是《先秦名学史》中译本的近两倍,这里无法一一比较两书细节上的差别。且举一例来对两者的异同略作讨论。这个例子即前文提到的对《易经》中“象”的解释。
在《先秦名学史》里,胡适是这样讲的:
这“象”或“”字有个很有趣的来历。它原来意指一只象。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对这个字的引申义作了这样的说明:“人希见生象也(因它只生产在‘南蛮’各国),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子·解老》)因此,象就是人们对事物所构成的映象或者“意象”。在《易经》里,象字被用在两种稍有不同的意思上。第一个意思,象只是人们注意到或感知到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如我们谈到的‘天象’……第二个意思,象是能用某种符号表示的、或者在某些活动、器物中所能认知的意象或者观念。
象字最广泛地用于《易经》里的正是第二个意思……(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34页。)
而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他则做了更长的一大段解释:
《系辞传》说:“象也者,像也。”(像字是后人所改。古无像字。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第5卷)和北大版《胡适文集》(6)均印作“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上海古籍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则印为“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8页。耿云志先生来信指出:“孟、京、虞、董、姚,应是指五位《易》学家。”经查:孟,是孟喜,京,是京房,汉代著名《易》学家;虞,是虞翻,董,是董遇,姚,是姚信,三国时期的《易》学家。)
可证)。《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篇》)我以为《韩非子》这种说法似乎太牵强了。象字古代大概用“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目视物,得物的形象,故相训省视。从此引申,遂把所省视的“对象”也叫做“相”(如《诗·棫朴》“金玉其相”之相)。后来相人术的“相”字,还是此义。“相”字既成专门名词,故普通的形相,遂借用同音的“象”字(如僖十五年《左传》,“物生而后有象”)。引申为象效之意。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的原本,都叫做“象”。这一个湾可转得深了。本来是“物生而后有象”,象是仿本,物是原本。到了后来把所仿效的原本叫做象,如画工画虎,所用作模型的虎也是“象”(亦称法象),便是把原本叫作“象”了。例如《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有人根据王弼注,以为原本当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句在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应在后。这是“物生而后有象”的说法。却不知道老子偏要说“象生而后有物”。他前文曾说“无物之象”可以作证。老子的意思大概以为先有一种“无物之象”,后来在这些法象上渐渐生出万物来。故先说“其中有象”,后说“其中有物”。但这个学说,老子的书里不曾有详细的发挥。孔子接着这个意思,也主张“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模型而成的。《系辞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和老子先说“有象”,后说“有物”同一意思。(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93—194页。)
乍看上去,似乎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对《先秦名学史》中引《韩非子》的话做了否定,或许我们可以说,他写《先秦名学史》时考据不精,也可以说他留美时期读的古代典籍不够,回国后读了更多的材料,因而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修正了《先秦名学史》的说法。但问题在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作在后,出版在前,而《先秦名学史》却写作在前,出版在后,如果说《先秦名学史》中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他完全可以对这段话进行修正。伯希和1923年的书评里也对《先秦名学史》中“象”字的解释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胡适引《韩非子》的这个解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摈弃了这个解释。然而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藏书里,有一册《先秦名学史》的胡适晚年手批本,这个手批本上有不少胡适批注、修改的字迹,根据扉页上的题字,这些批注和修改应该是在1951年5月以后。在这个手批本里,上引《韩非子》的这一节,他不仅未作任何修改,还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手批本),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书,馆藏号HS-N03F6-030-03。该书扉页上有胡适题记:“This copy is from the library of my sinological friend,the late Roswell S.Britton,who died in 1951.Hu Shih May 1951.”)这就不能仅仅用“因为他太忙,所以出版时并没有纳入他的新观点,而是直接用了五年前的手稿”来解释了。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先秦名学史》中引《韩非子》的解释,并非是他考据不精,而是别有用意。
那么是何用意呢?我们从他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窥见端倪。上述第一段引文指出“象字最广泛地用于《易经》里的正是第二个意思”之后,他又通过“未济”()、“既济”()、“谦”()、“豫”()、“随”()、“蒙”()等卦的卦象阐明:“古代的圣人,受这些现象的暗示,在他们的心里构想出种种‘意象’,并可说是为它们制定了象卦或用以代表繁多的天下之赜的名这样的符号形式。”他说:“‘意象’在孔子的逻辑中被认为最重要,不只是作为象卦或字这样的符号的‘意义’。‘意象’是古代圣人设想并且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度来表现的理想的形式……所以我们读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一章结尾又说:“在《易经》里,‘意象’是用三畫形和六画形的符号或卦表示的,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这些符号或卦也许是一种现在已经消亡的语言的文字记号。现在与卦相当的是名或字。名被看成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认为名正对社会和政治改革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因为它们是意象的最好的符号,因为迄今能追溯、能恢复的意象只存在于它们之中。”(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34—35、37页。
《先秦名学史》第二编第三章英文标题为“The Hsiang or‘Ideas’”,中译本译为“象或者‘意象’”。陈通造认为,胡适一贯将idea和柏拉图的Idea译为“意象”,将Idealism译为“意象论”。《先秦名学史》的译者对胡适这个习惯应该颇有了解。随着词义的演化,如今普通读者看到“意象”一词,多会联想到image(通俗意义上的诗文意象)或者figure(一般意义上的形象),而不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关键的“idea”。这一点与《先秦名学史》关系相当密切,胡适后来在别处坦陈:“我研究《易经》多年,终觉汉儒以来的注解总不能满意。后来忽然想到《易经》的‘象’和柏拉图的‘意象’(Ideas)(陈百年先生译为观念)有些相同。后来再读《易经》,便觉得‘'易者象也’一句真是全书的关键。从此便稍稍能懂得这部书了。”胡适:《〈中国古代哲学讲义〉提要凡例四则》,《胡适全集》第7卷,第260页。)
这里引用的都是《先秦名学史》中译本里的译文。通过这些引文我们可以发现,胡适不仅把《易经》中的卦象解释为“意象”符号,甚至把先秦哲学中的“名”也解释为一种“意象”符号,或者说卦象就是一种“名”,而与之相应的一切器物、制度、道德、礼俗则是“实”,“名”与“实”之间存在某种“形相因”的关系。他试图阐明,这种“意象”符号与器物、制度的“形相因”,正是孔子本人的哲学方法。他说,“儒家的问题就在于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即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理想关系的世界,以便现实世界模仿和接近”,(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4页。)这个理想世界即所谓的“第一原则”,以此来确立社会的器物制度和道德规范。孔子“把所有人类器物、制度归因于自然的起源,并把现时一切道德上、政治上的混乱归咎于它们与自然的、原来的意义和目的逐渐偏离,来达到上述目的”。(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37页。)
没有任何證据表明胡适曾经读过现代符号学先驱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直到1959年才有了英译本,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胡适纪念馆编的《胡适藏书目录》,他的藏书里也没有任何索绪尔的书,因此胡适在1917年不太可能了解索绪尔的理论;但他对《易经》中“象”或“意象”的解释,却完全可以用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来替换。他在“墨翟的哲学方法”一章中说:“孔子逻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名的意义,即‘所以谓’。”又引墨翟的话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这里的“所以谓”可对应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所谓”可对应“所指”。反过来讲,《普通语言学教程》译者如果把“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翻译得更加中国化一点,也可以译为“所以谓”和“所谓”。当然,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指涉的范围要更广,不仅仅限于“名”与“实”的关系。在胡适看来,“象”或“名”都是一种“所以谓”,他也称之为“主词”,而与之“形相因”的器物、制度、道德、礼俗等则是“所谓”,即“宾词”。(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7页。)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白,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为何只引《韩非子》的那段话来解释“象”了,古人没见过活象,但有人见过大象的骸骨,于是就根据大象的骸骨去想象活象的形状,那么,大象骸骨与想象中的活象的“形相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所以谓”(“能指”)与“所谓”(“所指”)的关系,正如《易经》中的六十四种卦象与卦辞、爻辞的关系一样。至于“象”字的训诂学意义上的解释,并非《先秦名学史》中论述的重点,胡适想要以此来揭示的,是这些“象”或“名”的符号,与相应的器物、制度、道德、礼俗之间,是如何构成一种“形相因”的关系的。这显然是一种方法论的解释,目的是找到一种与孔子思想相契合,却不同于占卜迷信的理解《易经》的方法。
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先秦各地方言语源不同,也可以说是语出多源,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诗经》中的《大雅》《周颂》与《国风》的区别,《大雅》和《周颂》是来自西部的周贵族的语言,而《国风》却大多是中东部地区的民歌,秦与六国的文字也各不相同,无论是音训、形训、义训,都只能根据文献记载,而许多民间的、口头的解释却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必须充分承认训诂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它是揭示古代文献真正含义的唯一科学的途径,如胡适所说,唯有“通过训诂的研究,我们才能摆脱传统训释者的主观偏见,并对古籍的真实意义获得正确的理解”。(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3页。)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对于那些仅存孤例的解释,如果缺乏充分可靠的文献依据,训诂学则难以穷尽先秦语言文字的全部真相。韩非是战国末期人,他对“象”字的解释可能是当时多种解释中的一种,用它来解释《老子》中的“象”或许是错的,因为其他文献中的解释与之不同,然而我们却不能认为他对“象”字的解释就毫无根据。何况,胡适在引用这个解释时,还专门指出,这是“韩非对这个字的引申义”。韩非的这个解释,虽然晚于老子和孔子,却远早于《说文》;哪怕只是他的一种主观解释,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能够让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的人对“象”字还有这样一种解释。而正是这种解释,启发了胡适用符号学方法来解释《易经》中的“象”。
在我看来,胡适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解释《易经》的卦象,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文要努力做到在解释《易经》的历史上,空前地几乎完全打破关于《易经》的传统的占卜与道学的观点,并对孔子的附说或者作为逻辑的理论,或者作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加以解释。”(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31页。)在这一点上,他确实超越了前人,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孔子的哲学方法,也为我们理解“十翼”中的孔子思想提供了一种更加科学的途径。他的这种符号学的解释,可能也受到了美国符号学先驱、实验主义哲学鼻祖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影响。早在1897年,皮尔士就发表了长篇论文“Logic as Semiotic:The Theory Signs”(《作为符号学的逻辑:符号理论》),(Charles Sanders Peirce,“Logic as Semiotic:The Theory Signs”,in Philosophical Wittings of Peirce,Dover Publications,New York,1955,pp.98-119.)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一文中也介绍过他的实验主义哲学。
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还将孔子的“意象”说与培根的“自然生自然”和亚里士多德的“形相因”说做了比较,当然是为了用西方读者听得懂的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但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他则完全抛弃了这类解释,甚至放弃了对《易经》卦象的符号学解释。尽管其中讲《易》的一章也谈到“易(变化)的道理只是一个象效的作用。先有一种法象,然后有仿效这法象而成的物类”,意思与《先秦名学史》中的相关表述大致相同,但我们已看不出任何符号学的影子。因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写给中国人读的,当时大部分中国读者尚不能充分了解西方哲学方法,拿西方哲学跟中国哲学做比较便显得不合时宜。即便如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仍被金岳霖讥为“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关于上述第二段引文,胡适引《说文》《诗·棫朴》《左传》《系辞传》里的例子对《韩非子》的说法加以纠正,但后面讨论的却不是孔子的哲学方法,而是讨论“物生而后有象”还是“象生而后有物”。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转换到“物生而后有象”还是“象生而后有物”的问题上来,“物生而后有象”比较好理解,就是先要有“物”,然后才有“物”的“意象”或“法象”,而“象生而后有物”则是说“先有一种法象,然后有仿效这法象而成的物类”,这个说法跟柏拉图所说的先有“理念”,然后才有模仿“理念”而生的万事万物如出一辙。胡适举了大量的例子,来阐明“孔子以为人类历史上种种文物制度的起源都由于象,都起于效仿种种法象”,这些例子包括《系辞传》里对“离”()、“益”()、“噬嗑”()、“涣”()、“随”()、“豫”()、“小過”()、“暌”()、“大壮”()、“大过”()、“夬”()、“未济”()、“既济”()等卦象的解释。我们看到,其中一些卦象的解释,也出现在《先秦名学史》里,但两者所要阐明的观点却并不相同。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要阐明的是,这些卦象或“意象”是一种怎样的“符号形式”;而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他要阐明的却是“孔子对于‘象’的根本学说……就是人类种种的器物制度都起于种种的‘意象’”。(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96页。)这种认为“人类种种器物制度都起源于‘意象’”的观点,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不属于“方法”的范畴。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对《先秦名学史》“逻辑方法”的继承与深化,李先焜在几个版本的《中国逻辑史教程》中已有论述,这里不赘。
以上只是《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两个相应章节或者说细节的比较,或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先秦名学史》中所举的例子和相关论述,都是围绕先秦哲学方法论来谈的。如果我们暂且忽略“逻辑史”和“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之间的区别,那么正如温公颐所说:“胡适认为写逻辑史应以各派逻辑学家的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为主……这样,就可以把逻辑史与哲学史明确地区别开来。”(温公颐:《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胡适:《先秦名学史》,第3页。)而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即使保留了同样的例子,也多是围绕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来谈的。也就是说,《先秦名学史》讲的是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的则是先秦哲学史。虽然胡适讲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时,不能不涉及他们的方法,但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讲哲学思想才是主要的,他所做的删节和增补,体现的正是“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与“哲学史”的区别。
本节从《先秦名学史》的书名、章节标题的翻译,以及其中的一个段落,将其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进行比较,大致已可说明,《先秦名学史》并非纯粹的逻辑史研究著作,而是一部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著作;《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两本性质不同的书。也许我们这样来回应罗素与伯希和等人的观点是较为合适的:即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先秦名学史》基础上修改而成,《先秦名学史》也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且不能被前者取代。
三、胡适为何要写《先秦名学史》?
胡适日记里并未记载他为何选定“先秦名学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四十自述》里则完全没有谈到博士论文,晚年的《口述自传》虽有提及,但也没有细谈。谈得最多的,是在他给好友许怡荪和韦莲司的信里。给母亲冯顺弟的信里,偶尔也会报告博士论文的写作进度。
胡适和许怡荪是安徽绩溪同乡,又是上海中国公学同学,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后,许怡荪1913年赴日留学,1916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却不幸于1919年3月22日因病英年早逝。许怡荪去世后,胡适为他作传,称“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胡适:《许怡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24页。)二人从1908年开始通信,直到许怡荪去世,几乎没有间断。现保存下来的胡适留学时期与友人的通信中,以与许怡荪的通信内容最为丰富,其中有很多长信,有的甚至长达数千字,谈到博士论文的就有6封,记述较详者有4封。
1914年6月5日,他在给许怡荪的信里说:
适近拟再留二年,俟民国五年始归。拟作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哲学史之第一时代”(先秦诸子),尚未动手作文。近方思于暑假内再细读先秦诸子一过,细细摘要录出,条分其学说,撷其精华,然后译之;译成,然后作论论其精粗得失,及其对于吾国学术思想之影响,暨其与泰西学理同异之点约二年可成书。(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45页。)
胡适1912年2月19日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后,同时修了英国文学、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专业的课程,到1913年春学期结束,他已修满了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两个专业的毕业学分,因此得以提前进入康奈尔大学赛基哲学学院念研究生,但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学制,他要到1914年2月才能获得学士学位,6月17日才得毕业。也就是说,他在进入康奈尔大学赛基哲学学院念研究生的第二学期末,甚至尚未参加大学毕业典礼时,就已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了。
1914年5月8日,他在日记里记道:“吾尝谓吾国人无论理观念。顷见留美学生某君作一文,其起句云:‘西哲有言:学识者,权力也。一国之人有学识,即一国之人有权力;一国之人有权力,即其全国有权力。有权力者必强,无权力者必弱,天演之公例也。’此何等论理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18页。)在6月5日这封长信里,他又跟许怡荪讨论了逻辑问题。“吾谓吾国今日大病在于无有论理观念,章行严所谓逻辑也……其最大之祸根,乃在援引先哲成语以为论理之根据。”他列举了若干“根据同类之史事为证”的例子,指出“此种奴隶根性之论理不去,终不能望一健全之舆论也。此病根在于用演绎法,而不用归纳法”。他还批评了“三段论”的演绎,“先假定一大前提,而不知此大前提或不根据事实,或竟全属荒谬”。又说:“近拟作一文,论题曰‘说术’。术者(method),求学之途径,论事之理法也。此文大旨有三:(一)归纳的论理(即物穷理);(二)历史的眼光(与古俱新);(三)进化的观念(人治胜天)。章秋桐日日谈逻辑,而其人所作文乃全无归纳的论理(《甲寅》中驳严复《民约议》),真可怪也!”(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45—46页。)我们没有看到他写的《说术》一文,也许后来没有写。他这里所说的“术”(method)显然就是方法。8月24日,他日记里又谈到沈约的《神不灭论》和《难范缜神灭论》,他说前者“此论盖用论理学家所谓‘类推法’(Inference by Analogy)也”,而对于后者,他则反思说:“刀是无机之物,人身是有机之体,本不可并论,亦是‘类推法’之谬。吾十一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譬,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旬报》作《无鬼语》,亦首揭此则。年来稍读书治科学,始知其论理亦有疵,而不知沈氏在当时已见及此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459、460页。)可见,胡适对逻辑或哲学方法问题的兴趣,大致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这时他还没有考虑把“先秦名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而是打算做“中国哲学史之第一时代”(先秦诸子)这个题目。
1915年3月上旬至中旬,胡适写了一篇“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胡适:《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席云舒译注,《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0期。)他对博士论文的想法忽然发生了变化。他在3月9日给许怡荪的信里说:
适近于所拟“博士论文”题颇有变动,前此拟以“先秦诸子”为题,继思此题有数难:(一)不能得大学教师之助,以其不知吾国哲学也;(二)不能得此间各大藏书楼之助;(三)参考书不能多得;(四)此题在今日影响甚小。以此诸难,适已决计弃去前拟之题(此题吾归国后当赓续为之,先以汉文著书,然后以英文译之)。今所择题为“国际伦理学”(International Ethics)。今之人皆谓国与国之间但有强权,无有伦理道德。此说之流毒何啻洪水猛兽!此说一日不去,天下一日不安。吾此文志在昌明西方先哲之国际道德说,以补今日国际公法之缺陷,虽明知人微言轻,无裨世乱,惟不能已于言耳。(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49—50页。)
3月14日他又写信把这个想法告诉韦莲司:
上星期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曾告诉你,我打算写一段时期的中国哲学,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最近我意识到写这样的论文,对我是件蠢事。因为写这样的论文,正是用其所短,我既得不到师长的协助,也无从利用此间的图书设备。等我回国以后,我有较好的条件来写中国哲学。
所以,我已决定放弃那个构想。我(现在)所择定的论文题目是《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他給出的理由是:第一,“有作一如此研究之必要”;第二,“我对此极有兴趣”;第三,“我可以利用此地的图书馆和系所(设备)”。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在你执行了我的建议,清理了你的书桌以后,我会寄一份今天下午刚写完的康德报告给你。”这里所说的“康德报告”,就是《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这篇论文。在此前后,他还写了“John Stuart Mill on Justice:a Study of the Fifth Chapter of his‘Utilitarianism’”(《约翰·穆勒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A Study of Locke’s‘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Hume on Space,Time and Causality”(《休谟论空间、时间和因果》)以及“The Argument of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分析论”的论证》)等多篇哲学论文,还做了两大本哲学读书笔记。同年6月15日至30日,他还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在康奈尔大学举办的“国际政策讨论会”。但他忽然打算更换博士论文题目,可能既有他给许怡荪信里所说的打算放弃“先秦诸子”这个题目的四点原因,也有他给韦莲司信里所说的选择“国际伦理原则研究”的三点理由,但还有两个更直接的原因:一是他日记里时时关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写《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一文给他带来的灵感。
可是几个月后,1915年7月4日,他又致信韦莲司:
我决定明年离开绮色佳。长时以来,一直在考虑哥伦比亚。我收到一份哥大图书馆有关中国哲学藏书的资料。我也给芝加哥大学写了信,但目前就我所知,哥大是较好的选择。等到收到正式的通知,我就决定去哥大了。学校决定了,我论文的题目也就定下来了——《古代中国非儒家的哲学家》。当然,这个题目还可能改变。(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68页。)
这个时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又回到了“古代中国非儒家的哲学家”,但为了解决图书资料的问题,他准备转学去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同年7月11日致母亲冯顺弟的信里,也告知了拟来年转学哥大之事,并列举了七条理由,其中有两条是:“儿所拟博士论文之题需用书籍甚多,此间地小书籍不敷用。纽约为世界大城,书籍便利无比,此实一大原因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页。)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还谈到离开绮色佳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1915年被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停发了赛基奖学金。康奈尔大学地处小城绮色佳,居民仅一万六千人,胡适熟人太多,常常受邀做演讲,以至于影响学业,被停发奖学金,加之康奈尔大学所藏中国哲学书籍太少,这是他决定离开绮色佳的原因。但选择哥大,则一是由于哥大中国哲学藏书较丰富,二是由于杜威对他的吸引。因为申请哥大十分顺利,所以不用等到明年,当年9月就成功转学去了纽约。到了哥大,他选修了杜威的两门课,一门是“论理学之宗派”,一门是“社会政治哲学”,他说:“我非常喜欢‘论理学之宗派’那一课,那门课也启发我去决定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237页。)
1916年1月25日,他给许怡荪的信里又对博士论文选题做了详细记述:
博士论文,初以“先秦诸子”为题,后以其太广,非三年所能了,故改为The Reaction against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China, 但及孔子以后之非儒诸家,首墨子,次及庄周杨朱公孙龙惠施尸佼卫鞅荀卿韩非诸家(荀卿属儒家而其“非十二子”乃并及子思孟柯,且为名学巨子,又为韩非李斯之师,故不能不及之也)。(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54页。)
上面这段话,说的仍是博士论文打算做“古代中国非儒家的哲学家”。他说:“适之择此题也,志在以新眼光读旧书,二年以来,所得之多,已非初意所能梦见;盖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二千年来惟其论理学之皮毛尚在人间,其精彩之处久成绝学,弥可痛惜。”(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54—55页。)这说明他此时对诸子学的看法已与一年前所认为的“此题在今日影响甚小”大相径庭。
他列举了拟研究的对象,并评价了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和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之得失:“近人治诸子学者,惟孙仲容先生之《墨子间诂》(书信整理者把《墨子间诂》误识为《墨子闲诂》,这里更正。)为最善。然孙先生不解哲学,其书但可为‘墨子’善本,而不足以言墨学也。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精于印度哲学,以是为根据,然后返观先秦哲学,故能通其学理,不仅为章句训诂而已。然太炎先生之诸子学亦未免有穿凿过当及支离破碎之处。彼能知学术之兴与‘地齐政俗材性’三者有关(见《原学》),而不能以此意推之先秦诸子之学术,故其书有支离破碎之病也。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然亦不敢盲从苟同,自视近所成就殊不无一得之可取。”他既指出了孙诒让和章太炎的长处,也指出了他們的不足,而他所谓的“以新眼光读旧书”,正是想要从“二千年来惟其论理学之皮毛尚在人间,其精彩之处久成绝学”这个新的角度,亦即向来为注疏家们所忽视的逻辑方法的角度,来重新研究先秦哲学。
如果说一年前他对逻辑的兴趣主要是由现实状况引起的,如章士钊等人日日高谈逻辑,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讲逻辑,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则可以说他此时对逻辑的兴趣,已完全是一种学术自身的兴趣,一种disinterested interest,一种非关利害的兴趣:
数月以来,专治“先秦逻辑”,初但以为本文之一小支,今则愈治愈有所得。昔之附庸,遽成大国,始知先秦名理之精,为后人所未梦见,而其影响所及,遍被诸家,先秦学说,无不以此为中坚,为根据。其专治名学如公孙龙子者,固不待论。他如墨子荀子韩非慎到诸家之论理学说,政治学说,心理学说,无不本其逻辑学说。今以此意返观先秦哲学,乃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其诸家之沿革得失,皆一一可寻。乃知古今学者之不明先秦学术,正坐不明先秦之名学。譬之无刀而割,无矢而射,其仅得其皮毛也宜矣。(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55页。)
可见,到了1916年1月,在杜威的“论理学之宗派”这门课的启发下,他对“先秦逻辑”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所谓“专治‘先秦逻辑’”,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专门以先秦的逻辑方法作为研究对象,二是运用西方现代的逻辑方法去研究“先秦逻辑”。
7月17日,他又写信告诉许怡荪:“论文择题大难,颇不易为……所作论文,限于名学一部,正以其为二千年来之绝学,但可求之诸子原书,别无他书可以相助(所可助益者章太炎书耳)。”并且发愿“他日归来,当以二十年之力作一‘中国哲学史’,以为终生一件大事,虽作他事,必不将此志放弃”。(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65页。)到这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已最终确定。他5月1日、6月9日给母亲冯顺弟的信中都说暑假将不外出,“拟今夏赶完博士论文初稿”;到了9月27日,又向母亲报告:“儿所作博士论文,夏间约成四分之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72、87页。)可见其“颇不易为”。直到1917年4月27日,他才写完初稿,5月3日打印好,又校对了一遍,4日交给了学校。“属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约九个月而成。”(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509页。)
以上讲的是胡适选择“先秦名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多少也揭示了他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但这些原因主要是他个人的,是他受了杜威的影响之后,“以新眼光读旧书”的所得。但我以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先秦名学史》开篇所说的:“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这在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近代哲学就是以《谈谈方法》和《新工具》开始的。”(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页。中译本把笛卡尔的《谈谈方法》译为《方法论》,系误译,这里依原文校订。《谈谈方法》的译者王太庆在此书的第一条注释里曾引笛卡尔1637年3月给Mersenne信里的话:“我并不命名为《方法论》,而名之为《谈谈方法》,这就等于《关于方法的引言或意见》,以表明我并不打算讲授这种方法,只想谈谈它。”见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论证方法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谈谈方法》的译者王太庆在该书“代序”《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中说:“经院哲学的方法是:以某些宗教信条为根据,依照一系列固定的逻辑公式,如三段式,推出维护宗教的结论,它所根据的前提是不是可靠,它是从来不管的。即使前提可靠,推出来的东西也只能限于前提里所包含的,一点也不能给人新的知识……经院哲学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信仰主义,一个是先验主义,一个是形式主义。这三个特点是互为表里的。”(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第ⅶ—ⅷ页。)这个观点跟胡适1914年6月5日致许怡荪的信里所说的如出一辙,胡适说:“三段论法……先假定一大前提,而不知此大前提或不根据事实,或竟全属荒谬:妇人,伏于人者也;苏菲亚,妇人也;故苏伏于人者也。又如:君者,出令者也;君者,民之父母也;……皆可用作大前提,而未必皆真确也。”(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46页。)需要指出的是,王太庆写《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时,决不可能读过胡适写给许怡荪的信,因为《谈谈方法》是2000年出版的,而《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直到2017年才出版,但他们对“三段论”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科学之所以不能发展,学术之所以不能昌明,除“信仰主义”“先验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知识被教会垄断外,哲学方法的制约更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了打破这种制约,培根在1620年出版了《新工具》,提倡科学的归纳法;笛卡尔在1637年出版了《谈谈方法》,提出形而上学的演绎法。正如王太庆所说:“培根提出了经验主义,来对付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笛卡尔则提出理性主义,来对付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这两个人都大力提倡具体的科学研究,来对付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第ⅷ页。)此后,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哲学经过近两百年的论争,欧洲的哲学方法论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西方哲学和科学也随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不妨帮胡适补充几个“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例证:有了康德的先验方法论,才有了他的批判哲学,有了辩证法,才有了黑格尔的哲学,有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才有了他的实验主义哲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胡适所说的“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近代哲学就是以《谈谈方法》和《新工具》开始的”之缘由。
即使到了17世纪,欧洲教会的势力仍十分强大,培根和笛卡尔提出的新方法又为何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呢?以笛卡尔为例,他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法,就是从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因,推到一个不可再推的原因,再从这个不可再推的原因出发,来演绎万事万物的原理。笛卡尔说,我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我甚至怀疑自己究竟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但唯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即“我在怀疑”这件事,那么,“我在怀疑”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因。既然有怀疑,就必定有一个怀疑者存在,所以我是存在的,即“我思故我在”。他又说,既然我在怀疑,那我就是不完满的,因为跟(确定的)知识相比,怀疑是不完满的。既然我是不完满的,我的脑子里怎么会出现“完满”这个观念呢?一个不完满的事物里面能生出一个“完满”的观念吗?他说不可能,因为那就等于说可以无中生有。“那就只能说:把这个观念放到我心里来的是一个实际上比我更完满的东西,它本身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也就是说,干脆一句话:它就是神。”(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第29页。)他就是这样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于是,“上帝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再推的原因,即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因”或“最后之因”。显然,笛卡尔这里所说的“神”或“上帝”已不同于天主教所说的“神”或“上帝”,而是一个由人自身的理性证明出来的“神”或“上帝”。根据同样的理由,人的理性也可以说是“天启的”或者“神”所赋予的,因此,人再去做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完全合乎“神”的意志的。可见,笛卡尔通过形而上学的演绎法架起了一座从宗教信仰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由于它承认“上帝存在”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原因”,因此没有被教会扼杀于摇篮之中,而是逐渐挣脱了教会的阻力,从而推动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尽管人们很快就认识到笛卡尔的局限性,后来欧洲哲学方法论的发展也很快超越了笛卡尔,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等论著中都批评过这种寻求所谓“第一原理”或“最后之因”的形而上学思想,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笛卡尔的哲学方法在17世纪所带来的变化。
中国的情形与此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胡适曾在1923年4月3日的日记里说:“程颐提倡格物致知,张载提倡善疑,皆前古所不敢道。这种精神,至朱熹而大成。不幸而后来朱学一尊,向之从疑古以求得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薛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故朱熹本可以作中国的培根、笛卡儿,而不幸竟成了中国的圣汤姆(St.Thomas Aquinas)!”(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3页。)他这里又提到培根和笛卡尔。这段引文虽然写于《先秦名学史》出版以后,其思路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明清两代,甚至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中国的思想学术也有“信仰主义”“先验主义”的特点,程朱理学和礼教成为社会的普遍信仰,孔孟之道成为先验的真理。当朱熹集注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試的教科书,无论对它进行怎样的批评,或者做出不同的解释,对社会都是起不到什么大作用的。程朱、陆王所信奉的是同样的儒家经典,可是对它们的阐释却大相径庭。胡适说:“宋学与明学之间的全部争论,就是关于‘格物’两字应作‘穷究事物’或‘正心致良知’的解释问题的争论。”(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6页。)他们的争论,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于作为社会信仰之根基的“天理”的解释,而不是要动摇这种“先验主义”的社会信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明末清初出现了毛奇龄、费密、胡渭、颜元、李塨等反理学的思想家,却未能动摇程朱理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动摇程朱理学的基础,把时代和社会从理学与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需要有新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261页。)
“朴学”又称“汉学”,即取法于汉代郑玄、许慎的学问,与程朱理学所代表的“宋学”相对,他们的方法就是考据学方法。简而言之,他们反对“宋学”,却并不是与之辩驳,也不是给出某种新的解释,而是从字音、字形、字义、断句等方面去考证某个字、某个词在先秦文献里共有几种含义,先秦文献中该字是否出现过宋儒所解释的那种含义;或者校勘古书的正误,或者考订古书的真伪。如果考证出先秦文献里某个字根本没有宋儒所解释的那种含义,宋儒的解释是以今释古,或者其他版本的古文献内容与宋儒的注释有出入,或者证明程朱理学所推崇的某部经典是伪书(如阎若璩证伪梅赜的《古文尚书》等),那么,程朱理学所讲的相关道理乃至相关思想,便不再可信;在铁的证据面前,哪怕是程朱理学最坚定的拥趸也不得不承认。朝廷修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于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第四,《读礼志疑》六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2页。)
从前人们认为清代“朴学”只有学术,没有思想,事实上,从胡适的角度看,在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方面,清代“朴学”所做的贡献,要远远高于绝大部分空谈思想的“思想家”所做的贡献。清代“朴学”以这种科学的考据学方法,釜底抽薪,抽掉了程朱理学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并且能被整个士大夫阶层接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程朱理学作为社会信仰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笛卡尔以他的形而上学演绎法,在经院哲学之外开出新路,最终对教会的权威形成反噬,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见,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学术之上,思想若不以学术为基础,则往往沦为游谈。
但胡适也指出,清代考據学方法应用范围太窄,仅限于古代经典的考证,未能运用到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他在《先秦名学史》“导论”中说:“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中译本这里所说的“近代中国”指的是宋代以来的中国近世,胡适专门做了一条注释:“就哲学和文学来说,要回溯到唐代(公元618—906)。”其实直到他写《先秦名学史》的时候,国内学界对整个古代哲学和古代思想的研究,也都还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而在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冲击,一直体现在种种关于“体用关系”的讨论当中。他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8、10页。)只有找到某种科学的哲学方法,对我们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哲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现代化的改造,才能使我们旧有的思想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并与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我以为,这才是他选择“先秦名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主要目的。
四、《先秦名学史》写得怎么样?
本文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罗素、伯希和、库布林、贝亚、温公颐、李先焜等国内外学者对《先秦名学史》的评价,其中多数学者都对本书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他们的评价都是在胡适已取得更大成就之后做出的,这就容易让人觉得,这些评价是否含有对胡适后来成就的看法。换句话说,如果胡适没有取得后来的那些成就,他们还会不会如此肯定《先秦名学史》这本书?
前文已分析过,《先秦名学史》中对《易经》“象”的解释——其实不只是对“象”的解释,也包括对“易”和“辞”、“正名”与“正辞”的解释——“空前地几乎完全打破关于《易经》的传统的占卜与道学的观点”,把“十翼”中孔子的论说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来讨论,不仅使我们对孔子的哲学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十翼”中的孔子思想提供了一种远比传统道学家和理学家的解释更为科学的途径。但这些只是此书中的局部内容,局部论述精彩,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整体上就都写得好,每一章都写得好,也并不意味着就完全实现了本书的研究目的。因为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它是否解决了它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才是它成功与否的标志。
那么,我们只要看《先秦名学史》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书中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如何解决的,就可以判断该书是否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准。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提出的问题是:宋代程朱理学试图寻找某种方法论来重振儒学,于是他们从《礼记》中找到了《大学》这本小书。宋儒对“格物”一词的解释十分接近于归纳法,虽然是对的,但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没有效果;明儒王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正心致良知”,在胡适看来,“他的逻辑理论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因而,“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7页。)那么,在我们接触到西方哲学之后,是不是直接拿西方现代的哲学方法来填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不足就可以了呢?胡适认为不可以。一方面,对于一种新的外来文化的输入,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吸收”,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就会“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而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来说,如果被强加一种外来文化,则会令这个民族感到不自在而产生抵触。怎么才能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怎么才能“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呢?(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9—11页。)这就是《先秦名学史》所提出的问题。
胡适认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把儒学从理学与道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先秦名学史》中译本把“rationalistic”和“moralistic”这两个词都翻译成了“理性”和“道德伦理”,但这里指的是“理学”和“道学”。中译本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8、9页。)不再把儒学看作是“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是让它回到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本来地位;二是要恢复先秦非儒家学派的地位,这些学派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失去了合法性,而正是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尤其在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欧洲近代哲学中诸如“为反对独断主义和唯理主义而强调经验,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充分地发展科学的方法,用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看真理和道德”等,都能在先秦的非儒家学派中“找到遥远而高度发展了的先驱”。(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0页。)因此,《先秦名学史》就是要“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既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唯其如此,才能“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也就是说,要把先秦的儒家和非儒家学派放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考察他们的哲学方法,并借鉴西方现代的哲学方法,从中发现并发展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使中国哲学得到现代转化和发展,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这里须做进一步解释的是,胡适为什么说程朱理学的逻辑方法没有起到效果,而王阳明的“逻辑理论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他在《先秦名学史》中未做充分解释,因为本书研究的对象不是宋明理学,而他在其他文章中的解释,我以为也还不够充分。程朱理学的方法是“格物穷理”,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页。)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这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258页。)宋儒的方法是“日格一事,而穷其理”,即每天研究一个事物或一个问题,穷究若干事例后,有朝一日“豁然贯通”,就能悟得最高的、终极的“天理”。通过若干事例来归纳出原理,当然属于归纳法。可是为什么胡适说“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没有效果”呢?因为宋儒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的,并非事物的一般原理,而是“理一分殊”那个“天理”。归纳都是有限归纳,它适用于证明事物的有限原理,而程朱理学的“天理”却是一种无限原理。五百年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一书中说:“印证一个一般真理的全部例子,不管数目怎样多,也不足以建立这个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页。)有限归纳不能证明无限原理,所以说用它来证明“天理”是无效的。陆九渊也曾多次明讥暗讽朱熹的学说“其言支离”,“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59页。)
陆九渊当然不是否认“天理”的存在,而是认为“天理”不应该以“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的方法来证明。胡适曾多次提到陆九渊的精神继承者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但他没有指出王阳明“格竹子”的方法错在哪儿。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是指穷究很多事物之后归纳出的原理,而王阳明“格竹子”却是“格”一个孤立的事物,从一个孤立的事物里面能得出什么原理呢?王阳明认为像朱熹那样“要格天下之物”([明]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的方法是错的,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他认为“格物”就是“正心”,“心即是理”,“心外无物”。这种把“理”和“物”都放到“心”上来看,貌似达到了“心”“理”“物”三者的统一,但却不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科学方法。例如《传习录》里的那个著名公案:“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明]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第122页。)由此可知,王阳明所谓的“心外无物”“心即是理”,既不是归纳出来的,也不是演绎推论出来的原理,而是一种“心”与“物”的“相遇”。这种“相遇”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个人完全可以快乐时看花感到愉悦、痛苦时看花感到悲伤;几个不同的人同看一“花”,其“明白”的事理也会不同;你不能说只要“心正”时看花,就能得到关于花的“良知”,即使你“心正”时看到的花全是红的,你也得不出“花是红的”这个结论(正如你看到的天鹅全是白的,你也无法得出结论说“天鹅是白的”)。评判一种哲学方法是否科学,只要看它是否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方法决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说王阳明的“逻辑理论”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原因。
如果把孔子和朱熹、王阳明的观点比较来看,我们会发现,孔子虽然没有讲过“天理”这个概念,但《系辞传》里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20頁。)若将这里的“天”的意志理解为“天意”或“天理”的话,那么,这个“天意”或“天理”就是外在于“物”和“人心”的,“物”和“人心”都要顺应这个“天理”的变化。而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从具体的“物”出发,试图揭示“天理”及“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虽然“天理”同样外在于“物”和“人心”,万事万物中的“理”都是来自同一个“天理”的“分殊”,但“人心”须通过“格物”去发现“天理”并达到跟“天理”的同一。王阳明则认为,“天理”和“物”都在“人心”里面,“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明]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上,第2页。)可见,尽管这三种解释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第一原则的世界”,但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跟《系辞传》里孔子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
古人对先秦典籍的解释,多取注疏和语录形式。《朱子语类》《传习录》所体现的,主要是朱熹、王阳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孔孟思想的本来面目。历代注疏则叠床架屋,每个注疏者又会融入别家别派的思想。戴震就说宋儒“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康德说:“如果有人让各门学科互相越界,则这并不是对它们有所增益,而是使它们面目全非。”([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李秋零译,第6—7页。)“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显然也会使孔孟思想变得面目全非。无论哪一种注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且容易使古人的哲学思想碎片化;唯有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客观的,并且能够使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得到系统化的解释。这也正是胡适要去寻找先秦哲学方法的原因。只有还原先秦的哲学方法论,才能恢复诸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才能使中国哲学和科学走向现代化。胡适对宋儒的批评,并非反对其“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反对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去证明的那个“天理”,不仅是因为宋儒把归纳的方法用错了对象,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把“天理”看作万事万物中的“理”的唯一来源,正是这种基于“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使程朱理学成为宋明以来新的社会信仰的基础。唯有破除这种“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中古遗产,恢复程朱理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而非作为社会信仰的地位,才能使科学得到昌明、哲学得到发展。这是胡适与程朱、陆王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有人批评:“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事实恰恰相反,胡适正是要以科学的方法而非传统的“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古典的思想文化,从而避免“引起旧文化的消亡”,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要倡导“整理国故”。
如果说“儒家的问题就在于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即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理想关系的世界,以便现实世界模仿和接近”将导致以下后果:
孔子把判断看作是关于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陈述,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把判断归因于一个绝对的和先验的起源,他和他的弟子实际上已经作出了一个普遍的命题:事物应当如何如何,而不考虑其后果。正如后来一个儒者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4页。)结果是,这普遍命题本身就被当作目的,完全没有检验其正确性的任何办法和愿望,也没有指导它们应用于具体情况的任何标准。因为,脱离了实际结果的普遍性命题,不过是空洞的词和抽象,依照怪想和偏见的盲目指引而浮现或幻灭。实际上,它们就像盲人关于黑和白的定义一样变得毫无意义和不负责任。(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6页。)
事实上,这也正是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的方法没有效果,而王阳明“正心致良知”的方法“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在“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第一原则的世界”,并且“把判断归因于一个绝对的和先验的起源”的哲学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不科学的。那么,在先秦非儒家学派的哲学中,能找到胡适所说的现代哲学和科学的那些“遥远而高度发展了的先驱”吗?能找到比儒家学派更为科学的方法吗?这些方法能弥补儒家哲学方法论的不足吗?
《先秦名学史》给我们呈现了墨家、庄子、荀子和法家的与孔子学派完全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其中,荀子虽然“一向被看作是儒家”,但他却“反对其他儒家学派”。此外,“他的两位弟子韩非和李斯,成为法家的两位重要代表”。荀子“否认名的神秘起源,代之以感觉经验和理智活动产生名这种理论”,他“摒弃了儒的‘象’的理论”,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10、116、119、111页。)这些都体现了荀子跟其他儒家学派的不同。关于墨家,李先焜说:“胡适一反中国哲学史认为儒家是哲学的正统的传统观念,指出:‘墨翟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这些论断,都是前无古人的。”(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92页。另见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版,第342页。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第342页。在后两个版本中,这一章的执笔者李先焜对前一个版本中的说法做了修订。)蔡元培在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里,认为该书有“四种特长”:一是“证明的方法”,二是“扼要的手段”,三是“平等的眼光”,四是“系统的研究”。(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39—140页。)可以说,这“四种特长”,在《先秦名学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第三点“平等的眼光”,不再把孔子和儒家放在“独尊”的地位上,而是将其放在与先秦诸子平等的地位上,分别评述他们的哲学方法的得失,因而《先秦名学史》能够通过客观的比较,来揭示先秦非儒学派哲学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无意于一一评述《先秦名学史》中各家各派的哲学方法,因为那将使本文显得过于冗长而又难以突出要点。“墨家的哲学方法”是《先秦名学史》论述的重中之重,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内容曾在美国来华传教士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921年10—12期全文连载,这是亚东版出版之前,《先秦名学史》中唯一公开发表的章节,可见胡适对这部分內容也颇为自信。他不仅论述了墨翟的“应用主义方法”和“三表法”,也着重论述了“别墨”的知识论和“故”“法”“效”“推”等方法。其中,惠施的“历物十事”和公孙龙的“二十一事”最能引起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兴趣。因为“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些命题,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希腊著名的“芝诺悖论”。“别墨的逻辑”一卷,讨论的是较为纯粹的逻辑问题,尤其是他对“效”(演绎法)、“援”(类推)、“推”(归纳法)等逻辑方法的论述,均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由于墨家——特别是“别墨”学派——的逻辑理论,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和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等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述评,本文也不再重复。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先秦名学史》所论述的墨家哲学中,超出逻辑史范畴之外的哲学方法论部分,不仅是因为前人的研究几乎从未涉及这部分内容,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可以回应学界长期以来对杜威是否能读懂《先秦名学史》,或胡适留学时期是否懂得杜威哲学的质疑,并回答《先秦名学史》是否达到了合格的博士论文水准问题。
胡适在墨翟的“应用主义的方法”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儒家和墨家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一般地说,这就是‘什么’和‘怎样’之间的区别,是强调终极理想和第一原理与强调中间步骤和结果之间的区别。”他说:“墨翟非常反对儒家的全部方法,反对那种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第一原则的世界,而对它们的实际后果考虑甚少或根本不考虑的方法。”(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4页。)
这当然不是胡适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从墨翟的论述中梳理出来的。如: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篇》,[清]孙怡让撰:《墨子间诂》下,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42页。《耕柱篇》作“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同上书,第432页。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做了注释。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5页。)
又如:
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篇》,[清]孙怡让撰:《墨子间诂》下,第443页。引文见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6页。)
前一句意思是说,评判“言”的真伪对错,要看它的效果,要看它能否“迁行”。后一句意思是说,一个盲人也知道黑和白的“名”,但你给他黑白两种东西让他去选,他却无法选择;天下的君子都知道“仁”的“名”,可是他们却未必知道选择“仁”应该怎么去做。“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亦即不能仅仅从原因(动机)上看,而要从效果上看。所以胡适说,墨翟想要“寻求一个借以检验信念、理论、制度和政策的真伪和对错的标准。他发现这个标准就存在于信念、理论等所要产生的实际效果之中”。把这个原则引申到制度或信念上,就是:“每一个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利于什么;每一个概念或信念或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它适合于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或品格。”(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4、55页。)
比较儒家和墨家方法论上的区别,用胡适的话说,“儒家关于‘象’的理论认为,产生于象的事物和制度后来体现为器具、制度和原理。按照这种逻辑,为了掌握眼前真实事物的意义,就必须追溯现在借以认知这些事物的名的原始的象,追溯它们的理想的涵义。”而墨翟则反对这种见解,他认为:“我们的制度、器具和概念并非来自先验的象,而是来自实际的需要。人类制度(这种制度是孔子和墨翟最关心的问题)的起源是由于某些实际的目标或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或目的,人类制度才被创造出来。因此,为了理解这些事物的意义,就必须问它们要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它们的实际效果构成了它们的价值,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意义。”(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4—55页。)再具体到墨翟的逻辑理论,他的“三表法”可以概括为一种“检验任何已知思想的真实性的要求”的方法,包括:“(1)跟已经确立的思想中最好的一种相一致;(2)跟众人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以及(3)付诸实际运用时导致良好的目的。”(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62页。)
如果说儒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第一原则的世界”的方法是一种“原因论”的哲学方法,“象”或“天理”就是人类的器物制度、道德礼俗的“第一原因”,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事物应当如何”,而“不考虑其后果”,引申到人的道德行为上,就是只要“动机”是正确的,“效果”如何则是不甚重要的。正如董仲舒所说:“正其誼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么,墨翟的哲学方法则是既考虑行为的“动机”,更强调言论、行为、制度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又以“效果”作为衡量言论、行为、制度的标准,它是一种“效果论”的哲学方法。由于墨家在战国后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这种哲学方法也随之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直到胡适把它重新发掘出来。
我在《胡适的哲学方法论及其来源》一文中曾阐明,17世纪以来的英国经验论、欧洲大陆的唯理论,以及康德的先验论,都是“原因论”的哲学,而胡适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验主义哲学则是一种“效果论”的哲学,(席云舒:《胡适的哲学方法论及其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6期。)即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所说的:“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转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转移到事实,从范畴转移到效果。”(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7页。杜威原文见《实用主义所说的‘实践的’是什么意思》,《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4卷,陈亚军、姬志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页。)把哲学的关注点从思维的“起点”转移到思维的“末端”,“从通则转移到事实”,从“原因”转移到“效果”,正是杜威一派实验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也是实验主义哲学在方法论上的一大革命,它打破了欧洲形而上学那种追求哲学的“第一原因”或“第一原则”的传统,把一切都放到“效果”上来衡量。杜威的“效果论”哲学之于20世纪美国哲学的意义,正如“原因论”哲学之于17—18世纪欧洲哲学的意义一样重要: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传统。胡适1916年1月25日给许怡荪的信里说:“古今学者之不明先秦学术,正坐不明先秦之名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不能理解杜威的“效果论”哲学的意义,也就难以充分理解他的“思想过程五步说”及其实验主义哲学的意义。
胡适对孔子和墨翟哲学方法的比较,显然是受到了杜威哲学的启发。因此,有人说胡适留学时期还不懂杜威哲学,这是毫无根据的。孔子和墨翟虽然没有将自己的哲学方法上升到“原因论”和“效果论”的高度,但沿着他们的思想逻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一推论:从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方法论出发,是有可能发展出20世纪西方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或者说,我们完全能够从先秦哲学中,找到适合移植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土壤。这个土壤虽然后来长期受到印度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改造,使人深信只有儒、道、释的思想才适合在这片土壤里生长,而胡适通过《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向我们阐明,只要拨开历史的积垢,我们这片土壤完全可以接纳西方那种现代的、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胡适虽然是受杜威哲学的影响和启发,才发现儒家和墨家哲学方法论的这种本质区别的,但他并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生搬硬套,而是从两千年来“论理学之皮毛”中披沙拣金,从其“久成绝学”的“精彩之处”发现的“先秦名理之精”。方法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那个“金针”,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那个“渔”,它只有科学与否、合用与否的问题,譬如工人伐木,用锯子比用斧头更科学,用它来凿井则不合用,不管它是由谁生产的。哲学方法论虽然要复杂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他山之石亦可攻玉,何况胡适只是受他山之石的启发,从我们古老的思想岩层中发掘了自己的攻玉之石。
我想,我们无须再去讨论庄子、荀子和法家的哲学方法,仅仅通过墨翟的哲学方法这个例子,已经能够充分说明,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很好地解决了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在宋儒和明儒的哲学方法之外,从先秦非儒学派的哲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方法。通过恢复、还原并发展这些方法,一方面,可以凭借先秦诸子的方法去还原先秦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个工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已经给出了可靠的证明;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破除两千年来儒家学说——特别是经由宋明以来程朱理学所延续下来的“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中古遗产,在避免“引起旧文化的消亡”的前提下,为中国哲学注入现代的、科学的生命力。《先秦名学史》的中文书名虽然叫做“史”,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先秦那段历史中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方法,但从它的论述逻辑上看,它并不是“史”,而是“论”。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和“论”在古典学术中往往不易区分,但从现代学术角度看,“史”是一种客观的述评,而“论”则是为了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知识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看,《先秦名学史》不仅是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它不仅有宏观的知识创新,在细节问题上,例如对“别墨”的逻辑的论述,即使是对《先秦名学史》持批评态度的周文英也不能否认:胡适对“别墨”的见解,“是对墨家逻辑研究的一个突破”;“在对惠施思想的研究上,与章太炎相比,胡适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245、250页。)而周文英之所以对《先秦名学史》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他仅仅把本书看作是一部逻辑史研究著作,从逻辑史的角度看,胡适对先秦哲学方法论的论述,自然大多超出了逻辑史的范畴。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里说:胡适博士论文口试时的六位主考都不懂中国哲学,其中包括胡适的导师杜威,在他们眼里,胡适的博士论文“简直像一本不知所云的中国哲学教科书(poorly written textbook),根本不同于一般博士论文钻牛角的‘体例’”。(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244页。)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里说:“他写《先秦名学史》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是受了实验主义的指导?我的判断是否定的。”他在书中长篇大论地试图说明,胡适当时对杜威的“实验主义”还不甚明了,《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都“糅杂”了温德尔班等人的方法,“他对哲学的起源、哲学史的目的以及方法论的部分论述,都是根据温德尔班。”(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307、313页。)认为杜威等人读不懂《先秦名学史》,或者认为胡适写《先秦名学史》时还不懂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其言下之意都是认为《先秦名学史》并非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至少它不符合杜威的要求。但正如前文所说,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与17世纪以来欧洲的“原因论”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效果论”的哲学,胡适从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因”或“第一原则”的角度解析孔子的哲学方法,又从“效果论”的角度分析墨翟的哲学方法,无论是说杜威读不懂《先秦名学史》,还是说胡适不懂杜威的哲学,都是站不住脚的。就像有人说胡适不懂康德,殊不知胡适早在1915年就写过两篇十分专业的研究康德哲学的英文论文。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警惕的,恰恰是不能把自己的盲区强加给研究对象。
我并不否认《先秦名学史》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些是胡适写博士论文时资料不足造成的,有些是他沿袭古人的旧说造成的。例如,他引《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他解释说:“它的中间是空的。”(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54、55页。)《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进一步解释说,第一句话指“车轮中央的空洞”。(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79页。)这是沿袭古人的旧说。但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话是运用借代修辞,以局部代整体,“三十辐共一毂”是以“车轮”代指“车”。这段完整的话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个原理。后两个例子意思是说,器皿中间是空的,才能供人使用;房子中间是空的,才能供人居住。那么,前一个例子自然应该是说,车中间是空的,才能供人乘坐。这是一种朴素的归纳法,即通过三个例子,来证明一条原理。如果把第一句话理解为,轮毂中间是空的,所以车轮才能转动,便不能跟后面两个例子形成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证明后面那条原理。而借代修辞在先秦文献里比比皆是,如《诗经》中的《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城”原指盾牌和城墙,代指守护国家的将才;《齐风·莆田》“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总角”代指幼年,指幼年结交的好友。古人解釋错了,胡适沿袭此错,也可以说错不在他。又如,他在介绍先秦“历史背景”时引了《孔子家语》里面的话,而我们知道,王肃的《孔子家语》是晚出材料。再如,胡适把《易经》“十翼”里的论说作为孔子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但他缺少一个限定,即“十翼”所代表的是孔子晚年思想。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汉]司马迁撰、[唐]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宋]裴骃集解:《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7页。)孔子晚年思想虽然代表他一生的定论,却不意味着他早年也必定如此,《论语》和《左传》里就有多个事例可以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是有过变化的,尤其是在“晚而喜易”之后。这些细微的瑕疵,对于整篇博士论文来说,自然是瑕不掩瑜。
我举这些例子,并非避重就轻,而是在我看来,如果把《先秦名学史》仅仅看作是一部逻辑史专著,那么可以说,其中大量的论述都不是逻辑史所能涵盖的;如果把它看作是一部哲学史著作,那么它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论述就显得非常不够;但如果回到它的本来意义上,把它看作一部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的著作,本书就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如果我们始终抱有某种成见,恐怕就很难看出本书的优点和长处。
五、胡适博士学位案之缘起与论争
胡适一生获得过36个博士学位,其中,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是他自己挣来的,其余35个荣誉博士学位,大都是英美各大学送他的,而且有不少是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名校,1939年,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还曾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学位。此外还有多所大学想要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迄今为止,他是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没有争议,将来恐怕也很难被超越。无论是从胡适的学术成就来看,还是从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来看,他的学术地位似乎很难被质疑。可是偏偏他从哥大挣来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却成了一桩聚讼四十余年的“学案”。原因就在于,他1917年留美结束回国,而哥大直到1927年才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整整迟到了十年。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和“案情”。
先说事实。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同年1月13日,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就在这一天,正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的胡适同乡、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写信给胡适说:“兄事已转达仲甫,已经代为谋就。孑民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关于此事,仲甫讯中已详,不多述也。”(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74—275页。)同月,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一封未署日期的信里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影印件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64页。“北京总长”疑系笔误,应为“北大校长”。原信无日期,《陈独秀年谱》系于1917年1月13日之后,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页。)4月11日,胡适写信将此事告诉许怡荪:“适已应蔡孑民先生之召,将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仲甫荐适自代其文科之任,适已辞之,因不愿任管理之重任也。此举兄倘以为然乎?”又说,“在北京尚不知教授些什么。适已有书去自述所愿,在专教中国哲学。不知此时之大学可能有高等之专科否?想一月内当可得仲甫回信也。”(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71页。)
4月19日,他写信给母亲冯顺弟:
论文五日内可成,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
此次大考,乃是面试,不用纸笔,但有口问口答。试者为各科教长,及旁习各科之教员,但想不甚难耳。
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
这几年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以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207—208页。)
许怡荪4月23日回信说:“日昨往晤独秀,知足下六月回国,良觌不远,可为额手称庆!……大学之事,微闻独秀苦于应付,甚望足下早来接手。内部英文文学教习难得好手,足下将来自兼教授,月薪约四五百元。”(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46页。)29日他收到许怡荪信后,回信说:
前已有书寄独秀,言不愿当文科学长。此次与蔡先生书亦言此事。今察兄来书,似独秀尚未以此举为然。适以为国立大学中乃使新进少年作文科学长,似非大学之福,故不敢当之。兄倘再见独秀时,乞为我达此意,何如?
适本意欲专授中国哲学,而以西洋哲学为辅。来书言独秀或欲弟兼任英文文学,恐任太重,反难尽职。大学非中学小学,似宜有专科教授,不宜一人兼任数科也。兼任或可暂为之,恐非久计耳。望亦与独秀言之为盼。(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73页。)
由此可知,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并准备“大考”之前,就已获得北大聘约,其中既有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又有陈独秀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甚至推荐他代替自己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而他则希望到北大“专教中国哲学”,不愿承担管理的重任。既获北大聘约——尽管北大教授聘书要到9月4日才发给他,(胡适的北京大学教授聘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HS-JDSHSC-2132-001。)学位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蔡元培也盼他回国“甚急”,但在美国读了七年书,不能不参加一下“大考”,况且在他看来,“大考”就像他在4月19日给母亲的信里所说,“想不甚难耳”。他5月4日向哥大哲学系提交了博士论文,22日参加了博士口试(即博士论文答辩),他在日记里记载:“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六人:Professor John Dewey,Professor D.S.Miller,Professor W.P.Montague,Professor W.T.Bush,Professor Frederich Hirth,Dr.W.F.Cooley。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二日),口试三时。”(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509、515—516页。)考完口试后,他便于6月14日离美回国,回国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直到他1927年再次赴美,向哥大提交了100本已出版的博士论文,哥大才授予他博士学位。
胡适回国后,很快就因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于是他的博士学位问題又在留美学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的风波。1919年9月7日,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朱经农写信告诉胡适,有一位跟他“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人造谣说“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试没有pass[通过]”,朱经农说:“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耿云志认为,这位“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人“很可能是指梅光迪”。(耿云志:《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见《重新发现胡适》,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但胡适不以为意,他给朱经农回信说:“美国一班朋友很有责备我的话”,这个责备有数种情况:“第一种是因为期望太切,所以转生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来。第二种是因为生性褊窄,好作不合时宜的言论,以自标高异,他们对新事业都下极严酷的批评,自己却没有贡献,这种空论家也只好由他去罢!第三种是顽固成性,除他的几句‘敝帚自珍’的旧式文字以外,天下事物都是看不上眼的。”但朱经农还是回信劝他:“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80—81页。)按照朱经农这两封信里的说法,只要胡适赶紧把博士论文刊印出来,“老胡冒充博士”这类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但留美学生中的这场风波,并非胡适博士学位案的起因。“案情”的真正发端,是1977—1978年唐德刚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一系列“回忆胡适之先生和口述历史”的文章。1957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部申请了一个项目,为胡适录制《口述自传》,因此跟胡适往来颇多,他常以“胡适的学生”自居。1972年,《胡适口述自传》英文稿由哥大口述史学部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刊布。1977年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购得该书中文翻译版权,社长刘绍唐又邀请唐德刚来翻译。唐德刚翻译了该书,并做了大量注释,译文先在1978年8月至1979年8月的《传记文学》杂志连载,1981年3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译文连载之前,刘绍唐又邀请唐德刚写了十篇总题为“回忆胡适之先生和口述历史”的文章,提前在1977年8月至1978年6月的《传记文学》连载,后来结集为《胡适杂忆》一书。在1977年10月发表的第三篇《三分洋货·七分传统》里,唐德刚“揭发”了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胡适博士学位案由此“案发”。
唐德刚首先提到,1952年,为了纪念哥大200周年校庆,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Howard P.Linton)编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闹了个“不可恕的大‘乌龙’”。接着是1961年,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编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袁同礼只知道胡适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可是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写的却是1927年,于是袁同礼便请唐德刚代为核实。唐德刚以神秘的口吻写道:“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我们不得不承认,唐德刚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很容易吊起读者的胃口,他自己对此也颇为得意,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里面,他曾引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话说:“他在看《传记文学》的胡适自传时,是‘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52页。)造成这种魔力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就是他经常把话说得模棱两可。比如这里他虽然没直接说“胡适是个假博士”,但引起的效果却是让人觉得胡适很可能真是个假博士,尤其是他后面又说:“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所以稽延了。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这就更让人觉得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可能真的另有隐情了。他指认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被“稽延”了,一是因为博士口试的主试教授都读不懂胡适的论文,二是因为胡适住校年限不够,三是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胡适很难通过一层层的考试。
事实上,关于袁同礼求证胡适博士学位年份之事,1960年10月,他曾亲自写信问过胡适,胡适在10月11日的回信中告诉袁同礼:“我的Ph.D.,论文考试是1917年完毕的,故我列在1917;但当时规矩需要一百本印本论文,故我在1917年回国时没有拿Ph.D.文凭。我的论文是1922年在上海印行的,我没有工夫送一百本给哥大,直到五年后,一九二七年我在哥大讲学,他们催我补缴论文印本百册,我才电告亚东图书馆寄百册去。我的文凭是1927年发的。”(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306页。)唐德刚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很可能就是他的性情使然。他还说胡适到北大任教后,由于北大“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胡适之多少有点胆怯”,于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個‘博士著’字样”。可是我查遍1919年2月初版以来,直到1929年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再版之前的各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未发现任何版本封面上有“博士著”字样,1929年以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封面上也无此字样。由于唐德刚是《胡适口述自传》的录制、整理和翻译者,他跟胡适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所以在大部分读者看来,他说的话具有天然的可信度,于是他的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就常常被当真了。
唐德刚的这一“揭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纽约的左派中文报纸《星岛日报》1978年4、5月份连续刊登了潘维疆的《胡适博士头衔索隐》(4月17日)、《胡适博士头衔索隐补述》(5月29日)、胡祖强的《从胡适博士头衔被考据说起》(5月13日)三篇文章,均认为胡适未取得博士学位。5月29日报纸上甚至以头条大标题形式称“胡适博士非真博士”。也许是担心事态失控,唐德刚又于5月30日投书该报,称潘维疆和胡祖强的文章有许多谬误和“乱说”,该报6月7日以“胡适乃真博士”为题刊出唐信。随后,《传记文学》1978年7月和11月又刊登了汤晏的《胡适博士学位的风波》和夏志清的《胡适博士学位考证》两篇文章。汤晏的文章对潘维疆的多处“谬误”进行了驳斥,却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反而做了一个毫无根据的“大胆的假设”,他说1917年胡适博士口试时,可能有某位主试教授投了反对票,所以1927年哥大又为他重新组织了一场口试,“可能只是拍拍肩膀,握握手,就算通过考试”,并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则胡适当然是真博士”。这种无凭无据的“假设”,反而会让人觉得越描越黑,起到的效果适得其反。有趣的是,《传记文学》还特地在汤文前面加了个“编者按”:“纽约左派中文报纸《星岛日报》于最近两三个月先后刊登几篇诬指‘胡适博士非真博士’的文章,该报认为系其‘独得之密’,并于五月二十九日用特大号字体做为头条要闻刊登。如此‘小题大做’,显系别有用心……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德刚博士以‘胡适乃真博士’长函于六月七日投书该报,予以驳正。”(汤晏:《胡适博士学位的风波》,台北《传记文学》1978年第1期。)这个“编者按”,明显是想跟《星岛日报》撇清关系,并保护自己的作者唐德刚。
夏志清的《胡适博士学位考证》一文认为,汤晏的那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假如六人中有一人投反对票,胡适自己哪有不知之理”?“杜威自己一直认为胡适是他生平最得意的门生”,如果论文导师“年轻位低,学问不扎实,可能别的考试委员会挑毛病,甚至不让你过关”,可是“杜威是名震全美的大学阀,哥大哲学系首席教授,即使胡适的论文写得不够标准,他要包庇他,别的主试人也不敢顶撞杜教授”。他又说唐德刚的“两条假设——规定住校年限不足;不务正业(搞文学革命、谈恋爱)”其实是唐德刚“想当然”的看法,“不成为理由”。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夏志清还提供了哥大退休教授富路德(Luther Cu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写给他的一封信,富路德在信里说:“事实很简单……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他认为胡适回国后工作太忙,没有及时出版他的博士论文,直到1926年“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话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富路德又以当事人的资格现身说法:“当我获悉胡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夏志清:《胡适博士学位考证》,台北《传记文学》1978年第5期。)富路德说他1927年邀请胡适在哥大做九次演讲是对的,但遗憾的是,他说那年毕业典礼时胡适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被证实他记忆有误。余英时认为,富路德是误把1939年6月6日哥大授予胡适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的事,混淆成了1927年的事,(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因为1927年哥大毕业典礼时,胡适已经回国。除富路德这封信外,夏志清的文章也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他提到杜威想要包庇胡适云云,同样“不成为理由”。
在《传记文学》1978年12月连载的《胡适的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的第一条长篇注释里,唐德刚回应了富路德和夏志清的观点。他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其模棱两可的文风:一方面声称胡适博士口试的结果是“大修通过”,一方面又说胡适那篇“光照百世、继往开来的博士论文,不幸地却被几位草包给糟蹋了”,那几位“草包”即是指六位主试教授;一方面说胡适1917年5月22日的《留学日记》里说的是“‘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他并未说‘通过’”,一方面又说“事实上纵使他说是‘通过’,也没有大错”……拨开这些文字上的迷障,他的观点实际上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哥大博士口试有三种情形,通称“三栏”或“三柱”,第一柱是“小修通过”,第二柱是“大修通过”,第三柱是“不通过”,他认为胡适“在1917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原因仍是六位主考都读不懂胡适写中国哲学的博士论文,所以没让他通过,按照规定他必须返校“补考”,等到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目睹了胡适在中国的声望,于是回国后就把“大修通过”改成了“小修通过”,并免去了胡适的“补考”;2.他承认“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一百本”;3.虽然他没再直接说胡适在哥大读博士的年限不足,但他认为像夏志清那样能在“三数年内”拿到博士学位的,“实在是凤毛麟角”,“1957年以前的博士学位九年读毕,算是快的;十二年是中等;十六年不算慢”,(胡适口述、唐德刚撰稿:《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胡适的自传〉第五章》,台北《传记文学》1978年第6期。另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242—246页。)言下之意仍是胡适的年限不够。正是唐德刚的这些说法,才使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成了一桩聚讼不休的“学案”。
此后学界的争论,大多是围绕唐德刚这些说法展开的,其中以耿云志、余英时、欧阳哲生、江勇振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我们来分别谈谈这些问题。
第一,关于胡适的博士口试是否pass,以及杜威是否把“大修”改成“小修”的问题。国内胡适研究的权威专家耿云志认为,胡适“口试没有pass”应该属实。他的理由可归纳为如下几条:1.胡适日记里写的是“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而不是记为“通过”,他认为唐德刚抓到了证据,却“不很注意这个证据的价值”,为什么记为“考过”呢?一是“因考试不顺利”,二是“当日不知道考试结果”,所以胡适有意选择了一个中性词“考过”,回避了通过与否的问题。2.1921年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给亲友的礼函中写的是证婚人“胡适博士”,陶行知也承认他是哲学博士,而朱经农则咬定“口试没有pass”是谣言,说明胡适并没有把真相告诉朋友们。3.有人说他“冒充博士”,这是涉及名誉的严重问题,胡适回国后完全可以马上出版博士论文,可是他没这么做,说明不仅仅是博士论文有没有出版、有没有给哥大提交100册副本的问题,背后可能还有其他隐情。4.胡适给母亲的两封信里都提到过博士学位问题,说明他对学位十分重视,可是当有人说他“口试没有pass”时,他却无法自卫,应属于无可奈何。5.博士论文题目是在去哥大之前选定的,他到哥大后忙于搞文学革命,没再对杜威哲学下更多功夫,并由此推断,“杜威对胡适的论文一直没有多大兴趣”。6.胡适在1917年4月19日的家信里一反常态,“对学位事表示出满不在乎的态度”,其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考试无把握的悲观情绪”。7.“考试期近,杜威对他的论文始终未曾赞一词”,可是两年后,陶孟和与郭秉文路过东京时拜访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一见面,杜威极力称赞胡适的论文”,前后态度判若云泥,是因为“事隔两年之后,胡适在国内的声名和事业都远远超出了他那篇论文的范围”。8.杜威曾给胡适写信,“只称胡适为教授而不称他博士;而信中提到郭秉文时,便称他为博士”。9.《先秦名学史》出版时,胡适补写的“附注”里说是作为“博士考试的一部分被接受”的,而不是说“被通过”。10.胡适说这篇论文曾受到读过它的人们的赞许,却不谈导师们如何评价。11.既然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已经有了更成熟的见解,就没有必要再出版旧作,而胡适将博士论文不加修改地出版,可见“确是为补领博士学位的需要”。最后,耿云志得出结论说:胡适在博士学位问题上“既不肯说实话,又不肯说谎话,遮遮掩掩,含含糊糊,时露窘相”,是因为他“好名之心太盛”。(耿云志:《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见《重新发现胡适》,第299—311页。)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十一条是我的歸纳,不全是耿云志的原话,但意思应无甚出入。
欧阳哲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杜威》一文中也支持了唐德刚和耿云志的观点。他说,胡适1922年1月所写的《先秦名学史》“附注”里有这样一段话:“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但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这就是它长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国内的英、美友人曾读到我这本书的手稿,屡次劝说我把这本四年前写的书出版,我现在勉强地把它发表了。可以高兴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主要论点、资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这表现在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中文修订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逻辑方法的发展。”欧阳哲生认为,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三点意思:
一是他本欲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也就是“大修”,但因工作繁忙而搁置,这实际暗含了他虽欲“大修”,实际只是进行了“小修”;二是他现在出版这篇论文,是应英、美友人的要求,胡适没有具体点名,但其中应可能包括罗素,甚至杜威这样一些国际著名哲学大师;三是他的这篇论文的主要成果已得到“国内学者的赞许”。这样一段字斟句酌的文字,其实是一种模糊处理,很容易给人一种他的论文只需“小修通过”的印象,以说明其博士学位并不是一个什么人们所想象的“问题”。
他进一步推论说:“作为一种相互的谅解,胡适向哥大方面赠送100册《先秦名学史》……并在哥大先做讲座,而哥大方面免除胡适的‘补考’,我猜测这是完全可能的事,且对双方也是比较体面的事。”(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9、90页。)
江勇振则认为,唐德刚关于杜威把“大修”改成“小修”,甚至帮胡适免掉“补考”的说法,“最大的缺点是毫无根据,虽然言之凿凿,基本上属于臆测”。(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他纠正了耿云志的上述第九条理由,即《先秦名学史》“附注”所说的作为“博士考试的一部分被接受”这个说法,他指出那句话正确翻译应该是“作为获取博士学位资格规定中的一项”,美国各大学都有此规定,要在论文标题页注明“本论文是作为获取博士学位资格规定中的一项”(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39—340页。)。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跟耿云志的上述第五条理由相似的观点,认为:“胡适写《先秦名学史》,其实灵感与论述的主轴,是来自于他在康乃尔唯心派老师的哲学史的观点;其方法学的启蒙,也是他在康乃尔所开始接受到的西方考证学……《先秦名学史》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误解与滥用比比皆是,甚至到了用实用主义的论敌讥诋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谈实用主义的地步!如果《先秦名学史》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这本论文怎么能通得过杜威那一关呢!”(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43页。)可是,耿云志这条里所说的“杜威对胡适的论文一直没有多大兴趣”这个观点,江勇振却并不同意,他引胡适1917年4月13日写给韦莲司的信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完的部分给杜威教授看了。他看了以后似乎很满意,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评语。”(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39、343页。)
第二,关于要给哥大缴一百本博士论文刊印副本的问题。富路德、夏志清均持此观点,唐德刚也承认哥大确实有此要求。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里,根据胡适1920年9月4日的“日程与日记”,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1881—1947)曾请他为哥大推荐一位中文教授,胡适说:“我实在想不出人来,遂决计荐举我自己……他原函本问我能去否,故极赞成我的去意。”又据胡适1922年2月23日的日记,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来信邀请他去哥大任教。余英时认为,这就是胡适选择此时出版博士论文的原因。“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此外,“1923年6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只是由于他后来取消这两个远行计划,因此才拖到1927年。余英时指出富路德记忆有误,并且也不同意唐德刚的说法,而是直接认定:“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9—12页。)
欧阳哲生则找到了哥大1927年胡适博士学位的注册档案,他说:“现在哥大保留的档案证明,胡适博士学位注册的时间是1927年3月21日,上面除了说明胡适向哥大提供了100册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这是亚东图书馆在1922年出版的版本),没有任何其他说明。但申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否要出版,且须交100册副本,这是否是哥大的一项成文定规,我以为仍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第89—90页。)然而,根据同样的材料,江勇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欧阳哲生在哥大档案馆所找到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地证明哥大当时确有缴一百册已出版的论文的规定。因此胡适非得呈缴一百册的论文,否则就是拿不到他的博士学位。”(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42页。)
第三,关于胡适在哥大住校年限不足问题。耿云志认为,唐德刚不久就“放弃了这个站不住脚的说法”,(耿云志:《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见《重新发现胡适》,第301页。)这里是指《三分洋货·七分传统》和《胡适口述自传》的不同说法。实际上,唐德刚并没有“放弃”这个说法,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余英时则认为,由于胡适在转学哥大之前,有在康奈尔大学的“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7页。)显然,在余英时看来,住校年限不足不是什么问题。欧阳哲生的文章中,虽然引述了唐德刚“胡适在哥大研究院只读了两年(1915—1917),住校时间太短,连博士学位研究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第85頁。)的观点,但他未做任何评论。
回顾一下上述观点。耿云志的观点主要是推论出来的,不可否认,他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推论十分精彩,可谓阐幽发微,且能注意到常人不易留心的细节,他的《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一文写于1978-1979年,当时相关研究资料还相当匮乏,因此他不得不借助于推论,但未能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余英时敏锐地发现富路德的回忆不可靠,因为胡适参加毕业典礼的时间对不上;他又推论出胡适之所以要在1922年出版《先秦名学史》,是因为他收到了顾临和哥大校长巴特勒请他去任教的邀请信,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去哥大补办博士学位手续,同时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但余英时在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这个论断时,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欧阳哲生发现的哥大档案,证明了胡适确实曾向哥大提供了100册英文博士论文,这是一项铁证;但他却在“猜测”哥大免除胡适“补考”是“完全可能的事”时说:“对其中的细节,我们目前无法取得其他的硬证,笔者曾向哥大教务部门索取胡适的学习成绩档案,但因事涉个人隐私,哥大方面不愿提供而作罢。”(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第90页。)而江勇振除了引胡适致韦莲司的信来证明杜威曾经读过胡适的论文,这是一条可靠的证据外,他的推论洋洋洒洒,即便是与欧阳哲生立足于同样的材料,他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见只有过硬的证据才更具有说服力,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则往往变成神仙打架,各说各话。
六、胡适博士学位案之重审
真正发现了有力证据的是我的朋友陈通造。他找到了从1848年直到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手册》(Catalogue,他译为“校情总览”)和哲学系的《信息简报》(Bulletin,他译为“院系简报”),其中包括1916—1917年,即胡适参加博士口试那一年的《学生手册》和《信息简报》,并且还找到了跟国内公开发行的版本不同的、封面印有“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且書后附有“Vita”的《先秦名学史》版本。
在1916—1917年的《学生手册》(Catalogue)里,“大学学位条例”对哲学博士学位作了如下规定:
申请文学硕士的学生在完成学业的时间里必须至少住校一年,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住校两年;但是,如果学生来自学习课程不被视同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课程的其他院校,其居留时间可按比例延长。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年限可计入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年限。学生在其他大学的学习经历可计入学分。在某些情况下,经特别安排,专门用于该领域研究的时间将记入部分住校时间。任何未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研究生住校至少一年的学生将不被授予学位。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圆满完成四个暑期班学习、申请博士学位的完成两个暑期班学习,加上正常学年的半年,将被视为达到了高等学位一年的住校要求。
每位哲学博士学位候选人应提交一篇论文,论文应包含对某一选题的原创性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并事先得到主修科目教授的批准。学位论文经批准后,应由候选人自行出版,并在授予学位前向系主任提交100份副本。如果学位论文已被著名科学期刊录用,并保证在两年内发表,则出于对论文重要性的考虑,经有关院系推荐,系主任可暂缓执行这一规定。系主任认为如有必要,可以要求候选人为论文最终出版提供一笔保证金。每篇此类论文的标题页都应印有以下字样:“作为满足哲学博士学位的规定项目之一而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作者全名、学位论文全称、出版年和出版地,如系重印,应注明重印出版物的名称、卷数和页码。每篇学位论文均应以简历形式附录作者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曾就读的教育机构、所获学位和荣誉以及他以前发表的出版物的名称。(Catalogue 1916-1917,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pp.220,222.)
而在1916—1917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哲学和理论科学系信息简报》(Columbia University Bulletin of Information:Facult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ure Science,1916-1917)里,则对上述规定作了更加具体的细化说明:
哲学博士学位条例
在政治学、哲学或理论科学系管辖下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如果希望成为哲学博士学位候选人,将由系主任根据其研究工作所在系的推荐进行预选。各系将根据以下条件推荐学生入学:
1.学生必须已在本大学或本大学认可的其他机构进行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学习时间至少相当于本大学规定的一学年。
2.该学生必须已使该系确信他已精通该系规则所规定的语言。
3.学生必须让该系确信他已准备好在该系指导下进行研究。
系主任将根据学位候选人所在系的推荐,对其进行终审,并任命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各系将根据以下条件推荐候选人参加考试:
1.候选人必须从事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至少两学年,其中一学年必须在本大学度过。
入学前的研究生学习年限可部分满足这一条件。
2.候选人必须通过系里要求的初试或满足系里的要求。
3.申请人必须撰写一份经系里批准并包含其研究成果的学位论文。根据系里的要求,该论文必须在毕业考试之前或之后出版。
学生应查阅有关部门公告或咨询他们所就读院系的行政人员,以了解该院系对候选人资格及毕业考试的要求。
每个学生都有一本注册簿,用于记录所修课程。在每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负责教授都会签名证明学生的出勤情况。在参加入学考试或毕业考试之前,学生应向系主任提交注册簿,以便系主任确认学生已达到住校要求。
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口试,必须在颁发毕业证书的三个日期(即10月、2月和6月)之一的至少两个月之前向系主任提出,以确保在该日期之前通过考试。
每位哲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应提交一篇论文,其中应包含对某一选题进行的原创性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并事先得到主修科目教授的批准。学位论文经批准后,应由候选人自行出版,并在授予学位前向系主任提交100册副本。如果学位论文已被著名科学杂志录用,并保证在两年内发表,则出于对论文重要性的考虑,经有关院系推荐,系主任可暂缓执行这一规定。系主任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候选人为论文最终出版提供一笔保证金。在每篇学位论文的扉页上,应印有“作为满足哲学博士学位的规定项目之一而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____系”的字样、作者全名、学位论文的全称、出版年和出版地,如果是重印本,还应注明重印出版物的名称、卷数和页码。每篇学位论文均应以“个人简历”(Vita)的形式,注明作者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曾就读的教育机构、所获学位和荣誉及以前发表的论著的名称。
政治科学系要求在举行毕业考试之前出版学位论文。
哲学系和理论科学系,學位论文在考生考试后方可出版。不过,学生至少应在考试前三周将论文的三份打印稿送到系主任办公室,供主考人员查阅。
哲学博士学位的一般考试并不局限于考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他地方修读的课程,甚至也不局限于这些课程所涉及的领域。考生应从整体上令人满意地掌握本学科知识,并熟悉本学科所包含的更广泛的知识领域。(Columbia University Bulletin of Information:Facult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ure Science,1916-1917,Sixteenth Series,No.22,June 17,1916.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Morningside Heights,New York,N.Y.,pp.14-15.)
这两份文件里,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相关的要点可归纳为:第一,候选人必须从事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至少两学年,其中一学年必须在哥大度过,即达到申请博士学位的“规定住校年限”要求,入学前的研究生学习年限也可以部分满足这一条件。第二,候选人必须通过系里要求的初试或满足系里的要求。第三,如果学生在其他院校学习的课程被视同于在哥大学习的课程,在其他院校的学习经历也可以计入学分。第四,必须在博士论文出版后向系主任提交100本;如果毕业前不能出版,只要能证明论文已被著名期刊录用,并在两年内发表,也可以毕业时即授予博士学位;如果前面两者都不符合,只要系主任同意博士候选人为论文出版提供一笔保证金,也可以拿到学位。第五,对出版论文的时间和格式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两份文件里,根本就没有唐德刚所说的“小修通过”“大修通过”“不通过”的“三栏”或“三柱”之说。对照上述规定,胡适1915年9月转学进入哥大,11月即通过“初试”,1917年5月参加博士口试,完全符合哥大住校年限的规定,甚至他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成绩也可以部分地计入学分。他1917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唯一原因,就是博士论文没有及时出版并提交100本给系主任。
前文提到,欧阳哲生怀疑“申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否要出版,且须交100册副本,这是否是哥大的一项成文定规”,他提出这一怀疑的理由是“与胡适同年(1917)博士毕业,却获得博士学位的蒋梦麟,其英文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迟至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第90页,注释①。)我们已经看到,哥大确有此成文规定。对于蒋梦麟为何能在毕业时拿到博士学位,陈通造在《新史料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再探讨》一文中已经做了精确的考证,是因为蒋梦麟答应回国后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商务印书馆为他提供了一笔博士论文出版的保证金,蒋梦麟向哥大哲学系交付了这笔保证金,所以他毕业时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陈通造:《新史料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再探讨》,《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2期。)
欧阳哲生提到胡适“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但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这就是它长期未能出版的原因”,他认为这就是“大修”改为“小修”的证据。其实胡适这里所说的,只是他自己想再修订一下博士论文旧稿,由于没时间修订,于是就直接拿旧稿去出版了,这跟唐德刚所说的“大修”改为“小修”毫无关系。而所谓胡适“在哥大先做讲座,而哥大方面免除胡适的‘补考’……对双方也是比较体面的事”,则是拿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来“猜测”美国大学的制度。
唐德刚之所以会有“三栏”或“三柱”之说,陈通造的文章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胡适留美时期,到唐德刚留美时期,时间已逾40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哥大规章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哥大官网上有1848—1945年的全部Catalogue,唐德刚是1959年获得哥大史学博士学位的,我们虽然没查到1959年的相关规定,但规章制度经常会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进行修订,比如唐德刚所说的“1957年以前的博士学位九年读毕,算是快的;十二年是中等;十六年不算慢”这种情况,陈通造解释说:“翻阅历年《校情总览》可知哥大本有研究生学业……最长六年的规定,而这项规定恰好在1917年废除了。此条一去,就为后来唐德刚先生所谓‘老童生’现象提供了制度保证。”唐德刚所了解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他以40年后的情形去解释40年前的事,这就是“从后视镜里看历史”,因此看到的并非历史的真实,甚至连历史的反光都谈不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Catalogue和Bulletin均极为常见,在哥大图书馆很容易找到,唐德刚入学哥大时一定也拿到过一册,即使他拿到的《学生手册》上的规定跟胡适当年已有很大不同,但要想求证当年的规定,总该知道去哪里找。何况他1962年以后还兼任过7年哥大中文图书馆馆长,他当年帮袁同礼核对胡适博士学位资料时,如果能去图书馆翻一翻这些《学生手册》,也许就不会出现他的那些“臆测”,让胡适“蒙冤”那么多年。
陈通造的文章还谈到,唐德刚和耿云志都称胡适日记里记载的是“考过”博士口试而不是“通过”,可是唐德刚自己整理的《胡适英文口述自传》里,明明白白写的就是“I passed the final oral examination on my thesis in the summer of 1917”(“1917年夏天,我通过了论文最终口试”),(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胡适英文口述自传》,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81页。)“考过”就是“passed”,根本不存在耿云志所说的“胡适有意选择了一个中性词‘考过’,回避了通过与否的问题”,唐德刚也完全忘了自己整理过的话。耿云志认为,胡适1922年给《先秦名学史》补写的“附注”里说这篇论文是“作为博士考试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而不是说“被通过”,他说:“说论文‘被接受’,本来可以理解成‘被通过’;但也可以照最普通的意思去理解,即他把论文交上去了,导师收受了,如此而已。”(耿云志:《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见《重新发现胡适》,第309页。)陈通造指出,胡适那句话英文原文是:“It was accepted by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s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它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所接受,作为我申请博士学位所需满足的各项要求的一部分”,却被中译者译为“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我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部分要求”,很可能是这个翻译误导了耿云志,其实“被‘接受’不是胡适的‘申请’,而是论文本身”。陈通造还发现,胡适1926年12月26日日记里记的应该是:“发电给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Dean处。”因为哥大的Catalogue和Bulletin里的要求就是寄给“Dean”(“系主任”),可是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和安徽教育版《胡适日记全编》的1926年12月26日日记正文里,却都把“Dean”印成了“Dena”。这个差错应该是胡适日记整理者曹伯言的误识。前文提到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是余英时给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写的序,后来收进《重寻胡适历程》一书,《重寻胡适历程》既有繁体版也有简体版,繁体版也是联经出版的,在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和《重寻胡适历程》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里都引用了胡适日记里的这句话,可是却写成了“发电给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Dewey处”,引文下面还特意重复了一句“这一百册论文直接寄给杜威”;而简体版《重寻胡适历程》和欧阳哲生的《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里,则都依《胡适日记全集》的正文,写成了“Dena”。也就是说,曹伯言和余英时都把“Dean”一词认错了,曹伯言认成了“Dena”,而余英时认成了“Dewey”。
耿云志说杜威1919年给胡适的信里,只称他为“教授”而不称“博士”,可能也是因为胡适博士口试没通过。陈通造则给出了有力的新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哲学系教授、杜威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拉里·希克曼(Larry A.Hickman)编的《杜威往来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I-IV),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irginia,USA:InteLex Corporation,2009.該书信集为电子版,未标注页码。)里,就有多封杜威写给胡适的信,杜威1919年给胡适的信里也经常称其为“博士”。例如:
4月22日,杜威在致家人Sabino Dewey的信中说:“请转告Lucy一定要给我们寄一张明信片,交北京国立大学胡适博士转。”抵达上海后,5月3日杜威向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请假:“我在日本时曾致信伍德布里奇院长谈了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询问我是否有可能在下一学年受邀到中国并留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我说如果此事可以安排妥当,我很愿意前去。之后胡适博士想已给您去电(他已写信确保我同意)。”还有一封同年11月13日杜威致哲学系同事Wendell T.Bush的信,提到他要在北大开课,“这些讲演由胡适博士(Dr.Hu)口译,所以每讲用时两个钟点”。这位Bush不是旁人,他和杜威都是当年胡适口试的六位主试者之一!
(陈通造:《新史料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再探讨》,《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2期。)
可以说,陈通造提供的材料,完全能够解决胡适博士学位案中的所有疑点。接下来仅需回应一下江勇振的观点。江勇振说:“‘哥大过去有一项规定,颁授博士学位必须在论文出版并缴呈一百本之后。’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1940到1950年代的留学生,他们根据自己留学时期对哥大的规定的了解,而把它想当然地回溯到胡适留学的阶段……哥大出版社的网站上说,哥大到1950年代为止,规定研究生必须在论文出版以后才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但没说明要缴多少本。”(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40页。)他认为欧阳哲生发现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要缴一百本的说法,无论他有没有亲眼看见第一手证据,他总算是承认哥大确有这一规定的。他也不同意唐德刚的那些“臆测”,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同样是说胡适没能通过博士口试。他引胡适《留学日记》“自序”里的话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他觉得胡适“这句话不但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还有误导我们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胡适“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杜威的著作”。(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297页。)幸好我在胡适1915年上半年的读书笔记里看见过他阅读杜威1908年出版的《伦理学》第十章“The Moral Situation”(《道德情景》)的一段记录,(胡适1915的英文读书笔记簿,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馆藏,档案号:0062-009。)否则我很可能会相信江勇振的说法。他的论证完全属于理论推演,并没有提供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据。他评论说,《先秦名学史》是胡适“汇通中西考证学的结晶,也是他挪用、糅杂新黑格尔、新康德唯心论、实验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成果”,(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297、343页。)它“根本就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所以,“这本论文怎么可能通得过杜威那一关呢!”
江勇振这个思路令人“耳目一新”。杜威是一位哲学大家,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哲学传统。他讲过:“过去讨论过而现在继续加以讨论的这些问题,只有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才成为真正的问题。”(杜威:《哲学复兴的需要》,王成兵、林建武译,《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可见杜威十分注重哲学问题的来龙去脉,强调要把哲学问题放到哲学史背景中去讨论。他的实验主义“效果论”哲学,正是在批判和超越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原因论”哲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如果说胡适从“原因论”的角度去分析孔子和儒家的哲学方法是“糅杂”了黑格尔派、新康德主义唯心论——特别是江勇振所说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史家温德尔班的方法,而他从“效果论”的角度去分析墨翟的哲学方法论又是“糅杂”了杜威的实验主义,那么,杜威批评黑格尔派和新康德主义唯心论时,也引述过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是不是也可以说杜威“糅杂”了黑格尔派和新康德主义唯心论的方法呢?如果我们不是没读懂《先秦名学史》,便不能否认本文第四节的分析,胡适对孔子和墨翟的哲学方法的比较,逻辑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相反,恰恰是江勇振的分析,展现了高超的“糅杂”技巧,例如他说:“他在《先秦名学史》里,赋予先秦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新意,称许那是可以用来把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在中国接枝繁衍的沃壤。”(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43页。)可是,《先秦名学史》里提到亚里士多德名字的共有四处,包括一处注释,(Hu Shih(Suh Hu):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Shanghai,1922,pp.6,37,39,102.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8、35、36、80页。)第一处只是提了一下名字,后三处可以视为有效征引,谈的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形相因”这个术语,目的是想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易经》的“意象”和“别墨”的“法”的概念;而关于“三段论”,胡适仅仅是在批评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所说的“墨家也有三段论法”这个观点时提到过,章太炎“把‘大故’和‘小故’解释为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和小前提”,胡适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别墨的演绎法并不采取三段论的形式”,他列举并分析了《墨子》书中的几个例子,得出结论说:“别墨演绎法的理论不是三段论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正确地作出论断的理论。”(Hu Shih(Suh Hu):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Shanghai,1922,p.97.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76—77页。)从这个结论里可以看出,胡适显然不认为三段论是一种完全正确的理论。但是到江勇振这里,就变成“赋予先秦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新意”了。且不说这个句子本身就是病句,在江勇振的书里,类似的“糅杂”俯拾皆是。
此外,这里我想再提供一些新证据,尽管不如陈通造的证据那么“硬”,但作为辅助性证据,它仍有一定的价值。陈通造文中引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写给胡适的两封信,信中谈到《先秦名学史》“有Vita的一百册”之事,跟胡适缴给哥大的100本博士论文有关。《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收亚东同人与胡适的通信,已由北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夏寅整理出来,其中涉及《先秦名学史》出版之事的信札共有三封。江勇振也曾提到胡适1960年10月11日写给袁同礼的信,胡适在那封信里说:“一九二七年我在哥大讲学,他们催我补缴论文印本百册,我才电告亚东图书馆寄百册去。”(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341页。胡适原信见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306页。)由此可知,作为《先秦名学史》的出版方,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汪原放对此事应该十分了解。
汪原放写过一本一百多万字的《亚东六十年》手稿,1983年学林出版社从中选取了16.6万字,出版了《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2006年学林出版社又增补了少量材料,更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重新出版,全书共20万字。但这两个版本里,都没提到《先秦名学史》出版之事。而《亚东六十年》的手稿现已分藏三处,最主要的一部分收藏在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另外两部分分别由两位收藏家收藏。庆幸的是,这两位收藏家所藏的汪原放手稿,我都得到了影印副本,其中有一部分“附录”,里面包括汪原放抄录的37封胡适跟他的往来书信,其中有4封,内容跟2020年8月25—30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与《胡适留学日记》手稿一同展出的胡适遗札完全相同,可证汪原放抄件的真实性。这批信札均未被任何胡适书信集收录。在这些信札里,有多封谈到《先秦名学史》出版之事,均为1922年3—11月所写。现将这些书信的相关内容,以及夏寅整理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的相关内容,按时间顺序录在下面,并稍作解释。以下凡涉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的信札,均注明出处;但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附录”里的信札均尚未出版,无法注明出处。
1922年3月3日,胡适在致汪原放的信里提到:“英文論文样子已寄给你了。此事要办须早办,随时请给我一信。”这是最早的一封涉及英文论文出版之事的信,信的下方有汪原放注:“‘英文论文’指《先秦名学史》,1922年10月初版印行。”这个寄信日期表明,在胡适2月23日收到哥大校长巴特勒的邀请信仅仅十天后,他就已经校对完一部分《先秦名学史》的清样,并将其寄给了汪原放。3月12日,胡适又致信汪原放:“博士论文印样另包寄上。”信末未署日期,但根据信中其他内容可以推断是3月12日所写,这句话是说剩下的一部分清样也已校对完,另包寄上。
就在胡适上一封信发出的次日,即3月13日,汪原放也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论文已经付排,是在商务印书馆印的。因为别家都不及他们快,而且印出来的东西靠得住。他们说定两个月可以出板。商务的生意真好,要又是我先找着王云五先生,由他请高梦旦先生出了一个条子,给印刷部鲍先生,他们的同事恐怕懒接这个生意,而且也决不能两个月就可以印出。高先生的条子是:汪原放先生来印一部英文书,这书是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请速排印。这个条子的力量真大!
前次兄说过,我们校过之后,还可以托昆山路一个外国人再校一次。我到商务送校来的时候再看,如果他们校的已经很少错处,我和希兄觉得可以付印了,那就不送去校了;如若不然,那时我再发快信请你写一封介绍信给我去请那位外国人校。兄意如何?(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62—563页。夏寅整理。信纸左下栏外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字样。)
这封信收录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因此了解的人略多。由此信内容可知,《先秦名学史》虽然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但却是由商务印书馆代为排版印刷的,汪原放找到王云五,由高梦旦批的条子,商务印刷部才肯接这个生意。亚东图书馆本来还想托一个外国人再校对一次,可是汪原放和章希吕商量后,觉得要是校对错误不多,就不用再送出去校对了,不然的话,就再去找那个外国人校对。至于那个外国人究竟是谁,我的朋友林建刚认为,很可能是胡适的哥大校友、时任《沪报》(Shanghai Gazette)编辑的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1893—1962)。但从后面的通信来看,最终并没有去找他校对。
1922年3月19日,胡适致信汪原放:
论文付印甚好。纸张请用较好的。有一篇序文(A Prefatory Note,或是A Note)中间拟改几个字,请你接到排样,即为寄来,无任盼切。(此序最后付印亦可。)
此书最难排的是小注。原本概用“*”,“**”,“***”,甚不好。寄上的样本改用“*”,“+”等,不知商务能照此办法否?如有困难,可一律改用数目字。如“1”,
“2”,“3”等。每篇(Chapter)为一串数目,每下一篇另起一个数目。
这封信提到的“A Prefatory Note”或“A Note”,就是耿云志和欧阳哲生文中所说的《先秦名学史》前面的“附注”。胡适还对注释序号提了一些要求。
3月30日,汪原放又复胡适一封长信,信中说:“论文昨日已经送了样来,排的很好,校的很好。小注是用数目字好,已和商务说过了。这书,我们当然尽力校对,恐怕原稿有错,我们会看不出来。”这封信出自汪原放手稿“附录”,是汪原放抄的自己的信。可知商务印书馆的二校非常认真,只需汪原放和亚东图书馆编辑做完三校,用不着再去找那个外国人校对了。
下一封信再谈到《先秦名学史》出版之事,则要到3个月后。6月29日,胡适致汪原放:“英文论文何日印成?稍缓倒不妨。如能让我将印成之页数先读一遍最好。千万将序文寄来一校改。印成时,一百部末后可留‘Vita’。那一百部不必寄来,另请装一木箱,以便运往美国。”这封信里,胡适交代了留“Vita”的一百部如何处理。显然,这一百部就是提交给哥大以获取博士学位的。
7月6日,汪原放又致信胡适:
《论文》已经排完了。今天商务才把“A Note”送来校对。“Preface”也一同寄上。请兄改后用快信寄回。单一百部印“Vita”已经和商务接洽了。
兄要把《论文》校一遍是做不到的了,因为商务是随校随印的,现在校过的都已经印成功了。商务的英文校对狠精工,我们细细的校也校出不多的错,这书大约照原稿是不甚有错的,只怕原稿有些错了的地方,只好将来再改正。(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第567—570页。夏寅整理。信纸左下栏外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字样。)
10月25日汪原放又致信胡适:“《先秦名学史》,商务答应十一月一号先订出二三百册。我决等书出了版再把告白登出。有Vita的一百册,如何分寄,请示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第607—609页。夏寅整理。)以上两封信的相关内容,陈通造的文章里均有征引。大约在11月8日前后,胡适复信给汪原放:“《先秦名学史》请寄廿册给我。有Vita的百册,请代装一坚固木箱,暂存尊处。”胡适的回信也未署日期,只能根据信中其他内容推断在11月8日前后。
以上书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先秦名学史》出版过程中胡适与汪原放的沟通情况,通过这些原始材料,再一次证明了带“Vita”的100本就是为了缴给哥大以获取博士学位的,这100本书,在1926年底寄去美国之前,一直装在木箱里单独存放于亚东图书馆。
余英时根据胡适1920年9月4日和1922年2月23日的两条日记,推断出胡适之所以选择在1922年出版博士论文,是因为那时顾临和哥大校长巴特勒都希望他去哥大任教,他可以趁此机会“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9页。)陈通造又发现了两条证据,可证明余英时这个推论是正确的,不过,关于胡适去哥大任教的动议,比顾临和巴特勒给他写信还要更早。在拉里·希克曼编辑的《杜威往来书信集》里,有两封信提到此事。(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I-IV),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irginia,USA:InteLex Corporation,2009.该书信集为电子版,未标注页码。)第一封是1919年6月1—5日杜威夫人在北京写给美国孩子们的家信。胡适4月30日在上海码头迎接到杜威夫妇,几天后就爆发了五四運动。胡适5月8日离沪返京,到北京时蔡元培已辞职离京,于是胡适被推举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维持校务。杜威夫妇5月底到达北京,杜威夫人给自己的孩子们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从6月1日断断续续一直写到5日,信中介绍了北洋军警抓捕学生的情况:“大学变成了监狱……里面关押着发表演说、扰乱治安的学生。”她提到胡适整天为保护学生而奔忙,夜以继日地写信、给报纸写文章,随后她告诉孩子们:“胡适想要接替因夏德教授离开哥大而空缺的讲席,不是今年,而是下一年。他担心,如果他留在这里,这些政治骚乱会妨碍他对(学术)工作的专注,以至于丧失这一习惯。”
同年8月1日,杜威写信给哥大哲学系同事、1917年胡适博士口试的主试教授之一温德尔·布什(Wendell T.Bush,1866—1941),信中也谈到:“胡适在这里很有影响力,他编辑的周刊发行量达五千份,在这个国家是很大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刊物中发行量也是很大的。他和一些同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正在广泛开展……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部按现代历史脉络撰写的哲学史。但时局纷扰,占去了他太多时间,以至于无法专心学术,令他不堪其苦,他还是想多做研究和写作的工作。若是哥大请他做汉学教授——如果那个席位还空缺的话——我想他会接受,至少是一段时间。”
从杜威夫妇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应该是他们到北京后,看到正处于五四运动风暴中心的胡适无法专注于学术工作,便跟他谈起哥大汉学教授夏德已离任,空出汉学教授讲席之事,而胡适也有意接受这个讲席,但不是在1919年,而是在1920年以后。既然杜威来华3个月后就写信推荐胡适任哥大汉学教授,那么说他两年后回国还要再把“大修”改成“小修”,并免除胡适的“补考”,就只能是一种无稽之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胡适为何在接到巴特勒的邀请信仅仅十天之后,就给汪原放寄去了一部分《先秦名学史》的校对清样,二十天后又寄去了另一部分清样。那时是铅字排版,排字工人排印一本书要花很长时间,汪原放的信里已表明,商务印书馆印刷部“恐怕懒接这个生意”,是高梦旦批了条子才排上的,商务1922年3月中旬就已说定两个月可以出版,却还拖到11月才“先订出二三百册”,这说明《先秦名学史》的出版计划早就开始了,否则胡适不可能在3月3日就校对完一部分排版清样并寄还给汪原放。这自然是胡适为计划去哥大任教而准备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任哥大汉学教授是否必须有博士学位,但胡适只要提交100册出版的博士论文,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即使哥大对聘任教授有学位要求,胡适也能满足这一条件,那么,他在此时出版博士论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是胡适接到哥大校长巴特勒的邀请信后,却放弃了去哥大任教的想法。既然不去哥大,博士学位也就再次成为不急之务了。但博士论文已排好版,也不能不印,所以才有了他跟汪原放的那些书信沟通。至于书印好之后为何却没有立即寄往美国,从现有一切证据看,均未发现另有原因,那就只能解释为,胡适并没有为博士学位问题大费周章,如有机会再次赴美,可顺道回哥大领取学位,既然时机未到,那100本带“Vita”的论文就只好先存放在亚东图书馆。
根据以上证据,完全能够得出结论:胡适的博士学位之所以迟到十年,只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缓缴了十年,没有任何其他原因。陈通造给出的证据足以回答前文提到的种种质疑。
陈通造的论文发表后,仍有学者认为,只有找到哥大1917年胡适博士口试时有六位主试教授签字的专家意见书,才能最终为胡适博士学位案定谳。但哥大校友档案只有当事人直系亲属才有资格申请查阅,我曾多次跟胡适的嗣孙胡复联系,希望他能向哥大申请这份材料,可惜至今尚未能如愿。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使找到这份专家意见书,也只能更加完美地证明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毫无可疑之处。
最后,我想再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胡适博士学位案的看法。胡适在1944年10月7日的日记里说:
我因研究《水经注》大疑案,始悟中国向来的法堂审案的心理成见是不利于被告的。我作英文Note述此案重审的结果,我只须说:“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hat Tai Chen had seen or utilized the works of Chao & Chuan”(这句话意思是:“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戴震看过或使用过赵一清和全祖望的作品。”)就够了。但我写中文报告时,才感觉这种说法不够,——在中国人的心里,“空穴来风,必有所自”,故被告必须提出有力的反证,单驳斥原告所提证据是不够的。……“罪疑惟轻”,虽是比较文明的名言,但这还不够。“罪疑惟轻”等于说“证据不够,只宜从宽发落”。这个从宽发落的人终身不能洗刷他的冤枉,不能恢复他的名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97页。)
他1952年12月5日至6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治学方法》里又说:
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來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由心证”。(胡适:《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120页。)
胡适这两段话,虽然说的是中国和西方审案心理和证据法原则的不同,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的不同。传统思维是“有罪推定”,“罪疑惟轻”;现代思维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在中国法律早已充分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的今天,仍有一些人持“空穴来风,必有所自”的观念,自觉地站在控方立场,无论控方的证据是否站得住脚,都要求辩方必须百分之百地自证清白,只要他们觉得尚存一个疑点未被证明,便不自觉地做“有罪推定”。须知这种“有罪推定”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冤假错案的根源,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本文已给出充分证据证明了唐德刚等人的“指控”不实,他们提出的所有疑点,均已被证明毫无根据。若从“无罪推定”的原则出发,只要控方证据不足,就可以立即宣告嫌疑人“无罪”。本文虽已充分证明胡适博士学位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但我们仍主张取“无罪推定”的原则,来结束关于此案的所有纷争——因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否,正体现在对待此类原则的态度上。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前言”里讲过:“我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如无充分的理由,就不承认某一著作,也不引用某一已被认可的著作中的段落。”(胡适:《先秦名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3页。)后来他又多次讲过:“我必须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東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胡适:《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第119—120页。)他曾把这个原则归纳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是,通过有限证据来证明某个事实或原理成立与否,只要找到若干充分可信的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即可证明该事实或原理成立,反之则不成立。但不能反过来要求根据这一原则来证明某个事实或原理之“必无”,因为要证明其“必无”,则必须列举无穷的反证,而这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从事实上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举例论证属于归纳逻辑,而例证总是有限的,正如有限归纳不能用来证明无限原理,它也不能用来证明某个事实或原理之“必无”。
从“证据法”的角度看,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则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证据不足就只能宣告他无罪。而要证明一个人无罪,则不能要求他面对出于任何动机的质疑——包括诬告、诽谤、谣言、伪证、栽赃、构陷等,都必须提供百分之百的证据来自证清白。他所应该做的,仅仅是把控方证据驳倒,而不是面对无休无止的质疑时,都必须提供一切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因为这不符合有限证据和归纳逻辑的原则。应该受罚的是诬告、诽谤、作伪证者,而不是任由空穴来风的谣言毁掉一个无辜者的清誉。既然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控方证据完全不能成立,那就只能还他以清白,替他恢复名誉。
七、结论
本文回顾了“《先秦名学史》的版本、翻译和研究状况”,并对“《先秦名学史》是一本写什么的书?”“胡适为何要写《先秦名学史》?”“《先秦名学史》写得怎么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先秦名学史》并非一本纯粹的逻辑史研究专著,而是一本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的著作,它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两本性质不同的书,即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内容比它更丰富,它也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胡适之所以要写《先秦名学史》,既有现实因素对他的触动,更有学术自身的因素,哲学受它的方法制约,哲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方法论的发展,唯有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发现、发掘和发展出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才能避免“引起旧文化的消亡”,并找到与西方现代文化沟通的桥梁,才能打破“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中古遗产,引导中国哲学和科学走向现代化。《先秦名学史》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它很好地解决了它所提出的问题,胡适用西方“原因论”和“效果论”哲学方法来阐释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方法论,通过对先秦各家各派哲学方法的还原,充分揭示了哲学方法的发展是科学和哲学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篇具有极高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博士论文。本文最后两节回顾了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来龙去脉,通过充分可信的证据,证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案是一场冤假错案,并主张取“无罪推定”的原则,来为这一“学案”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