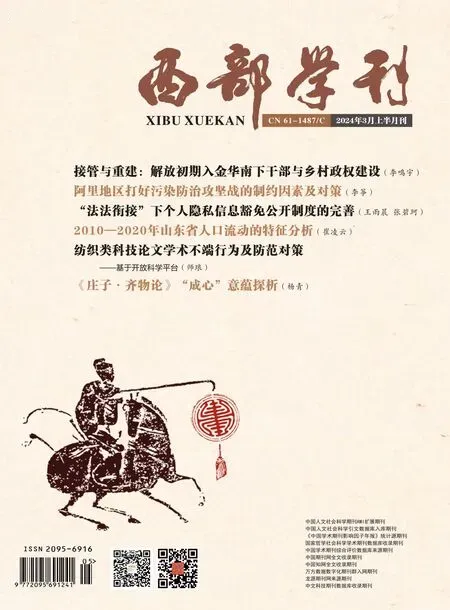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探究
叶 宁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福州 350003)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教育法治化得到极大完善。同时,随着全社会整体法治观念的提升,公民对于教育部门依法行政,教育相关组织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教育法律法规得到贯彻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育行政管理方式中的重要一环,教育行政处罚的规范化更是备受瞩目。
近年来,教育诉讼呈现多发趋势,特别是学生对于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学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做出的教育行政处罚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律途径救济。但诉讼实践中对于部分规范性文件设定的教育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存在诸多质疑,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类规范性文件是否有权设定教育行政处罚。2021年1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于行政处罚概念、种类和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完善。教育行政处罚制度的规范化应以《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为契机展开,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探究。
一、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界定
(一)设定权与行政处罚设定权
设定权是某个立法主体所享有的制定原创性法律规范的权力[1],是归属于立法权的一种。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从学理上看,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被称为行政处罚设定权。我国涉及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法律文件主要是《行政处罚法》,该法并未对行政处罚设定权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即何为行政处罚设定权,而是采取列举式方式对不同位阶的法律有权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范围进行规定。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是对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做出了全新的规定,明确了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归属。同时该法对行政处罚设定权进行了控制,在第十六条中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由此可见,我国对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是进行严格限制的。
(二)教育行政处罚
我国现有专门对教育行政处罚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是由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其在《行政处罚法》的基础上针对教育行政处罚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范,但该法对于教育行政处罚的概念并未进行法律上的界定。
对何为教育行政处罚进行界定不仅是明确其概念,也是在划定教育行政处罚的边界。在司法实务中,对于概念的模糊认知很容易导致法律适用的偏差。例如,在2015年审结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被诉案中,二审法院做出了“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做出的‘当次考试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的处罚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教育行政管理行为”的判决,并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判决书并未说明该处罚并非教育行政处罚而是教育行政管理行为的具体理由,不仅缺乏对当事人的说服力,对后续类似行政诉讼也缺乏借鉴意义。
现有对于教育行政处罚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于学术领域,我国对教育行政处罚概念并未进行法律上的确认。学理上将教育行政处罚界定为教育行政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依法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对其予以惩戒的行为[2]。这一概念描述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规定相呼应。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教政法〔2019〕17号),指出要加快修改《教育行政处罚办法》,夯实教育行政执法制度基础,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教育行政处罚的概念能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
(三)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根据我国法律对于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界定,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可以认为是在法律、法规、规章中,针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行为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教育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部分,其设定权的来源根据上位法的要求,应被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中。
二、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权力来源
(一)法律来源
依据权力来源不同,行政立法可以分为一般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一般授权立法即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直接根据《宪法》或有关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行为;特别授权立法则是依据特定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行政处罚设定权作为立法权的一种,在一般授权立法领域基于《行政处罚法》的列举式规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规定,且对不同位阶的法律所能设置的行政处罚种类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教育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定权需要依照《行政处罚法》的列举式规定,即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规定。我国现有教育相关法律,例如《教育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对于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均有相应的规定。《宪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教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共同构成了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权力来源。
(二)权力来源的限制
行政处罚作为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行为,其设定权被《行政处罚法》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有法律、法规、规章能够设定行政处罚,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进行设定。同时依据法律位阶的规范,下位法对于权力的限制不得超出上位法的授权[3]。《行政处罚法》依照此法理对不同位阶的法律所能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教育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定权的来源也应当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设定。不同位阶的教育法所能设定的教育行政处罚应当按照法律位阶效力规定受到相应约束。
(三)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实践
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内容并未由《行政处罚法》进行具体规定,而是散见于各个位阶的教育法律条文中。
我国教育立法之路自改革开放时期开启,现已经发展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为基本法,覆盖多位阶的法律法规的教育法律体系。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法,《教育法》对教育领域的行政处罚的种类以及适用情形在第九章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从法律这个位阶上对行政处罚进行了设定,同时授权部分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制定规范性文件设置行政处罚的权限。例如,在第二十九条中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了赋权“(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这就明确了赋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
在我国立法实践中,除了法律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教育行政处罚也有进行设定,例如教育部的多项部门规章就对教育行政处罚进行设定:《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应进行处罚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九条对作弊考生设置多项罚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校在《教育法》的授权下加入设定教育行政处罚的大军中,通过设定处罚来实现对教育教学的管理,例如北京大学制定的《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第四条“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悔改表现等,给予下列处分:(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研究生在考试中违纪、作弊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如下处分,同时,该门课程考试成绩以‘0’分计;……考试时,偷看、抄袭、与他人交换考试信息等构成作弊,以及其他严重违反考试纪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根据法律规定,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来源仅能为法律、法规、规章,且下位法的设定权不能超出上位法的授权。但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来源除了法律、法规、规章,还包含了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部分下位法的设定权超出上位法的授权,这就导致在教育行政处罚适用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下位法中的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合法性的质疑愈演愈烈。
三、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合法性分析
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法制框架中的司法救济是缺失的。但随着公民法制观念的觉醒,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行政主体地位、教育管理行为的可诉性得到确认,教育行政纠纷的数量逐步增加,对教育行政争议的关注点慢慢从具体案件向案件背后适用的教育法律法规本身转移。在教育行政纠纷案件中,对于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合法性争议主要集中在下位法能否超出授权设定教育行政处罚上。
(一)立法现状
我国教育法规范体系的基本框架虽已建成,数量也初具规模,但体系化程度仍然有待提升[4]。在我国教育行政处罚立法现状中,相关法律法规呈现“散”且“杂”的特点,位阶从法律至地方性法规均有涉及[5]。部分下位法呈现违反上位法授权,给自己增设行政处罚种类,使自己既是裁判者又是执行者的情况。这种情况明显有违“自己不能给自己授权”的法理。例如,作为部门规章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在第九条规定的教育行政处罚种类明显超出上位法《行政处罚法》的授权,从而导致在适用法律时会出现下位法抵触上位法的情况,这无疑会冲击我国法律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在2015年审结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被诉案中,涉案的多名当事人提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做出的“当次考试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的处罚决定不属于上位法《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这就将下位法是否有权创设新的教育行政处罚种类这一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二)诉讼实践
在诉讼实践中,此类纠纷频发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学校这一特殊主体,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教育行政管理行为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较为模糊的。学校管理过程中设定的罚则条款成了被诘问的重点,这就导致学校频繁地成为教育行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6]。学校在进行教育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会通过制定“校规”来明确自身以及学校师生的权利义务。为确保管理的有效性,“校规”中不可避免会设定一些处罚条款来实现对学校师生的管理,但这些处罚的合法性在学校师生权利意识发展的大背景下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因为这些处罚规定而权利受损的群体。
学校制定章程进行自主管理的行为是经《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授权的。虽然“校规”不属于我国法律的组成部分,但在学校的内部自治规则体系中,被视为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因此,在教育行政纠纷案件中,学校是依据此规定认定其制定的章程是属于内部管理规定,做出的处罚也是基于《教育法》授权的行为,因此“校规”中设定的处罚应当被认定为合法的。就教育行政诉讼的发展历程来看,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下简称“田永案”)到“甘露诉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以下简称“甘露案”),对于“校规”中罚则的质疑经历了从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到“校规”是否有权设定处罚规定的历程。经过“田永案”,学校处罚行为属于行政处罚已经得到确认,而“甘露案”则提出了“校规”设定的教育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不具备立法资格的。其只有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时,享有与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学校的“校规”在性质上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处罚法》限制性条款规定,“校规”不具备创设新的行政处罚的权力。
因此,不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校规”,其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但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遭到滥用的情况在各个层面“立法”实践中不断重复出现,这对于我国教育立法的规范化和体系化都提出了迫切要求。
四、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范化途径
在立法与司法的实践中,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都受到极大的质疑,这主要源于立法缺乏体系性以及对行政处罚设定的制约不足,使得行政处罚设定权无法在立法者所预想的框架中得到执行,这成为教育立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7]。我们应当以全面完善教育立法体系建设这一总体目标为出发点来对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范化进行讨论。
(一)增强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的系统性
我国教育领域立法数量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来不断增加,确立了一系列的教育制度,但由于教育覆盖领域较多,涉及教育管理的主体复杂,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呈现出较为碎片化的形态。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范化依赖于整体教育立法的体系化建设,需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教育法律体系来严格限制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运用,并且还需要相应配套的监督和救济机制来进行制约,使设定教育行政处罚的行为在法律框架中运行。
(二)限制设定教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位阶
教育行政处罚作为减损权益、增加义务的行为,在设定上需要进行严格限制,以免成为公权力滥用时的利刃。对于将公权力锁到笼子里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严格并明确限制能够设定教育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的位阶。根据司法实践中呈现的纠纷要点,很多行政处罚纠纷涉及的争议要点就是当事人认为处罚所适用法律的位阶违反上位法规定。为了确保立法质量和法律公信力,对于设定教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位阶进行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三)评估已设定的教育行政处罚
新《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评估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和必要性,对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事项及种类、罚款数额等,应当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这就确立了对于行政处罚的事后评估制度。利用这一制度可对现已设定的教育行政处罚进行事后评估。对发现教育行政处罚违反上位法规定或处罚不合理的,在法律层面无疑增加了一个救济途径。
——城市道路位阶值与位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