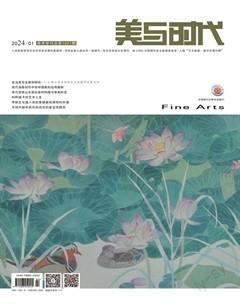岭南画派花鸟画写生观探析
摘 要:岭南画派作为20世纪国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其花鸟画创作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它的核心改革手段是在写生系统中建构了符合“折中”需求的写生观与方法。对此中西合璧的特殊观念的源流及结构性质做初步的分析,为岭南画派花鸟画学本体的学术建构进行有益补充,也为解决当下花鸟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关键词:岭南画派;中西合璧;写生系统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美术学院学术提升计划课题“岭南花鸟画的写生方法研究”(20xsc41)研究成果。
一、岭南画派花鸟写生观溯源
崛起于20世纪初南粤大地的岭南画派,其领军人物是广东籍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他们提出了“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倡导兼工带写、彩墨并重的艺术手法,在充满社会变革的激烈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与海派和京派并立,分别导引了当时中国画改革的不同方向。其中,写生是岭南画派绘画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它已经成为岭南画家创作的自觉前奏。岭南画派第一代画家多以花鸟见长,他们的写生观可以追溯到高剑父的先师居廉和居巢,具体表现为重视古法,通过日积月累的观察与体悟去通晓物性,熟察物理,并结合画理综合构建形象。其写生要领是重视对象的感知层面的提炼与物象通识及常形的结合,以及在这种结合过程中水与粉的灵动运用。此法在岭南画派二代不断变化的风格中始终贯穿,从画理层面支撑了学术的传承,使其在内部多元的风格取向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结构稳定性。此外,岭南画派对写生的看重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受到了当时地域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花鸟画写生是围绕着物象之“生意”展开的“师造化”活动。所谓的“生意”包含生命的实体状态、情感化的生命意象之表征与笔墨语言三个层面的意义。它们是与生命的特征形成通感的视觉感知,且通过递进实现:自然“生意”通过写生流向绘画,笔墨层面的“生意”则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并指向绘画作品中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因此,“生意”这一概念既存在于主体向外界索求的表象世界中,也存在于固有的审美经验里。传统写生观对生意的追求也是一步步由自然对象走向笔墨趣味的,而这个流变过程也促成了中国画的审美取向从早期的形神兼备发展出不求形似的逸笔草草。因此,传统写生观的目标在“形”与“意”的区间徘徊,涌现出了众多独具特色的画派和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传递出生机、生意,展现了中国画的丰富多样性和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
岭南画派的花鸟写生在画理上赓续了传统写生观追求“形”“意”协调、捕捉自然生意的总体目标,在造型方式上又与传统有所区别,这种差异也从技法上确立了岭南画派的风格特征。随着高剑父、陈树人等画学先锋留学日本所获得的写实训练植入写生,岭南画派基本审美趣味和创作方法逐渐定型与完备。可以说,岭南画派花鸟画的写生观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写生观念的形成也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恽南田写生观
恽南田继承了徐崇嗣“没骨”写生法,结合自己对自然形象形成的境界理解,高扬“造化在我”的思想,强调了深入观察自然、洞察生命的重要性,将写生的内涵与影响再度拓宽增强,震烁后世。后来的“二居”及岭南画派的写生理念皆延续于此。其写生观有两层含义,一为承载和发展黄筌一派的画法,二为作画中表现出的自然状态。而不用勾勒的没骨正是实现第二种理解的具体手段:既能造物成形,又可以信笔点写,在笔墨与形象、胸臆与真实间自由转换。如此宽泛而广博的表达空间给予画家极大的自由度,为岭南画派结合西方写实造型的手段提供了画理上的支持。
对于写生,恽南田有着与前人不同的理解。他提出的“摄情”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田画跋》中这样描述:“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以古意写心境、借物喻情等传统文化中的情感投射机制被他熟稔地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通过物象姿态、题款的内容、设色等图式语言综合表达出来。恽南田的这种“摄情”理论,其本质是在文人画的催化下,写生行为更多地注入主体情思的影响,强化创作者的主观意志,不仅拓宽了画作的表现空间,也丰富了画家的创作手法。
恽南田从技法到绘画观念对花鸟画写生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对晚清的“二居”影响深远。在流寓广西期间,二人汲取孟觐乙、宋光宝绘画之养分,以写生为本,开创撞水撞粉法,形成“二居”独特的岭南风格。
(二)“二居”写生经验
居巢和居廉都是19世纪广东地區的杰出花鸟画家,在宋光宝、孟觐乙处习得设色细腻一派的恽氏没骨写生技法,又兼修陈栝笔意,后期于可园及十香园作画收徒,影响遍及岭南地区数十年。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曾拜居廉为师,所习不止于撞水撞粉的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于写生的认识。高剑父曾经评其师居廉的写生方法为:“非古非今,洗脱畦径。”所谓“非古非今”既含有“法”从造化中来之意,与石涛的“法无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暗示了居廉对写生对象的观察方法有独到之处。至于方法,通过接下来的描述可以管窥:“师写昆虫时,每将昆虫以针插腹部,或蓄诸玻璃箱,对之描写。画毕则以类似剥制的方法,以针钉于另一个玻璃箱内,一如今日的昆虫标本,仍时时观摩。复于豆棚瓜架,花间草上,细察昆虫的状态。”从中可以看出,居廉在花鸟写生过程中,非常注重对物体形态的准确把握,运用了一些博物学手段去获得物象的结构信息,与传统拉开了距离。当然,他也强调自身感受与情趣的表达,通过观察和体验,理解和把握物体的本质特征和生命状态,然后将这些感受和理解转化为画面上的艺术表现。
“二居”的写生经验从对写生对象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到准确把握物体形态和神韵,为高剑父和陈树人提供了一种范式。具体来说,“二居”在写生时特别强调对所绘场景的真实还原,以“体物入微”的笔法去细致生动地刻画形象,以写实态度去尊重对象的客观化特征,并呈现出在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感。为了实现这样的创作目标,他们可能采取了长时间观察物象以获得习性的手段。相较于恽南田而言,“二居”的写生对自然本身的结构与情趣观照多过于传统审美中心灵化的体验,这样的写生态度也更贴合西方绘画中的科学精神,为后期岭南画派的革新埋下了伏笔。
“二居”的写生经验以及手法,借由“二高一陈”对岭南画派的影响,进入岭南画派花鸟写生的实践中。他们“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理念以及对写生、寓兴、写意等传统技法的现代演绎,使得岭南画派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岭南花鸟画的写生观念突破
(一)写生目的与观念的转化
1.写生目的的改变
岭南画派对中国画的革新是从观念开始的,而当时的发展主线也是“从‘文人画向‘画人文转换”。这就意味着从董其昌以后的文人传统正在被有意识地打破,西式实物写生成为一种武器去对抗中国画传承中摹古的积习,甚至文人“目识心记”式的“心观”系统在新国画运动中遭到攻击。蔡元培就疾呼:“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两种希望,即多作实物写生及持之以恒是也。”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推动下,文艺界对西学思想尤为重视,作为革新前沿的岭南画派自然也当仁不让地转化了写生的目的:传统文人绘画体物之道是强调主体、绘画与自身的关系,而现在更多地将绘画表达转向主题或意义的传达。写生从对自然的观照转化成解决创作问题(革新)的一种探索路径。它拥有明确的目的与方向,针对新的对象或表达需要所涌现出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写生去分析尝试。
2.写生观念的转化
宋以后,传统花鸟画的写生观逐渐成型,其中识物、体物与造物的方法深受理学格物思想的影响。从《礼记·大学》的“物格而后知至”到朱熹的“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格物致知的方法明确为对万事万物存理的考察与体证。这种带有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进入绘画后,于宋代画院开枝散叶。南宋邓椿在《画继》里记录了宋徽宗熟知“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以及“众史骇服”的故事。可见,通过长期观察将对象行为方式与规律总结成形象在画中表现的行为,是“格物”的关键。对“物理”的苛求带来的形象的精准与描绘的细致,形成了院体绘画的造型观念。
岭南花鸟画写生观念的突破与格物观念的转化有关,主要体现为将格物中对物理的执着与日本博物画中的科学写实主义相结合。显然二者在对待自然形象的理性思考与探究层面是有相通之处的,这种特质也使融合与转化更加顺理成章。高剑父在日本留学交流期间辗转于昆虫研究所、太平洋画会等机构,接触了大量的博物画和标本画;同时做了很多的标本画临摹,对很多昆虫的正侧器官及结构详细准确地进行描绘。这样的记录方式深深影响了其后期的写生。在1930年前后于尼泊尔的写生中,高剑父面对昆虫的形态依然采取了分类学的解剖视点与图文记录的组合方式,有明显的科学博物性质。
在传统的中国画中,画家们往往通过感性与长期记忆观察自然景物来获得形象,借此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然而,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准确地表现出物体的真实形态和结构。因此,通过对日本博物画及西式写生中的解剖学、透视学、光学等知识的学习,岭南画家们重新建构了写生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通过对物体内部结构和形态的深入研究,来更准确地描绘出物体的真实面貌。当然,他们并未抛弃传统花卉写生的基本原则,在注重西法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国画中对自然界观察和体证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高剑父的这种写生方式在岭南画派中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方法本身,而是通过其“折中”理念延展成一种科学观察与记录的写生观,从而为岭南各家所接受和承袭。
(二)西方式对景作画的融入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的“对景作画”并非是西式写生的特有,因为传统中国画的写生中也出现过直接或间接的对景作画的行为。如《旧唐书·阎立本传》中提及阎立本写真之事:“太宗嘗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唐朝名画录》记载边鸾入殿当场写生:“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浑灼……”但即使如此,在面对实物之时,中国传统的花鸟写生也非定于一个视点完成造型,否则边鸾就无法画出动态的孔雀“一正一背”之姿,最终呈现的效果也并非西画的模仿写实,而是求生动之意。然而更多的时候,造型的过程是在间接写生中得以完成的。其大概步骤为先四面观察对象,并于需要之处做粉本记录,之后便移于室内进一步提炼加工完成形态塑造。
西画对景写生却要求固定的地点,固定光源,对景刻画。如此即时性的作画方式所求的是物象在连续时空中的一个片段记录,对画家手眼模仿的要求与传统不同。因此,陈树人在《真相画报》中连载的《新画法》曾提出“眼之教育”“即写”“习作”等训练手段,以达成一种中西合璧的写生模式,试图通过加入西式即时对景作画的环节去实践“折中中西”的效果。
岭南画派这种强调对景作画来获得视觉经验的写生方式,为当时的中国画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画家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在传统经验中未被开发的区域,也正好契合了当时关注现实的创作思潮。当然,在绘画语言探寻与选择上,岭南画派的先驱们牢牢守住了传统笔墨的底线,在写实的造型中大量运用了中国画中笔墨的意识和方法,守住了中国画的底色,也体现了其“折中”的思想。
三、结语
传统花鸟画写生从“目识心记”训练中获得物象,形成长期理解或情感链接,最后用记忆获得大量的形象构建特征及符号,为后期的以心造物、随心造型创造条件。而西式即时性对景写生可以第一时间捕捉新鲜的感受与素材,通过重新审视对象获得更多细节和大量与传统相异的图像经验,这显然是力求革新的岭南画派前驱者们所急需的。
岭南花鸟画的写生将两种方法融为一炉,以此打开了传统花鸟画革新的通道,为20世纪初新旧相交、思想激荡的中国画坛构筑了一道耀眼风景。这种中西结合的写生方式至今依然影响着南粤及海外的一众画家群体。在中国画发展依然面对多元路口的今天,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重温花鸟画写生观在关键节点上所经历的变化,权衡其利弊,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薛永年,赵银邦.写生的传统与当下的意义:中国美术太行论坛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2]高剑父.新国画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3]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刘煜,博士,广州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