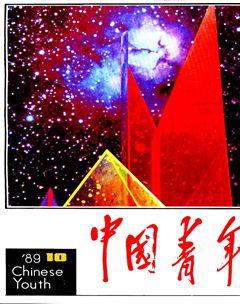青年监察官
成晓明
北京。花园北路35号。这儿坐落着一个令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寝食不安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也许有个别人自恃后台硬,暂时还不把它放在眼里,不过,走着瞧)。
乍一走进监察部,我多少有点失望。除了更简陋以外,它和其它机关没什么两样。一间间鸽子笼似的办公室,人们进进出出,抄写文件,打电话。然而当我了解到,这里的每一间鸽子笼,都在密切监督着数省或若干部委官员的行为;每一阵急切作响的电话铃,每一个签发的文件,也许都会唤起一片片党心民心的欢腾雀跃,我不禁肃然起敬。我的脑荧屏上,不时恶作剧地闪出几个大字:肃静!回避!
数以百计的人们在这儿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监察部成立两年多来,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已经承办和督办了上万件有关政府官员及全民所有制企事业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许多记者曾经来过这儿,试图挖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但这里纪律森严,他们无法撬开监察官坚硬的嘴巴。
我很荣幸地被接受采访。这是因为,一,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我的采访目的是去发现每一个年轻的灵魂,而不是别的。二,即便我偶尔听到了有关重大案件的只鳞片爪,我也是严格遵守新闻纪律的。
这年头,守纪律的人不能总是吃亏。
我的采访方法很笨。采访青年人时,为了套近乎,总是装得像大人物关心群众生活那样,首先问:“收入怎么样?过得不错吧?”在采访青年监察官陈银书时,我很后悔提了这个问题。
他惨然一笑,沉默好一会儿。
“我家在偏僻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按理讲,农民的儿子考进北大法律系,又在监察部这样的大机关工作,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一种负疚感时时噬咬我的心。我家弟兄多,生活很艰难。父母亲供我上中学上大学,吃了很多苦。我离家去北京的那天,望着父母满是皱纹和泪水的脸,暗自发誓,将来一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现在只有百把元收入,想尽孝心,又无能为力。父亲来北京看我,我都没脸见他。”
陈银书的眼圈红了,噪音有些哽咽。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对面,找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心里一个劲感慨。我们的监察官生活太清苦了。监察部一位副部长戏言说,国家机关是清水衙门,监察部是蒸馏水衙门。没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奖金少得羞于出口。莫非蒸馏水能把灵魂洗得更干净?
陈银书似乎对自己感情外溢有些不满,苦笑着摇摇头。“我曾想离开这里。有位学法律的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公司,当律师。我心动了。每月起码有200元啊。这样我就可以接济父母。我这算的是小账。算算大账就不想走了。我们每年查处的经济案件,动辄几万几十万!能给国家挽回多少损失?忠孝不能两全。青年人不能忘记对国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行政监察,让违法乱纪的官员为所欲为,国家就没有指望,我们的家庭也没有指望。说句实话,没有国家的培养,我现在还不是刨土坷垃吗?有人说我们是打手,把我们的工作等同于文革时期的专案组,好糊涂。如果惩治腐败的人被称作打手,我情愿当一辈子人民的打手!”
这位“人民的打手”承认,起初他和许多北大学生一样,都有那么一点“狂劲儿”。1984年毕业,他分到中纪委工作。有一天,中纪委领导下令他所在的部门抽人去办案。部门领导人拿着电话为难地说:“我们没有人。”这时,陈银书和三位大学毕业生就在办公室里。啊,我们不算人?陈银书全身的血往头顶上涌。他想,我要办个案子让他们瞧一瞧。
一出门就连连砸锅。在调查武汉市的一件案子时,没等讲明来意,年少气盛的他就厉声责问武汉市长,双方争执起来。结果案子办得很不顺利。领导狠狠批评了他。还是在湖北,他接到一个处级干部控告地委书记打击报复的申诉,立即拍案而起,主张严惩那位地委书记。老同志不露声色,拍拍他的肩,“走,下去调查去。”他们调查了一个月,所谓打击报复其实是一个误会。
在中纪委的这两件事对他教训很深。青年人单凭热情和正义感,十次有九次要栽跟头。作为一名监察官,谨慎、认真和生命一样重要。
去年10月,《人民日报》披露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走私、倒卖汽车案。中央领导批示:尽快查处。监察部由部长挂帅,司长亲自带队,会同有关部委组成调查组,进驻长沙。此案十分复杂,牵涉400多辆汽车、几个省、100多个党政军机关。加上有一些省部级官员出面说情,更使办案困难重重。
陈银书分管的案情涉及某重要机关。这家机关涉嫌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偷运小轿车。为了早日查清案情,他一天到晚忙着取证,找人谈话,翻阅一大摞一大摞的材料。几天过去了,案情仍然没有进展。虽然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火急火燎。吃不下,睡不香,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梦见的都是汽车。有人劝他说,这家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一致证明被查扣的车体和车壳是两个单位分别买的,用于汽车维修,不属于化整为零的问题,你何必还死抠呢。难道你不相信领导的证明材料吗?陈银书固执地说:“我更相信事实。”为了不让一个细小的疑点滑过去,他继续开展调查。白天找人谈话,晚上抱着一大摞材料,一页页查看,一句句推敲,终于从一位司机偶尔泄露的一句话中发现了破绽。司机说,他在南宁看到运载小轿车车体和车壳的三辆卡车在一起。既然两家买车,车体是深圳买的,车壳是南宁买的,为什么运载车体的卡车舍近求远,去南宁和无关的卡车碰头呢?陈银书顺着这个线索摸下去,又发现了一连串的重要证据。
后来,经有关方面继续调查核实,那家机关承认了违反国家政策,化整为零偷运轿车的错误。
谨慎,认真,给监察官带来了困顿和烦恼,也带来了更多的喜悦。
我有一位团委书记的朋友建议我去采访一下青年监察官杨一明。“那算一个人物。这小子把洛阳搅得天翻地覆呢。”
他给我讲了杨一明的一段故事。
当监察部派员督察洛阳市个别违法乱纪官员的消息传开后,洛阳的老百姓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央体察民情,忧的是来人是谁?后台硬不硬?后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来人姓杨,并很有可能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老百姓的心里开始高兴,而前一段利令智昏的官员们心里开始发毛(杨一明后来听说这种传闻,他说他感到悲哀,中国太需要法治了)。
洛阳市公安局长起初也吃了一惊。他曾直接或间接指使部下偷运和倒卖了50多辆汽车。显然,杨一明来洛阳,他首当其冲。他不愧是干了近40年的老局长,当他得知对手的底细时,很快恢复了往日的镇静和威严。杨一明哪是什么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干监察工作还不到一年,原来不过是个团委书记。团委书记,不就是领着娃娃蹦蹦跳跳,收集树种,采草籽吗?他深信,名噪河南的他决不会败在这位小青年手下。他呵斥那些愁眉苦脸的部下:“慌什么?挺起腰杆!”
公安局长坐在办公室里,设想着杨一明和调查组怎样上门找他谈话,他怎么样痛哭流涕,将主要事实蒙混过去,怎样发誓“下不为例”,然后怎样破涕为笑,把调查组带进酒楼……这些年,调查组他见得多了!
三天过去了。他有点发慌。调查组为什么不找他?杨一明这三天在干什么?一连串的坏消息传来了:“杨一明直接去市政府,咱们那辆蓝鸟露馅了!”“杨一明把一个分局长叫去谈话了!”“下午6时,一个身分不明的人,独自来到×科仓库,掏出小本记车牌号码。有人认出,他就是杨一明。”公安局长有点坐不住了。原来他们向中央某部门检讨说,他们只买了两辆车,纯属为了改善装备,只是资金使用不当。假如其它的车辆被发现,那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第四天,杨一明和调查组突然来到公安局。公安局长赶紧上前,“杨一明同志,我想找你汇报工作。”杨一明客客气气地说:“不必了。局长同志,我对你提点要求。一端正态度。二积极配合。三马上开列干部花名册。我要找人谈话。叫到谁,谁马上就得到。四积极思考自己的问题。”
公安局长这才领略到,原团委书记并非只会采草籽。他故意不找我谈话,是想先扫清外围,取得证据,他拒绝我汇报工作,实际上是不让我探口风。走着瞧!
公安局长的堡垒确实很难攻破。他当了多年局长,编织了一张法力无边的关系网。连省里都有人为他说话。他恩威并用,洛阳公安局的干警,哪个不怕他三分?杨一明和调查组用了一个上午,找了40多人谈话,听到的只是40个不同声调、不同音量的“不知道”。
中午,公安局长关切地询问“要不要用饭”。他的微笑中,暗含几丝嘲讽。杨一明心里恨恨地说:“我就不相信你是铁板一块!”下午,杨一明改变了战术,不再追问汽车,而是拉起家常。他从日常起居,一直讲到目前党中央下决心惩治腐败,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如何。终于,有一个同志怯生生地问:“你们不会马上走吧?”杨一明斩钉截铁地回答:“洛阳的案子不查清,我们决不离开洛阳!如果有人打击报复,你可以告到监察部。”说着,他扯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下监察部的地址和电话,递到那位同志手中。
那位同志把纸片小心翼翼地装好。“我可以走了吗?”
他还是没开口。杨一明有点沮丧。不过,那位同志临出门向他递了一个眼神。杨一明觉得这个眼神可非同一般。
当夜12点,有个匿名电话打来,让杨一明在某公园的第几根电线杆下等候,有要事相告。杨一明如约赶到。只见一个黑影从树丛中闪出,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上前低声说:“公安局一共倒买倒卖50多辆车。局长开始只让承认2台。你们又查出4台,他们又在订立攻守同盟,只承认6台。现在东南郊仓库里,还藏有20多辆没卖掉的车……”来人说完,紧紧握了一下杨一明的手,匆匆消失在树丛中。
杨一明赶回驻地,得意地对大伙说:“相信群众相信党,没错!”
第二天,调查组的汽车直奔郊区仓库。洛阳市公安局利用警车参与非法购车的案件真相大白。《人民日报》几天之后,刊登了洛阳市公安局长被撤职的消息。这天的《人民日报》在洛阳被抢购一空,堪称洛阳纸贵。老百姓走上街头,鸣放鞭炮。多少年了,这位局长依仗权势,专横跋扈,人民终于把他扳倒了!
据说,在他下台前夕,对部下大发雷霆:“饭桶,怎么搞的让监察部发现了证据?我要是还当局长,就提拔杨一明这样的人当侦察员!”
听完朋友讲的故事,我对杨一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征得监察部有关部门同意后,我星夜赶赴洛阳。
在洛阳市委招待所,我见到了杨一明。他小个子,四川人,说话很急,带着辣味。我对他讲起有关他的故事,他笑了,手一摆,“别听他们瞎吹。没有老同志的指教,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与人民的支持,我算啥?一个小萝卜头!过去当团委书记,感到青年工作很难搞。一开形势教育会,青年就发牢骚。青年虽然有偏激之处,但你不能讲他们的牢骚没有道理。有的领导干部硬是不像话!贪图个人享受,把中央的政策法令当耳旁风,不管不问老百姓的疾苦,活活把党的形象搞坏了。格老子!我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所以监察部调干部,我二话没说,干!”
他蓦地从沙发上站起,两手比划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们的人民真好啊。干了一年多监察工作,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刚来洛阳办案,总发现有人跟在我后面。我很奇怪,一问,原来是有的群众暗中保护我,怕我遭暗算。前不久动乱波及洛阳,许多老百姓要我住在他们家里,以防不测。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啊。你要是早来几天就好了。前几天,*,”他指着我坐的沙发。“就在你坐的这沙发上,司法机关逮捕了洛阳轴承厂的保卫处长。这个保卫处长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财产,作恶多端。轴承厂的工人不怕打击报复,到处告他。就在逮捕他那天,轴承厂的工人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放起鞭炮,扯起横幅。横幅上写着:感谢共产党。我感动极了,真想哭。人民真好。我们为人民做得太少太少啊。”
杨一明感慨不尽。
在监察部采访的最后一天,我碰到了青年监察官宁延令。他总是笑眯眯的,一副永远也不会发火的样子。他原来也是个团委书记,见面就称我是“娘家人”,端茶递水,很热情。我们用不着客套,一下子海阔天空聊起来。
我们聊起了他的本行,廉政建设。我深有感触地和他谈起这样一件事:
由于经济调整,某大型建设工程下马了。数万名建设者无活可干,靠75%工资艰难度日。有一位老工人因为无钱为女儿筹措学费,四处借贷又告无门,寻了短见。这位老工人30多年参与了许多国内著名工程的建设,却从他亲手参加建成的大坝上跳了下去。国家了解到工人的困难,拨了一部分贷款。可是掌握贷款权的某高级机关,居然向这个施工单位索要物品,作为贷款条件。工人们愤愤不平。
“你说,这些人还有良心吗?”宁延令几乎是吼了一声。“党号召领导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这些人居然公然损坏党的声誉!”
我突然发现,笑眯眯的宁延令也会发火。
我请他谈谈监察干部的苦恼。
“主要的苦恼是人们不理解我们,以为我们是专门整人的。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我们是不是专门整人?”
今年3月,宁延令所在的部门受理了揭发国家机关某局领导干部贪污的案件。案件很复杂。揭发人声称手中有确凿证据,一些痛恨腐败现象的老同志也支持他。而局领导则大喊冤枉。官司拖了好几年没解决。
宁延令他们组成了调查组,进驻该机关。起初,局领导对监察部门有偏见,以为是来整他们,以种种借口不配合调查工作,宁延令他们虽然憋着一肚子气,但他们本着对事实负责,对干部负责的精神,不辞劳苦,用了几十天时间,找上百人谈话,翻阅了几百份材料,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终于将事实真相搞清。原来,该局领导根本不存在什么贪污问题,只是在个别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有点不妥。
当调查结果宣布后,该局领导热泪盈眶,负疚不已。好几年了,说不清道不白的黑锅,终于从肩头卸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还有什么比廉洁奉公更要紧的呢?还有什么比人民的信任更宝贵呢?
通过处理该局的案件,许多人改变了对监察部的偏见。
宁延令还在不断地倒“苦水”。“我们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办案缺乏法律保障和手段。我们的监察对象,都是领导干部,有个别人接受贿赂的手法相当高明。有的案子明明有重大嫌疑,我们只能用谈话方式取证。去年《人民日报》报道了秦皇岛倒煤的新闻。咳,里面猫儿匿大了。我参加处理了一家公司的经理。他一分钱也没有,居然利用收交煤款的时间差,倒卖煤炭,两天就赚了十几万。假如他没有用行贿手段,从哪搞的计划内车皮呢?我们没有必要手段,只拍了小苍蝇,眼睁睁看着大老虎溜走了。真是恨得牙痒啊。假如我们具备一定手段,我们监察部门一定会令那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
他的牢骚发得如此回肠荡气,我深深感动了。我握住他的手,半晌无语,只是心底在喊:“人民监察官,人们在期待你们,青年在期待你们。珍重呵!”(图: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