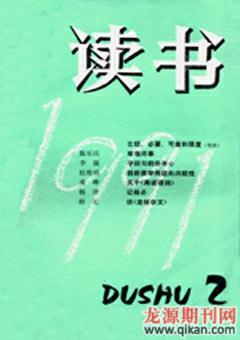关于《再话语词》
桑 晔
和王蒙先生抬杠
日前收到朋友寄下的一份复印件,印的是篇《再话语词》,王蒙先生的近作,原刊在三联书店今年九月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那朋友是位对北京时下的俗词俚谚运用自如的番鬼佬,感觉王蒙先生文章所云和他所知颇有不同,于是猜我可能感兴趣,“寄上供你阅毕一气”。
王蒙先生是我尊敬的作家,尊敬的原因之一是以他的身份曾提倡并希望当代的中国作家们学者化,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不妨潜心研究些学术。辛克莱是特别主张“作家过双重生活”的,但他所看重的另一重似乎是平民生活,除了创造和流通“精神”,还要参与物质文明的制造和流通,比方折腾他自己的旅馆生意。按一般的逻辑,辛克莱这种带有强烈的“到工农中去”色彩的论点,会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中引起反感才是;现实则相反,不少作家朋友到“流通领域”去实践“两个文明一手抓”,开公司开破了产。待到王蒙先生任文化部长,重蹈巴尔扎克旧辙,用写《人间喜剧》赚的钱清理“劝兴实业”欠下的满屁股烂账者,不仅有开“十年文学新潮”先河者,更有从延安时期就写作的老文艺战士。如此情势,由王蒙倡作家去学者化,实在是有反潮流精神的善举;尤其是在作家欠了“实体”的债 或“实体”蒙了作家钱都不一定还的时候。“诸位非要玩几点儿什么 才过瘾,这倒是条路子”,以小人之心度王蒙先生之腹,我从字缝 儿里看出这句。也可能我理解歪了,那就算歪打正着吧。
话本,大约是《豆棚闲话》中有句醒世之言说:“文不测字,武 不舂米”。除去迷信和胡说,测字很有文字学的内容,通小学的王 监生当街看相兼营勘阴宅阳居,恐怕就是知道这活计的自由度和发挥想象的余地比拆砌勘溯自己所穷通的字大得多;而杨志宁肯,也只有卖刀,是晓得精于技击不等于使得来夯力。所以,作为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的王蒙先生替语词释义,即使有比较多可以争议的地方,也不惹任何人生气,除非那气早在文章之外运着。因此,我相信王蒙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不会有气,贵我双方的争端所在不过是几个字。为几个俗言俚字写文章,至少王蒙先生是猜得出我这很没脾气,很没车找辙的德性样几。
帅 王蒙先生认为这个“五十年前在北京(北平)流行,现不流行有潇洒、利落亦含行时之意”的词“疑来自英语smart,否则实难解释”。难的原因是“我国古人不但不可能有帅的语词,也不可能有帅的观念”。
那么,我们在替这个俚词添文字表记时,何不用“率”字?若此,至少能对《后汉书》的“一方表率”,《西湖佳话》那“率着时尚的风习”,甚或元曲里“率率的把雕翎稳扣”的舞台丰彩产生联想。实际上,五十年前出版的《国语词典》中,此字即作“率”——“率,谓装饰轻俏,如‘打扮的真率呀。”这本初版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的词书,最大特点是广收北京话词汇,虽因政治原因在几度重印时产生了《国语词典》和《汉语词典》两种封面,内容还是一个(仅一九六七年中华书局版有简本),属常见的工具书之一。不大常见的,例如小鼻子和大鼻子在中国领土打人家的“日俄战争”时京都所印的《北京官话》,此字亦写成“率”。说是“这位爷,人样儿可真率。”由此,我们也能知道在百十年前的北京,“率”已不很冷僻,有心的日本鬼子听过几回的。用“帅”也未必就不行。老北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靠着听《水浒》看《穆桂英挂帅》了解历史,丰富见识,诸位把大赞扯着或插着帅旗儿的潇洒,俐落者“真他妈的帅”大而化之并推而广之并非不可能。由“扮相要帅气”发展百多年到“您可够帅的”,真不难。
盖 王蒙先生说是“八十年代的词”。
如果这“八十年代”是指本世纪八十年代,显然不对头。“盖”可不是新玩艺儿,《前汉书平话》是流行有不多年的话本,那说话人夸略输文采的刘邦“乃是盖代之雄”。倘若嫌这个太文,不足证明已走入流行口语,还是前述的《国语词典》,“盖”字的例句有“他的武艺把别人都盖下去了”,可见本世纪三十年代不是没这俚词挂在老北京嘴边儿。《儒林外史》是以其口语化被后来的文学语言批评家赞赏的古典小说,那里面的“盖”字用得极传神:权勿用撞了街道厅老魏的轿,老魏要锁了他审;张铁臂说这人可整不得,是娄中堂儿子的客;老魏便将就着“盖”了个喧,扯几句淡走了。虽然权本位,也到底是权本位,“一般干部”与“高干子弟”的哥们儿讲和圆场,好歹是“盖”个喧,气势终竟高着一截。顺便说一句,写这部书的吴敬梓先生一生未出仕,贫穷缩短了他和社会下层的距离,于是有“灌夫骂座之气”,“盖了帽儿啦”。似乎这“盖了帽儿啦”很令人费解,土得不行,其实正相反。盖是超乎其上,“盖了帽啦的是伞,镇着伞的是匾”,这句以没脾气的无奈嘲弄官本位的童谚可以被人忘了,“盖”,“伞”互见却是一般的词典都有的。没有“盖,通伞”词条,那词书不会比《新华字典》厚多少。对不起,说了错了,一九七九年版《新华字典》里也有这一说儿。
野 王蒙先生认为“亦是新词,却又令人特别是胆小如笔者生畏。因为常常用作‘路子野。”那么,“谁知道这样的人背后有什么‘猫匿呢?猫匿是指一种不大光明正大的手脚,如猫之便溺后,轻轻用土盖上,倒也不含犯罪,无法无天之意。”
吴语中的“野”和“很”通,是很大,很广等词的“很”在吴方言的表记,很不足畏。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它在何时进京,何时流行北地的问题。旧京人好听书,有部“粉词儿”,也就是涉嫌“扫黄对象”的书叫《海上花列传》,上面说倪如的心思重得“野”,您得当心点儿。《国语词典》收字是以“普通适用为标准”,“野”下有“天冷野了”,虽不如“路子野”干脆,到底有。至于“猫匿”,有的书上称“猫儿溺”,说是阿拉伯语“内容”之音转,俗用指“隐私”。如此书有据,“猫儿溺”,确无犯罪之意,番鬼佬也再不能说中国人没“隐私”概念,中国的privacy观叫“猫儿溺”,从西亚进口的“人权二手货”。
聊 王蒙先生讲“笔者幼时还听过一种有点不雅的歇后语—‘二郎神的××,神聊,可见聊音与《水浒传》上的‘鸟音相通。蒲松龄的名著叫《聊斋》,出处为何,是否与京人用法相同,幸有方家教之”。
“聊”字和“鸟”字根本不相通,音不通,义不通,两码事。那歇后语是“二郎神的××,神×”。这前面的××是“鸡八”,后面的×是——为了说明问题,只好违背“精神文明”一回啦。“ ”与“聊”音通,和专指女性生殖器的“ ”一道,被“新华”×掉了。大概因看“”跟“聊”音儿一样,才有了比“夜壶戴草帽儿,盖没影儿了”稍复杂的,如同“门头沟的核桃,满仁(人)”般的谐音转借,讽人口若悬河。歇后语除了谐音转借,也有象形会意,比方“王八大翻身,您就美吧”。把“羊大为美”这有违字源的说法发展成更邪性的“王八大翻身”,老北京真不笨。说到《聊斋志异》,在下并无研究,只记得这书开宗明义的段子有“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既然众人听厌了人语,不妨听点儿鬼话。那么,我猜蒲松龄先生的“聊”可能和此字的本意一样,是“姑且”。京人亦有此用法,“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是十余年前人人学过的“最高指示”。真正吃了文明亏的是我小时尚流行的“你这人没××味儿”,没××味儿,不够男子汉了,没种。干净的结果是好些人忘了这话,好些人忘了就一定有作家往书里写,写成个“没寮子味儿”,寮是僧舍,您是说没和尚味儿还是没和尚宿舍味儿,猜不透。上海话的“拉”亦如是,干净成“拉皮条”,众位识文断字者有了瞎注释的缝儿。
说山 抡或擂砍 王蒙先生将这四个俚词分三组说,我把它们并在一道,原文则不引了。
为啥“说山”,是因为《山海经》。这本很文又很怪力乱神的书不在说话人那“演义四十话本其半”(其实话本中的《宣和遗事》、《三藏取经》之类因敌不过演义的“正书”亦鲜有人说),但是源此书的段子一直存在,老北京把听这种不是正书的神吹海聊叫“听说山的”,然后大而化入生活了吧。“砍大山”的大山,恐亦源此——说话人替中国建设了太多的文明。王蒙先生舍“侃”字用“砍”,动感确实强了,我却依旧以为“侃”贴切。砍是掷或者斫,即使“砍大山”能强通,“砍故事儿”,“砍爷”,“砍出一部山来”太费解,换了“侃”,似乎好理解。侃字在旧时是叠用,侃侃而谈是从容不迫地说话;《论语》说“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是儒雅和乐的模样;《唐书》那“侃侃不于虚誉”却剧正不阿,理直气壮。“侃”很丰富,同样“很形象,有视觉、动作感”。试想一位京片子从容不迫、儒雅和乐、理直气壮地以刚正不阿的样子“吹牛皮、说大话、语以惊人、不着边际”该有多过瘾,该是何等境界。若此,“侃”出一部(不是一座)山来之类亦更有趣,颇见精神。“砍”,当然也不坏,既然人可以不用手来抡或擂,砍也行的。《二刻拍案惊奇》里江氏三人“杀猪也似的擂天倒地”,《孽海花》中有情有意的郎君“轮掉的”实际“抡掉的”而已;《金瓶梅》里房坍了都没压死的,到底“教舌头压杀”了。
棒 王蒙先生怀疑“来自法语的bor”。
棒字含有“好”和“强”的意思远于“五口通商”之前太多年,为啥要从红毛儿法兰西那译?难道是马可波罗带来的?我真不明白。比“帅”可能是Smart更莫名其妙。由此,我倒想起了一个英文的坏笑话说的是:“WhoyouBang?”甭查字典,这个“棒”棒就棒在是一般词书所没有的俚字。
份儿 王蒙先生说这词“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流行,有质量高、规格高使人满足之意……‘不够份儿,即有失身份……‘拔份儿(常见于刘心武小说中),即提高自己的规格……”
“份儿”并没有质量高、规格高的意思,“份儿”只是所谓质量或规格的标准尺度。在刘心武先生写小说之前,也在五十年代之前,这个词早已流行在戏剧界、服务业,甚至整个南城帽儿的市井小民之中(此词见于清末民初京俗著述甚多,姑不引征),而其所用,就是“分”或“份”字的本意。旧时的戏班、浴池、妓院之类是不发工资的,吃饭凭分份儿——将收入劈成一百份儿,班主兼挂头牌得一成是十份几,跨刀的得三份儿,弹压地面儿的警察“吃两个干份儿”;浴堂的池头得五份儿,看雅座儿的得满份儿(即一份儿),等而下之,扫地的得五分儿是半份儿,烧大炉的拿七分几半也不足一份儿——“够份儿”、“不够份儿”的说词便来了,“份儿大”,“份儿小”也有了。“拔份儿”是增加工资、提高地位,黄了班儿的角儿放出话说:“咱傍着郝老板是啥份儿还哈份儿可不成,得拔份儿哇”;谭老板说:“没那嗑儿,我肯用您是保良赈灾,玩艺儿边式不假,到了是开口跳,先委屈着拿满份儿,您骑着马找马”;投辙,认栽降级赴任,“跌了份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不错,钱份儿高,身份的规格,气派也“拔头份儿”。某“京味小说”作家在他的书里将“份儿”一律写成“忿儿”,显然是闪着舌头拔折了。记得我同张辛欣女士合作写《北京人》时,《温热烫汤》的浴堂业老把式很详细地论过“份儿”,老人对“话匣子里讨论红学,没有琏大爷咋来的琏二爷”也有意见,认为红学家读书太多,读迷瞪了:“二爷是老北京对半大老爷们儿的尊称嘛,来咱这儿洗澡,我给您破开这闷儿”。
王蒙先生的《再说语词》还有一些俚词俗字的释义,多属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或是“京腔中小女孩骂人的话”,我对这些完全外行;若果前述的还有资格“八个人儿杠房,大殡小抬着”,对“谝”“帮劲儿”和“德性样儿”的“龙门阵”,真是“猪八戒投曹锟的票,冒充哪一界呀”?!
诚如王蒙先生所说,即使是一个“具有‘好的意思的口语”,五十年来“在京腔中变化甚多”。但是,照我看来,新的似乎没有出现多少,变来变去,多是轮回,只是在新中国里重新出现或始终存在。
废两改元之后是“大头”,“小头”,“花边儿”,“子儿”和“哑板”大流行的时代;改发纸币,这些词儿渐渐没了。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了毛主席的像章,“大头”、“小头”、“花边儿”、“子儿”全都卷土重来,只少了“哑板”,却添了“大戴帽儿”、“小戴帽儿”。未久,这些都被冒儿了回去,“哑板”随开放苏生,“棣”这源于《汉书》“万物棣通”而被老祖宗辈儿“倒爷”用作“钱”之切口的词,又在新时期的个体劳动者中流行。头转向了的作家一时猜不出“棣在哪儿”的棣是啥模样,竟派了个“屉”字装它。切口里不是没“屉”字,但是数词代称,不是一回事儿。一九八九年春,我居然在北京东华门旧货市场听到了先前仅仅念过的词儿:“替头儿票子”。鬼拉人叫“找替头儿”,沾着鬼气的票子可不是沾着鬼子气的外汇,是伪钞。自然不会毫无进步——他们对毛、刘、周、朱四伟人头像的百元大钞不分是否“替头儿票子”,一概不要,伪钞制作之高明使得辨“哑板”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替头儿票子”这极易误导人想象的词没构成“恶毒攻击”之罪,当然也算大进步。恐怕是顾不上,也犯不上管这事儿了,据官方数字,“替头儿票子”一词被“朝华夕拾”,这年共收缴全国各地所流通的人民币伪钞一百余万元;到今年,仅福建一省,仅一个季度,已收缴了二百多万。
所以,王蒙先生的文章最后问,“随着女性的复再女性化”,女性习用过的一些词汇“会不会捡回来呢?”我抱定乐观态度。甭管什么化,当用的老话全能捡回来磨光了再练。“红叶未落黄菊绽”和“江山还是旧江山”的对立统一规律,《推背图》弄得特明白,所以只有六十象。六十,足够换着使了。
一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于澳洲比华利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