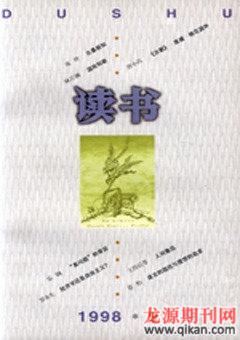政治朝圣的背后
程映虹
二十世纪西方知识界对经历着社会革命的非西方国家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既在进行着激动人心的社会实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对一些在自己社会中或是觉得单调乏味或是觉得压抑无望的文化人来说是一块可以任意驰骋其想象力的地方。从十月革命后到七十年代,他们如过江之鲫般游向苏联、中国、古巴、北越、阿尔巴尼亚以及莫桑比克或尼加拉瓜。有些人在奢望能有一次戏剧性地与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见面、从而为自己的专栏或报导增添特别权威的色彩的机会之余,也憧憬着能遇上一位传说中的性开放的革命女郎。但无疑多数人的动机并非如此轻佻。在他们的下意识里,他们是西方传统中马可·波罗、哥伦布和托克维尔的某种混合,肩负着发现精神上或社会制度上的新大陆的使命。一九一九年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olnSteffens1866—1936)在访问苏俄后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已经见到了未来,它正在成为现实。”一九三六年英国费边社理论家韦伯夫妇(悉尼和比阿特利丝)出版了访问苏联后的观感,两厚册一百几十万字的巨著取了一个与其篇幅相称的书名:《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第二版去掉了问号)。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对开放改革前的中国的印象是:在那里生活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那是一个美梦成真的地方:政府成为了人民的学校,而将军和政治家都是学者和诗人。
用“政治朝圣”来概括这类现象是富有象征性的,尤其因为它暗示着朝圣者在动身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具备了一种信仰或信念,他们其实是去证实而非发现。正如没有人是天生的圣徒一样,政治朝圣者之所以集中在某个社会阶层,并非因为它具有天赋的道德使命,而是由种种复杂的社会际遇决定的。正是这一点成为美国麻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保罗·洪伦德(Paul Hollander)十五年前出版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的苏联、中国和古巴之旅》(以下简称《朝圣者》)的主题。
这是一本对“知识分子”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值得一读的书(曾被译为意、西、葡三国文字出版)。洪伦德不但力图矫正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视此类政治朝圣为“受误导的理想主义的表现”(引自一篇书评),而且试图通过对这个世纪性现象的分析,对一些虽然时有争议,但相对来说仍受到普遍认可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特征提出质疑,它们包括:理性主义、怀疑与批评、公正、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天然隔阂、道德绝对主义(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坚守某种道德戒律)以及主张言论自由等等。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肖像,也许是很多身为知识分子者所不乐意见到或承认的。
洪伦德指出,所谓政治朝圣,主要发生于三十和六十年代,是西方文明或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或是面临深刻的精神和价值危机的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因而转向其他社会寻找替代。然而社会危机仅仅是为政治朝圣提供了一个契机,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现实处境。洪伦德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多元化、强调物质价值、大众文化日益压倒精英文化、政治权力受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英雄时代一去不返,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不可能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成为全社会注目的焦点,等等。然后认为这使得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和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用了“受拒斥”(alien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社会处境和心理反应。(实际上,他的观点和雷蒙·阿隆在分析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左倾化现象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观点很相似。雷蒙·阿隆特别指出西方社会中技术对文化的压抑、大众对精英的牵掣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不满的原因。)源于这样一种分析,洪伦德认为要理解政治朝圣现象,关键在于认识到那些成为朝圣对象的体制,在何种意义上迎合或满足了在自己社会中感到受拒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欲望。
洪伦德指出,社会平等与正义固然是这些新体制的最外在的吸引力,然而如果阅读大量的“朝圣”文献,不难发现实际上更为基本因而也更具吸引力的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这些体制赋予了世俗生活以神圣的意义,使得全体人民具有了同一感和目的意识,整个社会因而凝聚成了某种共同体。例如,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说他甚至在普通苏联人的面容和神态上也能发现那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目的意识;德国著名作家孚希特万格说他在莫斯科比在其他西方都市都更易获得方向感;美国六十年代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托姆·海登和斯塔腾·林德(前者曾与美国演艺界著名的左派女星简·方达结婚)说他们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到处都搏动着热气腾腾的富有目的意识的活动,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则总结道:最重要的是,你远离了多元性和争议这些美国的特征,被包容进一种信仰和目的的完全一致之中。
这种对意义、目的和同一感的追寻或者敏感,正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在一个日益世俗化、多元化、个人化的世界中的困境。洪伦德认为,对知识分子代表着理性这一假定的认可,使人们大大地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宗教需求。实际上,在宗教退出世俗生活的二十世纪,正是依靠象征性和精神价值生活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忍受这种无意义的生活。远自法国大革命起,他们就用理性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而这种对理性的态度本质上恰恰是非理性的。在二十世纪,他们进一步转向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找信仰的替代,而其目光又常常落在那些宣称建立在人类理性所发现的历史法则和人类理性所设计的社会计划的体制之上。在这些体制中,个人对社会、国家和未来的义务被神圣化了,世俗生活得到了升华,困扰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源于个人和物质本位的种种苦闷、困惑和孤独感在这里纯粹变成了被嘲弄的东西。
并非偶然的是,很多宗教界的访问者——很多人其实更可以称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既在宗教界活动,同时又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或教育家——认为这些意识形态上具有反宗教倾向的体制实际上远比西方社会更宗教化。例如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活动家谢伍德·艾迪曾在其《我们能向俄国学些什么》(一九三四年)中说:“俄国取得了至今为止只有在很少的历史时期中人类才取得的成就:全体人民生活在一种哲学之下,全部生活凝聚在一个中心意图之下。”英国贵格派教会人士巴克斯顿说: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复活并采用了最重要的基督教理念,虽然他们在言辞上是反宗教的,但实际上其社会比我们的更接近基督教理想。在这方面或许更突出的例证是有“红色主教”之称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立特·詹森(HewlettJohnson1874—1966),他曾于三十和五十年代访问过苏、中,有比较这两国社会与基督教理想的著作多种,并获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在他关于中国的论述中认为中国革命纯粹是一幕宗教性质的戏剧,其对自私和贪婪的憎恨与基督教观念如出一辙,而自我批评精神又类似原始基督教中的谦卑和悔悟。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洪伦德着力分析的另一个问题。与一些人(如曼海姆)强调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批评角色不同,他认为和其他社会集团一样,知识分子同样渴望权力,而这种渴望由于其自命为理性和知识的承担者而更具有合理性。然而在多元化的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完全不能满足其潜在的权力渴望。例如实业、商业、金融界人士的社会地位远在知识分子之上,而议会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的群众影响也大于知识分子(例外也是有的,如萨特)。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在表面上对权力采取疏远、批判或视其为肮脏的态度,因为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下,他们的影响力注定是有限的。因此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费厄认为:知识分子并非对权力本身,而是对自己被排斥在掌权者之外感到不满。乔治·奥威尔在脱离左派阵营之后也说:“权力意志的受挫是西方知识分子向左转的最内在原因。洪伦德认为,一旦客观形势提供给知识分子以从政或进言的机会时(如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改革期间),他们那种既想掌权又怕被指责为与政府和既得利益者合作的心态便典型地反映了权力是一种令其苦恼的诱惑(a nagging temptation)。
那么,在这一点上,那些被访问的国家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呢?首先,大量的“朝圣”文献中充满着一种惊喜和欣慰:世界上终于有一个国家,由一批通晓历史法则的领导者率领,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监督下实行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变革,用韦伯夫妇的话来说:“在全部社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奋的实验。”这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用理性指导和规划全部生活。其次,合乎逻辑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社会。例如,最高领导人本身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通晓从哲学、语言学到当代物理学和热带植物学(如何提高甘蔗的产量)的所有学问,而一些特别受到政府尊崇的知识分子的声望也充分说明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如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说高尔基在苏联的声望只有斯大林可以媲美。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许多访问者眼中,这些体制大大简化了社会结构,许多阶层、集团消失了,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的作用因而凸显了。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不但同西方社会中知识只是众多的谋生手艺中的一种形成鲜明对照,更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和优越感,正如爱德蒙·威尔逊所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给作家如此高的荣誉,也没有别的地方使作家有如此身负重任的感觉。”因此在这里,西方社会中理想家(知识分子)与实践家(掌权者)的分离被融合了,受拒斥感消失了。
这种对待权力的态度又和对待群众的态度有着内在联系。洪伦德指出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一种矛盾:既宣称信奉平等而实际又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精英阶层。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样一种理论:如果没有外部的灌输和引导,工人永远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革命要求,或者说如果不是自己代群众立言,群众自己永远不会懂得其真正的利益所在。这是一种典型的父权主义态度。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中想方设法投选民所好的议会政治家充满蔑视,而对慈父和先知类型的、同时又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群众运动家充满钦敬。在西方社会中,一个令其焦灼而又深感无能为力的问题是:如何使得群众放弃个人的、具体的、物质的要求而投身于知识分子所指定的方向。而在他们所访问的国家中,他们认为这个奇迹实现了。毫不奇怪的是,几乎每个访问者都谈到了当自己置身于集体狂热掩盖了任何个性的场合(诸如游行和狂欢)时的感受,他们视此为群众整体被重新塑造并获得精神再生的表现。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就说她怀疑在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一个人还有可能成为愤世嫉俗者。
当然怀疑甚至反感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见闻中还是存在的,因为毕竟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和所习惯的一切差距太大。但问题是——洪伦德强调说——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容易在事关自己利益或好恶的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从而总是倾向于接受有利于自己既成信念的解释。当他们见到消极面时,总是急于知道官方是如何解释的。例如,罗曼·罗兰曾经就苏联法律(三十年代)规定对十二岁以上未成年儿童可以因政治罪处以极刑的规定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质疑,认为这在西方人感情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会损害苏联的形象。但当斯大林向他解释了“敌人”是如何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并已导致出现了“到处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地下匪帮”在杀害与他们同龄的“先进”的男孩和女孩时,罗兰自责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所遗忘了的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本文所引有关罗兰的材料,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莫斯科日记》)任务的艰巨和反抗的激烈——这是几乎所有的访问者为许多不可思议的政策和措施作辩护的最有力的理由,就连爱因斯坦(虽然他当时并未访问苏联)也说,在这种特殊性质和规模的社会实验中,“个人确实需要暂时地、痛苦地放弃其自由”。很多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内是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平权运动的斗士,但面对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一张工人的选票等于六张农民的选票的规定(关于此政策的解释,参见列宁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却认为在“当时的”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导致了一种荒谬的推论:一些在被他们所否定的社会中尚能存在并维持的原则,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反而变得负担不起了。很多访问者归来后总是不忘提醒后来者在评判他们将要看到的一些事情时必须完全抛弃“西方的”标准,必须从目的出发来评价手段。然而洪伦德指出:正是根据首先在西方国家确立的一些标准,如平等、正义、自由、物质进步等,这些非西方国家才能对西方知识界产生吸引力(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根据经典作家的说法,也正是来源于西方,或更准确地说是西欧思想界的积极成果,与其他文明的“标准”毫不相干)。至于目的使得手段变得正当的说法,笔者记得悉尼·胡克曾在一篇评左翼知识界的文章中提醒得很恰当:手段从来不仅仅是工具,其道德质量直接反映或影响了目的的性质。
总之,种种社会和心理的因素导致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在“朝圣”旅途中完全或部分地丧失了他们在剖析自己社会时的那种犀利而敏感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而这又不能归之于信息量不足。波将金村庄式的布景覆盖面毕竟有限,很多问题是无法掩饰因而一望即知的。问题是在这里,信息在心理上被接收者分为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洪伦德说,当确定了一个事物“本质”的好与坏时,与此相矛盾的细节再多也难以改变既定的判断。正如美国作家约瑟夫·弗里曼所说:你可以写上成卷的有关这些社会的落后与艰苦的书,你的每一个具体事例都是真的,但你以此构成的整个画面却是虚假的。此外,消极的信息也可以被赋予积极的解释。例如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是好的,因为它体现了平等。而贫穷则被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旧制度的残余,二是有意义的奉献,三是体现了一种纯洁的、未受物质主义污染的生活方式,前者显然与新制度无关,而后者则是值得赞美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知识分子似乎乐于见到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比较不发达的、乡村化的生活环境中,在艰难困苦中显示人类的英雄气概如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去完成巨大的工程之类,(如苏联的白海运河工程和中国的红旗渠)。而一旦技术水平和物质生活提高了,其吸引力就大打折扣,这正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和古巴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知识分子心目中取代苏联的重要原因(洪伦德特别分析了萨特的言行在这种偶像转换中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对前工业化时代的乡愁也能在这些国家找到寄托。例如五十——七十年代访问中国的人都感到在人民朴素的穿着、简陋的房舍和周围的田野景色之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和谐,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但在进入未来,也在回到过去。例如英国作家菲利克斯·格林说从他乘坐的火车车厢里望出去,中国的乡野景色一如他在宋代的绘画中见过的那样质朴而富有诗意。
在一些知识分子眼中,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所访问的社会是如此黑白分明,以至于一些两个社会所共有的事物也有着不同的性质或解释。例如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剥削和奴役的象征,而在另一边则不同。有一则轶事说:一个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教师在参观苏联印刷厂时见到一台高效率的印刷机后十分惊喜,她说只有在你们的国家里,在劳动是自由的、不受剥削的、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的情况下才会设计出这样完美的工具,我回去后要就此好好写一篇文章。但当她走到机器背后时却不无尴尬地发现了一行小字:产于纽约布鲁克林。
五百多年前哥伦布航行到了美洲,然而他却以为自己到了传说中的东方。在他那封返航途中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著名的信中,后人发现他把他所看到的地方(不过是几个小岛)的面积和出产物大大地夸张了一番以符合马可·波罗等人的描绘。哥伦布固然可能是想得到王室更多的支持因而作了一番渲染,然而心理学家却认为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眼睛所见到的常常是心灵已准备接受的东西,这尤其发生在人们充满期待地进入一个新世界之时。因此,这类文字表现得更多的与其说是叙述者所见到的景象,不如说是叙述者自己的期待和信念。
其实,即使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新世界,但只要对自己的社会不满,单凭道听途说有时也能对另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社会产生丰富的想象和移情,正如爱的需求会创造出被爱的对象一样。在这一点上,启蒙运动时代一些西方思想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赞美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华盛顿邮报》对《朝圣者》一书的评论也许可以拿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是一本值得放在手边再三阅读的书,尤其是当有人告诉你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政治权力正以全新的方式被行使,人心被重新塑造,人性得到升华的时候。”
(PaulHollanderPoliticalPilgirims—travelsofWesternIntellectualstotheSovietUnion,China,andCuba.Publishedby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