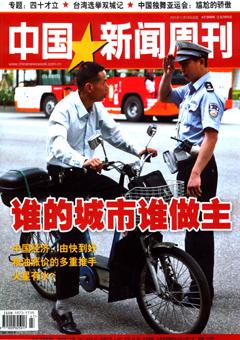随笔
明太祖的“国六条”
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发布了“国六条”,其内容如下:一、任何人不得超越等级建房;二、居民门窗不得使用朱红油漆;三、庶民住房不得超过三间;四、功臣宅邸两边可以保留五丈空地;五、军民房屋不许建成五间或九间;六、寺观庵院不得使用斗拱。
现在发布“国六条”,是为了限制房价增长过快,以确保经济的稳定;明朝发布“国六条”,是为了教育人们分清上下,以确保等级的稳定。两个“国六条”的实施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大明弘治年间,浙江太平府三分之二的商人把私宅建成了官邸;嘉靖年间,南京城私人经营的河房到处都是红漆彩绘。为了杜绝类似情形一再出现,明太祖在洪武三十五年对“国六条”进行细化,到正统十二年,明英宗又重申了“国六条”,然而收效甚微,臣民建房违规之势愈演愈烈。
那年月,再大大不过圣旨去,“国六条”就是圣旨,人们偏敢顶风而上,莫非是惩罚措施不严厉?《大明律》有规定,庶民建房逾制,轻笞五十,重笞一百。笞就是用大板子往屁股上抡,要是使得劲足,笞五十就能让人后半生瘫痪,没练过金钟罩的人没理由不怕笞的。问题在于,负责去笞的不是明太祖,而是地方官,地方官笞的力度大有玄机,建房者白花花的银子送上去,那地方官怕是不但不笞,还会给人家来个按摩。
所以说,中央政令一到地方就难以执行,是因为地方官有逐利倾向,正是地方官的逐利阻碍了“国六条”,这个道理人所共知。怎样能让地方官不去逐利呢?王莽早就试过德化的方法,他苦口婆心,号召有权有势的不要再搞土地兼并,而要把土地分给穷人,最后也只在历史上留下个笑柄而已。靠道德的约束力来消除地方官的逐利,就像臭棋篓子下棋,总指望别人会按自己想的走子。合乎常识的做法是把棋下得凌厉一些,逼着对方不得不按你设定的路子走。而要逼着地方官不逐利,仅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成的,还得有明晰的、多样的、不可侵犯的私权来对抗,大明朝不流行这个,今天的发达国家却无一不在这样做。
如果给明太祖提建议,不外如是:想让“国六条”得以贯彻,就必须遏制地方官逐利,要遏制地方官逐利,就必须让民众有足够的私权。想来明太祖会说:私权一多,地方官事就难办,我还指着他们给我办事呢。
效率与公平,这又是一对矛盾。
文/李开周
情欲艺术家
搞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放得开,都把追求爱与美当作自己的使命。
青海挨着甘肃的地界,有个北山林场,算得上是个艺术村,两省的画家都爱去那里写个生什么的。当然了,他们去的时候,一般都带着几个学生,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漂亮姑娘。
“男人的内心,一面是一堆闪亮的星星,另一面是一堆污秽的混合物”——林画家的嘴上总是挂着这么两句话。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他已经忘了。他想,说得对啊,就像我在画画的时候纯洁无比,可是难保见了漂亮姑娘不动一些非分之想,下流的念头谁没有?林画家在热爱女人这一点上,圈中人无出其右。
一次,林画家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和那记者说:“你看我的这双眼睛,里面沉淀着一个艺术家永恒的孤独感。”这话打动了许多涉世未深的艺术女青年,拿他当大师一样崇拜。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让她们觉得他就像一个孩子,解救了他无药可治的孤独,就相当于解救了他的艺术。
人爱何物,最后就会死于何物。正如水手死于大海,猎人丧生虎口。林画家老是叹息着孤独啊孤独,于是就有一个女人彻底解决了他的孤独。这女人是他在一家洗浴中心认识的,长得楚楚动人,从事的却是一份特殊职业。她极大地满足了林画家的情欲,而林画家也被她激发了勃勃雄心,演出了一场现代的“救美从良”——让那女人从此跟着他,离开洗浴中心。那女人自然满心欢喜,从此跟着林画家,过一种有真情的日子。没人觉得林画家奇怪,他是艺术家,做什么都在可以宽容的范围。艺术家么,本来就是些个半疯的人,他想干点啥,谁能拦得住?
林画家从此被这女人绑住,无论去哪里,都要先交待个底掉——她是欢场出身,判断林画家的风月情事那是再容易不过了。看一个女人,她只要扫一眼,便能判定和林画家究竟有无情感瓜葛,就连上没上过床,也是一目了然。基本上,林画家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就连开会也不放手。她,小鸟依人,无比温柔。不知道的人,以为林画家终于得了一份真爱;知道的人呢,谁都清楚林画家的痛苦。按这女人的话说,“你们这个圈子这么乱,我哪敢放心哪?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样踏实。”
林画家从此不再提及孤独的事,他过上了仿若中产阶级一般循规蹈矩的好日子。北山林场,他不再去写生了,专门在家里画些马灯、书箱、留声机之类的老物。这些画,一般尺寸都不小,听说市场上行情很好。
中国古代淫书《肉蒲团》,以淫为名,行的却是因果报应的说教之功。林画家的事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张海龙
慎选婚期
好友要结婚了,婚期定在一个所谓“幸好”的日子。为啥说是“幸好”呢?因为据说有一个曾经执迷不悔追求过这个女孩的男子,生日就在她婚期的后几天。
仿佛刚走过雷区身后就有爆炸声般的侥幸。想来万一她结婚在这位扬言发誓非她不娶的男子生日那天,那么,这个男子也许、估计、可能、大概要愤然一生了。
其实,怪也怪不得她,之所以会出如此让旁观者嚼舌的杂事,只能怪那个“愤然一生”先生,生得不是时候。
“愤然一生”出生在婚期高峰时段,10月1日。大多数待嫁进入备战阶段的姑娘,如果想选一个秋高气爽、天气宜人、亲朋都有时间可赴宴为自己祝福的时间来结婚,挑来挑去,似乎只有10月1日这一天了。择日竟然撞日,不怪好友日子没选好,只怪她初恋时候没高瞻远瞩一下那位先生生日可能带来的尴尬。幸好是十一那天订不到酒席,婚期只好提前两天,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婚期真的很难定。想到世间仰慕者众的女子,随便在哪天把自己嫁出去,都肯定会撞上一些男人的生日。那她的婚姻可能会祝福声弱弱,弥漫着的尽是不甘不愿忿忿恨恨的抱怨,那些个哀怨的人,觉得自己一直钟情的姑娘们不但辜负了他们的一世深情,还让自己的生日活活地就成为绝望纪念日,此生无法超脱。怎么办?
很难说不会出现什么大闹婚礼的惨剧,或是人不现身托快递公司送来大煞风景的礼物一份。侦探片中新郎新娘一旦有啥三长两短,第一嫌疑人总是情场失意人。若事情没那么糟糕,你递请柬给他,他欣然来了,淡然入座,可三杯五盏一下来,把喜酒当作闷酒来喝,喝到后来口不遮拦说当年的事诉不甘的心,这下,又难堪了!新郎官那斥巨资的礼服哇,千万不要成为敌对旧人的战甲!
婚期既然很可能撞在单恋痴心郎的生日那天,那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路可走。
一条是索性不嫁了。一辈子不嫁人,总不会伤害别人了吧。顶多没有婚假产假什么的好福利,现代女子怕个啥。养儿防老老早就过时了。
还有一种聪明的方法,就是要么定在2月29日结婚,闰年嘛,四年才一次,算上概率,至少愤然一生的男人数量上要少一点。我掐指一算,2008年和2012年各会有一个闰年。姐妹们要开始筹划起来了,要么就不结婚,要结就结在奥运年。
文/上上签
知音
2005年的冬天,我客居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国际公寓里。公寓的白天常常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是不工作的人。
一个飘雪的下午,我在厨房煮咖啡,随口唱着我喜欢的歌,我不知道那一刻有人就站在我身后。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吓到了我。他忙着道歉,他是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法国人。我回过神来,也道歉:是我的歌声打扰了你吗?我以为没有人。
他说,不,恰恰相反,是你的歌声吸引了我。是否可以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我唱的是《知音》,是我喜欢的一首电影插曲。
我沉默了一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翻译“知音”这个词。好朋友吗?不是。爱人吗?也不是。有很多东西,用汉语是很好表达的,因为有很多深邃的含义与情感蕴含在这些词句中。但是,却不可说,因为一说就错。比如“红颜”,比如“高山流水”。
所以我问,你想知道?他说:是的。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我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我想了想,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个男人,是一个将军,叫做蔡锷;有一个女子,是一个妓女,叫做小凤仙……
我讲完这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故事之后,随即将这首歌的歌词直译过去,但是我觉得很遗憾,一是我的外语不够好;第二,有很多美好的中国诗句与歌词,原本是不能翻译的。这就是即使曹雪芹活着,《红楼梦》也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当我说到“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时,我看到这个法国人表情上的动容,他的眼波变深,荡漾起一种柔情。我没有想到即使在国内,也很难找到对这两句倾心的同道,竟然在这陌生的异国有了知音。我第一次听到这两句的时候,就被深深打动。
最后,我说:这首歌的名字,也许应该翻译成“传奇”。
电影《知音》仅仅演到将军死,琴弦断,再未交待小凤仙的下落。真实的故事是,蔡锷走,小凤仙被袁世凯扔进监狱。出狱后,她并未回到蔡锷的身边,而是隐姓埋名,隐没他乡。蔡锷死于日本,小凤仙一生缄默其口,终生独自生活,从不提起这段传奇。也有人找到她,但是,她只是沉默。
所以真正的知音,是一种传奇。那包含相交的懂得与牺牲,那是超越友谊,也超越爱情的,所以,称之为“传奇”。
那个法国人盯着我,沉默了很久。他开口的时候,我打断了他。我轻轻地说,我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
他还准备说话,我再次打断他,也许,也许你可以去亚洲店,也许找得到这部电影。
第三次,我说,喝咖啡吧,已经凉了。
男人不再开口。窗外大雪纷飞,一片苍茫。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可是我不会是他的传奇,也不是他的知音。
文/夏雨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