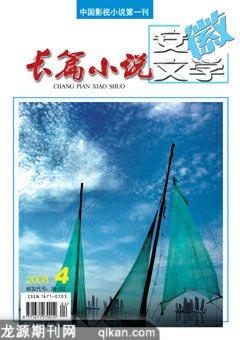平凡的父亲母亲(散文)
李民鸣
父亲走了整整十年了。
记得在我父亲走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在清理家里的衣物时发现了父亲的一个日记本,小小的一个旧笔记本,用一块干净的布包裹着。里面的内容写满了父亲对母亲日后孤单生活的担心和对儿女的惦记。他似乎有预感有一天走在母亲的前面,看到了母亲形单影只的景象,也看到了儿女们的哀悼和怀念。
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预想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心底仔细的人。
母亲操劳了一辈子了。父亲一直怀有对母亲的愧疚之心。这种感觉像白蚁,几乎要蛀空他的心。所以他一直想弥补母亲。所以下班后只要有时间就会走进厨房,和母亲同演一台锅碗瓢勺的热闹戏。出差他一定要给母亲挑选一件母亲和他都觉得最精美的礼物。而这礼物一定不是以价格来衡量的。是用他们自己的尺度。
我的母亲老来发胖得厉害,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的身材和风韵了,所以穿起衣服来她自己怎么看都觉得别扭。她觉得如果腰身合适她的尺寸的衣服,又觉得太长,而长短适合她身材的又太瘦小,绷在身上就像一节节莲藕,凹凸明显。怎么瞧都觉得线条太多。而我们这些儿女,怎么看都觉得得体富态,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就更是别样的美丽。
让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津津乐道的是:母亲自从父亲退休后就开始了新的课程,学打麻将牌。常和那些退了休的老朋友们还有邻居玩玩。母亲玩牌足实是小孩儿过家家,认真但不计较。只是这下忙坏了在家暂时为他们这些老顽童做招待的老服务生,我们的父亲。母亲上桌玩,他忙着斟茶倒水。被呼前换后的跑堂似的忙活,还乐在其中。忙完了。母亲会心疼的看看父亲,示意他挨着自己坐下来做她的陪衬。父亲一辈子都愿意做母亲的陪衬,这是他最愿意充当的角色。但其实母亲却为他做了一辈子的陪衬。他们之间彼此彼此。我们总会这样开他们的玩笑。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的端个凳子默默地坐在母亲的身边,全没有他做局长的风度了。静静地看自己的老伴和邻居们玩得开心。不时还说说笑话,逗得那些玩牌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开怀大笑。他是母亲的账房先生,当然是临时的。或说只是个柜台伙记。但决不是母亲的财政部长。母亲玩牌输多赢少。他坐在一旁乐呵呵的数着那些他特地为母亲准备的崭新的小票子,像孩子们的压岁钱一样。还不忘一边奚落母亲说:光绪皇帝变成光输女皇呀。(光绪的绪在地方话里念输。地方话的谐音) 哈哈。母亲有时会很抱歉的看着父亲手上的新票子所剩无几。这时父亲会心领神会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老人之间玩牌,讲的不是钱,是休闲消磨时间,一种乐趣。用点脑子,十元钱可以输赢一整天。母亲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旁敲侧击安慰母亲呢。这时会让所有人的都快活的赞同他的说法。大家玩得特别的轻松。就像坐在茶馆里喝茶一样。只要心态放平稳,打点儿小麻将牌,是不会影响健康的。
他自己从来不上外面去玩牌,但到儿女家串门子是例外,住上一星期半个月的,他也会凑凑兴,闹着玩玩,但他会故意的不守规矩,在牌桌上尽闹笑话,他是那样快活的一个人。
父亲对母亲格外疼爱,也特别的能包容。母亲在父亲面前总是显得像年轻人一样的很任性,即便是进淋浴间洗澡,对父亲也要大呼小叫的支使。要么是将衣服遗忘在外面,要么是水的温度不够适中。她洗澡父亲不得不站在浴室的门口守候着,而且看上去他好像是那样的心甘情愿,乐呵呵地。总之,父亲在家,她的事儿多得繁琐。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就会为父亲打抱不平,父亲总是笑笑。其实我们哪里懂得,这是父母之间的乐趣。母亲也是女人,她也需要在父亲面前撒娇。就像她有时在父亲面前蛮横不讲理一样,那是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幸福。
母亲在父亲走的时候,丧葬期间很坚强,她说:我的儿女们都成了泪人儿了,我不能。他走了,我要支撑起来,要热热闹闹的让老伴走得安心。
她真的这么做了,她给人打电话,她安排所有的事宜,她坚强得像个男人;像一个刚刚才学会爬的婴儿,而一夜之间就能走会跑了。她一改往日父亲在世时的怯弱和依赖,变得勇敢而且异样的独立,有主见。她让我们在极其悲伤的日子里看到了我们头顶上的那片过去由父亲撑起的天。让我们四个孩子紧紧的背靠着过去由他们两人共同建筑的顶梁柱。她那会儿变成了一座巍然的山,在我们的身后抵挡已经来临的洪水猛兽。她同时点燃了由过去和父亲共同为我们照亮的灯,让我们不至于在悲伤中迷失方向。她和父亲一直为我们撑起了家的伞,只要我们遇到风雨飘摇就会躲进他们的庇护下得到安宁,不会淋湿我们的衣裳。现在她要只身为孩子们继续过去他们共同营造的一切。母亲用行动又一次的让我们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崇尚。
没有了父亲,这个家是有些残缺的完整。但我们能够和母亲一起坚强。
父亲平日里身体棒棒的,很少听说他生病,只是那几年,他得了痛风症,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包括豆制品也很少碰。进医院前,只不过是一点点感冒症状,头一个星期,他还能自己走着到医院,然后也可以从医院走回家吃饭。跟平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医生说要吃药打针,消炎了就会好起来。父亲自己也认为没有事情,过不了几天就好了。住院也行,免得晚上吵醒了母亲。
可是,经过几天的医院治疗反而更严重了,由能够下床自己走动到躺在床上,由能够挑食吃东西到一粒米也不想进。由可以和医生幽默的开玩笑到昏迷不醒。当我们提出质疑时,医生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准确的回答。时间让我们没有空隙去和他们争论或说讨教,我们知道,已经晚了。父亲已经开始昏迷,他连一加一都不知道等于几,已经开始不断的输血而又不断的将刚刚输进去的冰冷的血吐出来。但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尽力了。对我们的质疑,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痛风症会让父亲免疫力下降,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疾病都有可能造成他的生命危险。
父亲的追悼会开得伤心欲绝。来了很多很多的人,看到那么多他过去的同事、朋友、部下和上级领导都凄凄地站在那儿摸泪,不舍地看着他躺在那冰冷的玻璃棺木里。是啊,这个世界像魔窟,一不小心就会失脚掉进去。想不通的料不到的突然的事件像天上的流星,只见一道闪耀的银光,那样的刺眼,你看都看不清就坠落了。
我妹妹的儿子才刚刚四岁,趴到玻璃棺木盖的父亲的头上,幼稚地看着爷爷问他妈妈:“爷爷睡着了,等我长大了,我就去叫醒他,将他挖起来。”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掉眼泪了。
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听母亲讲起父亲的好多好的过去。母亲告诉我们:你们兄妹几个出生的时候正值“文革”,家境很困难,尤其在我刚满一个月,有一天天刚擦黑,听到有人在外面叫:失火啦!失火啦!快救人啦,里面还有个刚生完孩子的月母子呢。母亲听到外面的喊声才意思到的确有些浓烟,也有几分呛嗓子。母亲怀抱襁保中的我,不顾一切的冲了出去。离屋子不远处,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母亲逃到河边,找了个她自己认为的安全地方坐了下来。
火势很猛,又正遇上天寒地冻,肃肃的寒风带着熊熊的火焰迅猛地盖过一家又一家。浓烟滚滚,烧焦的木房发出吱吱呀呀的倒塌声。哭喊的妇女和惊恐的孩子们紧紧地跟在救援人后面朝安全的地方转移。救火的男人奋不顾身的往火海里救人。房子被烧黑了,救火的人也被浓烟熏黑了。
那一幕惊心动魄,整条街成了废墟。母亲讲这些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仿佛是重演了一次庞贝城。
“谢天谢地,母女俩安全健康。”等父亲被组织上批准回家探望时,家里的一切都恢复原状了,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斗胆地问母亲,父亲这一生,坎坎坷坷,在你们的婚姻生活里,父亲总是在忙工作,在我们的记忆里,大多数都是你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带四个孩子,难道你没有怨恨过吗?她很慎重的说,他是区委副书记,整天都在农村蹲点,这个公社跑跑,那个大队看看,大事小事都得上心。多得像乱麻,理都理不清。搞实验田。开山辟陵的,都在最前线带头干。他在工地上为工人们的安危担忧,我在家里哪有一天睡得安稳。他在那儿是拼着命在干呀。她说这话时脸上仍然深深的刻着疼惜。
后来年龄大了,组织上调他回来,不要在下面忙碌了。可局里的事情也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呀。又是外贸企业,父亲还得从头学起,边干边学,那叫着吃力。整天也是东奔西跑,下厂看货,与客户商谈。我怨他,他怨谁呀。说来好笑,他身为外贸局局长,下面的职员都出国考察观光,他居然连一次香港都没有去过,他不是那种玩花架子的局长。
当我们不得不回到各自的城市时,我们担心母亲,我们想请她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母亲不肯,她让我们相信,她能行!她肯定能行!这几天不证实了她能行吗?
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呆着,没有洗脸,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她将一个袖珍播放器放在父亲遗像的下面,呆呆地听着那“南阿弥陀佛”的送行挽歌,她一直播放着这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曲子。母亲说,父亲听到这首曲子,会一路走好。
靠正厅的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祭台,祭台的周围那下垂的漆黑挽纱悲凉地吊挂着。还有那祭台上哭泣的香烛在香坛里不分昼夜地悲嚎,魂魄的轻烟在满屋子里袅绕。父亲的遗像就挂在祭台的上方,在镜框四周簇拥着一圈黑挽绸带,轻轻的为悼念的伤心人拭泪。镜框里那张熟悉的脸孔,那慈祥的微笑,仿佛还在昨天。
母亲凝视着他,她感觉那笑就是冲着她来的,她似乎又看到了他的嘴唇微微的张开了,像往常一样和自己说着话,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和。她有一种被温暖所包裹着的恍惚。突然,祭台上有一根香烛的芯蕊在摇摇晃晃,这样的悲伤连香烛也伤心断肠。她下意识的想去换上一根新的,可抬起的手颤抖得把不准方向。她又抬头望了望父亲,想告诉他,别着急,她将点着这长明香烛为他照亮回去的路。她几乎没有了力气。是啊,整整一个星期的伤心劳累,她时刻都强忍着比任何人都的承受的巨大悲痛。她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啊。
她看到父亲的笑僵持了,声音也微弱了,身体变得那样的凉,这满屋子的凉气充斥了一切。她觉得好冷,环视屋子,一切都没有了,好空好空。再听听屋里屋外的声音,好静啊。她突然扑倒在父亲的祭坛前,久久的长跪不起,一声哀号。可她除了能够叫出父亲的名字,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泉涌的湿透了衣衫。整个脑子里,除了父亲的形象,还是父亲的形象。
往事如烟,这夜多黑呀。这会儿她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从此将形单影只的度日如年。过去的人,往日的恩爱都变成了那冰冷的骨灰带走了,飘飞了。
母亲在父亲弥留之际,一直都坚持想让父亲回到家里去,不要在医院。她坚持说,父亲要从自己家里走,她要送他一程。但我们不理解她,我们还认为她这样说太残忍。总觉得在医院里就会有一线的希望,哪怕明知道这希望是在自欺欺人,但还是不肯放下哪怕唯一的一丝一毫的奇迹。其实母亲是对的。她的预感是绝对准确的。
是啊,只有她,最了解父亲,只有她,才有资格决定在父亲弥留之际应该呆的地方。她知道父亲一定想再看看那个他多么热爱的家,睡一睡他曾经睡过的床,他已经开始厌倦吊在他头顶上的挂针,不再相信什么灵丹妙药能够治好他的病,那些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的人,在他跟前晃来晃去的让他头昏。还有儿女们每天在他身边守候的焦急的眼神。他想回家,想最后一次回到干干净净的家。和母亲再叙叙年轻时候的恩情,再笑笑儿女们的趣闻,吃一口母亲亲自下厨做的、哪怕是稀粥也行。
他要穿戴整体,平静地和母亲说再见。他说不会在奈何桥头等她,因为他想她活得更健康些更长些更能够满足儿女们的祝福。他说他年轻时只顾了工作太少的分担母亲为孩子们和家庭的劳累。他觉得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父亲走了,他想早一步到天堂里等候一个女人,因为他爱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