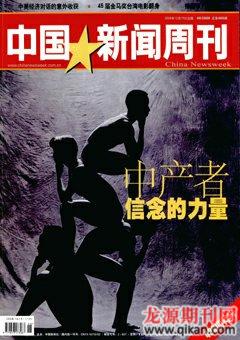北京律协直选的“三人演义”
韩 永
“人是利己同时利他的动物,我做这些事,为私利也为公益。跟作家一样,好的律师要有案例、有作品留下,为了公益,出名也是好名”
当程海在合肥因相邻权纠纷将辖区派出所告得热火朝天的2000年,唐吉田还在延吉市检察院,应付着工作上的灯红酒绿,因前途渺茫而痛苦不堪。而在南方的西子湖畔,张立辉大学毕业刚刚4年,法学理论正在艰难地转化为实践。
8年后,3个人坐在一起,共同谋划北京律协直选倡议。性格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过程中充满着合作与猜疑、高亢与低迷、坚持与放弃,律协直选就像一根线,串起了3个人,首尾相顾,进退身不由己。
“斗士”程海
2007年6月,在未征求会员意见的情况下,北京律协撤销了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身为会员的程海和张立辉去市司法局讨要说法,律管处的一位负责人说:“我有权成立,我也有权撤销。”
这样的对待,程海似曾相识。“文革”期间,由于父亲是“臭老九”,经常挨批,家里唯一一张像样的床也被人弄走。看着“红五类”的孩子一个个被推荐上大学,他真切地感受到平等是如此遥不可及。
下放到农村后,由于长期干农活,他脖子上被压出一个包,现在看起来依旧清晰。返城做工人,他被马列著作深深吸引,并且读出了别样的意味。“人的活动都跟利益相关,”他说。
1977年,高考恢复。初一都没有上完的程海决定试一试。他说这是自己一贯的性格,凡事喜欢尝试,有时候不问结果。高考前3个月,他称病在家,每天以80页的速度看书,最终考取合肥师专中文系。
他始终不安分。大学毕业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书,私下里开始考研。第一年,英语没过,第二年,专业课没过,第三年终于通过,被录取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他选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前卫的主题:劳动平等。当下全民关注的城乡统筹,他声称在当时的论文里已有提及。
再后来,他先在安徽省体改委做了几年企业改革,下海,先后做过基金经理、企业管理咨询,还申请专利做过童车的生意。在做律师之前,他前后换过七八份工作。
1999年,程海与隔壁的一家医院因对方的一堵墙发生纠纷,程海认为三牌楼派出所的处理有偏袒对方的嫌疑,于是将该派出所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就是一年半。派出所的人始终搞不明白,为了这点破事,辖区内的这个小个子为什么百般纠缠?
有一次庭审,程海的发言终于激怒了出庭的一位副所长,说:“要不是在法庭,我现在就抓你!”程海说:“现在已经休庭了,你来抓!”并为此事投诉到很多部门。官司虽然输了,但程海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对法律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于是在47岁时走进考场,第一年差了9分,第二年顺利通过,拿到了律师执业资格。
他说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开始通过一系列引人关注的事件,来诠释他对这份职业的理解:2005年下半年,他以安装电话外地人受到歧视为由,将北京网通告上法庭;2006年1月份,他因回家过年时的一票难求,状告有钱不投资的铁道部;2007年4月份,他因自由迁移户口遭拒,将安徽和北京两地的至少4家公安部门相继告上法庭。
巧合的是,在程海成为律师之前被拿来祭旗的合肥三牌楼派出所,在他一系列户口诉讼案中再成被告。这家曾经在评比中排名靠前的派出所,据说现在有好多人徘徊在下岗的边缘。
这些诉讼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招来了涉嫌炒作的广泛质疑。他说:人是利己同时利他的动物,我做这些事,为私利也为公益。跟作家一样,好的律师要有案例、有作品留下,为了公益,出名也是好名。
至少在律师界,程海已经名声在外。唐吉田一直想找机会结识一下他,律协直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
唐吉田“找到组织”
跟程海一样,唐吉田也有个“成分不好”的父亲。他刚记事时,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在山上开了点荒,被“工作组”发现,不仅收成被缴,母亲也受到惊吓,长病不起。
生活拮据,父母时有摩擦,家里气氛非常压抑。唐有时候因为不甘于被忽略,就经常会有惊世骇俗之语。在高中的一次晚会上,大家纷纷畅言以后的打算,唐吉田走到讲台上,两腿发抖,说了句:“我的理想就是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年之后同学见面,还有人跟他插科打诨:“怎么样,主席?”
他又发自内心地喜欢公共活动。1991年,唐吉田在东北师大读大三,写信给延边州委书记,就民族问题坦陈自己的看法。半个月后,他收到回信,用的是延边州委的信纸和信封,肯定了他的建议,赞赏他关心家乡的行为。他后来在报纸上很留意这位领导的签字,发现跟回信中的签字一模一样:姓的字体较大,名字越来越小。在所有参加的公共活动中,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一次。
今年他又做了一件让自己非常得意的事,就是律协直选。
长期以来,唐吉田一直感觉没找到“组织”。他有一些想法,有关于制度的,也有关于其他的,想找个人交流,但在延边要实现这个想法“比职务晋升还要困难”。
这些想法到了他在延边州检察院任职的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他发现,很多违法的背后,都有“公权对公民私权的侵犯”,而他作为检察官却只能维护本已强大的公权。
于是,他辞去检察院的工作,揣着一张律师资格证书,开始闯天下。他从延吉跑到上海,又从上海跑到深圳,但自己寻找同道中人的事情,始终像自己的业务一样,没有多大进展。
直到2007年7月份来到北京,他才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让自己“如沐春风”。这里每天都在开放着他梦寐以求的各种讲座和论坛,论坛上的各种发言,与自己是如此投缘。
“我得找机会接触这些人。”初来乍到的唐吉田,开始努力融入这个圈子。2007年11月,他找到中国律师观察网的赵国君,把自己的名字挂在一份由茅于轼牵头的有关取消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吁书上。这种呼吁书由于事涉重大,又由大家牵头,往往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一个陌生的名字要“混个脸熟”,这往往是一个很有效的形式。
经过半年时间的用心铺垫,唐吉田对这个圈子逐渐熟悉,圈子里的一些事他开始深度参与,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律协直选。
今年5月底,唐吉田首次参与律协直选的会议。他认为,对待律协,最初一定要把态度鲜明地端出来,这样后来才能进退有余。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支持釜底抽薪的直选方案,反对把这次活动办成一个弹性十足的论坛。
此后,唐吉田没有落下一次会议。在这部分人中间,一种“找到组织”的欣喜涌遍全身。
在5月底的那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程海,咄咄逼人的感觉扑面而来。“用东北话说就是‘狠叨叨的。”他不由得想起老人们经常说起的一句谚语:“‘地包天(程海嘴的形状)难斗。”
作为直选活动的三个联络人之一,唐吉田有一段时间面临来自司法机关和律所的双重压力,从内心里渴望来自“组织”上的支持,但程海只是对他说了句:“还维权律师呢,这点压力都不能排解。大家哪有时间去帮你,跟他们周旋就是了。”
当时,在呼吁上签名的很多律师都面临着与唐吉田类似的困境。有些律师在压力下选择了疏离,这一活动正面临着从内部被瓦解的潜在危机。
唐吉田推己及人,认为在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能只一味地强调冲出去,还要能够稳住人心。他提醒程海,不要总是不分场合地驳老朋友的面子,免得让别人感觉“这帮人也不比律协那帮人好到哪儿去”。
程海对此颇有微词,批唐吉田“人情大于原则”,就会“和稀泥”。唐吉田则批程海“在伤了敌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人”。
直选活动的另一位联系人张立辉,就曾因为自己分管的会员发展工作进展缓慢,被程海直白的指责“伤”过。
张立辉:“减压阀”
从初中时起,张立辉就隐约觉得自己长大后要做律师。
张立辉总是和善地笑着,带着十足的书生气。由于家境较好,他从小到大一直比较顺利。1996年大学毕业,1998年拿到律师资格证书,随后在杭州找了家律所,一直做到2004年。
那一年,张立辉来到北京,与另外两人一起,创办了该律所驻北京办事处。2005年,他加入北京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开始了自己公益诉讼的旅程。
2006年冬天,他去黑龙江参与一起公益诉讼,在哈尔滨坐上一辆私人捷达,连夜赶往开庭的双鸭山。车驶出市区80多公里,停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四周一片漆黑。车上两人开始对他出言不逊,进而辱骂和恐吓,他试图打开车门,发现车门已被锁上。他的心沉到了最下面。
当时,他6岁的女儿刚上一年级,还在杭州。他过一个月就要回趟家与女儿团聚,一个月不回,女儿就会哭闹不止。
他说自己当时还算清醒,好在对方只是劫财,他按对方的要求付了500块钱,劫匪就放他下了车。这件事之后,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天黑后绝不赶路。
直选一事,他当初并不特别在意,只说这是志愿者做的事,抽空做一下就是。结果他负责的发展成员一事进展迟缓。程海对此非常不满,说张立辉缺乏行动力,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说过几次。这事让张立辉很有触动。他说律师出于职业的习惯,往往动嘴多,动腿少,有时候流于空谈。此后,他要自己多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局面终有改观。
张立辉刚开始并不赞同走直选路线,认为还是不要激怒北京律协。并主张修改发给律师的短信内容,认为其太过挑衅。但从直选一事的发展轨迹看,激烈的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起着主导作用。
唐吉田说他是这个团队里的“减压阀”,舒缓着程海有时拒不退让所造成的紧张空气。在有些时候,两人还要联合起来,把偏离规则的程海一起拉入议事规则里。有一位同行评价张立辉,说他的风格有点像印度的圣雄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