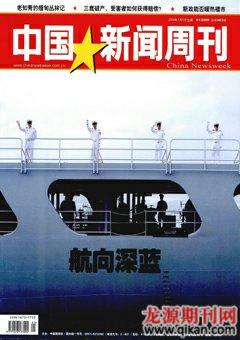随笔
有没有阳光温暖过卑微的你
每天去电影学院蹭课回来,都会路过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这么一群人,夜晚住晒不到阳光的地下室,白天则坐在北影厂门前的台阶上,从日出,到日落,耐心又焦灼地等待着机会的降临,渴盼着在某部电影里饰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哪怕,只是一个侧影,一具尸体,一双眼睛,一声叹息,或者,被无情的剪辑师,一剪刀下去,只剩半个臂膀。
他们在台阶上,边期待着门口有某个导演出来,边无聊地打着哈欠,说着笑话,骂着粗话,或下一盘不知道有没有结局的象棋。他们衣着黯淡,神情沧桑,像日积月累,阳光下灰尘满面的石像。他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一个群众角色,会疯狂地拥挤,争抢。但等待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则会谈起家常。这样的闲聊,于他们,是一种比电影更温暖的慰藉吧。
曾经在中关村一家电子产品店里看到过一个男孩,大约18岁吧,看到我经过,很温柔地喊我“姐姐”,又将我引至店中,倒水给我。我看一眼店内不多的相机样品,打算转上一圈便找理由走人。转至一款相机前时,我问,能给我介绍一下这款的功能么?他忽然就红了脸,低声地朝我道歉:对不起,姐姐,我,我是新来的,还不太懂,您先坐下等等,我们很专业的同事马上就过来为您讲解,好吗?
片刻的犹豫之后,我客气地向他道别,撒谎说:有点事,一会儿再过来看看。他却是一下子被我弄慌了,低低地恳求我:姐姐,再坐一会,就一会,好吗?我们店里肯定有您喜欢的相机,即便是没有,也可以为您去别家调货的。
我也低了头,不敢看他的眼睛,疾步走出店门,直奔走廊尽头的电梯而去。而他,却是不舍不弃地,跟在我的后面,一声声地,喊我姐姐。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站在门外的他,一脸的忧伤与失落。
忆起在北京的798艺术区,看到过一只纯种的波斯猫,不知道悄无声息地在我身后跟了有多久。我只知道,当我无意中回头,看到它在冰冷的傍晚,被风吹起的脏兮兮的毛发,突然间心内涌起无法抑制的悲伤。
我终究没有将这只流浪猫抱回去。我只是从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瓶酸奶,放在它的面前。它温顺地看我一眼,而后低头去喝酸奶,每喝几口,它就会停下来,蹭一蹭我的鞋子。我就在它低头的时候,悄悄走开了,一直没有敢回头。
这个城市的阳光,日日普照,分给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温度与热量。可是,当我走在路上,看见那些卑微的生命,我总是希望,有足够的温暖,将这些同样具有尊严的生命,温柔地环住。
文/安宁
公交车上
我们镇上有一个远征军的老兵,1943年他被抓壮丁,走到市里,用了两天的时间。现在不一样了,不说出远门,到责任田也很少完全靠腿的:年轻人有摩托车,老年人有自行车或三轮车。我的一个亲戚,他们村在外地打工发财的人很多,有一回他到责任田,一路上碰到十几辆高级轿车,有奔驰、宝马,也有奥迪。
城里赶路自然全是公交车。据我个人对公交车的观察,这个移动的空间可以是卧室、书房、客厅、办公室,甚至可以是水房及其他。
公交车上睡觉是最常见的事,有仰躺的,有趴伏在前座靠背上的,也有站着睡的,让人常常想起红军们的连续行军。既是睡觉,不免要打呼噜,我见过最厉害的一位仁兄,呼噜声完全压倒了发动机的声音,当然有人怒目而视,但更多的目光充满着尊敬:他真是好心态、好福气。
看书和玩游戏也是公交车上常见的事,坐着看书或玩游戏是不值一提的,我印象里的读书人都是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仍能高举手机或者阅读器的达人。修指甲、理头发也都是小事,但我在430上看见一个姑娘,把自己的头发,从立水桥北站打开,捋一捋再扎上,再松开,再扎上,一直到炎黄艺术馆还没有最后搞定。
做手工的不多,但不是没有,我见过扎纸花的,卷纸窗帘的,我本人有一回特别着急,还在车上整理过文件,一百多页,一页一页硬是在车上给捋得整整齐齐。
我在62路上听到过一次水房歌唱家的歌唱,那是一个姑娘,估计不到20岁,正是爱歌唱的年龄,她从小营桥上车就开始唱,唱到对外经贸大学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同伴——另一个姑娘拉拉她的袖子,因为很多人都在看她了。但是她毫不在意,一直唱,我到平安里路口南下车的时候,她还在唱,不知道能不能唱到终点,因为我看见很多人看她的目光都有点忍无可忍了。
公交车上似乎不该做这么私人的事,但难道能规定除了思想动什么都不能动?这个问题比较难。不像我在部队的时候,大家往141车厢里一塞,干部说唱歌,就一起唱歌,干部说打牌,每班都立即就掏出两副牌来。
但在国内坐公交车总比国外强。陈逸飞在意大利乘公交车,车到了站司机却不开后门,他当时还不怎么会说意大利语,只好哑巴吃黄连,眼睁睁地看着车又开了。等他总算发现中门才能下车的秘密,却又因为不知道下车要按门铃,结果车到站后,“任由我如何用肢体语言和眼神向司机示意要下车,司机仍‘铁面无私地把前后门一关,把车开跑了。”
语言不通,眼神有什么用?又不是搞对象。
文/李落落
请柬猛如虎
年终岁尾之际,如我所料,请柬也随之增多了起来。
之所以能够预见,是因为年终赴宴已成为了惯例。该结婚的结婚,买了房子的人,到此时也已装修完毕,要赶在年前入住;以前曾在这个时段结婚的同学朋友,生孩子也大都是在这个时段,故而,总会有喝不完的满月酒、百日酒、周岁酒……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曾经同时参加了六场名目不同的酒宴,对于不善于交际、人际圈子很小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每到一处,都是随便吃两口,未等菜上齐,更等不及新人前来敬酒,就得匆匆告辞。彼时,主人的脸上往往会有佯怒的神情,一再声称这是看不起他,于是又一再解释,连声道歉,说尽好话方才得以脱身。等到走出喧闹憋闷的酒楼,被街上的冷风一吹,方才想起自己是花钱消费的顾客,却反要赔尽小心地讨好商家,哪有这种本末倒置的道理。
我5岁读书,年龄在同学中是最小的,我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已有“童婚”的同学向我发请柬。而每次收到请柬,提前一周左右,就会有一种心理焦虑的症候,总觉得有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在心里挂着。这样的循环,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按理说,到了我今天这个年纪,身边的同学朋友,未婚者已经屈指可数,生孩子的也已生得差不多了,我收到请柬的几率应该很小。换在以前,二十年,小媳妇都熬成了婆,我也应该熬到头了。
可就在我对着同龄人的背影刚想长吁口气的时候,身后的另一拨又赶了上来。从早些年开始,我就不断接到朋友的侄儿侄女辈的结婚请柬,若是隔上几年不见,偶尔遇到,对方就会叫怀里抱着的孩子叫叔爷、舅公,听得人心惊肉跳。再者,如今的离婚手续简便,几十块钱,几分钟,一切就已搞定,我又无奈地陷入到了一个赴二婚、乃至三婚宴的轮回当中。
如果以为请柬多是朋友多的一种体现,那就大错特错。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颇为离谱的二婚宴:某天我上朋友家,遇到他家隔壁租店做服装加工的裁缝在发结婚请柬,看到我这个主动撞到枪口上的猎物,他大笔一挥,一边问我的名字一边写请柬,而且理由听起来还挺充分:“你们都是朋友,请了他不请你也不好。”脑子一时短路的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去拒绝。等到了喜宴现场一看,天啊!整个酒楼就像是个菜市场,酒席足足摆了近百桌。于是,我就像意大利光头裁判科利纳在自传中写的那样:“我站在千百人中间,感到的只有孤独。”
文/青丝
不可能被爱上
男人总是说女人很笨。韩国喜剧片里,常常便有男主角气到吹胡子瞪眼睛,骂女主角:“你怎么这么笨啊!”他对她那么好,她却从来不领他的情。不喜欢她干吗对她这么好?笨。
同类型的笨女人,台湾偶像剧里更多。有个男人为她痴来为她狂,她却作无辜状,忽闪眨巴着大眼睛:“怎么可能!人家话都没跟他说过两句。”
这么不识相,放中国古代,是羞红的一张圆月脸:“小女子何德何能……”放乡村爱情,就装斯文吧:“看你说的,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哪会看上俺那!”
不知道是真谦虚还是假客气,反正,被某个男人喜欢虽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一旦说穿,女人的第一反应总是抵死不承认。越是靠谱的喜欢,越要抵赖得贞烈一些。
我的一个女友被邀去看电影,铁板铮铮的约会邀请,她却仍在那上演丰富的内心戏:“电话里他的语气好随便,不够慎重也不够深情,也许只是普通朋友的相邀——哎呀,他会不会和朋友打赌说一周之内请到我看电影?”她就是不相信,凤追凰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女人的感情账算起来很有心理学基础:如果我一开始觉得这事一点没戏,最后却成了,那有多开心啊!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有戏,最后没戏固然伤心,事成也不见得有多幸福。就好像我身边很多女孩子都已经做好金融危机年底单位不发年终奖的心理准备了,其实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消息。但女人就是喜欢置死地而后生的感觉。掰着花瓣,他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怎么?他喜欢我!一定错了。重新再来一遍,辣手摧花无数。
有时想想也真矫情。我从前一再奉劝自己,桃花来的时候千万要沉着优雅,要大家闺秀,不要小家碧玉。可轮到自己碰上这事,还真的一筹莫展。该怎么说?谢谢,还是承蒙青睐、三生有幸?难道说,这厮真有眼光?想来想去,我只能摇摇手:“不可能啦!”
原来抵赖才是处理感情事务的一键式服务。难怪明星们喜欢对记者说:“普通朋友啦!”
我后来发现还是港剧比较诚实,很少搞女人装笨的套路。感觉来了,女人思思春,像梁咏琪的歌里唱的那样:钟意他/他的胡碴/幻想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想得真远!虽然,常常未必能走到最后。
现代都市女子大都聪明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情爱雷达随时接受各种信息。别说一个男人爱自己了,多朝自己看上一眼,灵敏的雷达都会启动蜂鸣。所以我们不可能傻到被爱上也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容自己装傻——可惜有时候雷达就是没反应。实在是像《西厢记》里唱的:有心争似无心好。
文/上上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