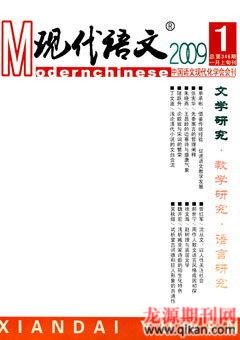试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悲剧意蕴
刁国利
摘要:高明作南戏《琵琶记》有意改变传说中蔡伯喈的负心汉形象,无意中却加深了这个形象的悲剧意蕴。他恪守封建纲常导致忠孝不能两全的痛苦,他的懦弱和贪婪致使他在“三不从”的外在压力面前委曲求全、顺其自然。是时代的必然和自身的弱点使他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独立意志,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情非得已的负心汉。
关键词:《琵琶记》蔡伯喈负心忠与孝贪欲
高明本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态度来创作《琵琶记》,其创作本旨显然是宣扬忠孝观念,所谓“只看子孝与妻贤”。然而,由于文本的丰富性,由于道德观念从着眼于集体到着眼于个人的倾斜,今人往往更容易看出美丽的道德面纱背后的痛苦和矛盾,以及主人公蔡伯喈“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的尴尬处境和一生不得自由的悲剧命运。蔡伯喈悲剧的造成,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封建纲常强加给他的二难选择,在忠与孝中痛苦地挣扎;一方面也自有其性格根源,即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贪欲,两者互为表里使得他虽矛盾痛苦却仍然安于“三不从”的现状。
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渗入到各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三纲五常”中包含着令无数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既然要以君为纲,就应从忠君事君出发,舍小家以全大家;但以父为纲又规定儿子必须听从父命,应孝敬父母,应牢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在封建纲常内部便产生了不可兼容的矛盾。
蔡伯喈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仕人,他自恃才高,有心于功名,却不得不顾虑重重,如第二出:
[瑞鹤仙]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沈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具尽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
他想蟾宫折桂,却又念及父母年老,恐怕两处耽搁,忧虑无人事亲。这也构成了悲剧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辞试不从。在蔡公的坚持下。他被迫选择了光宗耀祖,“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但这不代表矛盾已经解决。在蔡伯喈金榜题名之时,他又陷于两种压力之中:一个是皇恩浩荡,想要辞官回乡便是不忠,官拜议郎便是不孝;一个是洞房花烛,心有所愿,理所不容。这两种压力将他推向博取功名,蒙上不孝的罪名。由此,矛盾的火花再次碰撞。蔡伯喈想两全其美,在地方事亲不得实现之后,他就时时刻刻在夹缝中生存,永远遭受良心上的谴责。在第二十一出[一枝花],二十三出[喜迁莺]中可以集中看到他倍受煎熬的心理:
[一枝花]闲庭槐影转,深院荷香满。帘垂清昼永,怎消遣?十二阑干,无事闲凭遍。困来湘簟展,梦到家山,又被翠竹敲风惊断。
虽然是豪门相府,庭院幽深,风光无限好。但却心事重重,度日如年,无从消遣。遍倚栏杆,更见内心慌乱、心神不宁。
[喜迁莺]终朝思想,但限在眉头,人在心上。凤侣添愁,鱼书绝寄,空劳两处相望。青镜瘦颜羞照,宝瑟清音绝响。归梦杳,烧屏上烟树,那是家乡。
愧疚之心,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挥之不去。本是萧史弄玉之配,却更添愁绪。父母日夜期盼云中锦书,而他自己无能为力,也只好借琴抒愤。辞官不从、辞婚不从将蔡伯喈推向悲剧的边缘。
尽管封建纲常内部存在着忠与孝的矛盾,但并非每一个步入仕途的人都会陷入二难境地。有的人选择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也有人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宁愿做“不识字烟波钓叟”;但更有人不知道如何选择,只会安于现状,安分守己,不忍舍弃亲情爱情,却又无力反抗。蔡伯喈系此种人。三次让“不从”变为“从”的机会均被他错过,未能遂心,如第十三出中所说“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被利绾名牵,热心于功名。在父母严命之下,被迫出行,又于飞黄腾达之时,迫于功名富贵、皇威权势,无力回天。内心的懦弱与贪欲使他只想顺其自然,只在意识中希望两全其美,不敢抗争,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只好在外界压办大到一定限度之后,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自以为一切与己无关,都是时势使之然,自家是最终的受害者。
这在第四出蔡公逼迫伯喈赴试中,稍露痕迹。他一出场便唱道:
[一剪梅]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闹。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闱,难舍亲闱。
从中隐约可见他有志于仕途,亦想“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优柔寡断的他又顾虑重重。他在郡中辟召之时“自家力以亲老为辞”,但可笑的是,似乎未见成效,自言自语“这吏人虽则已去,只怕明日又来,我只得力辞”。倘若他有决绝的意志,宁肯为了“孝名”而抛弃“功名,以他的才华和封建纲常做论据,对方一定理屈词穷。从这两句话中又可见他懦弱的本性与阿Q式的自我安慰。他“怕”字不离口,“只得”二字又显出他的无奈。
在力辞考试不得之后,他又说道“如此,卑人没奈何,只得收拾行装便去”,唱道“只恐锦衣归故里,双亲的怕不见儿”。他总是担心恐惧,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态。
第五出中赵五娘指责他抛弃父母时,他又有一番个性化的解释。
[前腔]我哭哀哀推辞了万千,他闹炒炒抵死来相劝。将我深罪,不由人分辨,只道我恋新婚,逆亲言,贪妻爱,不肯去赴选。
这一段话形象地勾勒出了伯喈的软弱无能。内在的性格弱点加上忠孝两重枷锁使他必然寻求解脱之路,自欺道:“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在第十二出伯喈拒婚中,他以“妻室青春”,“纵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血”,“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虚伪地推辞,以致第十三出中媒人回报牛丞相:“乔才堪笑,故阻佯推不肯从。”伯喈内心还是期望攀龙附风,不敢与权贵做正面冲突。在第十五出上表辞官辞婚之时,语言又多做作,并且未提及最有力的证据“妻室青春”,只是打着官腔推辞“念邕非嫌官小”,“重蒙圣恩,婚以牛公女。草茅疏贱,如何当此隆遇”,并未显出真心真意。他又力以亲孝求辞官,但这可以用最有力的对立面——事君来驳回。从中可见他的懦弱,辞婚辞官不成,他又只能顺从地接受。终日自怨自艾。
成亲之后,他有回乡之意,却又屡屡不敢提及。在第二十三出中,当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与院公吐露心声时,院公说道:“男女每常见相公忧闷不乐,不知这个就里,相公何不对夫人说知。”看来,连院公都认为他应该大胆地说清,私下怨叹,徒劳无益,而且从牛小姐的性格看,他早些说出来,牛小姐也会站在他这一边,可是他连试着说出来的勇气都不俱备。后世多有人指出《琵琶记》情节不够严谨之处,如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就曾指出蔡伯喈何以至于考中状元三年不与家中联系,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从可能是作者疏忽的角度出发,仅从剧本本身来看,这不正是他软弱性格的一个极为明显的体现么?
牛小姐再三盘问,他才吐露实情。第二十一出中,夫妇二人借琴纠缠,他却吞吞吐吐,不说明白,只是话里藏机,恨无知音。第二十九出中牛小姐盘夫,他又躲躲闪闪,将牛小姐气走:“由你,由你。待我不劝解你,你又只管闷;待我问你,你又不应。我也没奈何,相公,夫妻何事苦相防?莫把闲愁积寸肠。正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屋上霜。”伯喈自言自语被她听见,才真相大白。但他又阻拦她去禀求父亲,怕被驳回。殊不知这样还有一线希望,远比郁郁寡言不去争取强,只是寄希望于天降奇缘,与父母团聚,一夫二妻,两全其美。
综观蔡伯喈的仕途之路,无论他为他的不孝找到多少条理由,无论高明用多少章节来抒写他内心的愧疚、对家乡父母妻子的思念,在现代读者的眼中,他仍然难逃一个负心郎的罪名,而这就更加显出他的悲剧性。
蔡伯喈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有他独特的一面,然而从他身上又可以看到千千万万个仕子的影子。他是具有普遍性的情非得以的负心汉。他所遇到的二难选择,几乎是每个仕子都要去面对的,只是高明将他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科举之路可谓是布满了荆棘,仕子们一路风风雨雨走过,受尽折磨。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有《张协状元》一剧,写一介寒儒,依王贫女之力,上京赶考。考中之后,为了将来,他忘恩负义,置王贫女于不顾,甚至想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民间亦流传关于陈世美的故事,千百年来张协、陈世美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负心汉形象的典型,而经过高明重新塑造的蔡伯喈则被认为是全忠全孝的代表。但三人实无差异,有着相似的历程,只是张、陈二人的负心故事更赤裸、更露骨,而蔡伯喈的故事中增添了复杂内心世界的描写而己,展现出恶劣人性中善的一面。知识分子在刚刚捧起书本时已注定了他将来的道路。逆,则穷困潦倒一生,被人耻笑;顺,则高官美爵、娇妻美妾俱有,不能自主。在仕宦之路,伯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迷茫,一样无措。他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惆怅,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