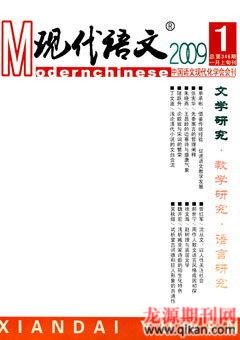意象营造的巅峰
林倩婷
摘要:《原野》是曹禺话剧“生命三部曲”之最,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为成功、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曹禺以他宏放的戏剧观念、多方位的戏剧艺术实践,借鉴中西戏剧手法,用凝练的笔触,着意渲染悲剧气氛,突出意象的营造,达到了现代话剧意象营造的巅峰。本文试图通过浅析《原野》视觉和听觉意象的营造两方面,理解和把握作者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一个经典的悲剧环境。
关键词:曾禺《原野》视觉听觉意象
一、引言
曹禺,原名万家宝,他是一位大师级的剧作家,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个符号,是使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为话剧剧场艺术——舞台意象营造带来新曙光的改革符号。在他的话剧作品中,1937年写成的话剧《原野》——人们称其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之最,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为成功、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
曹禺的经典话剧《原野》,把焦、仇两家两代人在十年间的恩仇爱恨高度浓缩在短暂的时空里。通过仇虎的报仇雪恨行为,了结了两家的刻骨冤仇,演出了焦、仇两家无一男人幸存的悲剧。在这部悲剧里,曹禺以他宏放的戏剧观念、多方位的戏剧艺术实践,借鉴中西戏剧手法,用凝练的笔触,着意渲染悲剧气氛,突出意象的营造,达到了现代话剧意象营造的巅峰。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在狭小的话剧舞台空间里,《原野》把主人公人物的思想、信念、意志、道德、欲念,把峥嵘的“生命的蛮性”、“复仇”、人与人极爱和极恨感情交织的主题,甚至是把作者本身的情感,全部融为一首诗,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试图通过浅析《原野》视觉意象的营造和听觉意象的营造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作者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一个经典的悲剧环境。
二、视觉意象的营造——奠定环境悲凉的基调
话剧《原野》的序幕,一个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的压抑年代,一个带有血色、野性、蛮荒、神秘色彩的北方农村,一场激烈复杂的心理搏斗,一出农民复仇的血泪悲剧即将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天,一片愁云惨雾的原野”场景环境中缓缓展开。发荒的暮色,怪相的黑云密密匝匝地遮满了天,苍苍茫茫的原野是沉郁的,上面长久地回荡着火车那一声撕心裂肺的长鸣。这种沉郁的气氛,为全剧奠定了悲凉的基调。
舞台背景环境是阴森、诡谲、恐怖的,而且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暮秋的原野,面目狰狞,密布着幽暗的赤红色的云;黑林子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矮而胖的灌树在风起时,如一堆堆无头战鬼般黑团团的肉球;厚雾里不知隐藏着什么……这些拟人化的阴沉、恐怖景物象征性地把封建势力统治的黑暗现实形象地展现给观众。这样的视觉营造,扑面而来形成了一种压抑、躁动、神秘的氛围,一种混合着郁闷、焦虑的复杂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作者赋予舞台场景不同的个性,烘托出冷酷、残忍的悲剧气氛,从而映衬出主人公的内心变化。譬如,巨树的出现:“在黄昏里伸出乱发式的枝桠”,“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是那样严肃险恶地矗立当中,仍是一个反抗的精灵”。巨树,正是主人公仇虎的写照:粗犷、丑陋、强健、抗争,在剧中始终与仇虎心态融合统一。又如“巨树前”铺着的“直伸到天际的两根铁轨”,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与幸福的向往和希望;“黑幽幽的森林”则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将人类网罩其中,这样的意象营造暗示了旧中国的黑暗社会是人间的地狱,像一只看不见的黑手,肆意虐杀着无辜的生命。
三、听觉意象的营造——加重渲染沉郁苍凉的悲剧氛围
与视觉意象结伴而行的是听觉意象,它有助于加重渲染沉郁苍凉的悲剧氛围。
《原野》的舞台音响效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序幕一拉开,就传出了仇虎脚上铁镣的响声,他举起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的音响;结尾,仇虎未能走出“黑林子”,戏剧在仇虎用力掷出铁镣的“铛锒”声中收结。
《原野》还极力渲染回荡在原野上空的声音:尤其是羊群哀伤的咩咩声,风吹电线杆发出的呜呜声浪,野塘里的青蛙断续的鸣叫声,乌鸦哀号的声音,蝉鸣声,火车“吐兔图吐、漆又卡叉”的声音,白傻子那似吟似唱的神秘歌声,从焦家传出的“仿佛就是从那菩萨的口里响了出来的”幽深的钟磐和木鱼声,啄木鸟剥剥地发出空洞的啄木声,再加上几声零星的枪声、惊雷声、钟摆声……这些音响看似杂乱无章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原野的上空,幽郁而苍凉,沉郁而悲壮,黑暗而恐怖,却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到了第三幕,除原有的自然之声更加凄厉外,还增添了恐怖的鼓声、焦母招魂的呼喊声、催命的枪声,还有仇虎神秘的歌声。这时鼓声是多重奏中的主旋律,是声觉形象之一,虽然它单调、微弱,但和焦母不断缠绕林中的叫魂声夹杂在一起后,却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了。与此同时,剧中民间小调的不断重复运用的独特手法,即仇虎神秘的歌声“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阴风吹了个女鬼来”来烘托、渲染恐怖气氛。仿佛阴风四面袭袭,阴沉沉地吹起,幽灵在呜咽在哀嚎在低声应和,鬼气沉沉、哀哀凄凄。有人曾对此高度评价过,“民间小调以一种富于感召力的方式被用来合成戏剧动作和戏剧主题”,“虽然被融入戏剧动作之中,但又存在于别一种感情层面上”。
四、视觉意象与听觉意象的完美契合——重复出现且有渐进变化的表现手法
《原野》的环境描绘,不管是听觉或视觉的都依据剧情发展的需要通过重复而有变化的手法,随之加重描述的分量,使之成为戏剧发展的外在驱动力,使剧情前后呼应,自然协调,增强感染力,于规定的环境气氛中使演员与观众达到和谐的共鸣。剧中重复最多的是羊群哀伤的咩咩的叫唤声,野风吹过电线杆的呜呜声,池塘里青蛙的鼓噪以及火车隐微的汽笛声等。例如,对蛙声的描法,先是序幕中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随着懦弱的大星的登场,“塘里的青蛙又叫了几声”;焦母出现时,“青蛙在塘边鼓噪起来”,烘托了主人公出场的气氛。又如,序幕中电线杆“呜呜地响”,第一幕“暮风吹着远处的电线杆,激出连续的凄厉的呜呜声音”;到第二幕仇虎与焦母正面交锋时,“风吹电线呜呜的声响,像是妇人在哀怨地哭那样幽长”。再如,巨树发出的声响,“叶子哗哗地响”;小黑子、大星遇害后,仇虎陷入内心谴责,“白杨树伸出巨大如龙鳞的树叶,风吹来时,满天响起那肃杀的‘哗啦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隐喻了仇虎内心惶惑惊恐的情感;当仇虎与金子陷入绝境时,“一阵风吹来,白杨树叶‘哗哗地乱嚎”。最后还有,乌。鸦的叫声,第一幕开始时“偶尔有一两只乌鸦在天空飞鸣”;接着“乌鸦在天空成群地呼唤”;焦母出现时,“外面雾里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凄惨地呼噪”,因此,乌鸦成了焦母幽灵般的形象的意象对应物。
可以看出,这种渐进而有变化的手法,随着悲剧气氛的加重,慢慢加重描述分量,让观众产生移情作用,更自然地融入特定的环境与剧情中。
五、结语
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中认为:“美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话剧《原野》十分注重营造视觉和听觉的意象,十分注意描绘戏剧环境,烘托戏剧气氛,不仅视觉之“戏”有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艺术魅力,而且音响效果亦有弦外之音、音外之景的审美效果。可以说,作者曹禺在借鉴西方话剧技巧的同时结合了中国民间话剧艺术,成功地进行中西融合和再创造,超越了原本单调的歌唱、话语等手段,转而利用舞台背景(在剧本上体现为景物描写)和音响效果,使其剧作更具有表现力,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