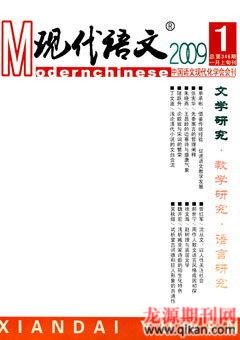困境中的探寻
丛坤赤
摘要:在《城的灯》中,李佩甫一方面既把城市作为现代化努力的方向,又直陈城市的污浊肮脏,另一方面他既从乡土文化中寻求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生命意义,又直面乡土的黑暗与颓败。在对城乡文明的双重认同与质疑中,他既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又表现出对理想的迷惘。
关键词:李佩甫《城的灯》城乡交融探寻
“乡下人进城”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热门话题,与多数这类文本所采用的苦难叙事不同,在《城的灯》中李佩甫力图淡化城乡之间的对立,而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进行重新思索。在对以冯家昌与刘汉香为代表的两条不同进城之路的双向书写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部小说对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城乡社会有了更准确和深刻的表现。
一、生存困境中的抗争与无奈
在一次访谈中李佩甫说到:“近年来,我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一直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发现我错了,贫寒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更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贫穷(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对人的戕害甚至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冯家昌是极有代表性的。”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财富观,李佩甫对冯家昌有了复杂的情感态度。
冯家昌的童年是在以“穷”为核心的苦水中泡大的,让人心痛的穷苦经历培养了他既好胜坚强,又充满仇视怨恨的复杂性格。在“这是一棵会跑的树”的呐喊中,在对刘汉香赠鞋的拒绝中,以及在对“人,一个人,手,两只手”的生活信念的追求中,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那既自尊又自卑的独特性格。这种性格既夹杂着人格意识初步觉醒的现代因素又带有野蛮报复的原始色彩。少年冯家昌在屈辱卑贱的生活中朦艨胧胧地意识到人应该活得像个人样,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人”他并不清楚,只有当国豆支书把它落实为“四个兜的国家干部”时,他的人生目标才逐渐明确起来。然而这一目标的确立却意味着他从对一种等级制度的反抗转化成对另一等级制度的依附。当他拿着利用支书手中的权力而获得的通行证向城市挺进的时候,他人性扭曲的悲剧命运就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因为从那一刻起人已经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冯家昌性格中的现代诉求逐渐丧失而其中潜藏的恶却逐渐暴露出来。
基于对城乡二元结构中乡下人生存困境的清醒认识,李佩甫没有过多地谴责冯家昌,而是尽量地把其堕落原因归结于外在的生存困境。事实上除冯家昌以外,小佛脸、红楼三绝等人的经历都一再证明冯家昌的种种丑恶行为在当今社会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有它的普遍性、有效性,他的悲剧既是人性自身的悲剧更是生存困境制约和压抑的结果。所以当冯家昌背叛了爱情要接受灵魂拷问时,作者却借刘汉香之口说到:“这样一个被‘仇恨包括着的人,他一旦离开了屈辱,还会回来么?”对不会回来的原谅正是李佩甫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体现:他既要拷问出人物灵魂中的恶来,更要拷问出恶中之善来——在冯家昌的人生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趋利本能和作者对其合理性的认同。离开一种行为产生的环境做凌虚蹈空似的评判是毫无意义的,在作品中李佩甫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却并不满足于作抽象的人性解剖,他更热衷描绘的是人物背后的社会现实,他最执着探寻的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如何走上现代化之路。
对冯家昌的原谅并不代表对他的赞赏,作者在承认物质生活重要的同时,并不认可他所采取的手段。成功之后的冯家昌试图用金钱去赎罪,却并不能减轻心灵上的负罪感,在作品结尾,他试图返乡却已经无家可归。对于城市来说,冯家昌只能做一个边缘人;对于乡村来说,他又因背叛而被拒绝回归。在物质上他成功了,在精神上他却失去了家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返乡之举是在酒后进行的,酒醒之后他还会放弃副厅级干部的身份继续返乡之旅吗?应该不会吧。因为他的堕落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堕落,是有计划、有谋略、刻意为之的,因此这种返乡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虚假的。正如丁帆先生所说:“现代城市人还毕竟没发展到逃离城市的奢侈情绪,所谓返乡只不过是在城市呆久了,精神上所需要的调节与补充罢了。”冯家昌感到恐慌、孤独却未必会真正忏悔,他绝不放弃对城市的追逐,哪怕它是一座物质的空城,正是在被城市与乡村双重拒绝而又执迷不悟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进城之路的失败。
二、城乡二元对立的融合与困惑
作为一个有着浓厚乡恋情结的作家,李佩甫既渴望乡亲们能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富足的生活,又绝不甘心让他们去做城市边缘人,在对冯家昌予以最后一抹怜悯与鄙夷之后,他便把探寻新路的希望寄托在刘汉香身上。刘汉香是一个将现代与传统兼容并蓄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又有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的身影。她坚守于黄土地,同时又不保守僵化,有着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渴慕与追求。她不负众望,把乡村变成了城市;但遗憾的是她自己却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的欢乐就突遭横祸香消玉殒了。作者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结局呢?他为什么要让平原上最圣洁的女子死得如此惨不忍睹?带着疑惑,我反复阅读文本,通过一次次的文本细读我终于明白刘汉香的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非常“及时”的。
当刘汉香下决心去探寻一条新的进城之路后,她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神化”,正是这种“神化”一步步剥夺了她的生命力。当刘汉香决心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时候,她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打发”了,“打发”成一个没有性别特征的神圣化的人,只有这样她才会拥有必要的权威和号召力。因为在一块有着极端权力崇拜传统的土地上,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权力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像卸任后的国豆马上变成了一个靠墙根晒暖的小老头。当乡亲们对刘汉香的致富计划表现出茫然和麻木时,正是神圣化使乡亲们“信”了刘汉香,像羊群一样跟着她走。当致富计划初见成效后,刘汉香又要面对果实被无穷无尽地“礼仪化”的尴尬。渗透着自己心血和汗水的果实被无端地“礼仪”着,自己不但不能生气反而要笑脸相迎,这种极端压抑个人正常情感的超凡能力通常情况下只有两种人可以做到:一是冯家昌似的城府极深又怀有不可告人目的人,再就是刘汉香似的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无欲无求的神化的人。正是在与老百姓以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毒气”与“恶意”抗争的悲怆中,刘汉香迫不得已地让自己变“大”、变“神圣化”。
刘汉香的神圣化过程也是一个生病的过程。在作品中她每神圣化一步,乡亲们就会感叹一次:“她有病,病得不轻。”“有病”的意象让我们看到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数启蒙者的身影。难道一个人只有“病了”或者“神圣化”了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吗?而一个“有病”者,或者说被启蒙对象认为“有病”的人,又如何能承担启蒙重任呢?正是这种二律背反的荒谬困境决定了刘汉香的死是必然的,如若不死她会怎样呢?是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有一天病好了而放弃启蒙,还是像呼天成一样有朝一日圣像坍塌而暴露出
启蒙的虚假?“神圣化”是刘汉香的悲哀,更是黄土地的悲哀,而这正是无数试图探寻启蒙之路的先行者共同面临的困境。正如县长赵广春所说:“我们都曾经有过真正的理想和信念,只是,做着,做着——我们把它做假了。”在刘汉香的惨死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乌托邦的坍塌。
三、探寻与迷思
在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引言:“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冯家昌从个人及家族利益出发向城市突进,取得了城市身份却扭曲了人格,他所行的是可憎之事;刘汉香从集体利益出发力图变乡村为城市,她的人格从超升到神化直至虚幻,她所行的是虚谎之事,他们都进不得那城。这里的虚谎并非欺骗的意思而是虚无渺茫的意思。刘汉香曾做过这样一个梦:她用一根大盘绳肩着那块土地,坚忍地、吃力地往城里走去,却接二连三地被戴袖章的人拦住要“证”,她先掏出自己的红鲜鲜的心却被拒绝了,不得已她挖出了自己的双眼。这个梦的象征意义是鲜明的,刘汉香带领村民集体进城的心是真诚的,然而她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呢?
刘汉香把乡土变为城市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种植月亮花,作者极为精心地描绘了这种花的培育过程:月亮花不是天生的而是嫁接的,它的母本就是当地野生的青蒿,而且是集三代优良品质于一身杂合而成的全新的健壮的青蒿,它的父本是鸢尾花等四种花的杂交新品,另外还要有热豆腐水做触媒……如此细致入微地写一种虚拟之花的培育过程是大有深意的。李佩甫曾经说过:“我的作品大多是写‘土地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做为‘植物来写的,主要是写生命的丰富性,也就是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多色调。细细品味,月亮花在具象层面是上梁村村民发家致富的手段,在抽象层面上它不正隐喻了作者对城乡融合之路的探寻吗?城乡融合的母本当然是乡村文化,然而并不是乡土中的所有因素都可以纳入城市化进程。刘汉香还做过这样一个梦:当她用一盘大绳拴住那一点九八平方公里的土地往城里走的时候,乡亲们不断放上一些不该放的东西:猪圈、鸡窝甚至虱子。于是她发现那地太死了,那绳又太新了,她的肩在流血,她的心在流血……乡土文化是我们的立足之本,但其中有太多腐朽落后的东西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的启动,鼻涕树事件、寻找美事件正是刘汉香对乡土文化中愚昧、消极成分的摒弃。母本是需要更新提升的,那父本呢?月亮花的父本是四种植物的杂交新品,这是否暗示着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一种完美的现代文明可供我们全盘接收呢?现有的城市文明或者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未必能与乡土文化很好融合,所以我们必须杂取众家之长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父本来。即使母本、父本都找到了,成功融合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配合,而这必将是一个更加漫长曲折的过程。
刘汉香虽然培育出了月亮花,却还没有真正参与乡土的城市化转变就香消玉殒了。她的死是令人哀伤的,但其中是否也隐含了作者对城乡融合之路的迷惘呢?由月亮花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是否真的能让上梁村人不再“心穷”?也许它只不过让老人们胸前多了一方手绢颇似一场闹剧罢了。如果刘汉香知道“花镇”的命名是在送了许多礼之后才申报成功的,她将作何感想?四年之后,县长赵广春借助“月亮花”一跃而升为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与冯家昌是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来的月亮镇是否真的是刘汉香向往的那个“有花”的地方,它与吞噬冯家昌的城市有何差异?面对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李佩甫既有现实的清醒又有理想的迷茫,“城的灯”就在眼前闪耀,却最终也没有人能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