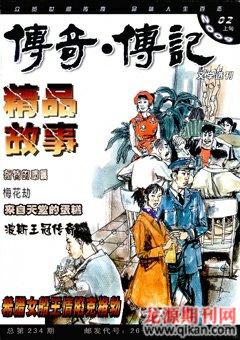希腊女船王情陷克格勃
阿 文
20世纪70年代末,克格勃利用美男计企图控制希腊女船王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阴谋,曾使世界为之一震,影响巨大。西方国家花了很大力气,才使女船王清醒地从情网中挣扎出来,得以结束这桩以政治为目的、以色情为手段的婚姻。
1979年12月14日,是希腊女子克里斯蒂娜申请同丈夫考佐夫离婚的日子。当时她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样一则声明:
……两个星期前,我和谢尔盖·考佐夫在瑞士圣莫里茨离了婚。离婚是在和睦的状态下进行的。按照协议,他获得一艘船。
这则声明,内容简洁,语气平和,一般读者也许不会很在意,以为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离婚声明而已。然而,几乎整个西方政界、经济界、情报界人士则因看到这项声明而长吁一口气——危机终于过去了!
一个希腊女子的离婚,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人关注?克里斯蒂娜究竟是什么来头?考佐夫是怎样和她结婚,又怎样走向离婚的?故事还得慢慢讲起。
女船王的婚事
前两次婚姻的破裂,足以说明克里斯蒂娜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爱情。
197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在莫斯科的某个大餐厅里,正在举行着一个丰盛的鸡尾酒会。来宾们高举酒杯,频频向女贵宾,一位年仅28岁的女郎敬酒。特别是青年男子,一个个在女主人面前,争着大献殷勤。
这位女贵宾就是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
是她长得如花似玉吗?不是。她相貌平平,而且还结过两次婚。但她有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瞩目的光环——她刚刚从她死去的父亲奥纳西斯那里继承了全部遗产——一支庞大的油船队。
奥纳西斯家族在西方世界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拥有一支总吨位为600万吨、共52艘巨轮的大船队。这支船队,在当时甚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海军还要庞大。克里斯蒂娜的父亲阿里斯托特·奥纳西斯因此享有“希腊船王”的称号。在奥纳西斯家的52条巨轮中,有40条是油轮。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为假如把全世界的油船总吨位数分成330份的话,那奥纳西斯便独占15份,与法国全国拥有的油轮总吨位相等。而偌大一个苏联呢,仅占六份。由奥纳西斯指挥的这个世界第三大船队的总部设在蒙的卡罗,而船队则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个庞大的船队在12个国家中有90家公司,与217家银行有业务上的来往。可以想象,这支船队对西方国家石油供应起到了生死攸关的作用。它担负着把中东的原油运往世界各地的任务,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从中东进口的大量石油均由其承担运输,因而对它信赖性很大。因此可以这样说,奥纳西斯船队的一举一动,直接牵动着世界石油工业和运输业的神经。
“希腊船王”不仅拥有庞大的船队和数额达20亿美元的家资,而且还有一个供奥纳西斯家族游乐嬉戏的岛屿。这个有800平方千米面积的小岛叫斯科皮奥斯岛,在世界地图上可以找得到。斯科皮奥斯岛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在战略上也有重要意义,它是扼制地中海北端的战略要地。
1953年,老船王奥纳西斯斥资2000万美元,建造了一艘以三岁女儿克里斯蒂娜名字命名的豪华游艇。从建造这艘巨轮上最昂贵的私人游艇开始,源源不断的巨额资金打造了克里斯蒂娜成长的“金光大道”。这个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最热衷的就是乘坐私人专机去世界各地旅游。
然而,奥纳西斯家族虽然是西方世界屈指可数的富豪之家,但也有不少意外灾难。
1968年,阿里斯托特·奥纳西斯同他的结发妻子离了婚,然后同被暗杀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未亡人杰奎林·肯尼迪结了婚。这件事当然牵动了全世界的新闻机构,曾引起了轰动。但时隔不久,这对半路夫妻便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1973年,老船王年仅24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又不幸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因伤势过重而死。在儿子横死、妻子离心的双重打击下,奥纳西斯一病不起。1975年3月15日,阿里斯托特·奥纳西斯因患普通的伤风感冒而引起了并发症,经多方抢救无效而一命归天,而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只能是女儿克里斯蒂娜。因此,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在继承10亿多美元的资产后,自然成了统治庞大的奥纳西斯油船王国的女船王,并且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她继承了遍及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以及造船、旅游、航空、矿山、地产等产业,还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商船队与8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天之娇女”被从享乐的幕后推到世界船业竞争的残酷台前。幸运的是,克里斯蒂娜继承了老船王“骁勇善战”的聪明头脑。在全球海运公司纷纷倒闭的形势下,克里斯蒂娜的船队不仅没有在大萧条中破产,反而还略有盈余。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守住了老船王的家业,而且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平心而论,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作为一个年轻女人,无论相貌还是性格均非上上之选。又由于父母缺乏感情过早地离婚,使她从小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爱抚和教养,因而致使她养成了一种乖僻放纵、目空一切、喜怒无常的性格。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她的婚姻却因与整个油船队紧密相连,为世人所瞩目。
克里斯蒂娜虽只有20多岁,却已结过两次婚。早在1970年,老船王奥纳西斯就向世界宣称:其女儿和希腊另一家大航运公司的继承人俾斯奥杜已正式订婚。从这门婚事上,人们不难看出老船王要把女儿的终身大事,也纳入到他发展油船王国的轨道上来。
然而事与愿违,从小就养成目空一切性格的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对父亲包办的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她没有把年轻有为而又风度翩翩的俾斯奥杜放在心上,始终在感情上激发不出对他的爱。1971年夏,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竟违背父命,下嫁给美国的一个年近50岁的地产商布克。这一来,老船王的计划全给搞乱了,一怒之下,老船王也采取了极端办法,把每年给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7500万的生活费用全部断绝。一向娇生惯养、挥金如土的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会来这一手,顿时感到手足无措。在父亲的威逼下,她只好于当年的12月12日宣布与布克离婚。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夭折了。
第二次婚姻也是在维持了几个月后告吹的。1973年1月,老船王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因乘坐私人飞机失事而丧命,他因此大病缠身,一蹶不振,长期卧床。
1975年2月,生命垂危的老船王,仍念念不忘与实力雄厚的俾斯奥杜船运公司合并的计划,为了扩大油船队,他要求女儿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答应嫁给俾斯奥杜。看着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百感交集。想到父亲的养育之恩,为了能让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她狠了狠心,同意了这门亲事。
3月15日,老船王在得到女儿的回答后,心安地离开了人世。不久,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与俾斯奥杜结了婚。
对于这门婚事,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本来就是一千个不愿意。勉强遵奉父命结婚后,她也只和俾斯奥杜维持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这样违心地结合几个月后,她又突然单方面宣布与俾斯奥杜解除婚约。
这两次婚姻的破裂,足以说明克里斯蒂娜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爱情。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她曾对人说过,“我在短暂的人生中,未曾有过多少欢乐!”
离婚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里,她把她的“王国”管理得有条不紊,她用她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管理才干证明,她不愧为奥纳西斯家族的杰出继承人。然而她最缺少的是“真正的爱情”。按照她的解释,只要是真心实意地爱她本人——克里斯蒂娜,而不是爱着她的钱财的意中人,她就愿意把一切全托付给他。可是她几乎阅遍所有向她送来鲜花的男子,没有一个是令她满意的。
然而,没过多久,她所渴求的心目中理想的人终于找到了!
1976年,克里斯蒂娜的船队陷入不景气之中,为寻找租船客户而发愁时,苏联当局看准时机,邀请她去莫斯科谈判租船业务。这天正举行着欢迎克里斯蒂娜的盛大的鸡尾酒会。
当鸡尾酒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中上等的个头,宽宽的前额,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虽已年近四十,但看上去依然举止潇洒、风度翩翩,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美男子!他叫谢尔盖·考佐夫,名片上写着的公开职务是苏联航运公司的业务副主管,而实际上他却是克格勃的特务。
“乌鸦”上阵
尽管他个子不高,相貌一般,但两眼炯炯有神,善于通过眼睛表达对女性的渴求,常常使女人在他的眼神下倾倒。
苏联对希腊油船队早已虎视眈眈,企图控制这支油船队也是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因为在他们看来,目的一旦达成,就可以进一步通过各种途径控制中东石油的出口,削弱西方各发达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信赖,进而搞乱搞垮他们飞速发展的工业,制造内乱,从而击败他们。这支油船队不能不算是在东西方争霸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为此,苏联当局密令克格勃,要不惜血本想方设法与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拉上关系,而且要动用一切手段来控制她,让她成为苏联的筹码,为苏联的战略目的服务。
但长期以来,由于希腊油船队与西方各发达国家业务联系比较多,关系也十分密切,这点对苏联是极为不利的。为此,苏联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是寻找突破口。尽量多掌握一些希腊油船队的情况,尤其是女船王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情况,以便使用最佳途径控制女船王。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坐上女船王的宝座后,尽管老船王在临终前妥善安排了一些忠实可靠的同事、专家来帮助她处理具体业务,但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还是需要靠自己挑起经营船队业务的重担。因此,她边学边干,在希腊比雷埃夫斯的办公室里坐阵指挥,并经常出入设在美国纽约的航运公司总部。在遇有重要业务时,还时常亲自出马。这些情况对克格勃来讲很重要。因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抛给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一个诱饵,她就会亲自上钩咬食,这样钓住她的可能性就很大。
二是寻找时机。真是心想事成,时机很快就被他们等到了。1976年,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中东各产油国接连不断地宣告石油减产。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庞大油船队因此而生意清淡,无油可运,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这给克格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们经过密谋后,认为如果利用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寻找出路,扩大业务的心理,适时向她抛出诱饵,不怕她不上钩。于是,苏联当局批令苏联航运公司和希腊油船队谈判租用五艘大型油船的事宜。
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接到苏联航运公司想租用大型油轮的电报后,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一旦达成租赁协议,就可解当时的燃眉之急。于是,她立即拿定主意,要尽力促成这笔买卖。为了显示自己的经营才能,她不顾各方的劝阻和反对,决定亲自出马与苏联航运公司谈判,谈判地点就在莫斯科。
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的这些举动,正中克格勃的圈套。他们接到她的答复电报后,经过一阵紧张而忙碌的研究后,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谈判和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拉上关系,并设法和她增进感情,使她坠入情网,进而争取和她建立婚姻关系,达到控制她,为苏联所用的目的。为此,应选择一个精通航运业务的人去勾引这位女船王。因为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不仅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而且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大企业家。在对待自己的感情与婚姻问题上,她无疑要受事业的左右。如果只选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而不懂业务的美男子与她接触、调情,恐怕十有八九不容易使她倾心。这位女船王走南闯北,跑遍世界各地,接触的美男子多得不计其数,也没见到她对谁倾心爱慕。就连风度翩翩、年轻有为的第二个丈夫,她也说离就离了。更何况如果只是选一个英俊小生,也没有恰当的理由安排他和女船王进行接触。
最后,克格勃物色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与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谈判,他就是谢尔盖·考佐夫。考佐夫表面上是苏联海运部货船司油船科科长,实际上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学院(苏联当局专门培训克格勃人员的学校),是号称“乌鸦”的专门执行“美男计”的克格勃间谍。这个年仅四十的汉子已有妻女,相貌并不俊美,但两眼炯炯有神,善于通过眼睛表达对女性的渴求,常常使女人在他的眼神下倾倒。不仅如此,他在穿着上也十分考究,更让女人开心的是他谈吐风雅、精明干练,往往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情迷女船王
考佐夫得意地向他的总部发去了报告:“鱼儿”已经上钩,请下第二步棋。
经过一系列准备后,女船王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率领人马来到莫斯科。苏联航运公司在克格勃的授意下,把他们当成贵宾进行了隆重的接待。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一行人一下飞机,他们就安排了丰盛豪华的接风洗尘宴会,而且规格相当高,苏联政府的要员也出席了此次宴会。航运公司总经理在致欢迎词时,对克里斯蒂娜本人进行了十分得体的赞扬,褒奖奉承恰如其分,使女船王听了心里感到特别舒坦。接着又频频举杯敬酒,表示了亲密合作的诚意。当天晚上,还特意安排他们在莫斯科大剧院贵宾席观看芭蕾舞《天鹅湖》。这一系列活动,无疑给第一次进入苏联的女船王,留下了十分满意而难忘的印象。
更让克里斯蒂娜开心的是第二天便进入谈判。当双方代表落座后,她惊奇地发现坐在她对面谈判的苏联主角,竟是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但他在一大群人高马大的代表中却显得十分精明潇洒,严肃中含有笑意,精明中不乏风趣,粗犷中充满细腻,他就是考佐夫。这时考佐夫的矮小身材在克里斯蒂娜的眼里不仅不是什么缺陷,竟反而给人一种新奇感,使人觉得很特殊。应该说,克格勃这一手是相当高明和成功的,女船王见到考佐夫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好奇的感觉,并对这位谈判对手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谈判一开始,双方代表就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就希腊油船的吨位、船况、性能、租用时间、租金、租用手续、船员安排、行驶航线,以及海关限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商讨。双方讨价还价,互不让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考佐夫。他对所谈判的问题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又非常在行,对问题的理解既深刻中肯,又能以丰富的航运和航行经验,结合租船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该坚持的坚持,该让步的让步,有理有利有节,处理的纹丝不乱。坚持时语调和缓,有理有据,让对方心悦诚服,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观点;该让步时,他充满友谊,不卑不亢,充分显示出对希腊朋友的尊敬和理解。在整个谈判中,考佐夫自始至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人物。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明了,并能切中要害。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幽默风趣,开个适当的小玩笑;时而严肃坚定,时而微笑友好,表现出十足的灵活性,又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考佐夫在谈判中一切表现,让女船王十分钦佩。自她主管希腊油船队一年以来,大大小小参加过许多业务谈判,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考佐夫这样头脑冷静、知识丰富、反应敏捷、举止优雅的谈判对手。这个矮个子才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精通航运业务而难对付的谈判高手。考佐夫的所作所为,不仅在克里斯蒂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这位年轻女船王在心中产生了对他的好感,认为这个矮个子很有意思,把如此重要的谈判变成这么轻松愉快的交涉,使她感到特别受用。
几个小时的谈判结束了,双方最后顺利地达成了满意的协议,都感到今后合作前景美好,心情十分舒畅。尤其是克里斯蒂娜和考佐夫两位主角的愉快,更是不言而喻。他们不仅看到了谈判的成果,而且通过这次谈判,他们互相都有了深层的了解,博得了对方的好感,似乎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别墅里的放映设备都是现成的。很快,放映录像开始了。
呈现在克里斯蒂娜眼前的,是她在里面度过了新婚之夜的莫斯科的家,在她和谢尔盖睡过的那张床上,坐着母女两人,一个是考佐夫的前妻娜塔沙,一个是考佐夫的女儿卡佳……
“卑鄙!”克里斯蒂娜看到这里几乎在沙发上跳了起来。
接着看到的是考佐夫与娜塔沙的互相谅解的亲热……
这时克里斯蒂娜双颊滚动着泪珠。
再接下去是考佐夫用她给他的钱买来的裘皮、钻石戒指、耳环等贵重饰品,通过考佐夫的手一件一件地送到那个可恶的女人手上……
克里斯蒂娜看不下去了,像母狮般地吼道:“够了!够了!”
那位西方记者十分满意地结束了他的录像放映工作。
此刻的克里斯蒂娜也恢复了理智:“拷贝有多少?”话语里透露着担心。
“只有这一部。”新闻记者知趣地回答。
“给什么人放过没有?”话语里带有明显的恐惧。
“您是第一位观众。”新闻记者话里带着讨好的口气。
“你们也真够无耻的!”克里斯蒂娜愤怒地说道:“我敢肯定你是个披着记者外衣的秘密情报人员!”
“为了西方世界的利益,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太太!”新闻记者回答得很巧妙。
“磁带我全买下了,连您的辛劳费。这些钱足够了吧。”克里斯蒂娜边说边将一打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法郎丢在桌子上。
新闻记者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心里早已明白,这位女船王毕竟也是常人,她是不会甘愿让家丑外扬的。他高兴地把大把票子装进口袋里,道了声晚安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名新闻记者走后,克里斯蒂娜又气又恼。在事实面前,克里斯蒂娜开始有所醒悟。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是一个女船王,拥有上十亿美元资产的油船队,在世界石油运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考佐夫同她的恋爱的全过程都是有人导演和安排的,她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可笑的感情木偶。而尤其让她大为恼火的是,自从和考佐夫结婚后,克里斯蒂娜同西方石油商谈判的机密文件、报表经常泄露出去,经希腊情报部门证实,确系奥纳西斯家族内部的间谍所为。直到这时,她才不得不相信,考佐夫确实是一只多情而狡猾的“乌鸦”。于是,她下决心同考佐夫离婚。
于是,从沸点到冰点,克里斯蒂娜的第三段罗曼史已接近尾声。迫于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考虑到油船队的兴衰,同时也不愿意让奥纳西斯家族几代人挣下的这份家业在自己的手中败掉,更为摆脱克格勃的控制,克里斯蒂娜狠了狠心,在感情与事业的天平上倒向了事业一边。为此,克里斯蒂娜特邀了美国、法国、瑞士的律师们,为她办理离婚手续提供支持和咨询。当然,这位女船王没有也不愿把这段令她伤心、对旁人是笑料般的冷酷现实和盘托出,否则那就是自己毁掉自己的名声。
考佐夫看到了这一点,便乘最后的这一线机会进行勒索。考佐夫提出:离婚可以,但从做她的丈夫的那一天起,克里斯蒂娜本人和公司的收入的一半应当属于他。按照考佐夫的计算,这“一半”就是1.2亿美元。这个计算数字也使西方各界人士大吃一惊。经过西方有关各界人士和律师的出面调停,最后于1980年2月,考佐夫答应以一条油轮为筹码,结束和克里斯蒂娜这段曲折的、不太光彩的罗曼史。
谢尔盖·考佐夫履行完交接手续后,便兴高采烈地乘上他的这艘“丈夫船”回国与他的真正的妻子团聚去了。
其实,他获得的岂止是一条船?尽管克里斯蒂娜矢口否认,西方和希腊的反谍专家们还是有理由断言,一些石油生产国和美国的有关石油运输和储量的数字和大量事实已经部分地泄露了;西方石油大亨和奥纳西斯公司就伊朗国王是否能下台的分析和在石油运输以及储备上准备采取的措施,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为了掩盖这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克里斯蒂娜仅仅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和考佐夫正式离婚。然而,这一新闻公之于众后,再度引起世界的轰动。关于考佐夫的克格勃背景也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每日快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公开披露:“谢尔盖·考佐夫,这位娶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为妻的俄国人,直至他们上月末离异之前,一直是克格勃的特务。他的任务是向莫斯科提供有关西方石油的储备、供应和运输的具体情报。”
让西方国家哭笑不得的是,离婚后的克里斯蒂娜仍然对考佐夫念念不忘,十分眷恋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苏联当局为了掩人耳目,批准了考佐夫去英国定居的要求,并很快给他办理了离境签证。而在英国从事航运业的考佐夫也不忘情人,仍经常去巴黎同女船王相会。两人藕断丝连,依然情意绵绵,有时还一起外出旅行。1984年3月17日,克里斯蒂娜与法国的第耶雷·洛沙尔结婚,但她在婚后,还与考佐夫保持联系。也许克格勃为女船王精选出来的考佐夫的阴影,将会永远烙在她心中。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哈尔滨出版社《生死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