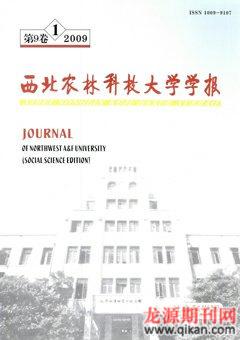论董仲舒的生态哲学思想
黄孔融 王国聘
摘 要: 董仲舒的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主张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探讨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仁民爱物的观念,透过阴阳五行学说,研究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明确人类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并把古代君王的道德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幅天人感应的生态图景。
关键词:生态哲学;天人合一;自然规律;董仲舒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97-04
董仲舒的哲学观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天与人的伦理本体合一的精神,是万物最高的生存境界;“与自然和谐”承认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生存和发展要服从自然规律,要尊重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董仲舒的哲学观体现了一种建立在农业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态构想,这种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朴素的生态哲学观,实现了人道和天道的彻底贯通,把人际道德和人对自然的道德完整地统一起来。[1]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生态思想的基础。
一、“天人合一”与仁民爱物论
儒家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 人与天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人与万物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基本点就是把自然与人类看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并认为天地万物存在变化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系统。“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孔子,发展于孟子、荀子,后经董仲舒理论化、系统化后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结合道家、法家、阴阳家各派学说,第一次对天人感应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提出“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如此气势恢宏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也表达出人类要对自然环境负责这一果敢坚决的态度。他认为天是至上的,“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寒之。”(《举贤良对策》) 同时,他又认为,天地人又是互相结合,不可分割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这是一种天、地、人和合的思想,也说明了人道与天道应相辅相成,人与自然界应和睦相处的道理。
此外,董仲舒还强调和谐是事物的常态。他认为宇宙的基本精神是中和,“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者,天下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他认为,和谐是天地生成之原因,德行应该要讲究和谐的原则,道理应该讲究适中的原则,这些都是天地美好通达的道理,宇宙良性运行的规律。若把这些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当今提倡构建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思想对比,尽管相隔了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却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种如出一辙的感觉,着实令我们佩服古代圣哲超群的智慧和先见之明。
儒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万物的爱护的可贵认识,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说,均源于儒家天人合一、天人相和、以德主和的中和观。[2]这种中和观是以仁德为天地自然的本质,把人与万物视为一体,把爱人与爱物相联,提出“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即要视天下百姓为自己的兄弟同胞,视宇宙万物为自己的朋友;要由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所以,我们看到,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而且也非常重视“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这样才使得儒家思想的仁爱精神更加丰满充实。孟子就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
董仲舒的思想中同样闪烁着这样的“仁”性光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质子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为仁?” (《春秋繁露•仁义法》)也即是说,如果仅仅爱人还不足以称之为仁的,只有将爱扩大到爱鸟兽昆虫等生物,才算做到真正的仁爱。他在《春秋繁露•离合根》中也强调了这一思想,“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即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才能表现出仁爱来。这里的“不以喜怒赏罚”是指不能搞人为的“喜就赏”、“怒就罚”、而应顺应自然,讲究“自然之赏”和“自然之罚”。可见,儒家的“仁”不仅包含了人际之间,还包含了人际之外的世间万物。而且,他还认识到水土流失与山林砍伐的关系,“春旱求雨……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春秋繁露•求雨》)只有保护好名木山林,不要过分毁林开荒,才能风调雨顺,不出现“春旱”的现象。 [3]这些充满生态意识的思想竟是出自两千年前,实在是难能可贵。
儒家“仁民爱物”思想以仁爱友善的态度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这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人们应帮助自然界生灵万物的生长发育,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可贵思想。所以,我们就能见到这样一幅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理想生态社会的美好景致,“毒虫不蛰,猛兽不搏,抵虫不犯。故天下为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春秋繁露•王道》)
二、五行顺逆与自然规律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说,儒家也讲阴阳五行说,并且在董仲舒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董仲舒著作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人阴;秋,出阴而人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按照阴阳五行理论,董仲舒的生态理想说到底就是要顺合阴阳、顺合五行。他把宇宙世界看成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并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制定出一条有序的生态链,把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放入这个系统中,并以此规定人类生产、生活和行为的基本内容与方式,各种宜行之事和禁忌之事,这也涉及到人类在天地间的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4]
同时,董仲舒认为人类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阴阳五行理论。如果人类恣意妄为,无视自然规律,就会使“水、火、木、金、土”产生恶变,涉及动植物的生存,以致发生自然灾害,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鳣鲸不见,群龙下。如人君出入不时,……事多发役,以夺民时,……则茂木枯槁…”"(《春秋繁露•五行顺逆》)即是说,木代表春天,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也是农业耕作的大好时节,人君应该鼓励人民进行农业活动,不要耽误时机。这样一来,草木光艳,肥鱼众多。否则,就会草木枯槁,生计萧条。那么,一年四季中的其他季节同样重要:
“火者夏,成长,本朝也……恩及于火,则火顺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黄鹄出见,凤凰翔。如人君惑于谗邪,……咎及羽虫,则飞鸟不为,冬应不来,枭鸱群鸣,凤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兴,恩及馃虫,则百姓亲附……如人君好淫佚……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诛,咎及馃虫,馃虫不为……”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恩及于金石,则凉风出,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麒麟至……咎及于金,则铸化凝滞,冻坚不成,四面张罔,焚林而猎,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白虎妄搏,麒麟远去。”
“水者冬,藏至阴也……恩及于水,则醴泉出,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则龟深藏,鼋鼍呴……”
我们可以透过以上的五行学说来发现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资源与宇宙万物的生态思想。自然界是一个充满客观规律的有机整体,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其不同的生产规律和生态规律。人和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而应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能动的改造和利用自然。例如,在春生夏长的季节,应禁止入山伐木、焚烧山林,禁止毁伤鸟巢禽卵,禁止大型的渔猎活动,即使祭祀礼仪也不许供奉牲畜,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这便是人类必须履行的生态义务。但是,在秋收冬藏的季节,人类则应该及时收获谷物、积聚菜蔬、伐薪为炭和从事大型渔猎活动,以利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服务,这又是人类应该享有的生态权利。 [4]在我们看来,儒家的生态理想在客观上体现了一种古代朴素的生态中心论。虽然在那时没有“生态”这一概念,但肯定会讨论有关环境问题或者所谓的“生态”问题,因此他们也有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生态思想。
三、天人感应与君主负责论
“天人感应”理论是董仲舒灾异说的理论根据。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所以,自然天象成为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祥瑞,是帝王兴盛和德政的征兆;而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被看成是上天对人类行为的警告。[3]天地发生自然灾害,是与国家行为有关的,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特别是作为“天子”的人君的行为。因为,人君可以与“天”互相感通、应合,人君可以积极主动地去体会、领悟天的性情。所以,天所施降的自然灾异更主要的还是与人君的行为有关,甚至就取决于人君的行为。如果作为人君的“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在《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亦得到充分体现:“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次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即是说灾异的根本来自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在其最初萌芽的时候,天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谴告于人君。但是,如果谴告无效,人君不能及时纠正过失,天又以种种怪异现象惊骇之。而如果人对惊骇也无动于衷,还不知道畏惧恐吓的话, 则夺回其天命,接踵而来的是殃难与咎祸。但是天与人一样,也要讲仁义道德的,如果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人类与自然界就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就会出现“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春秋繁露•王道》)的美好景象,否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春秋繁露•王道》),等到那时一切就太迟了。
董仲舒建构灾异谴告学说的目的,是想充分引起人类尤其是人君的内心反省,“内史反听”从而求得天意,实现“察身以知天”,“以身度天”,通过“察物之异,以求天意。”[5]但是,为什么只有人能够感知天命,而其他生物却无法做到呢?因为,董仲舒以为,在天地的精华所生成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类更加高贵,更加能够施行仁意的。人类就应该代表万物与上天共同施行仁义道德,特别是对自然界的道德。“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地,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他甚至还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人是上天所派生的,处处与天相应,“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此外,董仲舒还把人君的道德与自然之罚直接联系起来。把人君的五种过错和“自然之罚”的种种迹象联系起来: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王者言然,我们知道所谓的自然之罚与人君的道德过错实际上并无联系,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为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做君王的道德修养不到家,易产生以上五种过错,这样就会破坏天地人这个生态系统,会有“自然之罚”。 [3]而这种托天管人的做法无非就是限制人君的权力,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君“侈宫室,广苑囿;骄溢妄行,夺民财食;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等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
董仲舒的这些哲学思想虽源于汉代,但却蕴含着跨越时代的合理因素和历史价值。当今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着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若仅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是不够的,而要唤醒一种被尘封已久的、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董仲舒的生态思想是古代社会落后的生产技术的反映,是农业生产顺天应时的经验总结,带有被动性和自发性,但其中表现出来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思考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与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相契合的一面。重新认识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有助于弥补现代生态伦理构建中思维方式的不足,可以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提供理论基础。要构建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就应该重视和发掘中国的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汲取其中的精神营养和生态智慧。这些思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新审视社会的生态价值观念,构建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同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阎丽.董子春秋繁露义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 刘湘溶.论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J].湘湖论坛,2004(1):38-41.
[4] 王文涛.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J].中州学刊,2005(6),111:50-152.
[5] 谢树放.儒家中和观及环境伦理哲学启示[J].伦理学研究,2005(1):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