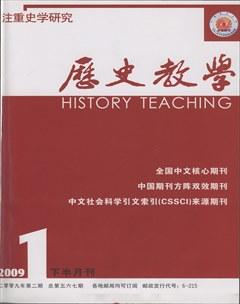旧制新法的冲突
吴 昱 关晓红
摘要作为晚清海关尝试以新式邮政方式收寄华人信件的机构——华洋书信馆,在初期的冬季邮件陆运中便遭遇邮件被扣及邮差被逐的事故。究其原因,乃为主办者违反清廷规制所致,但其背后又牵涉清廷官员对待洋务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华洋人以清朝官员身份举办新政时的矛盾与挫折。在这一普通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传统制度与新式机构的冲突及磨合。
关键词华洋书信馆,冬季陆运,邮件被扣,近代海关,德璀琳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28-05
华洋书信馆是近代海关第一次尝试以新式邮政方式管理收寄华人信件的机构,然而该馆开办不久便遭遇邮件被扣事件,以往的研究虽有触及,但多简略记述事件经过而未深入探究其中缘由。比勘旧存新出的各种史料,则愈发可见该事件不尽是顽固官吏阻拦新制。在陆运邮件的过程当中,既有新旧观念的冲突,也有不同机构的利益纠葛,而皇朝规制与外人新政之间的碰撞,更可体现近代中国在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传统制度与新式机构如何冲突与磨合,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一、以华竞华:华洋书信馆的创办初衷
开设华洋书信馆的构思,源自近代海关对开办新式邮政的追求。总税务司赫德在《烟台条约》谈判期间就曾建议加入开办邮政的内容,而李鸿章亦“告以信局无甚流弊,曾允试行”。1877年5月间,赫德授意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准备开办新式邮政的相关工作。不过,该试办最早是在代运使馆邮件的范围内进行,而德璀琳在1878年3月至5月间开办口岸间的邮件互运,则仅限于在华洋人的信件往来,对于是否办理及如何办理华人信件业务,当时并未纳入正式开办的日程。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开办条件有限,而众税务司又担心新式邮政侵及民信局的利益,故建议德璀琳慎重行事。另一方面,虽然建立京津间骑差邮路的方案为总税务司署所采纳并获得经费的支持,但传递速度缓慢,且费用高昂,使得德璀琳对华人邮件处理问题,只能采取“用合同方式来控制现有的私营信局,要它们从事接收和投递中国人的邮件的工作”的思路。在1878年7月间,德璀琳与天津的大昌商行订立协定,“大昌商行将作为我们的代理人在北京、上海和芝罘代我们办理此事”。
不过,华洋书信馆的开设在德璀琳眼中仅是基于现实的权宜之计。在其设计中,海关仅负责运送华洋书信馆的邮件而不直接参与书信馆的具体事务,通过华洋书信馆与民信局的竞争,将相关的业务逐步控制到前者手中,再由海关进行整合与管理。他在1878年7月25日致函江海关税务司赫政时称:“目前,我想达到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邮件在上海、北方口岸以及北京之间的运输业务掌握起来。为了使海关办理这项比较困难的工作时,不致增加负担,我已与大昌商行订立了一个临时协定……我们已派文案吴焕去监督称为大昌邮局(华洋书信馆)的工作,并把地方信局有利可图的差使和工作组织掌握到我们手里来。”这样的设计,使得海关不需为新业务再付出额外的费用,同时由华人自主收寄信件,避免因为外人身份而使得中国民众产生不信任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主管新式邮政的海关税务司对书信馆的管理及承包邮路的主办者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也为华洋书信馆冬季陆运邮件发生被扣事故埋下隐患的伏笔。
媒体的议论显然与德璀琳的设想大相径庭。1878年7月22日的《申报》载《新设华洋书信馆》一文称:“兹闻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等五处,已由官招商合股,设立华洋书信馆,先行试办,为将来邮政局之嚆矢……信资甚廉而投递又甚妥速,与本地各信局诚堪并行不悖。”然此新闻有两点并不明晰:一是举办方式。时人以为试办之华洋书信馆,应为将来邮政局之雏形,但按德璀琳的说法,试办邮政的海关,与设立华洋书信馆的大昌商行之间为合作关系,既不同于外洋之国办邮政,也与“官招商合股”的机构有别;一是认为新设之华洋书信馆与其他民间信局“并行不悖”,并未察觉海关主办新式邮政的用意,而时人投书递信时,亦难以引起其注意与民信局的区别。
1878年9月4日,《申报》又登载了《华洋书信馆章程序》,相较月余前的报道,透露出了更多的信息。此文以邮政为裕国便民之举,是“因时制宜,力求强富”的事业,而“天津关德税务司璀琳……于邮政一端,尤所留意。见泰西之能获利,料中国无难举行……奉经直隶爵阁督部堂李,核准在于京城、天津、牛庄、烟台、上海五处,设立华洋书信馆,先行试办”。该序还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以吸引一众商民聚股汇财,“是望所冀望风遥集欣欣者,患(焕)然可来,庶几不日而成,源源者招之即至”。是文有几点颇值玩味:虽然指出泰西邮政实为官办,但于华洋书信馆却是“稍事变通,议归商办”;开办归功于德璀琳与李鸿章,毫不提及赫德首倡此事;而该文目的仍在招股敛商,实与民信局的开办方式无异。按近代欧美邮政制度,均由国家开办,利润亦归之国家所有,虽然该文撰者亦同样认识到此点,但由于是时清廷并无开办国家邮政之计划,而试办亦交由外籍税务司所总管,以致新式邮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外人之事”。因此在德璀琳指示下开办的华洋书信馆,亦只能以民信局的方式去试图取而代之,进而统一民间书信的收寄传递。
二、明流暗涌:支持者?反对者?
虽然海关并不直接参与华洋书信馆的管理,然借助海关的经济支持及递运资源,华洋书信馆与民信局相比还是颇占优势,因此难免其他民信局担心侵及自身的递信网络及收寄群体。德璀琳在1878年9月30日呈文赫德时曾表示:“有人反对邮务计划,这是完全在我预料之内的。那些鼓动反对的人是谁,目前我不愿指出,我也不想细谈他们那些隐秘或公开的反对理由。”他自信地说:“如果我们保持冷静,不断地认真进行工作。这种谩骂和捏造不久就会消逝下去,而我们要建立的机构终于会建立起来的。”而通谙洋务的曾纪泽,在几天后(1878年10月5日)亦“写片缄致李相,言华洋书信馆初开,不能周遍,诚不能阻禁民间信局,然不能不与民局争利。设马递以备封河时寄递文牍,即系争利之法,以民局断无力设多马也。设马后,却须接递民局之函,乃能两益。洋人于封河后亦系马递,但皆七日一发,不为甚便。中国书信较多,宜变通办理乃佳”。九月十三日(10月8日),曾纪泽又“拜法领事狄隆,英正副领事佛礼赐、宝士德,税务司德璀琳,德领事穆邻德四处,税务司谈最久。民间信局,有携带货物偷漏关税者,海关设法盘查,而信局哗然,以为华洋书信馆既经税务司建设,遂设法稽留民局函件,以为擅利之计,纷纷向各署控告。盖两事适同时相值,而民间误会,乃有此争。余嘱德璀琳宜联络民局,相辅而行,方能济事”。
曾纪泽的担心,月余后便被证实并非杞人忧天。该年11月9日,德璀琳在天津华洋书信馆经理刘桂芳的推荐下,与候选参将、二等侍卫佟在田签订了“承揽冬季12--2月,三个月的接力邮寄
工作。每隔一日,从天津、镇江两地对派信差运送邮件30斤,一般情况下,应在九天内投到。对此业务需付关平银1500两”的邮递合同,仅仅十来天后,“(十月)二十日该信局纠人到关,并赴华洋书信馆喧闹”。事情的起因,是江海新关要求专办上海与牛庄、天津、烟台三口递信的福兴润、全泰盛、协兴昌三信局,“抵口后由江海新关拨派扦手提验信包,如无私货,随查随换”。但三信局担心海关有意留难,为华洋书信馆的递信提供便利。虽然经上海租界会审分府示谕:“嗣后凡有轮船寄到北洋三口各商信件,均各遵照定章,候关查验,不得稍有争闹,自羁时刻。倘查出夹带私货,由关照章人官充公。该信局等如敢抗违,立予严办,决不姑宽。”但这一忧虑并未消除,双方递信路线既有重合,则难免利益冲突,而带有海关背景的华洋书信馆介入民局最为集中的江南地区,难免引起一场明争暗斗。
有意“以华竞华”的德璀琳,希望用建立新的邮路和邮递方式取代民信局,“原先的目的是建立一条既迅速又经常化的邮路,以便树立威信,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和照顾,从而制服同我们对抗的‘信局子”,但选承办者却所选非人。在1878年1 1月17日德璀琳拜访李鸿章时,“提及承办人为候选参将二等侍卫佟在田,并请为其颁发护照事”。而李鸿章对这一选择大为惊诧,“一字一句地说:‘此人是一位高级军官,此人还是一名与一件诉讼有纠葛的人,并曾经反对县府,因此,我对他不得不绳之以法”。德璀琳表示自己并不了解佟在田,并建议废除合同,但“中堂略加沉思后,说:‘不,让他履行合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完全能办好此事。不过要以我的名义警告他,他可趁此机会挽回名声。但如干不好,又行为不正,我——中堂——必对他严惩”。接着李鸿章颁发了护照,并交德璀琳以便开办。
上段颇带戏剧色彩的描写,在李鸿章的叙述中仅是“至本大臣前因贵税司面肯填发佟在田护照,彼时即告以佟在田声名不佳,必须留心防范”。寥寥数言,丝毫不提及其曾考虑给予佟在田以改正的机会。究其原因,或是中外官员在交谈翻译中出现的理解偏差,或是熟谙宦术的李鸿章的权宜之策,无论如何,至少李鸿章并不需为此事负上直接的责任。
佟在田在组织邮路初期,工作尚能令德璀琳满意。“去年(1878年)11月18日至12月中旬,我一直未见佟在田。与此同时,我听说,他已赴山东建立邮路,邮差、马匹在天津备妥,并已发往南方”。不难看出,德璀琳对华洋书信馆及承办邮路的佟在田并无紧密的监管,也不了解佟在田组织递运的具体安排,其派员邓其琛前往济南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得到有关的可靠消息并掌握邮差”。可见,在与李鸿章交谈之后,德璀琳对佟在田还是存在着顾虑,只是因为佟在田本身具有功名,又获银号股东担保,因此即使被李鸿章质疑,德璀琳还是签下了这份合同。
然而仅隔一月,佟在田承办的邮路便出现严重事故。1878年12月31日德璀琳报告裴式楷,“一些信差在该省夜行时,被地方当局拦截并拘留,并说,邮件到达时间比应到的时间要迟”。到“1月1日,书信馆得到消息,数名邮差在山东邮路上,被捕、入狱。南北线各类邮件,在山东各地被扣留。更糟的是,我同时接到通知说承办人佟在田失踪。是日,京报公布判决。全文说明了根据直隶总督的指控将佟革职并予以逮捕的理由”。在派遣邓其琛前往山东调查该事后,德璀琳才发现“至本月(1879年1月)16日止,邓其琛抵济南府时,当局留难的态度并没有转变。邮件及信差仍在德州、泰安被扣,书信馆在济南监督交换邮件的人员,也已被驱逐出济南”。在后来德璀琳给赫德的报告中,他用了“山东当局所给予的毁灭性的破坏”来形容这次事件,可见事情的严重程度。而所有的信件,也不得不“每周二由专差直接将邮件由北方送往镇江。每周五经北京由衙门信使送往镇江”。而这些信差,全部都是“具保信差”,而且德璀琳还要求为这些特派专差“各发护照一份”,避免邮路再因阻挠而被迫中断。
按清朝体制,带运公文信件的人员,均由官府出示护照,证明身份”。而民信局收寄信件,亦须先在官府备案。然而华洋书信馆的开办,在传统体制内并无成例可循,故海关税务司请求相熟地方官签发的护照,居然出现了“镇江道台颁发的护照,山东竞不予理睬”的情形,这多少也反映了新式机构在传统政制中运行的尴尬境地。
三、来龙去脉:违反体制或人事纠葛
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北京总税务司署的高度关注。1879年2月6日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理文案税务司裴式楷和管理汉文文案税务司葛德立致函德璀琳,表示:“我们现在了解到,陆路邮运安排已失败;贵关发给本署书信馆的一份通告中亦承认有必要放弃您所拟定的陆路邮运安排……因此我们有责任调查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最令人不满意的结果。”两人根据文格给总理衙门的报告,要求德璀琳对包括安排佟在田承办时,是否知道他有诉讼纠纷、及有否发给信差旗帜兵器和号衣等问题作出答复。且裴式楷怀疑,德璀琳的独断作风,是否会令其背着总税务司署签发了某些有违海关职责的文件,从而引发此次意料之外的事故。
面对各方的质疑,德璀琳在多份信函及报告中,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1878年12月21日,“二等侍卫佟在田在刘桂芳的陪同下不期而至天津海关。他告诉我(德璀琳),他仓促返回天津,实不得已。因为天津县台以去年四六两个月的争吵为由向省宪提出申诉,要求将佟革职并拘捕。此次前来海关,意在向我申述其案情,并恳请我过问此事,代其说情,以使其能继续履行邮政合同。我无须重复佟的陈述,如果属实无诬,至少在我看来,他是可以免罪的。”因此,按照德璀琳的思路,邮件被扣很有可能是与佟的官司相关,所以他决定:“现寄上天津县法庭对佟在田的判决书抄件,我设法得到此件,意在查明此人被控告的真相,此件恰好证实我以前曾说他受贬黜与邮务上的事并无关联。”而十天之后的十二月初八日(1878年12月31日)内阁奉上谕:“李鸿章奏请将在籍侍卫革职究办等语。直隶天津县在籍二等侍卫佟在田,屡次生事讹诈。该县奸媒萧氏窝娼贻害,民人王三保买良为娼。经地方官先后访孥,该员出为阻挠说合,并有包庇流娼、捆人勒赎等事。种种妄为,实属行同无赖。佟在田着即行革职,饬传到案,从严究办。钦此。”日此上谕刊刻邸报,德璀琳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不过,佟在田组织的邮路之所以被破坏,除其本身牵涉的官司外,主要还是因为违反规制,而这些在山东抚台文格看来违规的行为,恰是清廷在聘请外籍税务司时,对其职权未能明确规定的结果。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三(1879年1月5日)德璀琳札郑藻如函中称:“当经护理总税务司将前情申请总理衙门查照,并于十月间本税司谒见李中堂,将沿途安设马拨、置设信差、络绎传递情形一一面禀,兼请赐发护照,即蒙李中堂立发给承办马差之员护照一纸,面交本税司转给只领遵办。其沿途巡查之人自未便纷纷渎请中堂发给,故本税司查照历年津京寄信据
悉本关发护照之成案,由本税司缮发护照。”但在山东官员看来,这种签发护照的权力并未写入任何条约。郑藻如曾照录山东巡抚文格的咨文予德璀琳,其中有“税司不宜发照设拨”,“税司设立马拨、号衣等事非遵条约之道……”针对咨文德璀啉回应道:“第本税司再四思维,若撤号衣、旗、照均无不可,惟不用马,则信包断难尅期而至,诚恐各国公使因本关寄信稽迟,仍不免自用马匹在内地络绎驰递,致与俄国由恰克图自行马递至京津无异,按照万国公法亦碍难禁阻也。且中国不准用马寄信,亦例无明文。”但在清廷官员看来,马递与军报相关,并不适宜用于递信,故“用驴、用车、用人”都可以,但用马则大为不妥。
德璀琳在1879年2月15日致信裴式楷时承认,在签发护照上并未得到山东官员的批准:“我未向邮差颁发过任何护照。在中堂为佟在田所订协议履行期间颁发有效的护照的条件下,我曾为邮路巡视员颁发过五份护照。本地地方官及山东地方官全然不知此事。我亦未向任何地方官请求为邮差个人颁发护照。在此之前,去年4月我曾请求道台为运送邮班用的马匹颁发通行护照,但他依据旧规拒绝了。上述五张护照,是我签发的,未得到地方官认可。此五张护照皆用税务司印。”这些邮路巡视员沿途检查邮差工作,车厢外插着“白衣料制的小三角旗,类似外国商行向内地送货用的旗子。旗子印有‘天津海关字样的中英文字”。而邮差们“所着服装酷似天津北京、天津牛庄邮路邮差所着的服装印有‘圆圈儿或‘津海关信差字样”。他们甚至还随身携带武器,因此德璀琳才格外强调“我既未发过旗子也未发过服装,更未发过武器。这些东西一定是承办人或邮差自己装备的,我想就这方面稍加解释,官府派遣的邮差夜间出行经常携带武器。山东南部时常发生强盗拦劫,自卫护身特别需要这种‘家伙”。不过,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没有经过照会、驱赶马车又携带武器、还悬挂容易被误以为是外国商行旗帜的队伍,与不知名的盗匪同样具有危险性。而当官员查看护照,又没有该省大宪的用印,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下,最安全的莫如先扣押人马和相关物件,待查明状况再行决定如何处理。
除规制问题外,潜在的人事纠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1878年12月31日德璀琳获知陆运邮件被扣押始,他常与山东海关道郑藻如进行交涉,也常致函直隶总督李鸿章及总理衙门请求帮助,但却从未与山东巡抚文格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其唯一一封函信,也没有被相关人员送达。文格此人“色厉内荏,好指摘人过失”,所以当时已有人向德璀琳建议将相关邮务安排通知文格,但德璀琳并未采纳。自以为与李鸿章有良好关系的德璀琳,认为“衙门有此举动,是议拟成立邮局的转折点,关系到邮局的前途,以及我们为中国谋利益的无私努力,能否继续进行下去,李中堂是赞同此事的,他一定坚持站在我们一边”。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之所以未曾将邮政大计及如何处置一一通知文格,如果我理解正确,是由于他和文格相处不和所致”。字里行间,无疑相当信任李鸿章及其在清廷政坛的影响力。但李鸿章是否如此信任德璀琳等外籍税务司,则颇值后人思量。李对总税务司赫德观感不佳,源自《烟台条约》谈判时期赫德为英国争取甚多利益,故与德璀琳的关系良好。或许正如赫德对金登干所说的:“李鸿章把我看成是对他非议的人之一,不希望我的势力太大,他挑拨我的下属来反对我。”所以德璀琳以为李鸿章全力支持新式邮政,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不过,李鸿章与文格的关系亦并非仅仅“相处不和”,两人在观念及行事上有较大的差异。李鸿章对文格的行事和见识均有非议,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879年1月21日)李复函郑藻如时认为,总理衙门“持论甚正,但于此事本末毫无推求,于各国邮政办法毫无咨访,仍执一哄之见,与文式翁、张樵野等一般识议,自以为是耳”。而且字里行间亦暗示,扣留邮件实另有隐情:“津京信馆之设将近一年,执事在津当差已久,岂独无闻见耶?封河以后添设马拨递镇江,势亦出于不容已,仍为各口通信起见,非为内地另设驿站也。”可见众官员函往信复之间,各种明忧暗患跃然纸上。在反对者看来,未经朝廷明令行文而设置“驿站”,不仅有违体制,亦易扰乱地方秩序,恐怕也是山东当地官员解释为何驱逐信差、扣押信件的借口。但在主办洋务的李鸿章看来,此事不过为沟通各口信息起见,如果邮差确有滋事,可以照例拿办,若以“另设驿站”为名,则难免过于牵强。至于山东方面提出的另一理由:“至尊虑日后内地消息洋人得信最先”,李鸿章驳斥日:“此等迂论最易动听,其实即无马拨,洋人得信亦不在后。”除反映出山东方面对事件的忧虑外,还不难看出是时该地官员仍将华洋书信馆视为“外人之事”,担心洋人利用此机构获取清廷信息,这一想法恰又与德璀琳举办华洋书信馆“以华竞华”的初衷相背而行。可见近代举办的新式事业及机构,不谙洋务的官僚并不以新政的性质为判断,而常以主持者的国籍族群身份为依归。阻碍清廷近代化的因素,亦未必纯是各种守旧思想或封建势力,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更多是一种思维定势与行事习惯,甚至于一种基于危机感和防御心态的臆想。
华洋书信馆冬季陆运邮件,本为海关举办新式邮政中一普通事件,然而开办初期即遭遇扣压风波,当事官员虽以邮件承包者身负罪责为借口,而其背后所牵涉的,却是晚清新旧制度所关联的利益冲突、理念差异及人事纠纷。利益冲突,为新式邮政与民信局的利益竞争;理念差异,表现为口岸与内陆官员在对待新式制度上的理解与行为;而人事纠纷,则为自李鸿章、文格至德璀琳、佟在田等人之间的错综关系。自清廷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及逐步开放口岸之后,传统体制便在外来制度的逐步渗透下,缓慢地排斥或容纳它们的存在,在之后漫长的三十多年里,新式邮政还将在传统体制的束缚与妥协中,缓慢成长。
而华洋书信馆经历此番风波后,在组织上亦有一番大变动。1879年返华的赫德在了解了相关开办情况后,一改德璀琳的急进作风,主张以稳妥的方式逐渐推进新式邮政的建设。而此番风波后,华洋书信馆又因主办者的越权操作而被海关勒令停止合作关系,这一原意作为与民信局竞争的机构,最后反而逐步沦为民信局群体的一员,在1896年清廷正式宣布开办国家邮政后,成为被管理和吸纳的民间递信部分,逐步湮灭在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