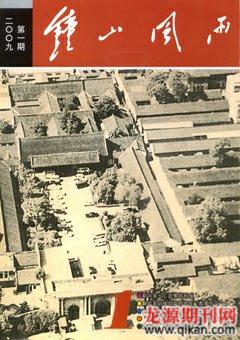关于日本战犯在抚顺改造的回忆
万 东
2007年12月4日,应“抚顺奇迹继承会”的邀请,侵华日军前乙丙级战犯坂本清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举办了一场“侵华日兵见证会”。会上这个老兵发表了长篇见证演说,为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深深地忏悔,真诚地叩首谢罪。坂本清,1920年生于日本千叶县,1940年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烧杀抢夺,犯下滔天罪行,1950年7月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被中国政府宽大释放回国。
家父张国栋当年以国民党集团战犯身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虽然管理所规定国民党战犯与日本战犯不准进行交流,但同在一个管理所,在劳动和庭院散步时可以天天见面。所里还有一个“外交组”,由于家父精通日语,从而成为这个组的成员。这个“外交组”经常为管理所进行一些日语口语和文字方面的翻译工作,因此家父亲见、亲闻了许多日本战犯艰难曲折的改造和转变过程。1975年家父被特赦后曾详细谈及过,留下不少这方面的口述。这些口述既是当年日本战犯改造事实的一个缩影,也直接回答了坂本清为什么会在87岁高龄仍要继续奔走于中日各地举行听证会,以亲身经历去指证和控诉日本当年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内容丰富的改造生活
家父回忆说: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方式与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方式基本一样,也是以思想教育为主,劳动改造为辅。
首先是三保障:一是人格保障。即对日本战犯给予人格上的尊重,不仅不打不骂,连训问时的态度也非常平和,今天说不通,明天再谈,明天谈不通,后天继续,直到说通为止。那些管教干部虽然很年轻,可无论犯人怎么冲他们发脾气,他们都不急不躁,很有修养,令人佩服。二是生活保障。不单是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的保障,还包括文化、娱乐、体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保障。三是健康保障。即定期体检,有病能及时就医。
日本战犯每天的改造日程是上午半天学习和讨论,下午半天劳动。学习内容有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大政方针、当天的《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管理所对不同战犯进行了分工,日本战犯负责蛋禽和家兔的饲养,有时也安排一些如拔除道路两侧杂草或春季栽种果树等劳动,当然日本战犯改造初期是不参加劳动的。晚饭以后就是自由支配时间,学习室里有《中国画报》和各类图书,俱乐部里有象棋、围棋等任其自选。

逢年过节,所里照例要举行文娱活动。1956年7月以后日本战犯人数少了,但也排练几个节目参加演出,他们表演的伞舞优美极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里还不定期举办运动会,因国民党战犯与日本战犯的运动会是分开进行的,所以尽管未能亲临他们的比赛现场,但能够听到从他们赛场上传来欢快的呼喊声和有节奏的“加油,加油”助威声,其热闹程度并不亚于国民党战犯数百人的赛场。
日本战犯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毒素的熏陶,极为顽固,初来抚顺时,大多数不肯脱下军装,一个个横眉冷目,每天清晨都要面向东方,念念有词,“遥拜”天皇,祈祷起誓,对管教干部不理不睬,拒绝改造。他们不看我国报纸,不听我国广播,幻想笫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再大干一场。管理所认为这是立场思想问题,立场思想是可以转变的,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日本战犯的每天“遥拜”,管教干部听其自便,不予干涉,但对他们耐心而细致地进行启发和教育。这样经过数月甚至1至2年的时间,他们在思想上才渐渐有了疑问:“天皇让我们到中国来做什么?我们给中国人的又是什么?现在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无数次这样的疑问之后,他们就自发性地用集体早操替代了对天皇的“遥拜”。
一次又一次的心灵震颤
家父说:在日本战犯有了初步转变之后,为加速对他们的思想改造,管理所釆取了多种教育形式。首先是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参观学习,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触到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心灵震颤。
每一次远行,都是国民党战犯与日本战犯及伪满、伪蒙战犯同包数节车厢一道前往的。在参观鞍山钢铁厂时,讲解员说:“日本战败撤离时,将整个鞍钢破坏殆尽,曾狂言:‘留下这块土地给中国人种高粱吧。可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不仅恢复了生产,产量和效率都早已超过了旧日水平。”这时国民党战犯对新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日本战犯则羞愧地低下了头。在哈尔滨参观死难烈士纪念馆时,看到李兆麟将军率领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打击日军以及李将军与战士们围着篝火度过漫漫长夜的镜头,日本战犯们都自觉地双手垂直,双脚合拢,低头表示着深深忏悔之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率领所部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后援不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残暴成性的日军竟将杨将军剖腹,在肠胃中寻找食物,发现全是尚未消化完的青草,这一发现使在场的日军肃然起敬,眼前的日本战犯则双膝跪地,低头认罪。

对日本战犯震动最大的是一次参观一处叫平顶山的地方。平顶山原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日军占领期间,曾在一夜之间屠杀无辜村民三千余人,并将尸体掷入一个大坑,参观时尚见累累白骨纵横交错为若干层,令人惨不忍睹。日本战犯受到良心谴责,当即下跪,伏地痛哭,最后还是在管教人员劝说下控制痛哭认罪的情绪。
战犯离所参观学习,除了以上三个地方,还到过沈阳、长春等城市。
管理所还多次邀请遭受过日军迫害的人员来作报告。记得有一次一位受害者在讲述他遭受种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景时,脱去上衣和外裤,露出全身各部位留下的疤痕,日本战犯当即全体下跪请罪,有的痛哭流涕,说自己也多次犯过类似的罪行;有的还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曾在那里呆过,愿意接受极刑,当然这些战犯没有一个受到极刑。
管理所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组织和安排日本战犯亲属来华探望,因此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穿着日式服装的日本战犯亲属,其中有高龄的老母亲,有中年的妻室,还有年轻的小姑娘。管理所对她们非常热情,辟有专门的接待室,让其与亲人畅述离情。所领导还邀请亲属们参观日本战犯的寝室、学习室、俱乐部及浴室等。亲属们在与自己亲人见面时感情会特别激动,不断地流泪,回去时对中国政府的改造政策和给予生活上的优待一再表示感谢,并反复叮嘱自己的亲人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获释回家。日本战犯亲属的来访,对日本战犯思想的改造无疑起着巨大的触动作用。
他们由“鬼”变成了人
家父说:20世纪50年代初,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着2000多名日本战犯,1956年7月,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首批宽释宣判。宣判那天,日本战犯们都认为自己要被判刑了,一反常态地平静了许多,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无论中国政府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也不为过。宣判时,他们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生怕听漏了一个字,但结果令人难以置信,除罪行特别重大的40余人以外,其余全部被宽大释放,并妥善安排回国。所有的日本战犯都愣住了,全场鸦雀无声,数秒钟过后,有的热泪长流,有的捶胸顿足,有的伏地痛哭,一边哭还一边说:“请处死吧!”其情其景甚是感人。
留下来的40余名日本战犯到60年代中期也先后被宽大释放回国了,家父接触到的就是这批战犯。在接触过程中,家父了解到这40余人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中官阶最高的,也是罪行特别重大而又顽固不化的,但他们最终都在管教干部的耐心启发和教育下,经过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心灵震颤,由“鬼”一步一步转变成了人。
一个外号叫“聋子”和另一个外号叫“哑巴”的两个日本战犯,就是他们当中转变的典型。那个所谓“聋子”,早先思想最顽固,别人早已不再“遥拜”天皇,可他还是天天“遥拜”不止,管教干部开导他不听,同犯规劝他更是置之不理。有一天他竟用筷子将自己的双耳戳聋,使忠告不再入耳,可见其顽固至极,岂料“聋子”双耳急性感染,高烧不止,病情危急,以至昏迷。在紧急抢救和日夜护理中,医务人员以及管教干部对他精心照料,喂吃喂喝,洗衣擦身,帮助拉撒,日夜守候在床前,使“聋子”终于脱险。
恢复休养期间,“聋子”询问护士:“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费心护理我?”护士回答:“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保证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回到日本去,替日本人民做好事。”管教干部的态度更为诚恳,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多次检讨自己失职,说之前对他关心不够,以至没有及时发现,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故,心中非常难过。“聋子”得知后深受感动和教育,由于失去听觉,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过去不愿意阅读的学习材料,积极参加原先不愿意参加的各项活动,不久就彻底转变过来了。被宽释回国后,他利用在所里学得的面食手艺,在东京开了一家小面食店,招牌就叫作“中华面条”,店堂里还悬挂着介绍中国的各种图片。他多次表示:“要尽微薄之力来宣扬中国的伟大,致力于中日友好,借以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恩悔罪之情。”
“哑巴”的故事也很感人。这个日本战犯一向愁容满面,沉默寡言,亲人给他来信,他多是不复,偶有复信,也是寥寥几句,似有满腹心事。他从不与人交谈思想,管教干部找他谈话也是缄默无言。上世纪50年代中期,管理所公布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战犯家属可以来华探亲的决定后,其他战犯痛哭流涕,感谢中国政府,而他仍然缄默无言。后来当管教干部反复向他宣传政策,说只要努力争取,就一定能够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时,他突然哆嗦了一下,“扑通”一声跪倒在管教干部面前,号啕大哭。管教人员多少次的耐心启发和教育,他自己多少天的良心谴责与心灵煎熬,终于使他开始悔悟,边哭边说自己如何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他无数条罪行中,有一条最令人发指:一次进山扫荡,他闯入一户农家,发现屋后草堆里藏着一个青年少妇,少妇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见此情形,他兽性大发,一把抢过婴儿,猛地抛向身后,只听“哇”地一声,孩子就没了声息,他却像野兽一样扑上去,将痛失孩子、哭喊救命的少妇强压在地上。当他满足兽欲正准备出门时,同一个急奔而来的青年农民相遇,他凭借手中的武器,又将这个青年农民活活刺死。当他说完这幕亲手制造的惨剧时已是泣不成声,要求中国政府对他处以极刑。管教干部当即肯定了他坦白认罪是悔悟的表现,要他打消顾虑给亲人写信,让亲人来看他,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到日本与亲人团聚。
“哑巴”低着头回到小组,在庭院里背着人又痛哭了一场。从此以后,他完全变了,积极参加学习和各项讨论,还经常向管教干部汇报和交流思想。他将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滔天大罪原原本本地写成一篇《悔罪录》,经“外文组”译成中文,贴在俱乐部的专栏上供所有战犯阅读。
中日友好的使者

家父说: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是在中国实行惨无人道“三光政策”的罪魁之一。抗战中他指挥的部队在河北唐山地区制造了一条纵横数十里的无人地带,几天之内烧毁了连片的村庄,数十万居民瞬间失去家园,数以千计的居民惨遭杀害,遗尸遍野。在河北遵化、迁安两地,他下令在20天之内将长城沿线附近的居民统统赶走,所有房屋全部烧毁,还坐在飞机上亲自监督这次行动,发现尚残存一片绿色,便立即严令部下要“烧光毁尽”。那时的铃木启久已沦为人性灭绝的魔鬼。
自从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后,他从当初的顽固不化,到历经两次自杀,再到认罪赎罪,致力于中日友好,其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一次大会上,他悔恨地失声痛哭。铃木启久将上述罪行写成一篇名为《悔罪录:制造无人地带》的长文,作为认罪材料多次在会议上认罪忏悔。他的认罪材料经“外文组”译成中文,也在俱乐部展览过。铃木启久回国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保卫和平和反对侵略的神圣事业”,“要致力于中日友好”,“有生之日,就是我向中国人民感恩悔罪之时”。他牢记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的教诲,继续反省,重新认识自己的罪恶,将原先的《悔罪录:制造无人地带》改写成《悔罪录:罪恶的无人地带》公开发表,将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罪恶再度公诸于世。
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以后,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日本各地设有分会,专以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总会还发行了一份名为《前进、前进》的会刊,设有专栏,专门刊登会员撰写的亲身经历及揭露和批判军国主义的文章,还有会员把在中国漏交的罪行也发表其上,并声明这是向中国人民的补充交待。这些交待材料再通过邮件寄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大部分都经“外文组”译成中文,打印成材料,作为全体战犯的学习材料。
“中归联”的总会长叫藤田茂,也是前侵华日军的中将师团长,被宽释回国后经常发表演讲,宣传中日友好,控诉侵略战争的罪恶,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多次收到恐吓信。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当年我率领千军万马杀向中国,都征服不了中国人民,现在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意愿,是时代的潮流,怎么可能阻挡得了呢!”
以藤田茂为团长的“中归联”访华团曾多次应邀来我国访问,除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参观外,每次都要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看看。1973年家父亲见藤田茂及团员三四人来到管理所,当时藤田已八十高龄,身体健壮,谈笑风生,管理所金所长亲自搀扶着老人上下台阶。藤田要求见见医务室的刘护士长,以面致当年精心护理的感激之情。藤田茂一行到宿舍、学习室、俱乐部和运动场参观时,边走边看边谈,还指指点点地说,这房间他曾住过,那片苹果园中有他种过的树等。在欢送会上,藤田茂团长深情地说:“我活着一天,就要为中日友好努力一天,并要教导子孙世世代代永远同中国人民友好下去”,“我们来到管理所,不是什么参观访问,而是回娘家啊!”
家父还翻译过一些从日本寄给管理所的信件,其中一位日本妇女的信因译过之后又看了两遍,所以留下很深的印象。信的大意是:“我的丈夫原先在家庭中一向专制粗暴,说话写信都是对下级命令的语气,没想到在贵处改造几年,变得通情达理,委婉温和,写信也不像过去潦草,挥笔下令了,因此我不能不对您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家父感慨地说:“日本战犯之顽固堪称世界之最,然而,在中国改造过的日本战犯回国后却成为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并用亲身经历来宣扬中国的伟大和促进中日友好。世界上何党何国有此本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的‘改造政策做到了,真是了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