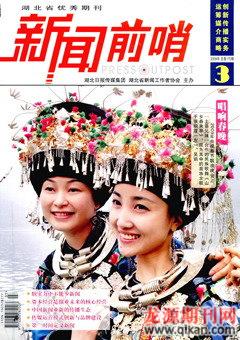纪录片如何“纪录”
王 丹
摘要在纪录片创作领域,一直有不同创作流派的探讨和争议。很多人说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用纯粹的旁观者的视角,应该不干预被拍摄者的生活的自然状态。但是从《生命的延伸》这部纪录片来看,恰恰创作者之一也是亲身经历者,而且创作者的介入还推动了事情的发展。这会不会与过去我们接受的“纪录片客观记录生活的”观念产生冲突呢?
关键词纪录片纪录方式探讨
2008年11月10日,湖北省麻城市一位36岁的青年木匠柏洋(化名)不幸遭遇车祸而脑死亡。其家属经过思想斗争后提出器官移植,让柏洋健全的器官有益于社会,结果成功救活了上海和郑州的3名重症患者。经过检索,这个案例是黄冈地区的首例多器官捐献,是湖北省的第4例、也恰恰是中国推行国际标准器官移植的第100例。100例成功的器官移植已经使得440多人受益。借用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移植办公室主任陈忠华教授的一句话:“100例是家属迈出的一小步,但是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
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内涵在中国还不是广为人知,但是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医学的发展都是意义深远,值得电视人加以宣传。为此,武汉电视台科教生活频道《纪录片之窗》栏目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并于12月21日播出了片长3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生命的延伸》。
一、创作始末——以点带面讲述器官移植
这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摄制作的片子。我们是第一个确定该选题的媒体,也是电视媒体中对此事唯一的报道者。广东电视台等也以口播的形式报道过。目前,国内大约30多家报纸和网络关注过,但是,我们最为迅捷,摄制组深入到了现场,以纪录片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案例的始末,并把涉及到器官移植的方方面面予以反映。全片应用现场音,使用搬演手段,直面真人、真事、真物、真情,力求还原现场感觉,谋求真实和感人的视觉、听觉效果。事后表明,我们在当地的采访过程还间接地推动了当地公安部门对于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
器官捐献者的各位亲属第一时间正面接受采访,这也是一个突破。以前的案例中大多亲属因各种顾虑都不能全面配合采访。我们摄制组与死者亲属、村主任和书记、当地法医、当地医院等做了广泛沟通,使他们敢于直面镜头、配合采访和拍摄,完整地再现了事件的全部。
通过制作这部片子,我们了解到:今年是中国国际标准器官移植推行的第5年,具有纪念意义。5年前的2003年11月,武汉市江夏区一名9岁儿童被车祸夺去生命后。家属申请捐献器官,成功救活了两名儿童。那是我国首例国际标准化的器官捐献。
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理解和支持器官移植。截止2008年11月底,在网上登记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多。我们在器官移植的内部网站资料中看到,他(她)们的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各异,但是他们无偿捐献器官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生命延伸、让爱心传递、让社会和谐。
参与中国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陈忠华教授告诉我们,经过5年来各方的努力。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逐步完备。《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先后出台施行。这是我国政府严格履行生命伦理原则,科学制订的管理法规,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正式走人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2008年10月,深圳红十字会已正式成立了器官捐献办公室,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纪录片《生命的延伸》播出后,收看过的居民、学生、教师、医生、律师、经理等各方人士来电来信发表感言:“通过片子,我获得了很多器官捐献的知识。器官捐献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值得大力弘扬的事情。片子中反映了器官捐献的很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移风易俗很不容易。虽然是一件沉重的事情。可是报道的效果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片子,很有震撼力,是非常值得的。建议今后继续关注柏洋家属、追踪相关话题。”
二、创作冲动——缘于柏洋事件的波澜起伏
我们在过去的新闻实践中得知有关器官移植在中国大地的背景和实际状况,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我们也为家处农村的人们有志于用器官移植的方式捐助他人的事迹所感动。但是真正触发我们创作《生命的延伸》纪录片的诱因在于:我们了解到麻城这个案例的整个过程有一些起伏、曲折和冲突,它们已经构成了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基本元素。
比如说,病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死亡了,而是有一个抢救的过程。抢救中证实确已没救了,脑死亡了,只是心脏一直在跳动。随之而来的是:病人的家属(妻子和妹妹)也不是一开始就提出要捐献器官,而是有一个思想反复酝酿的过程。而且她们提出捐献的最初目的也很淳朴,只是为了引起社会重视、加速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破案,后来才上升到不要让亲人突然在世界上就消失了、要让亲人的部分器官还能够救治他人、亲人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伸的境界。
接下来又发现想做成器官移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想捐就捐得了。因为不光家属不知道怎么捐献,医院的医生、麻城市当地的法医也不知道怎么捐献,整个黄冈地区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捐献渠道几乎陷于迷途。直到辗转找到器官移植的国内权威专家陈忠华教授,这在理论上就知道了器官移植应该怎么做?怎样做会有把握?这些构成了整个事件的波澜起伏。
到了这个时候,都以为柳暗花明,一切都会顺利了。但是事实上成功的器官移植还会面临6大实际问题:器官是否合格?配型是否成功?有无急需的受体?医院是否配合、各方能否协调?交通是否顺畅?有无经济或法律纠纷?这些问题导致每10个愿意捐献器官的案例中只有1个能够成功。这又面临新的困局。
这些矛盾、冲突导致了事件的波澜起伏,也吸引了我们。正是由于事件的这些多元素、多变化、多悬念构成了纪录片形成的要素,才引发了我们创作的冲动和决心:要把它做成一个可以展示的纪录片给大家看。
我们在了解事件过程的同时很快形成了本片创作的基本思路:以发生在湖北麻城的事件发展为构架,以死者亲属之一在片中做主线串连,充分展示各种冲突,最后构成柏洋家属成功捐献器官的完整过程。把个案与中国整个100例由点及面地相联,做出真实记录,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展示其深远的社会意义。
三、创作手法——看似干预,实则客观
在纪录片创作领域,一直有不同创作流派的探讨和争议。很多人说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用纯粹的旁观者的视角,应该不干预被拍摄者的生活的
自然状态。但是从《生命的延伸》这部纪录片来看,恰恰创作者之一也是亲身经历者,而且创作者的介入还推动了事情的发展。这会不会与过去我们接受的“纪录片客观记录生活的”观念产生冲突呢?
我们觉得,这是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手段的探索。纪录片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应该很客观地反映社会、反映事实,这是它的基调。但是实际上这里牵涉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叫“客观”?
我们面对的所谓“客观”是靠什么感知的?是靠我们的眼睛感知的、靠我们的耳朵感知的,靠我们的其它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而感知器官是有可能出错的。也就是说,眼见是否为实?——这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你听到的东西是否有杂音?——这也是一个问题。这是从感知的角度来看的。感知的东西离真实的客观很可能有偏差。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你拍摄的、编辑的、反映的的确是客观的存在,但是你反映什么?反映哪些?怎么反映?却有你主观的选择。因为客观的存在非常多。比如说,一天的生活丰富多彩,而早上刷牙这样一个动作可能是其中很无聊的一部分,你要不要去着力反映它?你反映它是你的主观选择,你不反映它也是你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所谓客观,任何被感知的或者在创作中涉及的一切的客观都是在主观因素参与下的客观,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
对于《生命的延伸》这个片子而言,我们的确打破了原来那种不干预生活、不干预事实的纯粹客观的创作手法。我们的撰稿人王光艳其实就是事件的亲历者,他是死者的堂兄,对于死者妻子和妹妹提出器官移植后如何寻找捐献渠道、到成功捐献都起到了跟踪、协调和促进的作用。他对于我们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组织还原现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片外,他是亲历者,而在片中,他是出镜的串连人,也是撰稿人。表面上看,他已经干预了生活、干预了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感知中或者作品中所谓的客观不是纯粹的客观、而是搅和了许多主观元素的客观”的这么一个概念后,我们就可以为了真切地反映客观现实,有意识地进入到生活中去,进入到某个事件中去。
我们进入事件后是否会破坏原有的真实、原有的客观呢?我们肯定不会有意地破坏它,我们只是把原有的客观、原有的真实,用一种比较简捷、有效的方法,把它提炼出来,把它很好地再现出来。虽然创作人员介入了,参与了,我们对于整个事件的真实。并没有本质的影响。而是说把“天时、地利、人和”的方便之处运用到极致。准确地把家属的心态、心理的变化表现出来了,把医院最初的诊断、到对于脑死亡的判断、到最后成功地进行器官移植整个的过程以及事件的意义都准确地提炼了出来,对于整个事件原有的真实,只是化繁为简,更便于视觉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