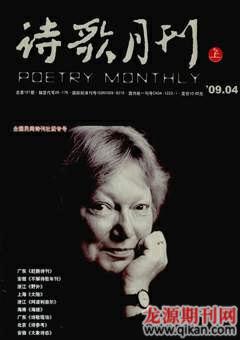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备忘
采访时间:2008年9月14日
采访人:姜红伟
受访人:赵思运(山东荷泽)
姜红伟:请你谈谈自己的简历和诗歌创作、发表、出版、获奖情况。
赵思运:按照大家给我贴的标签,我属于“中间代”写作者。我的学术方向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评诗是我的副业,本不是我乐意所为,更多的是朋友对我的“期待”。写诗却是我的爱好,是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产物。
1986年开始写诗,但是在官刊很少发表。我特别喜欢在民刊发表,而且大部分都是先在民刊发表。我的《毛泽东语录》组诗不可能直接在官刊发表,而是在网络和民刊产生一定影响以后,赵丽华把他选到了《诗选刊》,然后林贤治编进了《2004文学中国》。《木樨》、《一个疯子从大街走过》等也是这种情况,都是从民刊走进《诗歌月刊》和《现场:先锋网络诗歌风暴》、《2007文学中国》等选本。
出版了一本诗集《我的墓志铭》,用的是美国的惠特曼出版社的刊号,在中国大陆也相当于民刊。我自己喜欢的作品都收录进去了。朋友劝我找个体制内的出版社出版,呵呵,无所谓了,因为我不愿意把我最喜欢的作品阉割掉。
诗歌也获过奖,但是,那有意义么?
姜红伟:请你谈谈你对民间诗歌报刊这个概念的理解。
赵思运:民刊,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官方的存在于民间的期刊,他以独立的精神方式,彰显民间话语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刊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都具有非体制性。严格地讲,那些地方文联、作协、大学生社团、企业社团办的报刊,即使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刊号,它们也不能称为“民刊”,因为它们属于体制化范畴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应该是具有独立的诗学立场、文学立场和思想立场的同人联办的刊物。在这种意义上,《诗歌月刊·下半月》、《星星诗刊·下半月》、《诗选刊·下半月》乃至于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都可以划分到民刊的范畴。
姜红伟:你为什么喜欢收藏民间诗歌报刊?你怎样看待民间诗歌报刊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所起的重要
作用?
赵思运:我最喜欢民刊的自由、独立精神,以及超越现实物质功利的心态。民间诗歌报刊身上的蕴含的很多质素在公开发表的报刊中很难体现出来。
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无论是诗歌精神、诗歌观念还是诗歌文本,都是如此。可以说,离开了这难以数计的民刊,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个时段的诗歌史。目下,官刊、民刊、网络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空间格局,出现了诗歌资源整合的趋势。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当下的民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大批的文学青年的试验基地。二是像《诗歌与人》那样的品格,勾画着文学史乃至诗歌史的形态,为文学史提供着新的概念、新的作品,他们提出的“70后”、“中间代”延续了诗歌史,少数民族诗人专号、女性诗歌专号、翻译专号等,都是对诗歌史的丰富与补充。三是具有体制外的独立品格的民刊。而我更看重的恰恰是第三种类型。因为第一类大多有被招安的渴望,第二类也被官方刊物有限度的接纳,只有第三类,才具有着无法被官方立场化约的价值尺度。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语境中看,其意义就更加显示出重大了。
姜红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民间诗歌报刊的?
赵思运:大概1998年。2002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以来的几年,大家赠送的民刊更集中一些。
姜红伟:你收藏民间诗歌报刊的途径有哪些?
赵思运:主要是民刊的主办者赠寄送的。阿翔也曾经寄送给我一部分。
姜红伟:你的民间诗歌报刊收藏重点是什么?
赵思运:当然是产生较大影响、存在时间相对较长的民刊了。我更关注的是1980年代及以前的民刊。我尤其关注那些诗学立场鲜明、价值立场尖锐的民刊。如果他们的诗学立场能够融合特定的人文立场和精神立场,无疑会更有史料价值。在人文、学术普遍放弃思想的时代,文学和诗歌就需要承担起人文的责任。比如,广东的肖铁主办的诗歌民刊《今朝》于2006年第一期改刊为大型思想人文刊物,深意在焉!它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诗歌乃至包括文学的无力感,我们需要另一种言说思路,来介入生存语境。
姜红伟:除了民间诗歌报刊收藏外,你还收藏了哪些诗歌资料?请举例说明。
赵思运:我对诗歌资料的搜集很杂。我在高校中文系工作,只要在精神气质上与我达成一致的诗歌资料,我都尽量搜集,有诗人的作品,有诗歌理论批评著作,也有重要的诗歌史料。
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我会特别留意。如徐敬亚等编选的《1986-1988中国现代诗群大展》、唐晓渡等编选的《先锋诗歌选》、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系列、张清华编选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系列、树才编选的《中国最佳诗歌》年选系列、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等。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爆发出而又被历史屏蔽了的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作品,如《右派诗歌》、《红卫兵诗歌》、《西方性爱诗选》、《维权诗选》、《xx诗选》。廖亦武编著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也颇值得珍藏。
姜红伟:在你收藏民间诗歌报刊的过程中,你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困扰你进行民间诗歌报刊收藏和研究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赵思运:搜集的难度非常大。近年的好一些,很多主办者主动寄送了很多,加上网络信息比较发达,基本都能够搜集到。但是,80年代的期刊以及更早的就很难找到。甚至主办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民刊的价值,保存的资料很不完备。
民刊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热情。在现行的科研体制里面,民刊研究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科研资助的,因为在科研体制的眼里,“民刊”是毫无意义的,是文学爱好者的园地,是诗歌的低级形态。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专家对新诗是无知的,对民刊更是无知。在正规的学术园地里,也很难找到民刊研究的发表园地,因为这些园地都只关注所谓的“重大诗学话题”和主流文学史论及的“有重大影响的诗人”。
姜红伟: 到现在为止,你大约收藏了多少种民间诗歌报刊?你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有影响的民间诗歌报刊有哪些?
赵思运:由于生存空间的狭仄,我的十几箱书籍,包括前几年搜集的民刊,一直束之高阁,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粗略估计,大概有200多种吧?我认为最有影响的诗歌民刊有:
《今天》、《启蒙》、《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巴蜀现代诗群》、《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大陆》、《撒娇》、《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幸存者》、《他们》、《象罔》、《大学生诗报》、《诗参考》、《诗歌与人》、《倾向》、《北回归线》、《诗江湖》、《女子诗报》、《水沫》、《第三说》、《垃圾派》、《垃圾运动》、《低诗歌》、《翼》、《赶路》、《诗歌现场》、《葵》、《活塞》、《今朝》、《一行》、《诗文本》、《诗歌报》、《阵地》、《唐》、《极光》、《扬子鳄》、《自行车》、《原创性写作》、《或者诗歌》、《独立》、《现在诗歌读本》、《存在诗刊》、《剃须刀》、《诗丛刊》、《太阳》、《爆炸》、《丑石诗报》、《诗歌月刊·下半月》、《星星诗刊·下半月》。
姜红伟:你是否有过举办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展览的想法?
赵思运:还没有考虑过。刘福春、世中人等都举办过民间诗歌报刊展览。我认为很有意义。应该感谢他们对于民刊的整理与挖掘所做出的贡献。
姜红伟:你曾经创办过民间诗歌报刊吗?现在还在继续创办吗?
赵思运:在高中和大学办过两种。
1984年在山东省郓城县第三中学,与马敬青等人创办春草文学社,出版《春草》报。这是全县第一家文学社。后来我们还合作出了一本复印诗集,名字叫“青涩的橄榄”。那是我初学写诗的日子。
1986年我考取山东菏泽师专中文系,加入了黄河浪文学社,1987年主编《黄河浪》社刊。1990年,我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菏泽师专工作,一直见证了“黄河浪”的奔腾。黄河浪文学社是山东省菏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文学社团。如果有人著述菏泽文学史,黄河浪文学社当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黄河浪》的指导老师和主要写诗的成员有赵统斌、耿立、赵思运、李雪晴、王永伟、韩旭、张秋歌、秦绪林、傅子栋、张恩涛、马合成等,社刊《黄河浪》半年一期,一直坚持到现在。
姜红伟:据你了解和掌握,目前在中国有哪些人在搞民间诗歌报刊收藏和研究?他们的收藏和研究成就如何?
赵思运:我知道的诗歌民刊收藏者有“汉语诗歌资料馆”的世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四川民刊《独立》主编发星。较开放的官刊编辑估计也会收到很多民刊,比如《诗歌月刊》的阿翔、《诗选刊》的晴朗李寒。在学者里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清华曾经做过民刊研究,在《上海文学》杂志开过一年的专栏;南开大学文学院的罗振亚在其博士论文《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里论及很多诗歌民刊资料,相信他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姜红伟:你是如何将民间诗歌报刊资源转化为研究成果的?目前,取得了哪些成就?今后你在民间诗歌报刊收藏、研究上有哪些计划?
赵思运:其实我算不上民刊收藏家,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关于民刊的基本看法,我有篇文章《民刊何以“民刊”?》,《大陆》、《赶路》、《2006-2007双年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7月版)都曾收录,网络上也比较容易搜索到。目前正在撰写《中国当代诗歌民刊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