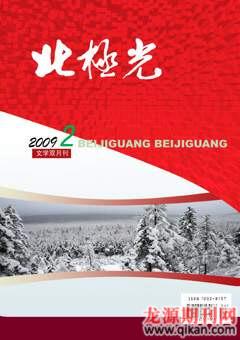散文二题
徐国春
童年的记忆
我的出生地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每年有多半的时间是刮风,风带着沙子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里冬天的风雪天气,刮着白毛风嗷嗷响,漫天都是白色。这种恶劣天气,牧区的草原上就会冻死很多牛羊。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龙梅、玉荣在暴风雪中为保护公社的羊群和风雪搏斗被冻伤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感人。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是简陋的泥草房。教室没有桌椅,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课桌是一块板两边垫着砖。冬天来临,教室四处漏风,窗户有几块玻璃碎了,外面刮风下雪一点也不客气地钻进教室里,靠窗户的同学身上落一层清雪,扎人的寒风把手和脸冻得发木。那时候备战备荒闹革命,到处都是防空洞,我家炕下面就是地洞,防空警报一响,全家人就躲进地洞里。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班级就有地洞,而且在我脚下。我经常逃学,就是从脚下地洞钻出去的,洞里面四通八达,从学校的地洞就可以进入防空洞。防空洞很大,上面是砖砌成半圆,下面是水泥地,能排列6辆卡车。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点上油毡纸拿在手里,靠油毡纸点燃的那点亮光很难辨别方向,完全凭着记忆在防空洞里自由出入,只要油毡纸火焰被风吹得呼呼地响,一定是到了洞口了。顺着防空洞可以到工厂也可以回家。老师经常找家长,我经常挨揍。后来不用老师找家长,家里人就知道我是不是又钻地洞了,因为在地洞里呆时间长了,点燃的油毡纸把脸熏得黑糊糊的,邋里邋遢,满身都散发着油烟味儿,回到家免不了挨揍或者罚站。
那个年代,学张铁生交白卷,学黄帅写大字报,整天不上课,学校一片混乱,到处贴着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我不会写就让我父亲代笔,我再抄下来,内容就是老师经常告家长我经常挨揍的事儿,对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来说,受到这样的精神洗礼,感觉就是好玩。隐约地记得,我天天在外面玩,像个野孩子,不按时回家吃饭,经常胃疼、头晕,一饿了就吐酸水,脸色蜡黄,骨瘦如柴。那时家里孩子多,父母照顾不过来,胃疼得厉害了,母亲就用一粒去痛片放在酒盅里,倒满酒点着,待药片融化后,趁热喝下去,又苦又涩,进入胃里就舒服多了。头疼的时候也是用酒揉搓头部,这样的土方法减轻了不少疼痛。
我自幼就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外面的墙上到处都是我的大作,甚至家里的户口本也无一幸免。画的是军官、大刀、枪。因为户口上被我画得乱七八糟的,家里人曾受到户籍警严厉的批评。童年时的眼中世界,及所感受到的那种种奇异的事物,譬如铺天盖地的大雪、天空中出现的彩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黄花的大草原、闲置下来的旧厂房、秋日雨后出现的像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冰上旋转的冰尜,那达慕大会奔驰的骏马等等,都会在充满幻想的少年心灵里引起莫名的向往和憧憬。
我父母的老家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离家20年了,我母亲想家,经常哭。父亲没有办法,就调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了却我母亲多年的夙愿,大兴安岭离莫旗不远。那时候莫旗隶属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后来又归回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了。
从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来到大兴安岭,眼前的世界变了,到处都是林海松涛,浩浩荡荡,莽莽苍苍,冬天则是白雪飘飘,一派银装素裹,满目琼瑶。
家搬到大兴安岭后,我父亲单位没有房子,借住在我叫王叔、王婶的家里。他们家是三间板夹泥的草房,我家住在西边,房前是开阔的菜园。后来知道王叔家是菜农,他们是那么的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短暂的夏季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在菜园子种上了各种蔬菜和花草,有的是让人吃的东西,如黄瓜、茄子、倭瓜、豆角、苞米等,有的则纯粹是供人观赏的,如矢车菊、爬山虎、大烟花等等。当然,也有半是观赏半是入口的植物,如向日葵。一到昼长夜短的夏天,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几近疯狂地生长着,它们似乎知道属于它们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就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调零令人痛心和震撼。
王叔家有个女孩儿和我同岁,生日比我小,她叫我哥哥,我们俩一起上学放学。我从锡盟带来一小木箱画本,经常借给她看,给她讲在锡盟发生的故事。她喜欢看我画画,总是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我,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她也是我的模特,每次画她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地打扮自己,喜欢梳一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就像《红灯记》里的铁梅。她的眼睛如秋水一样,清澈纯净,没有一点杂质,柔美的像月光一样欢乐。她把我画的画贴在墙上,那些画在她的心里是温暖的,又是奇妙的神圣的。
我们经常和邻居家的小孩儿一起到离家不远的小河边玩耍嬉闹,一起下河围成圈子用筛子捞鱼,大家叽叽喳喳地向前行,每次捞到鱼,她的眼睛变得鲜亮起来,随之发出清脆的笑声。玩得是乐此不疲,忘乎所以,欢声笑语填满了整个小河。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想起来依然回味无穷。
有一句俗语,“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她的身上。那天放学了,我没有和她一起走,她自己随着放学的同学像小鸟儿一样,蹦蹦跳跳快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明媚的阳光依然温暖地照在她的身上。她丝毫没有察觉到灾难就隐藏在她幸福快乐的背后。学校不远的地方新挖一条很深很长的沟,我们放学都要路过这里。沟不是很宽,我们都可以蹦过去。这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蹦过去,掉在沟里,把腿摔破了,同学把她拽了上来。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都很皮实,不像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手破点皮家长是呼天抹泪的。我们习惯了,摔坏了卡破了经常的事。她回家跟王叔、王婶说自己腿摔破了。王婶说,没事儿抹点紫药水,腿疼我给你揉一揉,拽一拽就好了。上学的路上她感觉腿还是有点疼,还是坚持上了几天学。一天放学的路上,她对我说,哥,我腿好疼。我说,坐下歇一会儿再走。她说,哥,我的腿像针扎一样钻心地疼,就在大腿根。我搀扶你慢慢走,我说着慢慢地小心翼翼把她扶到家。王叔写了一张请假条,让我交给老师。半个月过去了,她的腿没有见好。王叔和王婶着急了,送到了医院。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由于耽误了治疗,股骨头坏死了,需要转院到哈尔滨治疗。王叔家是菜农,就靠菜园子里种的菜换点钱,家里根本没有积蓄,只好在本地医院治疗。我那个时候对贫穷没有什么概念,自从她得病没有钱治疗,还有王叔王婶的眼睛里,透出沉重的悲伤和无奈,我对人生有了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一个活泼可爱花季般的小女孩儿的不幸中感悟来的,看到了人是多么的脆弱。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她出院,是两个胳膊拄着拐杖回来的,她那忧郁的目光,在我心中生出缕缕苍凉,像那茫茫的暮霭一样在心间蔓延。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永远不能上学了。看着左邻右舍的孩子走出各自的家门,快快乐乐地奔向学校,她凝望着瞬间就变得空空荡荡的街道,她饱受着心灵和肉体的折磨。我那时候不懂怎样去安慰她,她的心情是可想而知。我每天放学都会远远地看见她,架着双拐伫立在家的大门口,等着我回来。她的眼睛里丝毫没有一点委屈,一点抱怨。她总是微笑地对我说:哥回来了,快给我讲讲学校发生的事。她对生活和学习的渴望,还有无奈的隐忍,藏在她的微笑深处。
过去很多年了,她那孤独的身影总会浮现在我心灵的河岸,带着一种隐痛,一种久远的情感,在我心魂中飘然而出。
色彩岁月
我小时候就与画画有着难分难解的缘分,家里的邻居就是画连环画的画家,我经常到他家玩。后来家搬到大兴安岭,父亲有一个朋友是群众艺术馆馆长,黑龙江省画院院外画师赵文贤先生。赵文贤先生第一次到我家,看了我平时画的画,高兴地说:走,到我家去。把我领到他的家里,拿出珍藏在家里的许多名画家的真迹让我欣赏。记得有潘天寿、王雪涛、谢之光等一些著名画家的真迹。让我大开眼界。先生拿出一本《芥子园画传》还有几只毛笔和几张宣纸,告诉我一些用笔的方法。我回到家里开始临摹《芥子园画传》中的各种皴法,什么“斧劈皴,乱柴皴,荷叶皴”这皴那皴,于是,开始天天皴。通过日积月累的修练,追求国画艺术的审美境界,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那时候的我既轻松又快乐。与此同时父亲又领来一位老师,是实验中学历史教师刘司斌先生。刘先生对书法颇有研究,在学术上非常严谨,为人谦和,刘先生刻苦治学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他的书法刚劲、平稳,运笔很有力度。我有时间就到刘先生家求教书法和古诗词。书法初学柳公权的楷书《玄秘塔碑》,先生说,颜筋柳骨,根据我的性格先练习柳体为好。写了一段时间,开始学隶书《张迁碑》,教我读贴、临帖、背贴,从悬腕到悬臂。我沉浸在书法点画赋予线条变化的情感之中。每日起来即背诵《唐诗三百首》,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吟。”
恢复高考以后,地区群众艺术馆开办美术班,请来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的老师上课,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素描,什么是色彩。中学毕业连个技工学校都没有考上。呼中林业局教育局招代课教师,正好我在艺术馆学画画发给一个结业证书,我拿着结业证书和美术作品,只身来到呼中林业局应聘美术教师,分配到呼中第一小学。当时代课教师工资低,从生活费中省下钱买颜料和宣纸。教学之余,有张有弛,高一浪低一浪从事我的艺术生涯。画的一点一线都是我心中的语言,不论是千姿百态的树,还是起伏的山峦,是渺茫,还是激荡,都在展示着我真切的情绪。那是宁静的世界,是自由的王国。挥毫泼墨,有情感有生命的形象跃然纸上。瞬然间,那些恼人的琐事荡然无存。也许这就是荷兰画家凡高的那种内心的冲动。用颜色画出生命的流动,真真切切。在充满快感的绘画中体验着梦中久远的思想,把幻想变为现实,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就像爬上山顶时要大声呼喊,高声歌唱。我常常领着学生到山林里写生,我最温馨的记忆就是呼玛河。特别是秋天,河水从大山深处款款地走来,清冽冰凉。河卵石闪着光,像女人妩媚的眼睛,只是在你心头轻轻地一颤。我背着画夹子,沿着河在山中穿行,在那些早已被秋意浓妆艳抹的山路穿行,满山飘摇的色彩,随着明媚的阳光在山峦起伏中变幻着。我不时地停下来,支上画架。突然感觉到除了画笔的声音,大自然静谧的似乎不能让人接受,但因为有水声,静而不寂,清爽宜人。微风吹皱了河水,把山和树投下的斑斓色彩揉碎了。我环顾四周寻找能入画的景色,惊奇地发现河的对岸长满了桦树,在护河柳还有夹杂红紫的映衬下,那近乎透明的桦树黄得纯净且饱满,厚实而明丽。用水彩是很难表现的,只有油画才能表现出来,必须有及其敏锐的色彩能力,画出一片厚重的、协调的色彩,绚烂的桦树林就会跃然在画布上。太阳西下,阳光更加灿烂,那片桦树林更加明亮。你会发现勤劳的山区人,在地里起土豆、白菜、大萝卜等。他们把这些蔬菜储存在地窖里,在漫长的冬天里,就不愁没菜吃了。你会看见他们坐在堆满白菜的马车上,卷一支蛤蟆烟,很舒畅地吸一口,望着一群牛在河边喝足了水,日暮归家。我的心中有一种沉醉,眼前就是一幅幅巴比松画派的油画。我有一方闲章“自然之子”。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学校的锅炉工是上海知识青年,和我住在一个宿舍,业余时间喜欢写诗下象棋。他有事没事就看我画画和翻阅我的书籍。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学画画为什么不去考美术学院,当代课老师熬到什么时候才能转正。我有点茫然地说:美术学院?到哪里去考……
我知道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个美术系,特别难考。你考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我笑了笑说:就我的经济条件,哈师大我都没敢想过。不过他说的话,还是让我萌生了考美术学院的念头。放暑假回家,我到赵先生家把我考美术学院的想法说了。赵先生很赞成,他说你的素描和色彩离考学的距离相差太远,我介绍你去哈师大进修学习。不久就收到哈师大寄来的进修通知书。我拿着进修通知书和单位领导说明我要进修美术。领导非常支持。说道:学费你自己拿,工资照常开。我那时心情特别激动。我回家,跟我父母说,我要去哈师大进修美术,需要学费。我父母一脸愁容。我没有想到家里会没有钱。我在家是软磨硬泡,父母拗不过我,还是把学费凑齐了。现在想起来真是难为他们了,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
我第一次自己离家到省城哈尔滨。下车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发GE3C2A耍哈师大在哪啊?问吧,总算遇见好心人告诉我坐11线到哈师大下车,下车了还是晕晕乎乎的,好不容易找到哈师大艺术系。同学领着我到主管美术培训班老师那里报到,交了学费。跟着同学来到住的地方,进屋一看眼前一片凄惨,屋里乱七八糟,床是用简易的木板做的通铺,屋里潮湿,墙面很脏,墙皮已经脱落,贴了不少同学画的画。我想在这里可以获得新的技巧、新的思想和新的感受。就这样,和11个同学挤在一张铺上的求学生涯开始了……
每当我想起为了艺术如醉如痴的梦境,为了进入艺术的殿堂而迈入生有尽而艺无穷废寝忘食的日子,以及如烟如雾的甘苦,至今仍缠绕着一种无法摆脱的眷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有一年就要超过了考学的年龄,有一个同学在齐齐哈尔教师进修学院上学,给我寄来他们学院的报名表,在信上说:你不要考美院了,你画画得好,文化课太差了。考我们学院吧,一定能考上。就这样我考入齐齐哈尔教师进修学院。
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的学校,在生存与守望的同时,我也困惑过。逛书店时,囊中羞涩,只能用贪婪的目光浏览那些让你心中痒痒却又买不起的书,仿佛自己是站在食品店华贵玻璃窗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
终于,我调入杂志社做美术编辑。从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呈现出明亮的绿洲。
书画艺术,往往对心理意志的磨练达到极致。青灯古卷,晨钟暮鼓,漫长的苦练与短暂的成功营造出“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恬然心态,使生活充满惊喜与诗意,心田清泉长流,灵魂天籁回响,那是局外人体味不到的。浸漫于诗书画,聆听旋律悠扬的音乐,涉猎于文史哲学,会惊叹书画之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并为其仅仅以线条墨韵展现如此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而折服而沉醉。尤其是登上巍巍的山川,心随大江奔流,极目远眺,水天一色,观云海之变化无穷,看星汉之灿烂辉煌,这一切融入于尺卷,简直是一曲自然与生命的赞歌。
在生活中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自然,风花雪月的日子一片一片的从天空中滑过。我常常站在画室的窗前,凝望着眼前熟悉的景象,一座座高楼,栉次鳞比的小区,一条条清洁干净的街道,繁华的商场,都在日新月异中变化着。春暖花开的时节,山城人喜欢到北山公园晨练。公园依山而建,蜿蜒崎岖的小路在山林中穿行,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天,重新回归大自然,汲取天然的真气,强健柔弱的身骨。幸福快乐的生活绽放在山城人民的欢声笑语之中。我的画就属于这片静美富饶的土地,一条线,一块墨色,一片调和的浓淡与青赭。
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年的往事,我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思考,以及我的故乡我的童年。许多往事似烟云般逝去了,一种久远的岁月色彩,是忧伤,是快乐,是希望……
责任编辑 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