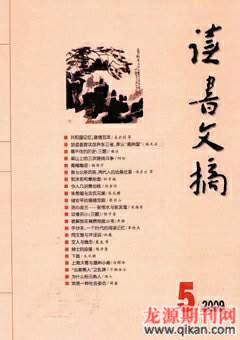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平津沦陷,胡适向蒋介石上条陈
台湾蒋介石档案中,藏有陶希圣致陈布雷函手迹一通,函云: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怅。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断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后以字行。湖北黄冈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1927年参加北伐军政治工作。1929年主编《食货》半月刊。193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恩,布雷为其笔名。浙江慈溪人。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1937年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常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函中所称川越,指川越茂,原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被提拔为日本驻华大使。次年奉调回国。1937年6月,再度使华。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川越声称赴北平“避暑”,自上海北上,滞留天津,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均由使馆参事代理。经中国政府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川越才于8月3日离津,经大连南返。函末署五日,知此函为1937年8月5日作。当日,陶希圣与胡适共同访问陈布雷,企图对时局有所建议,未遇,便由陶希圣出面,写了这封信,要求陈向蒋介石陈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但他同时又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他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四原则: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组织;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积极部署军队,企图防守沧县至保定一线。陶函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应时之策。虽仅一人署名,但函中明言“我等”,则代表胡适观点无疑。
卢沟桥事变后,在对日态度上,国民党和知识阶层人士分为和战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与日本作战必败,极力主和,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8月3日,川越茂离津时,曾就卢沟桥事件向记者表示:“吾人担任外交,非努力将此种事件设法由和平解决不可。结果如何,固当别论,自应尽力从事者也。”又称:“仍冀中日关系于最后危机线上可以转换,尽力调整国交。”陶、胡对川越茂的南返存有希望,提出不要拒绝他入京,而要利用他“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与日本达成“一刀两断”的方案,其内容为保持冀察领土完整,保守河北中部的沧州、保定一线,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而其交换条件则为“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何处是陶、胡所指“力所不及之失地”,函中未明言,但同函附有条陈一份。
原则: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左(下———笔者)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河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河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其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五)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外交手续:
1.两国政府商定上项方针(不公布)之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退两国军队,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原状。中国军队撤退至河北省境外,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北平、天津及河北省曾被日本占据地域内之政警务由中国政府派文官大员接管。其治安维持,由中国保安队担负。两国政府宣布军队撤退时,同时声明在公布之后三个月之内,由两国选派全权代表在指定地点开始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
2.第二步为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依据两国政府会商同意之原则与方针,作详细的节目的讨论。此第二步之谈判,应不厌其详,务求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树立新的国交。谈判期间不嫌其长,至少应有两三个月之讨论。交涉之结果,作成详细条约,经两国政府同意后,由两国全权代表签字。
此条陈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共4页,根据字迹,一望而知为胡适亲笔。据此可知,陶、胡二人所主张放弃的“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三省。条陈中,陶、胡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
陈布雷见到陶希圣的信件和胡适的条陈后,于8月6日转呈蒋介石,同时写了一封短函,表示自己的意见,中云:
兹有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敬祈睿察。
函中,陈布雷明确否定了陶、胡之见,但肯定二人的“忠诚迫切”。蒋介石见到后,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介绍了胡适的“主和”主张,加以讥刺,但他未点胡适的名,而是称为“某学者”。参谋总长程潜很生气,直斥胡适为“汉奸”。当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时,蒋介石又说: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仗],难打胜战[仗]。
显然,蒋介石所称“许多人”,包含陶希圣和胡适;所称“有人”,更直指陶、胡。蒋所称“以长城为界”,正是胡适在条陈中所述意见:“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所称“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也与陶函所述不能将国力“轻于用尽”的意思相近。然而,蒋介石又说:
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信义”,而且贪欲无尽,得寸进尺,吃到一块肥肉之后还想吃下一块,占了一个便宜之后还想占下一个。以为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可以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止步,换来中日间的长久和平,实在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幻想。在这一点上,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因此,蒋介石又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仗]不可。”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陶希圣、胡适的意见被否定。蒋介石在信封上用蓝色铅笔写了一个“胡”字、一个“存”字,将二人的信件“留中”了。
胡适条陈之后,蒋介石档案还收有陶希圣《中日外交意见书》一份,建议“以非常之方法准备外交谈判”。其方法有三种:1.派遣要员直接与川越茂“作侧面而有力之秘密周旋,在京沪急转直下以达于正式谈判”;2.派在野重要人员直到东京,访问日本近卫首相与广田外相以至日本军部,作开始谈判之先声;3.在伦敦由中国驻英大使经过或不经英国外交部之周旋,与日本驻英大使开始作谈判之准备。陶希圣认为,以上三种方法中,以第三种较为适宜。《意见书》中,陶希圣进一步提出与日本谈判的“最高与最低限度之条件”。他说:
今日中国不能战胜日本,故当然不得不作最高限度之让步。今日中国已能抵抗过度之侵略而维持生存,故可以要求独立自主之存在,非一•二八以前或塘沽协定以前忍气吞声可比也。所谓独立自主之存在,一则如政治经济组织之完整,二则如国防之自由建设,三则如国际关系之自决,皆其必有之条件。故共同防共、五省自治乃至于走私等等,皆在最低限度之下,不可容许。然为保持此最低限度,在最高之让步,不可不以盖世绝代之魄力而为之。最高之让步,全为保持完整独立自主之政治经济军事之组织,不恤将六年来之一切纷扰,一刀两断而解决之。为此,宜一改过去只定最低限度之容忍条件,消极的拒绝其要求或降低之之态度,积极的提出我国保持完整独立自主国家所能处之代价,具体简明言之,宁割地而不丧权,不复效过去宁丧权而不肯割地,以致地仍失而权亦不保。
《意见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盖世之魄力”作“最高之让步”,“宁割地而不丧权”,可见,其主要意见仍是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意见书》最后称:“依此痛苦之认识,另提交涉条件,兹不再赘。”并以括号说明“胡适之先生写成另交”。可见这份《意见书》仍为陶、胡二人的共同意见。《意见书》并称:“上海战起,首都被袭,更无从再谈不战。”“上海战起”,指8月13 日淞沪抗战爆发;“首都被袭”,指8月15日日本飞机两次空袭南京。据此,知此《意见书》写于8月15日之后不久。当时,抗战已成国策,但是,陶希圣、胡适仍然担心战争会毁灭中国精华,主张通过“割地”,以外交手段结束军事。《意见书》说:“若我尽吾六年来之菁华而置之于疆场,则菁华既竭,分崩又起。故当在外交上乘我力未竭之时,求收束军事也。”
早有此议
胡适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5年6月17日,胡适就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要求“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当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亲日派分子白逾桓等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以及东北义勇军一部退入滦东“非武装区”,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为了施加武力威胁,日本还从中国东北调关东军入关。6月10日,胡适从何应钦处得知,“日本人的要求完全接受了”,心里觉得“难过得很”。次日,胡适特撰《沉默的忍受》一文,号召国人接受教训,“把国家的耻辱化成我们的骨血志气,使骨头硬,使血热,使志气坚韧刚毅,时时提撕警醒自己”。同月17日,胡适因担心国民政府“在枪尖之下步步退让”,“自己,一无所得”,发展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便错误地向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可以看出,胡适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向蒋介石所上条陈的基本内容在1935年6月华北危急时就已形成了。
王世杰反对胡适的意见,6月28日复函称:
故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方亦决不因伪国之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在我国政府一经微示承认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
王世杰清醒地看到了胡适主张的巨大危害:日本不会因得到部分满足而停止侵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无法立足,在国内则面临分裂、崩溃的危险。但是,胡适执迷不悟,7月26日致函罗隆基,告以致王世杰函内容,函称:
雪艇(指王世杰———笔者)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的一句,他们尤不愿谈及伪国的承认问题。他们不曾把我的原电及原函转呈蒋先生,其实这是他们的过虑。
胡适否认自己的方案是“妥协论”,要求罗隆基将此函带给蒋介石一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曾应邀参加蒋介石所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在听了蒋的谈话后,他表示“非常兴奋”,建议调用全国的军队充实河北国防,而且肯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不屈服,不丧失主权”。但是,很快他就发生转变。7月28日,胡适下山飞抵南京。29日,得悉中国军队在南苑等处惨败,宋哲元等退出北平,胡适大为紧张,即积极活动,力主与日本“和谈”。30日,他到高宗武家吃饭,与所谓南京的“青年智囊团”萧同兹、程沧波等人商议,决定外交路线不能断,由高宗武负责打通此线,同时决定寻找“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中的要人,胡适看中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做“社稷之臣”,在蒋的身边“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31日,胡适致函蒋廷黻,声称“这几天是最吃紧的关头”,“焦急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同日,胡适应邀到蒋介石处吃饭。蒋称“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蒋的意见得到在座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支持,胡适觉得不便说话,只表示:“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当日,胡适日记云:“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这则日记说明,胡适自知自己放弃东三省的主张难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但他还是要竭尽心力去游说。8月3日,胡适、吴达铨、周炳琳、罗家伦、蒋梦麟等在王世杰家密谈。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慌,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周炳琳、蒋梦麟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8月5日,胡适遂与陶希圣共同拜会陈布雷,企图通过陈向蒋介石递条陈。次日,胡适得到蒋介石的谈话通知,胡适事先准备了一封长函,用以补充谈话中的不足。其主题为:“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其理由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其步骤为:先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情况;第二步,两三个月后举行正式交涉。显然,与上引8月5日条陈及陶希圣函的精神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此函未提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而代之以“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会谈情况,据记载:“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
胡适抛弃“和平梦想”
胡适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当然大错特错,但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所在。1935年6月20日,胡适在致王世杰函中,说明自己的目的是“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从而取得“喘气十年”的机会。他说:
察、冀、平、津必不可再失。失了之后,鲁、晋、豫当然随之而去。如此,则中国矿源最大中心与文化中心都归敌手。如此形势之下,中央又岂能练军整顿内政?
胡适估计:“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因此,他在提出向日本“求和”的第一方案的同时,又提出不计利害,苦战四年,等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同年6月27日,他在致王世杰函中说:
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的决心不可。
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胡适提出,必须准备:1.中国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全部被日军侵占毁灭;2.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陷;3.长江被封锁,天津、上海被侵占,财政总崩溃。胡适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他说:
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之后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胡适并不认为,他的第一方案一定成功,因此,提出必须以第二方案为后盾。他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能免于一战。”他并以俄国史为例,说明列宁和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后,与德国讲和,“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他要中国人向苏俄学习,说“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痛苦”。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意志坚决,中国士兵作战英勇。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行前,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自此,胡适“态度全变”,“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不久,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决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争取国际支援中国抗战。次年,又出任驻美大使,投入中国的抗战外交。
(选自《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