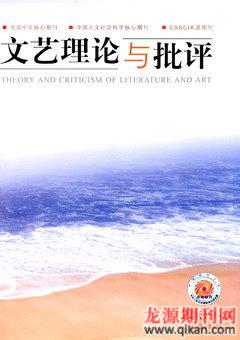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
旷新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现代中国,形成了我们的新传统。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进步以及新中国、新社会、新诗、新文学等以“新”为特点的一整套规划和实践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性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的突破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言文合一和白话文运动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空间。而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中说:“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白话文运动是一个追求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运动。它的后面蕴涵着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主义目标。这种普遍性一方面是寻找世界共同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形成民族共同的语言。实际上,现代国语的创造既是一个寻求普遍性的运动,同时又是一个解构普遍性的运动。在近代以前,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官方文件和文献都是使用“文言”书写的。在东亚,文言具有拉丁文在欧洲同样的地位和作用。文言创造了东亚共同的文化和价值理想,形成了一个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体。但是,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国语)。因此,这个寻求普遍性的民族主义目标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古典的东亚共同体瓦解的过程。现代民族主义语言的追求,导致了东亚以文言为中心的统一书写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解体,东亚由大同走向了分殊。每一个了解日本、朝鲜、越南文献的学者都会对此深有感触。不仅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的文献也像中国一样原来都是文言书写的,而且东亚古代的知识分子不用翻译,可以通过笔谈直接互相沟通。此外,甚至古代东亚的文人,不论他是朝鲜、日本,还是越南的文人,都可以在中国朝廷为官。文言创造了一个古代东亚大同世界,成为了东亚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空间。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民族内部语言与书写、文人士大夫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为代价。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大一统国家。稳定的书写即文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曾经高度评价文言在不同地域与方言之间有效交流的功能。他说:“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文言文一直由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传承和使用,这些职业文人形成了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即士大夫传统和文人统治。不过古代文言在创造这种东亚共同体及其同一性的同时,却在社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言即掌握书写特权的文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外国的“文人”可以入朝为官的同时,中国的不识字者却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和参与国家政治的可能性。布鲁斯特在《中国的知识底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中指出:“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literary laste)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黎锦熙抱怨:“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字统一,实在不过少数智识阶级的文字统一,实在不过少数智识阶级的人们闹的玩意儿,说的面子话。纵然他们彼此共喻,似乎得了文字统一的好处;也只算统一了上层阶级,民众实在被屏除在统一之外。”
晚清,在西方的暴力入侵下,中国的“天下”破裂了,并且被迫卷入到了现代建筑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之中。西方民族主义成为了普遍性,反过来,中国“天下”成为了特殊性。中国为了获得普遍性而必须克服自己的特殊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了中国将自己结合到普遍性中的运动。在语言上,这表现为激进的废除汉字和实行拉丁化的主张。日本、韩国、越南早已经创造了拼音文字,但是,拼音文字一直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压抑。在殖民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脱离汉字书写而进入拼音化的过程。尽管中国没有像土耳其一样事实上放弃自己原来的书写完成拼音化,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拼音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表现了对“世界语”的狂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语”则被称为“普通话”。总之,白话文运动和拼音化运动包含了一个寻求普遍性的冲动。谭嗣同在其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及其“冲决网罗”之精神的《仁学》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世界主义精神。他猛烈抨击了被认为阻碍了自由交流的汉字:“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对拼音化的憧憬和向往体现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的憧憬和向往。他们希望中国摆脱野蛮落后的象形文字,获得与世界共同一致的“文明”语言。
中国现代的历史是一部知识分子寻找和创造自己语言的历史,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历史的脉络。房德里耶斯说:“语言是最好不过的社会事实,社会接触的结果。它变成了联系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就是由于社会集体的存在。”彼得·特鲁基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向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每一次突进都伴随着语言的改造和变化。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谈到文学大众化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
晚清,在民族危机的威胁下,掌握着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级与大众之间的隔绝与对立的状态,不能适应民族主义动员的要求,受到了维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诟病。为了扫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这种隔绝与对立,为了拆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掌握书写特权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从晚清开始了白话文运动和言文合一运动,扫除这种文与言的隔绝与对立。
欧洲现代国语的产生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一致的。现代国语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
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国语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有效工具,而且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吴汝纶在《东游丛录》中引日本伊泽修二的话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国语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亟亟也。”卢戆章在《颁行切音字之益》中将言文合一和创建现代国语作为政治认同和普及教育的手段。他提出:“(一)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二)语言文字合一,以普教育也。”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序言中,王照不满中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的现状,为了实现“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朝野一体”的现代政治理想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政治动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言文合一、教育普及的现代主张。随着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晚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
可是,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仍然有很大的局限,白话仅仅是下层启蒙的工具,而文言则是上层阶级的专利品。
正如在晚清“中体西用”的二元论一样,在语言上也同样存在着“我们”和“他们”、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对立。因此,晚清白话文运动不是消除了文与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而是凸显了这种对立。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晚清白话文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仍然采取一种双重态度。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区别就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要求彻底否定文言与白话、语言与书写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的主张。
白话文运动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但是,四库全书等知识体制却将白话文贬低和排斥在外。“五四”白话文运动则颠覆了文言和白话的这种等级关系。白话文被突出到了中心的位置。从根本上说,白话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书写语言,而是一个话语体系。白话文一方面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语言事实,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建构。白话文是现代民主和科学的载体,是新知识分子开创的价值空间。白话文运动将林纾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提高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人的发现”和“人的文学”的创造,是和白话文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白话文运动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它使中国人生存的意义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朱自清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五四”白话文运动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个主要目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对立,不仅是古代与现代、死文学与活文学的对立,而且也是上层与下层、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的对立。白话文运动否定和推翻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等级关系,企图创造一种新的全民共通的语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中,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劳工神圣”的呼声,李大钊发现了“庶民的胜利”这种世界历史的新潮流。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涌现出了四百多种白话报刊,由这种白话文的新媒介,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猛烈地爆发出来,形成了强大的潮流。用鲁迅的话来说,它使“无声的中国”变成了“有声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国民党的改造以及国民革命的兴起作了直接的准备。
白话文运动同时使书写形式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学术的典范。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指出,“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孔恩(Thomas S.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话语的革命,造成了思想文化上总体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尽管以“人类”的名义和旗号,但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形成了对“五四”的“文化批判”。瞿秋白等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五四”白话文是一种“新文言”,仍然将广大民众排斥在外,因此,他提出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