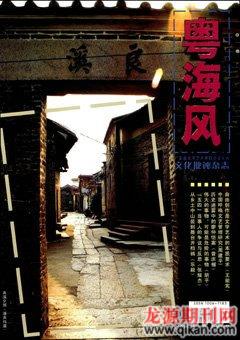间离效果,抑或乌托邦心态?
李 松
自从“样板戏”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以来,学界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的否定态度:从政治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样板戏”沦为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因而大加挞伐;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出发,认为“样板戏”对人们造成了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加以控诉;从艺术自律的角度出发,认为“样板戏”的“三突出”、“高大全”都是艺术谬论,因而进行指责。以上看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从不同的精神立场全盘否定“样板戏”。各自立场反映了政治态度、情感体验与艺术标准的差异,都有一定的历史成因与学理依据。我们的确也有必要去反思:“样板戏”如何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推动社会化的政治运动,它的创作原则在当时如何成为其他艺术形式的标杆,它在京剧、舞剧、音乐的现代化过程中取得过哪些不菲的艺术成果,它又为何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拥有广大的热心观众。与上述否定性判断相反的是,张广天先生认为,京剧革命(指“样板戏”革新)“通过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全面批判整理,以促使新中国文化复兴高潮的到来”,[1]因而他认为“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值得肯定。张闳先生认为“‘样板文艺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的确符合现代主义美学的某些基本精神”,因而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现代主义”[2]。韩毓海先生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中对“样板戏”也有高度的褒扬,他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延续性”入手质疑洪子诚先生的“断裂论”。洪子诚先生曾经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从“延安讲话”后形成断裂导致“一体化”,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到 80年代又恢复了“多样化”。而韩毓海先生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3]韩毓海先生从间离效果的观众接受角度论证了“样板戏”艺术模式的合理性,这一论证角度不乏新意,其观点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学接受的文学性问题[4]。我并不想简单否定“样板戏”的艺术价值,而是觉得,从间离效果去论证“样板戏”的传播效果未免牵强,且论证上有过于主观夸大的成分。因此,我想从乌托邦的接受心态的角度,对“样板戏”艺术创作与表达效果之间的关联作出学理的分析。[5]
一、问题的焦点:“样板戏”与间离效果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史诗剧理论中提出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理论(或译为陌生化方法),他否定了亚里斯多德的共鸣说(Einfuhlung)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论,认为间离效果通过史诗剧的叙事性(史诗性)取代传统戏剧的戏剧性(冲突和激情),切断了观众与“戏剧的世界”的通道。布莱希特认为,从舞台世界与现实世界、角色与演员之间的间离来拆除舞台上的“第四堵墙”,通过以事件和理智为要素的叙事性,“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6]韩毓海先生正是从间离效果的理论出发认为,“样板戏的创作和改编,确实找到了中国传统戏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就是以一个装扮起来的、扮演的戏剧的审美世界、理想的世界,来反观和质疑现实的世界。它以彻底的戏剧精神,彻底颠覆了现实世界的规范和戒律”。[7]为了论证舞台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批判反思的革命力量,他引证了1944年毛泽东对延安平剧院演出《逼上梁山》的指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8]韩毓海先生认为,毛泽东要将帝王将相占领舞台的被颠倒的世界再颠倒回来的观点,“首先极其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戏剧的精神,继而说明了戏剧精神与革命精神之间的联系”[9]。我认为,毛泽东的原意是,文艺应该反映社会广阔的现实生活,工农兵应该取代帝王将相成为文学的表现主题。这一看法涉及到文学题材、主题、目的、功能的问题。而韩毓海先生从间离效果的理论立场出发认为,“样板戏”体现了创作者“将现实世界在舞台上‘颠倒和变形的能力”,“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以革命的戏剧精神质疑、批判社会现实。这对毛泽东的原意似乎有脱离语境而过度阐释之嫌。
韩毓海先生认为,“样板戏也确实铸造起一个理想化的审美世界,里面的人物都是高大全,一个个道德高尚的劳动者样板被树立起来了。这是样板戏的缺点和可笑之处,但是同时你别忘记了,人们在看样板戏的时候,恰恰绝对会把它当作一个戏,而不会完全投入进去。样板戏其实非常强调‘扮演意识。比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却扮成一个土匪,《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却扮成一个老板娘。这种扮演的过程令人始终都会觉得,这是戏,而不是真的;什么是间离效果?这就是间离效果”。[10]韩毓海先生在此处混淆了间离效果的“扮演意识”和剧情扮演的区别。间离效果的目的是创作者有意为之,即通过演员和角色的间离,使观众不至于混淆两者而对剧中人物形象丧失必要的理性反思;而《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扮演”是剧情发展的自然结果,演员的扮演恰恰需要对角色的表现惟妙惟肖、传神逼真,而不是彼此分裂。如果演员的扮演令人觉得这是戏而不是真的,恰恰是一大败笔。而且,历史的实际情形是,建国以后的50年代,国外戏剧理论对中国戏剧创作影响至深的是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50年代至70年代布莱希特及其少数几部剧作在中国备受冷遇。
那么,是否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与“样板戏”的创作理论是迥然不同的呢?应该说,二者也有相似点。它们的创作思想都有理性化的特点,都重视教化功能。但是,即便如此,二者的相似并不能统一为间离效果。其差异具体表现为,“史诗剧的基本要点是更注重诉诸观众的理性,而不是观众的感情。观众不是分享经验,而是去领悟那些事情”。[11]“样板戏”主要通过英雄形象感染人、教育人。“革命样板戏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12]演员钱浩梁说“我们演戏,不是简单地给人娱乐、消遣,而是在干革命”。[13]“样板戏”遵循的是“高大全”、“三突出”的理性化艺术规则。
二、间离效果理论溯源:布莱希特对梅兰芳戏曲的“误读”
要分析韩毓海先生“样板戏”间离效果论的悖谬之处,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布莱希特创立间离效果的理论背景以及他的戏剧观与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理论的异同。
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的创构受到梅兰芳戏曲艺术的启发。他认为戏曲应该摆脱激情,破除幻觉,理性反思。布莱希特在俄国看过梅兰芳的一次演出后热情赞扬道,“这种演技比较健康,而且(依我们的看法)它和人这个有理智的动物更为相称。它要求演员具有更高的修养,更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经验,更敏锐的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力。当然,这里仍然要求创造性的工作,但它的质量比迷信幻觉的技巧要提高许多,因为它的创作已被提到理性的高度”。[14]布莱希特根据自己的戏剧观念,从演员应该具备的修养、知识、经验和理解能力以及演员和对象之间的分离,看到的是演员本身应该具有的理性反思能力。他以美国名演员劳顿扮演伽利略的角色为例,指出:“演员在舞台上有双重形象,既是劳顿,又是伽利略,表演着的劳顿并未在被表演的伽利略中消失……在舞台上站着的确实是劳顿,并且在表演着:他怎样在想象着伽利略……观众一面在欣赏他,一面自然并未忘记演员劳顿本人,即使他试图完全彻底转化为角色,但他并未丢掉完全从角色中产生的他的看法和感受。”[15]布莱希特并不是绝对否定体验的必要性,但是他认为演员应该通过角色体验化身为角色身份,关键在于还应该进一步通过演员表演来解释角色身份,最后达到演员与角色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认为,“几句术语去阐述一下什么是史诗剧是不可能的。最根本的也许是史诗剧不激动观众的感情,而激动他们的理智”。“在感情和理性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真正的感情,这是我们所需要的。”[16]布莱希特认为理智、思想激动到一定程度则变成感情,他寻求的是一种理智和感情相结合的辩证的戏剧。他在《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中盛赞梅兰芳和中国戏曲艺术,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一个年轻女子,渔夫的女儿,在舞台上站立着划动一艘想象中的小船。为了操纵它,她用一把长不过膝的木桨。水流湍急时,她极为艰难地保持身体平衡。接着小船进入一个小湾,她便比较平稳地划着。就是这样的划船,但这一情景却富有诗情画意,仿佛是许多民谣所吟咏过,众所周知的事。这个女子的每一动作都宛如一幅画那样令人熟悉,河流的每一转弯处都是一处已知的险境,连下一次的转弯处在临近之前就使观众觉察到了。观众的这种感觉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而产生的,看来正是演员使这种情景叫人难以忘怀。”[17]布莱希特看出了中国戏曲表演的本质特征——虚拟性。中国戏曲演员以假定性为前提,谙熟自己一招一式的表演功能,通过程式化的艺术手段展现一个艺术化的舞台世界,从而达到表现社会生活的目的。例如以轿舞来表现坐轿,以跑龙套象征千军万马,——虚中见实,实中见虚。在中国文化语境看来,演员的表演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特点。这种程式无疑具有理性的规范性色彩(适合模仿),同时又具有极其丰富的写意性。但是,其写意性并不是布莱希特意义上的演员与对象、演员与观众、观众和角色之间的感情间离。虽然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也并不完全是以理性为内核的政治剧与道德剧,他同时也注意审美效果。[18]西方传统戏剧重写实,要求演员将自我化入情境与角色之中,通过写实化的场景和动作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中国戏曲更重视“写意”,在“形似”与“神似”两方面更注重后者。这种写意特征与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其写意性主要表现在舞台时空处理的灵活性、表演形式的程式化(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分类)、“四功五法”(唱念做打与手眼身发步)以及戏曲表演和设置的虚拟化(虚拟性的布景、道具和舞台设置)。黄佐临在对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三种戏剧观进行比较时,他总结说,中国“戏曲艺术是‘有规则的自由行动”。“同时,梅兰芳的表演他并非完全是外部技巧,他也像斯氏那样对内在感情的创作活动极为重视。”“内在的创作,而不是外部的标志,才是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精神实质。”[19]梅兰芳的表演性体现在唱、念、做、打艺术上的精湛,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声情、腔调等个人特色。“梅、斯、布三位的区别究竟何在?简单扼要地说,最根本的区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戏剧一向具有高度的规范化,从来不会给观众造成真实的生活幻觉。”“对梅兰芳,也就是对我国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来说,理想的方法是把内心活动的‘内在技巧和外部的表现技巧相结合。”[20]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艺术的“误读”在于,他只是看到了外部的表演技巧,并因此受启发提出间离效果。当然,这种“误读”并非错误的解读,而是布莱希特带着他文化的有色眼镜对中国戏曲进行了自圆其说的接受与阐释。“样板戏”在写意性、抒情性、程式化方面恰恰继承了中国传统京剧的特色并加以创新,它所要表达的效果并不是韩毓海先生所认为的间离效果。
我们可以从观众的现实观剧体验来加以论证。据1965年4月30日的《人民日报》记载:
让我们从《红灯记》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革命的红灯接下来!”观众给剧院来信中这句火热的语言,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这样喜爱《红灯记》。广大观众指出,这出戏里赤胆忠心、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教育作用和鼓舞力量,这是在传统戏里根本找不到的。许多观众说,他们看《红灯记》时,忘记了是在看戏,而是同剧中的英雄人物在思想感情融成了一片,感到自己也在和他们一起战斗。一位连看六次《红灯记》的京剧老观众说,他看了一辈子京剧,什么名角都看过,从来没流过泪,可是这次却禁不住为《红灯记》中革命英雄的伟大情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红灯记》在深圳演出时,港澳观众中发出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位香港观众在一篇观后感中指出,《红灯记》里“自始至终有一颗中国人民革命的心在剧烈跳动,中国人民的革命火焰在猛烈燃烧”,“使人热血沸腾,思想上感情上都得到最大的充实。[21]
从上述对“样板戏”的观剧效果的描述可以看出,观众受到人物形象的感染,“忘记了是在看戏,而是同剧中的英雄人物在思想感情上融成了一片,感到自己也在和他们一起战斗”,这不是间离效果所能实现的,而恰恰是共鸣的美学体验。
京剧与“样板戏”都建立了脸谱化的艺术规则,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发展”上的不同表现。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化是观众欣赏趣味与艺术表演范式互动的产物,观众的接受心理遵循着一定的艺术惯例。“样板戏”的脸谱化则始终贯彻着政治理性,它力图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明确的政治符号固定下来。“样板戏”艺术观念的哲学基础是政治建构论。它的创作规律体现为政治正确生活体验艺术反映符合预设。在创作方法上,它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塑造这样的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22]在作品的主题上,“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23]可见,“样板戏”中的所谓现实、真实是根据政治预设建构的产物,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文艺实现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
三、体验论的异同:“样板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如果从间离效果出发分析“样板戏”的话,按理说,间离效果的创作宗旨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有矛盾的。我认为“样板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倒是有共同之处的,二者都强调以现实生活的体验为基础。江青要求《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海港》、《磐石湾》等“样板戏”剧组应该反复深入社会生活体验角色的战斗历程,培养刻骨铭心的革命情感。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样板戏”中演员体验的过程是将个人思想与革命精神彻底融合统一。“演员探索表演这些艺术形象的过程,也就是理解、学习、歌颂这些英雄形象和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即使是工农兵出身的演员,也必须重新接受再教育,决不能有什么例外。”[24]“样板戏”的主题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都体现了“文革”的目的——对世界观的改造,提高防修反修的能力。[25]“样板戏”强调生活体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自我生命意识,而是符合“政治正确”的现实世界。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不论演什么角色,他总应该从自我出发”。[26]“要牢牢记住:艺术的道路,就是你自己,而且只是你自己。”[27]“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表演自己。”[28]可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遭受批判的原因不仅仅是内心体验的问题,而且还因为他说的体验是基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而不是阶级体验。如果上述分析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明“样板戏”的创作目的并不是追求间离效果,遑论无法达到间离效果。
四、“移情”与“深情”、“和解”与“女吊”:“样板戏”与西方戏剧比较
韩毓海先生认为“样板戏”观众接受心理的“感天动地,不是一般的感动,它与欧洲近代戏剧的‘移情有本质的不同”。他解释说,“所谓移情,就是通过同情地理解剧中人的悲剧命运,使得观众即现实中的人变得更清醒、更宽容、更理智,用老百姓的话——看得更开一点”。[29]移情(empathy)作为一个心理美学的术语,它指的是主体在欣赏活动中通过内模仿的审美过程将自我情感投射于对象,通过对对象的审美想象而直接体现到自我的存在,实现自我与对象的融合与统一。既然欣赏过程最终实现的是观众与角色的同情与共鸣,又怎么可能“使得观众即现实中的人变得更清醒、更宽容、更理智”,并且“看得更开一点”呢?要能够“看得更开一点”的话,需要观众与对象某种程度的疏离,通过冷静疏离后的返观从而理性沉思,而“样板戏”欣赏体验中通常达成的是移情式的个人体验与政治理念的融合,使阶级情感得以宣泄,革命理想得以提升。
韩毓海先生认为,“像《窦娥冤》、《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这样的中国戏剧,其艺术目标却在于通过‘感动而使人进入‘深情,最终使得一个‘感天动地的戏剧领域成为可能,西方戏剧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解,而中国戏剧的最高境界却是感天动地的不懈抗争,它连绝望都不允许,都要反抗,它要一直抗争到感天动地。鲁迅临终前反对西方式的‘和解,而推崇那个追命到天涯的窦娥式的‘女吊,鲁迅说到了这就是中国戏剧精神与西方戏剧精神的不同。为什么说鲁迅的心是与毛泽东相通的?从这里你看到他们是相通的”。[30]
如果“样板戏”的“艺术目标却在于通过‘感动而使人进入‘深情,最终使得一个‘感天动地的戏剧领域成为可能”的话,那么这种情感体验恰恰与韩毓海先生说的间离效果是自相矛盾的,而与共鸣是一致的。
韩毓海先生认为“西方戏剧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解”,而中国戏曲是追求“追命到天涯的窦娥式的‘女吊”。这种判断似乎有悖于一般的戏剧常识。人物用行动去抗争命运与社会是西方悲剧的实质,而中国古典悲剧作为苦情戏(或称为苦戏、怨谱、哀曲)主要描写主人公的悲惨遭遇。韩毓海先生认为“追命到天涯的窦娥式的‘女吊”抗争到感天动地,如果回到《窦娥冤》文本本身,我们发现,其实窦娥的抗争精神是要打一个折扣的。窦娥认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她有着浓重的宿命感,逆来顺受、甘于忍耐。当窦娥面临恶人与贪官狼狈为奸的时候,她为了保护婆婆而屈认自己毒死孛老,但是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反抗的出路也只是寄托于上天为她作证。她的三桩誓愿只有在天意、天德、天理想象性的正义预设中才能得以实现。倒是西方戏剧(一般指悲剧)通常通过悲剧人物的矛盾冲突与曲折的情节来展示主人公的崇高与悲壮。西方戏剧的结尾通常以悲剧的爆发——毁灭作为结局。哈姆雷特用自己的生命殊死搏斗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最后他与敌人同归于尽。西方悲剧人物大多如此。而中国戏曲通常以大团圆为结局,以喜剧的方式实现冲突的和解。窦娥临死时控诉不公,惊天动地,但是鬼魂复仇的结局不是自己努力抗争的结果,而是借助神灵相助。其他如《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清忠谱》等同样如此。这种因果报应、神灵应验不是主人公的抗争,而是寄托着人们的同情。剧作者的这种安排反映了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感情需求。
鲁迅固然在临死前推崇追命到天涯的“女吊”,他力图以尼采式的决绝抵抗虚无的希望与惨淡的人生,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认为中西戏剧的区别在于“女吊”与“和解”。韩毓海先生此处的判断显然牵强附会,他还根据这种臆想的区别,认为鲁迅与毛泽东的心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也就更加显得大谬不然了。不但理论的基础有问题,而且在没有扎实的实证与严密的推理的前提下作出如此断语,显然太想当然了。
五、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样板戏”的政治美学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样板戏”的特点呢?我认为“样板戏”体现了角色体验与表演写意的结合。中国戏曲以歌舞为主,其主要特征是抒情性。它着力展现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而不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动作及过程。“无声不歌,无做不舞”。人物通过歌舞传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的“冲突”。王国维认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中国戏曲创作依格律写歌词(“填词”),要求歌词讲究平仄押韵以及格律,且能合乐歌唱。“样板戏”充分继承、发展了京剧在音乐唱腔、语言修辞方面的长处。[31]它的创作依然遵循着“寓教于乐”的教化方式(虽然此处的“乐”已经置换为政治美学)与“润物细无声”的感染方式,它力求通过舞台上下人物感情共鸣实现身份认同。如延安时期演出《白毛女》时,有士兵沉浸于戏剧悲剧氛围中无法自已,义愤填膺想要射杀台上的黄世仁为喜儿报仇。“样板戏”对舞台美术、人物造型、音乐唱腔、舞蹈动作等高度重视,尤其是“样板戏”电影对灯光、舞美、音响、道具等等精益求精,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制造舞台幻觉,使观众如醉如痴沉浸其中。与布莱希特破除幻觉的努力相反,“样板戏”创作的目的恰恰是要使观众如醉如痴,起到催眠作用。黑白分明的善恶对比、斩钉截铁的政治话语没有给观众任何时间和思维的余裕去对主题、情节、人物、结构进行冷静的理性反思,更谈不上探究背后形而上的哲学内涵。在狂热的剧场社会里,现实的意识形态灌输与舞台上的政治主题共同塑造着观众的乌托邦理想。
韩毓海先生“认为样板戏不是被什么艺术样式超越了,而首先是因为它本身难以为继、不能再继续超越自身了”,另一个原因是“它所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同样使样板戏很难长期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现代艺术也要与其经济承受能力相协调”。“所以,样板戏的失败不在其艺术,而在于作为舞台艺术的演出经营模式即艺术生产模式。”[32]我认为,对“样板戏”的评价一定不能孤立地从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与手段去进行评价,必须将作品、作者、世界、读者视为一个立体动态的结构。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我认为“样板戏”的失败也不在于“作为舞台艺术的演出经营模式即艺术生产模式”的原因,应该看到政治上驯服的民众为“样板戏”的流行提供了与之匹配的精神温床。而政治谎言一旦现形,民众激昂亢奋的热情势必难以持久,“样板戏”也将随特定的政治气候成为历史记忆。韩毓海先生从间离效果来解释“样板戏”的合理性,而实际上恰恰是间离效果实践上遇到了现实的困难。间离效果的理性沉思与批判现实功能的形成,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观众必须具备一定的接受水平,即思想层次、艺术修养。“样板戏”共鸣效果的形成与当政者对艺术的性质、目的、功能的界定以及当时的政治氛围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不是通过角色与人物的间离,而恰恰是通过角色与人物完美结合的形象去激发观众的革命激情。中国观众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习惯了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和虚拟化的表演形式,并不会因为虚拟的场景、动作以及唱白而走出戏曲情节,相反,他们沉浸在戏曲所构建的虚拟故事中为人物的遭遇牵肠挂肚。在这种体验性的观剧心理中,观众无法进行舞台与现实、角色与人物的分离所带来的理性反思,恰恰是舞台与现实的融合可以使人们觉得舞台世界更真实,角色与人物的完美演绎使人们觉得形象更丰富。翻译家绿原认为,“对于布莱希特那几出剧目的演出,如果没有必要的帮助和启发,一般观众恐怕很难越出‘陌生感或‘间离感的限制,达到作者所期待的客观观察和主动思维,从而得出对剧情应有的结论。看来,布莱希特的理论和实践真正中国化,也就是中国读者观众的新的欣赏趣味的形成,远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需要热心的专家学者加以解说、鼓吹和推广”。[33]绿原作为当代中国戏曲发展历史见证人的这番体贴之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困境。
“样板戏”构筑的是一个政治、道德、审美的乌托邦,它沉淀着一代人的梦想与光荣。乌托邦(Utopia)的原意是指正义、美好、善良、幸福、自由、真理等意义,体现了人类对于建立一个和谐、自由、幸福、完美的世界的愿望。然而从该词的构成规则(希腊语ou意指没有,topos意指处所、地方;拉丁语指乌有乡)来看,它又体现了理想和现实、此岸和彼岸之间无法弥合的断裂。而“意识形态展现了个人同其真实存在情况的想象性关系”[34]。它不像军队、监狱、法庭以暴力方式实现强制性的规约,而总是力图通过文学艺术耐心地循循善诱、形象地精彩演绎,许诺一个指日可待的真实存在。“样板戏”要实现在人们内心深处进行灵魂革命的目的,达到“防修”、“反修”的意识形态免疫功能,因而必须树立美学的政治形象、发挥艺术的感性功能,使台下观众沉浸在崇高的精神体验之中,从而灵魂得到革命的洗礼。其次,“样板戏”所承继的传统京剧腔调、造型等多种表意功能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悦耳悦目、悦心悦意的艺术世界。虽然舞台世界与现实世界、演员与角色是分裂的,但是这一假定性规则却大大拓展了艺术的表意空间,具有诗性的超越。这就是为什么“样板戏”在褪去特定政治色彩的市场化社会仍然拥有广大的欣赏者,仍然不失为艺术经典的原因。
结语
布莱希特认为间离效果或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35],这种感觉“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36]。可见布莱希特希望通过触发观众的理性来教育观众、改造社会。而在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中,角色的体验与表演、感性与理性是和谐统一的,共同演绎着角色丰富、细腻的心理世界,带给观众美感的享受和境界的超越。“样板戏”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京剧优良的表演艺术,为观众乌托邦的革命愿景提供了替代性的满足。但是,它对政治理念的简单图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艺术的魅力,也给“样板戏”艺术的自我革新设置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1] 张广天,《江山如画宏图展——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1期.
[2] 张闳,《“样板戏”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艺争鸣》, 2008年第5期.
[3][7][9][10][29][30][32]韩毓海,《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J].《粤海风》2008年第1期.
[4]可参阅王先霈,《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从乌托邦心态入手分析“样板戏”的接受效果,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刘艳,《“样板戏”观众与乌托邦文化》,《艺术百家》,1996年第3期。刘忠, 《“样板戏”文学的审美效应与乌托邦文化》,《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郭玉琼,《戏曲现代戏的记忆与乌托邦》,《粤海风》,2005年,第4期.
[6][15][16][36][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p83—84、86、134、83—84.
[8]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N].《人民日报》,1967年5月25日.
[11][35]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p23、204.
[1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革命新文艺——谈革命样板戏的历史意义和战斗作用》[N].《人民日报》,1974年7月16日.
[13]钱浩梁,《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N].《人民日报》, 1967年5月27日.
[14][17] Bertold Boecbt, Schriften Ium Tbeonter,Foankfuzit a.m , Bd. 16, 1957.P620.
[18]参见邹元江,《史诗剧:审美效果与道德效果双重实现的“伟大形式”》,《戏剧》,2002年第1期.
[19][20]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J].《百花洲》,1982年第1期.
[21]新华社,《<红灯记>是京剧革命化的样板》[N].《人民日报》,1965年4月30日.
[22][23]《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N].《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24]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J].《红旗》,1969年第6、7期合刊.
[25]参见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年5月1日。宋永毅主编,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编纂,《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制作及出版,2002.
[26][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四集[M].郑雪来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P357.
[27][俄]安塔洛娃笔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话录》[M].历苇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P87.
[28][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集[M].林陵、史敏徒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P280.
[31]参见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汪人元,《京剧“样板戏”音乐论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刘云燕,《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33]余匡复,《布莱希特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P3.
[34][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C].《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P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