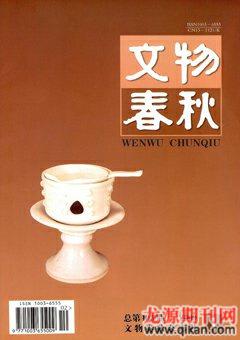关于冀北山戎的几个问题
张立柱
【关键词】冀北地区;夏商周时期;山戎;戎族;四坝文化
【摘要】本文以史籍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力图梳理出商周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的山戎民族的一些轨迹,认为山戎人不是土著民族,而是夏商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西戎的支属,商晚周初逐渐东迁进入冀北地区,是在冀北发展起来的戎族。
1998年我在承德参加会议时得知:山戎系春秋时期的部族名,活动区域包括今河北滦平和丰宁一带,盛产戎菽、冬葱。由此对山戎产生了兴趣,总想搞清它的几个问题。循着山戎的线索翻阅相关资料,发现山戎人与秋千有关系。史载: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者。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绳悬木立架,……名曰秋千。山戎人还是最早发明并使用火锅的,北京延庆龙庆峡山戎墓葬曾出土了青铜火锅,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其火锅又分两种类型:一是锅灶联体,下部点燃木柴,上部是铜锅;二是单体火锅,架于柴草之上将水煮沸。最近,我陆续查阅了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及一些文物资料,慢慢梳理出山戎的一点梗概:一个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老民族,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又活泼生动的民族文化,经过文物工作者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经过山戎寻觅者不懈的探索、分辨、比对,正在逐步揭开神秘的面纱。
山戎,华夏中国少数民族的一支,有过强盛,有过衰落,黄金时代在西周末到春秋时期,战国中后期被秦和齐打散。在河北北部的燕山、军都山一带及潮河、滦河流域,有许多山戎人的墓葬和聚居地遗址,有他们的征战场和祭祀地。山戎人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手工业工具和产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河北、北京、天津同属于一个文化区,自西向东在赤城、宣化、怀安、延庆、丰宁、滦平、隆化、兴隆、宽城、迁西、迁安、昌黎、抚宁等县市,均有山戎遗迹的发现。
一、戎族——氏族社会时期的游牧民族
在新石器时代中叶,我国北方和西北高原与丘陵地带是一片尚未开垦或尚未完全开发的地区。这里有草地、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民族仍然处于氏族部落状态,被称作西戎的氏族部落便是其中之一。
夏因禹建朝夏地、称夏伯而有国。《尚书》注说:“冕服彩章曰华,大国曰夏。”夏是中原之国,对居于其东、西、南、北的不同氏族以衣着、居地或其它特点称谓之,如、皮肤鸟夷、畎夷等。《尚书·禹贡》中有“夷”、“戎”、“蛮”的记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了尧舜之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传说,还提到了“蛮夷率服”,“望夷猾夏”,“西戎、析支、义渠”等。可以这样设想,既然尧舜时已有了戎的族称,那么夏时存在是必然的。再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夷、狄、戎、蛮等字,而实际存在的族称应早于文字的出现,所以戎族在夏时就已存在应为不争的事实。
夏代的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缺乏文字记载,这些年的考古成果尚不能够把夏代的历史全部连贯起来,所以文献中零散的记述以及对考古资料的辨认研究都是值得关注的。《禹贡》中“黑水西河惟雍州”,是说它的地理位置和重要作用。古代九州之一的雍州位于黄河中游以西至甘肃张掖的广大地区,其东部是夏族的主要分布区,而众多的少数民族则居于雍州西部,这里就包括属于西戎氏族集团的一些部族。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提到夏代的畎夷:“帝葵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元年,踵戎来朝。” 宋代人著的《路史》说:“葵不务德,……于是犬戎侵岐居之。”后者说的犬戎就是畎夷。夏代后期他们入居于陕西岐山一带,而岐山以北是他们的主要游牧区。《史记·匈奴列传》还记有:“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北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荤育即熏育,殷时称鬼方,西周称严允,即犬戎。夏时期,我国北方和西北已经居住着称为“熏育”、“畎夷”的戎族。
西戎是继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之后的四坝文化的主人,也是近4000年前的河西先民。西戎人距夏人的主要生活区不远,容易借鉴夏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学习夏人的先进文化,在戎族中改革最早,先一步踏入了青铜时代。
四坝文化是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命名的。1976年以后在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带发现黑、红彩夹砂彩陶和直刃弯背青铜刀,锥、斧、镰、矛、镞等工具和兵器,还有镜、镯、臂钏、指环、耳环等装饰用品。安先生发现这些陶器、铜器的工艺及纹饰既不同于马家窑文化,也不同于齐家文化的特征,命名为四坝文化。经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相当于夏代中期。
商代称诸侯国为“方”或“邦”,有关文献上有“万方百姓”、“万邦为庆”,都是众多的意思。居于商都北方和西北的有薰育、猃狁、犬戎、畎夷,甲骨文记有土方、鬼方、狄,从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看,这些都是部落群名称。他们已经从夏时的零散部落组成了某种人群的共同体,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但是有不同的政治中心。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里说:“土方是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古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鬼方“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大的游牧部落。”与土方、鬼方同时活动在商代中心区域西部、西北部的余无戎、燕京戎、奚落鬼戎、骊山戎、犬戎以及羌方、熏育、北羌等,较之夏时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散落的力量结成部落联盟,为寻求新的牧场和狩猎场经常游动,与商朝属地不断发生冲突。商王武丁之前,这类记载较少,从武丁开始文献资料多起来,仅殷墟甲骨卜辞就有数10条。
在这些记载中,多次提到羌,有羌方、北羌、河曲羌、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源于三苗,本姜姓之戎的别种,被舜逐至三危,即河关之西南羌地。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析支、义渠、渠搜、昆仑都是羌人部落,又同为西戎集团成员。武丁伐羌,最多时用兵达13000多人,远远超过征土方时的5000人。羌人曾占领过商属的大片土地和草场,武丁也曾俘获大批羌人,还俘虏过羌人的部落首领。只要成为俘虏就变为被强制生产的奴隶,还可能被作为祭祀品或随葬者。武丁及其后的征战反映出羌人力量强大对商造成的威胁,说明争夺的残酷。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的记载得出结论:“殷人之敌在西北,东南无劲敌。”殷商时的“四夷”概念,在夏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古籍中不仅较多地出现夷、狄、蛮、戎的记载,而且甲骨文中也把这些族称固定下来。基于征战的印记,象形文字的戎是一件兵器,用戎来称谓西方的主要民族,西戎的概念逐渐形成。
周武王灭商,追谥封王上至古公为止。这个古公父在商武丁元年被“赐以岐邑”,成为诸侯,经多年苦心经营,为周人发展奠定了基础。《尚书·武公》说:“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竹书纪年》记载公季时期与西戎进行过多次战争:“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徙之戎,捷其三大夫。”这些记载清楚表明,公季时期与西戎的战争频繁而且十分激烈。
公季死后西伯侯继位,是为周文王,他也多次兴兵伐戎狄。《史记·周本纪》记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竹书纪年》记有:“三十四年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尚书》疏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这个时期,周室伐西戎之力度也是相当大的。
周武王继位后大行分封,特别将功臣、近臣封在与西戎、北狄打交道的重地。封首要功臣姜尚为齐王,召公长子为燕王,镇守北方要地,将晋王封予成王弟叔虞,守卫山西曲沃到太原一线。《春秋左传正义》称姬发提醒他们注意“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注意应因戎人的风土习俗。这时期的西戎因连年征战,兵力受损,加之武王初立,军师强劲,所以战事相对平静。
到周穆王时,仍对犬戎、西戎用兵不断,加剧了民族矛盾。穆王孙周懿王在位时,“王室遂衰”,西戎和北狄同时伐周,迫使懿王迁都。《竹书纪年》记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入侵岐。十五年,自镐徙都犬丘。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山戎,败逋。”周宣王时接续出兵“西伐西戎”,及至周幽王时,“四夷入侵,中国皆叛”,褒姒乱政,国人悉怒,申侯与缯、犬戎攻幽王,杀于骊山下。几代周王征伐西戎,最后还是申侯联手戎人将周幽王推翻,也算历史为戎人讨回了一点公道。
周平王东迁,离开自武王至幽王经营了300年的镐而迁都洛阳,主要原因是戎狄的军事攻击。《史记·秦本纪》记载:“周避犬戎乱,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山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奉诏伐戎,得胜,于是“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以岐为基地,逐渐发展成为春秋时代的西部强国。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与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民族集团自夏代开始活跃于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生息发展了1500年,其主力族群最终被秦国击散。
二、山戎——商晚周初迁徙到冀北的戎族一脉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熏育,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这里说的“北蛮”应该是笼统方位,即北和西北;其中的山戎还不是春秋时的山戎,应当是后来被称作北狄的游牧民族部落群;猃狁、熏育则是居于西部和西北,后来被称作西戎的游牧民族部落。司马迁生动地记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我们从有关史料对西戎和北狄的描述中也读到了相似情景。司马迁接着记述了西戎的部分部落从古雍州以西到岐山以北,再到山西北部、内蒙古北部。《竹书纪年》则记载商与西戎、周与西戎连连征战的历程。这一方面说明义渠、析支、西羌、犬戎等西戎部落一直繁衍生息在西部、西北部,为生存发展不断与商、周发生争夺地盘的事,有时争夺还十分激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西戎民族集团中的部分部落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被毁坏的家园,是不是已经开始迁徙转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东南是强大的华夏,往北走是荒漠一片,向东去才是最佳选择,那里有自己的兄弟族群,彼此相距并不太遥远,从而这些先民成为北戎、后称山戎居地的最早踏足者和创业者。
《史记·匈奴列传》写道:“夏道衰,……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父,父亡走岐山,而豳人悉从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却。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这段记载记述了公元前777年,申侯联手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救周王始秦发迹史,其后110年,齐桓公应燕国请求救燕伐山戎,这是公元前664年的事。从这个时间往前推,公元前13~11世纪是商武丁、帝辛时期,也是周人初起,商周与西戎连年征战的时期。根据相关史料的追索,这个时期很可能就是西戎集团的某些部落尝试东移的阶段,其中有的到达陕北、晋北,也有的南进到华夏腹地又被迫转移。《匈奴列传》将西戎、畎夷、犬戎、戎夷、戎狄等作为一个民族集团来看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西戎与北狄的关系是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合抗敌。
犬戎引人注目。史载犬戎居地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北部,周朝中期已经比较强大。犬戎所处介于北戎和西戎之间,应该与双方都有联系。也有文献认为犬戎属北狄民族集团,有一定的道理。山戎或北戎春秋时属北狄,他们和犬戎本来就是相通的民族群落。
《匈奴列传》接“周襄王遣使告急于晋”记述:“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狄、白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诸、绲戎、狄、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里记述者仍将戎、狄合称。陇西八戎含河西走廊中西部的戎、陕西北部的戎、晋北之戎和燕北之戎,他们分散居住,各有各的部族首领,有联系而不相属,百有余戎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泛指西戎和山戎,并非专指山戎。
这样的散落状况,西戎人大约持续了600余年,而北戎历200余年发展成军事联盟性质的族群,即将单个部落的“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组合为整个部落联盟的军事行动。春秋早期,北戎、山戎人开始强大起来,有些华夏之国也开始与戎人结盟,借用戎人的力量。有关史籍载:
公元前721年春正月,鲁会戎于潜(今山东济宁);秋八月,鲁公与戎盟于唐(今山东金乡);
公元前716年冬,周大夫凡伯聘于鲁,戎伐凡伯于楚丘(今河南濮阳以北);
公元前714年冬,北戎伐郑;
公元前706年夏,北戎越燕伐齐;
公元前677年夏,鲁公追戎于济西;
公元前674年冬,齐人伐戎;
公元前670年冬,戎伐曹;
公元前668年,鲁公伐戎;
公元前650年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史记·匈奴列传》载:“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狄,戎狄朝晋。后百有余年,……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
戎人强大之后伐鲁、伐郑、伐齐、伐曹,魏国、赵国与北戎、西戎边界相接。这时候的西戎义渠部落被秦击溃。公元前7至6世纪,中原国家兵器先进,齐国和赵国重兵征讨,使山戎军事联盟的力量遭受重大挫折,有的部落融于赵、燕、齐、秦,有的投入东胡、匈奴。尽管零星山戎部族在冀北地区还存在,但作为一个统一的族称,山戎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消失了。太史公在《匈奴列传》终了发出感叹:“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戎族之中,包括西戎各部落、北戎和山戎部族,不是没有出众的组织与军事人物,他们能在局部或一时的战争中取胜,但不能积累发展成战略和全局的胜利,实在是因为缺乏指挥、运筹、才能、品德杰出的领袖人物!
三、戎人西来的判断因由
山戎人不是土著民族,也不是春秋时期才来到冀北的,他们是西戎的支属,准确地说是在冀北发展起来的戎族。他们在西周后期、春秋时期被称为北戎,大概有西戎的因素吧。判断戎人西来,大体有如下考虑:
其一,史籍对西戎的记载早于山戎,且有考古资料可予以佐证。甘肃省自1976年相继出土了一批属四坝文化范畴的文物,其所有人当归西戎。《史记》中“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是指公刘世代为官掌管农业生产,夏朝中落失去官位,率其族人迁至戎地,改革西戎的风俗习惯,恢复农业种植,使那里的游牧民族改变为畜牧加农耕的生产方式,并建起了都邑。《盐铁论·和亲篇》评价说:“故公刘处西戎,戎狄化之。”其时间是在夏代中叶,而史籍具体记载北戎的历史事件则始于公元前8世纪。
其二,冀州开发迟于雍州,戎人东迁在情理之中。《尚书·禹贡》记载,夏禹将华夏分为九州,后依各州田亩等次顺序排列是:雍、徐、青、豫、冀、兖、梁、荆、扬。田亩等次体现了各州开发先后的农业生产水平差异,显然古雍州的发展水平在古冀州之前。游牧民族向尚未完全开发的地方转移,合情合理。
其三,西戎和北戎的生活习性相近,葬俗相似,当属同宗戎族。有关史料记录了戎族的生活习性,从“儿”到“少长”到“士”,从“宽”时到“急”时,描写得形象逼真。“利则进,不利则退”,这对于戎人不是难为情的事,这种天性决定了与之相关联的习俗和习惯。葬俗是民族文化的展示形式之一。西周至春秋时期,陇西四戎与岐梁四戎合称西戎八国,而晋北戎、燕北戎虽“自有君长”,但对归去者的葬俗一直传承,无大差别。四坝文化的墓葬形制多是长方形竖穴,以仰身直肢单体葬为主;燕北滦平、丰宁的山戎墓葬形制亦多为长方形竖穴,仰身直肢单体葬式。出土遗物同为夹砂红陶器和动物纹饰青铜器。燕北山戎的家畜有马、牛、羊、狗,没有猪,陇西四坝文化域内也多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定,东移支属仍保留着初始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
其四,相近的崇拜物,是同族的文化体现。西戎崇水怕水,因为有水才有草,而水大又会淹没家园。山戎崇龙崇蛙,因为龙能生雨,有蛙就有水,滦平出土的蛙面石人属半人半神的图腾。西戎、山戎都崇犬,有的部落将族名与犬联在一起,如畎夷、畎戎、犬戎。他们崇犬、爱犬,以犬为贵,北戎犬与玉、马并称三宝。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更是游牧民族射猎或放牧逐狼豺的协助者。山戎墓多有狗殉葬,腿骨在下,头骨在上,祈愿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伴。
其五,商末周初的连年征战是戎人东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商周奴隶主需要更多奴隶充当会说话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扩地占有戎人的资源,伐戎使之臣服,从而增强实力,霸有天下。从商武丁开始,经周公季历、周文王、周武王,华夏王朝连续讨伐西戎,虽然各有胜负,但戎人遭受了重大打击,伤亡惨重,其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遭到了极大破坏。为了图存寻找能够生活的环境,为了免于被奴役、被殉葬,一些人、一些部落逃离祖居地走上迁徙之路。当然,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也造成逃离,部落内部矛盾引发的残杀或仇恨使得一些人出走同样可能。西戎民族集团的部分部落由西或西北往东迁移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12~10世纪,即商武丁中后期到周文、武、成、康前后。他们逐渐到达冀北山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勿庸置疑,相对集中的迁徙之外,还会有零星的迁徙者。其路线大致是:陇西→陕北→晋北蒙北→冀北,先在今赤城、延庆、丰宁、滦平一带的燕山、军都山、潮河、滦河流域扎根,然后扩展至今天津北及唐山、秦皇岛北部一线。初称北戎,后叫山戎。
其六,山戎不具有土著民族的特征。一个地方的土著民族,相关史籍特别是区域志书或多或少的会有些历史记载,而冀北相关市县的志书均没有春秋之前关于山戎的史料,也没有夏商周之际关于山戎的故事或传说线索。就地理和生存、发展条件看,这里应是黄土民族,以农耕、畜牧相结合,而不是单一游牧民族。远古时代及夏商周时期这里是尚未完全开发的“荒蛮之地”,初始民族难于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有所作为。北戎、山戎的活动,应当是迁徙民族沿习已有的生产方式,然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
主要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范晔《后汉书》。
3、战国·魏《竹书纪年》。
4、宋《路史》。
5、《尚书·禹贡》。
6、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
7、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8、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9、甘肃省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