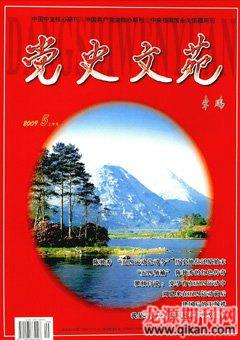“五四领袖”陈独秀的红色传奇
吴志菲

在北京沙滩繁华的五四大街路口,安设着一座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大型雕塑。有人惊诧地发现,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却独缺五四运动中那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被毛泽东曾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于是,有学者呼吁“整改”一下这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了“左”的思想束缚而创作的雕塑,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的新一页”。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曾连任5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成龙便成蛇的伢子”扶大《新青年》
陈独秀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陈章旭修习四书五经。陈独秀尽管聪慧过人,但是他不爱死记硬背,更不喜欢八股文章。因此,他常常背不出书来,“白胡爹爹”很生气,开口便骂,抬手便打,可是打归打,刚烈倔强的陈独秀总是一声不哭,也不讨饶。“白胡爹爹”从毒打小孙子而小孙子仍旧不哭的沉默中,似乎悟出了一些道道来,他对人说:“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清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在安庆府学宫参加府试,名列榜首,考中了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学习。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邮寄,他都一一亲自动手。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向已是出版商的老朋友汪孟邹提出想创办杂志。几年前,在陈独秀的建议下,汪孟邹在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经营情况不是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办杂志。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200元。
这年9月15日,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1916年初,发生了一件让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寄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尽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强硬,陈氏兄弟害怕打官司,不得不劝说陈独秀尽快改名。陈独秀性格倔强,他说,本人连暗杀团都参加过,大牢也坐过,好几次差点被杀头,难道还怕打官司?陈独秀坚决不肯改名。陈氏兄弟毕竟是出钱的投资方,生意人不愿多惹麻烦,软硬兼施地劝说了几个月,陈独秀终于同意改名为《新青年》。
很快,《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1916年底,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两家书店的合并募集资金。
这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到北京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但是,蔡元培对于胡适一无所知,没有答应。
从这天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让陈独秀有些感动。
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3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其中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即沙滩)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到了北京大学,陈独秀便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陈旧腐败的高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机盎然。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总司令”发动和设计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从未存有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赃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当时,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先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再分别前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北京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6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800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6月8日,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了具体的5条要求,表达了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宣言》起草好之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胡适,由胡译成了英文。为了避开监督,李大钊提出不要把《宣言》拿到《晨报》所在地印刷,最好在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那里安全一些。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一道,前往该处。至印完,已是深夜1点多钟。而印刷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很高,印完即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6月11日晚10时,他约高一涵等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传单。正在此时,从屋顶阴暗处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不假思索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给那人,此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一伙埋藏在花园暗地里的暗探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随后,一名暗探脱下灰大褂给陈独秀穿上,并将他带离。
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罗章龙等召来,商量营救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首先是将陈先生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于是,13日,北京《晨报》最新披露这一消息,随后,各大报纸相继报道。《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李大钊欣然作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说:“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南陈北李”打创建中共的“组合拳”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返回北京。
其实,他并没完全获得自由,在京期间,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的带篷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
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正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由公路出走来到天津。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随后,陈独秀乘车南下来到上海。不久,陈独秀得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到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对了一遍,决定作为图书正式出版。
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魏金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多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信息又格外关注。他们在北大图书馆会谈时,便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倾心交谈,坦诚相待。魏金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句话与“南陈北李”一个多月前所商的“计划”不谋而合,李大钊当然认同和向往。然而,他历来是个认真、稳重的人,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闻名国内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所以,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4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妻子高君曼突然前来通报: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驻海参威处派来的代表魏金斯基和夫人,还有翻译杨明斋。
3人带来了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魏金斯基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印刷费遇到了困难。魏金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陈独秀同魏金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李大钊)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192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却门窗紧闭,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让他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此时,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9月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陈独秀曾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谈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当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伊始,陈独秀便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发起组内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旧中国,处于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陈独秀曾安排这些青年在上海发起组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是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
正当他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时,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一向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自然对陈独秀格外青睐,早想请陈独秀来广东。11月1日,他郑重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很想去广东任职。于是,陈独秀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前往广州。
次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同李达和上海发起组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李达便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开会的通知。陈独秀接到李达、李汉俊的通知信后,立即在谭植棠家召开会议,他说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大学预科校长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以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么这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去上海参加会议,只有让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病逝后,他的墓冢已开辟为“独秀园”,墓碑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7个大字。这里长眠的是一位不寻常的“先生”,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正义和光明而叱咤风云的“先生”。陈独秀的一生,颂扬声与叹息声始终相伴。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评价。陈独秀的人生曲线,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迷茫与艰辛……○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