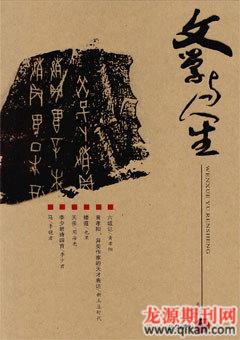黄孝阳:异类作家的天才表达
新土豆时代
当太阳出生时,天空中总布满血污。那些在床上酣睡太久的人,身体已为略带甜腥的梦境所侵蚀。所以,纵使黎明把窗户玻璃敲得当当作响,他们所做的多半是报以轻蔑。让他们的轻蔑在他们的屋子里像一只没头苍蝇嗡嗡乱撞吧。事情不会因为他们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一批年轻人冲出被某种话语把持了太久的铁屋子,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作为栖居地之一的小说文本,应该打破民族、国家、语言、时间等各种障碍,在世界的高度上,汲取历史的以及当下的营养。这才是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写出世界的文学,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学,又或者说中国文学期刊的文学。这是常识。遗憾的是,有这样抱负的却总是太少。大家都对中国当下文坛的现状不大满意。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小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更毋论后现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群,浅尝辄止,很快便退回传统。这是一个农耕社会留下的伟大传统,值得尊重、继承。但这四个字还远远不够。中国人是聪明的。因为这种聪明,权衡利益得失后,往往有巧,无拙。在传统占据主流话语的今天,期刊、出版(尤其是出版),留给真正年轻严肃写作者的空间几近于无。那些屈指可数的冒出头来的年轻者,多半是对传统的那套审美体系心领神会者,但这也造成他们之间的作品面目相仿——抹掉人名,你难以知道这是出于谁人之手。他们实际上是未老先衰者。中国的当代文学要想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需要的是那种有足够激情的偏执狂。他要在懂得一切现有的写作成规后,能漠视这些看上去神圣不可触犯的权威。对美,对那些人类最基本的命题有着自觉的追求。他所撰写的文字,不停留在为人玩味的观察与叙事上,有汉字的韵,有钱塘江的潮,有那皎皎明月,有邪月下死去的尸体。他要能把思想、艺术与文学融为一体。甚至是科学。小说家。不是小声说话,不是满足读者的叙事者。我们都承认他虚构世界,这个世界里就应该包含所有,也自然就有现实世界里科学、艺术的影像。科学与文学,或许这两个词都是上帝掷下的那同一粒骰子的两面。
我拜读过黄孝阳的《时代三部曲》,然后惊异了,中国还有这样的写作者。想起王小波说的一句话——一流的作品往往只有三流的名声。若不是朋友推荐,我还真错过了。《身体愤怒》写的是一个愤青,这部作品中的“我”自许为一堆狗屎,其所作所为,更是令人指责。但读者却恨不起“我”,因为这个“我”便是对赤裸裸的人性展开的批判。贯穿小说的几个女人无不强烈地具有些时代的象征,皆男有喻义。小说诙谐幽默、跳跃而飘逸,让人在阅读中发笑,在笑声中沉思,在沉思中落泪。作品的深度及表现力令人震撼。《作秀时代》写的是一个白痴,整部小说由杂乱而清晰,随着那特有的灵动和故事框架,整个时代的特质也凸出纸背。这是一个作秀的时代。那些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他们苦闷、浮躁、疑惑、思索、找寻……作者写白痴,而这个白痴却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思想与观察。作者利用个人的天赋以及对文字的娴熟对“作秀时代”极尽嬉笑怒骂,有泪,有苦,有忧。而《生死事小》这部作品空灵的始终就在一个多维的空间里跃动,现实与回忆,苦难与激情,最终归结为人与生命。这部作品就艺术角度而言在三部曲中最值得称道:文字漂亮。结构成熟。边缘、意象、细节、感知,从中淬取的美是这样令人赞叹不已。
我也读过黄孝阳的《网人》——
我们与现实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关系。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时都怀着光荣与梦想。然而,生活说,我们只是尘土。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从小县城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现实就如一把钝的刀子,割开他的肉体与灵魂。疲于奔命的他不堪城市的蹂躏,选择回家,褐望能找回失去的尊严与自由,但终究无颜面对年迈的父母——儿须成名酒须醉,“家”的重量让他的心灵无法承受。他回到路上,在路上,在萧瑟的村庄,在青砖灰瓦的寺院,在被时间遗忘的小城……他不停地敲打键盘,试图借助文字对抗无情的现实。记忆不断重叠。两点之间的距离并非直线最短。重叠,这个动作,让人生的厚度趋于零。时间在他把自己“清零”的过程中摇摇晃晃,时缓时急,或轻或重。他成了“遗失在光阴之外”、一个不再有“长宽高”的人。他开始向着整个世界坦白着自己的愚蠢与无知、浅薄与狂妄、眼泪与绝望、欢笑与喜悦,坦白一切。他说,亲爱的读者,我愿意赤身裸体站在你们面前。
我还读过黄孝阳的《遗失在光阴之外》。这是一本独特到难以用好坏来形容的小说。如果说它好,那绝对是用平庸的词汇来糟蹋这本小说。我们毕竟还没有到沈从文那样的大师级水平,在晚年评价一件艺术品只用“好,好极了”来形容。这或许是一个七十年代生人的自言自语,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本人的经历。里面夹杂的哲学思辨、个人精神狂想与社会生活碰撞的火花,让我们或多或少有些社会经历的人大吃一惊。作家的内心就像是鸟的翅膀,人世间的种种情绪,正面的以及负面的,比如爱,比如泪,比如欢笑,比如绝望,都在文字后摇摆着透明的光。而且,文字还是精确的、准确地掐在生活的脉搏上,一扇扇门被推开。究竟是哪一扇门才富有意义?我不知道,一只老虎在跑,跑过了金光闪闪的天空,天空中火红的玫瑰堆积在白色的云层上。我分不清自己的眼睛都看见了什么?时嗔时痴时笑时怨,自己好像是一个在坐过山车的人,跟随着作者的文字,在天地间旋转翻覆。我无法对这个文本评论更多,我只是想说,我喜欢它。“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是因为作者的博学或细腻或温情或技巧或思辨或深刻……好像都不是,尽管它们也都是或轻或重地击中了我的子弹,但应该不是致命的那一颗。把书放下,听着音乐,慢慢地想,窗外的风吹来几片清凉。我突然意识到的是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字后面掏出来的那颗真诚的心。这就好比聆听一部气象万千华美森严的交响乐章,固然让人心潮澎湃,心旷神怡,然而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流行歌曲,有时只需几个音符一句白话,便使我哭得活像个委屈的孩子,卸尽所有伪装。
现在,我在读《那些城》,是电子档,还未出版。只有十万字,却整整用了我七个晚上。没有去联众打牌,没有与朋友去泡吧。没有开车在高速上飙车,只是坐在桌前,安静地坐着,然后整个人都掉进黄孝阳垒起的文字迷宫。我该说些什么呢?
有人说,黄孝阳的文字从来都是匪夷所思。若非得用两个字来描述,便是——边缘。在表达得出与表达不出的两个人群之间,还有更大的一群从不表达,只在看,只在想,只在默默承受着的人群。黄孝阳的边缘。介乎表达得出这一群与表达不出那一群之间。最原始的欲望和生活里的不公平绞在一起,拧出黄孝阳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便是一团沸腾的泥浆,它可能涌动在众人思想、灵魂的深处。也可能表露为社会生活里的某处。没有什么比失落更令人沮丧,失落是异端的渊薮。
有人说,黄孝阳的小说就像是子弹,可以击穿胸膛。他没有简单复制生活,而通过灌入灼热的血液,为每个与他一样挣扎在泥沼与绝望中的人指出可能的方向。他是用生命燃烧汉字的人。这决定了他的小说可以令人不断地拿起来重新阅读。他的文字绝对不可以用臆想来评论。
有人说,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写作中。黄孝阳无疑是个异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当代文坛我还没读到类似他这样的作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更新,都在尝试。他像地下的岩浆,左冲右突,平静的地面上随时都有他冒出万丈岩浆的可能。我真为这个家伙的奇思怪想所折服。别的作家学东方学西方,学这种流派那种流派,这家伙啥也不管,只师从自己的内心,就像花果山的石猴出世一样,他注定不会同于花果山的其他猴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家伙是个天才。
是的,这就是黄孝阳。但请原谅我,我以为这些评论还不够,黄孝阳的意义绝对大于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我不想再说更多,任何阅读都是误读,但误读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一切经典都取决于我们的阐释。是我们,具体的你我他,给了一部作品真正的灵魂。去阅读黄孝阳吧,所有活着的人,你们会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找到自己。